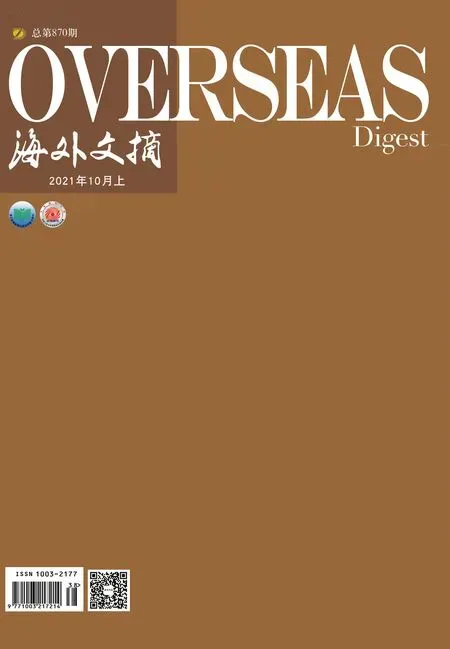認罪認罰案件中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的矛盾分析
馬瑞鳳
(湘潭大學,湖南湘潭 411105)
1 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
1.1 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建議權
2010年最高檢發布了《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指出:“量刑建議是指人民檢察院對提起公訴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適用的刑罰種類、幅度及執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議。”在這一文件的指導下,直到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量刑建議才正式入法。(1)2018年刑訴法修改,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系列實踐經驗上升為法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量刑建議問題也被明確。量刑建議權是一項程序性權力,是指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結合被告人的行為性質、情節輕重以及社會危害性等因素,對被告人行為性質定性,即對被告人的定罪問題提出明確請求后,就被告人的量刑問題提出的一項請求權。
量刑建議權具有公訴和法律監督兩方面價值。具體來說,在公訴方面,一是量刑建議的提出以較為全面的案件事實為基礎,有利于法官全面掌握相關案件的量刑信息;二是量刑建議的提出有利于辯方進行量刑辯護,特別是在認罪認罰案件中,量刑建議是在控辯充分協商的基礎上作出的,更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在法律監督方面,量刑建議制約著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量刑裁判權受限的情況更顯著。
1.2 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裁判權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實體方面可以劃分為定罪裁量權和量刑裁判權。其中,量刑裁判權是指法官通過一系列法庭審理活動,在對被告人的行為定性之后,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和被告人的情況決定判處何種刑罰的權力。可見,量刑裁判以定罪為前提,具有終局性、強制力,法官就被告人的行為定罪量刑后,即產生法律約束力。
1.3 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的關系
1.3.1 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的區別
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行使主體不同,分別由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行使。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對當事人產生的約束力不同。量刑建議權是控辯雙方協商的結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就量刑問題同檢察官進行協商;而量刑裁判是法院作出的量刑裁定,量刑裁判一經作出,即對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被告人一方在提出上訴的情形下,或者檢察機關抗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改變既有的量刑。
1.3.2 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的聯系
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雖然分別屬于不同的司法機關行使,但由于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二者在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第一,二者的共同目標在于懲罰犯罪。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以為法院量刑提供參考,最終目的是使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得到法律制裁;法院作出量刑裁判是對刑事被告人行為的否定與懲處,是對檢察機關公訴權的承認。因此,二者在懲罰犯罪的目的上具有一致性。第二,有利于保障裁判的實體公正。雖然量刑建議權是一項程序性權力,但仍然具有保障實體公正的意義。刑事訴訟證據是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依據,只有證據具有真實性、合法性與關聯性,才有可能成為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依據。法院作出量刑裁判,是通過審查證據、法庭辯論等庭審過程,并最終按照刑法的規定作出的,是對實體公正的一種維護方式。
2 美國法中的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
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中,法院仍然有權對控辯雙方關于罪名協商以及如何和量刑進行最終的決定。美國檢察官檢察官的裁量權幾乎不受限制。檢察官在法官裁判有罪之后的量刑程序中,仍然可以積極提供量刑材料,還可就量刑問題提出異議。雖然檢察官可針對諸多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并且控辯審三方都樂于參與辯訴交易,聽取檢察官的量刑建議,但這并不影響美國法官的量刑裁判權。提及美國的量刑問題,不得不提到飽受爭議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量刑指南的出臺初衷是正當化與合理化的,但由于量刑指南的強制實施,為其失效埋下了導火線。美國量刑指南中量刑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對象是法官,而對于法官來說,量刑自由裁量權被消減,本該由法官承擔量刑問題中的主導角色卻發生了錯位,被轉移到了檢察官與緩刑監督官身上,司法功能被嚴重削弱,量刑指南設立初衷也難以實現。
3 認罪認罰案件中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存在的矛盾及原因分析
3.1 矛盾
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矛盾的實質在于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是否會侵犯法院的量刑裁判權。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了檢法的不同職能,并且職能相互獨立,但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機關一般應當提出明確的量刑建議,且針對該量刑建議,法官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拒絕接受。這將導致人民法院的量刑裁判權在檢察院量刑建議的牽引下活動,特別是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采納率較高,對法院具有較大的約束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量刑裁判權。
3.2 原因分析
首先,我國量刑建議制度不夠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長期存在“重定罪,輕量刑”的問題,短時間內難以解決量刑問題。其次,法官對檢察機關的主導地位存在難以適應的現象。在檢察機關沒有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時,法院在量刑環節中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享有量刑環節的主動權。但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處在主導地位,人民法院只有在幾種特殊情況下,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正是這種角色定位的轉變,使得原來一直承擔審判職能的法官對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存在消極態度或者量刑裁判權被侵犯的主觀心理。最后,由于檢察官量刑能力較弱,導致法院接受量刑建議的程度也不高,加劇了審判人員對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的不信任性。
4 認罪認罰案件中量刑建議權與量刑裁判權平衡路徑
4.1 加強檢法溝通協商加之調整法官主觀心理狀態
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將占據主導性地位,這是法官必須接受的事實。因此,法官必須調整心理狀態,以適應確定刑量刑建議帶來的新變化。其次,加強檢法溝通。法官與檢察官在量刑建議上的矛盾與沖突難以避免。對于二者關于量刑建議的分歧,應當通過審前的溝通,就量刑建議問題檢察機關聽取審判機關的建議。
4.2 提高檢察官量刑能力
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加強對檢察官的培訓工作;第二,承辦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針對辦理次數較多的常見犯罪的案件,進行量刑建議等有關問題的匯總與案例分析,總結常見犯罪量刑建議的采納率與未采納率及具體情形。第三,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時,應增強說理性,明確量刑建議的事實依據與證據。法院審查認定犯罪與裁判量刑,是通過事實及證據的審查、判斷作出的,因此,只有通過增強說理性,以客觀真實的事實和證據說服法官,才能提高量刑建議的采納率,并且法官少有反對意見。
4.3 值班律師參與量刑協商過程
在認罪認罰案件的審前階段,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但在審判階段,現行法律并未賦予值班律師身份轉化的權利。如果被告人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后出現反悔情形,法院是否還應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認罪認罰案件設計之初,是為實現訴訟效率,為減少當事人在庭審中對量刑建議問題提出異議,需要值班律師在審前積極參與量刑建議的達成過程,為被告人解釋關于定罪量刑等方面的疑義,以期減少被告人異議。
5 結語
審判機關肯定量刑建議是對檢察機關公訴能力的一種承認。但量刑建議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法院的量刑裁判權,這阻礙了訴訟效率與公正的實現。法院在審查量刑建議時,應充分聽取被告人一方的意見,在被告人仍有異議時,應謹慎采納量刑建議。對于被告人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對量刑建議的異議的救濟,可以通過上訴進行,但上訴程序的進行無法達到認罪認罰案件的效率目的。因此,還需進一步探討被告人對量刑建議異議的救濟程序,或者法院在審理時及時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提出異議,以取得當事人信服,獲得司法公信力。
注釋
(1)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193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