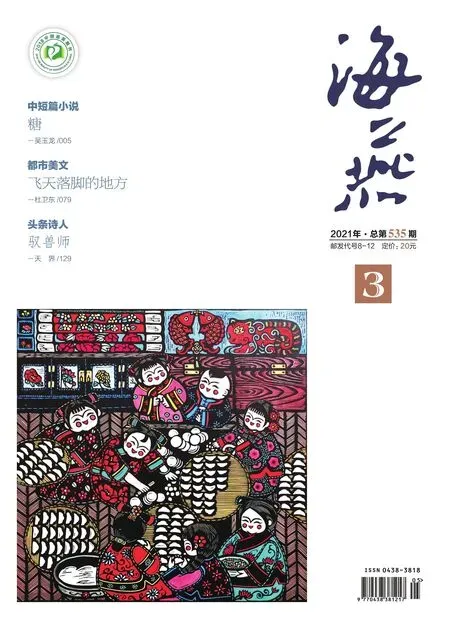遠 方
來了。來了。人群中有人在喊。
可我除了眼前一雙雙踮起的腳,什么也看不到,騷動的人堆里我唯有拉緊娘的手。
娘俯身抱我舉高,越過眾人的頭頂,零星的船只散落在黃昏的梅江上,來往穿梭,船兒嘟嘟作響,哪一艘船上載著我爹?
娘沒有說話,眼睛鎖住江面。娘把我抱得緊緊的,勒得手臂發(fā)疼,我叫了一聲娘。娘回過神來,指著就要靠岸的船說:快看,你爹就在這艘火船上。
船漸漸靠岸,人頭攢動的船上有人揮著手臂,哪一個是我爹?
上個月泉叔從南洋回來捎回了爹的信,還有一張照片,娘眼里噙著淚指著相片里穿著白色衣服的男子說,這是你爹。中秋回來。
家里只有我和娘以及阿公阿婆住在一起。我還在娘肚子里的時候,爹就去南洋做工了,下南洋的人當然不止我爹一人,阿婆說,誰家男丁不過番,誰家沒有番外客?番外就是南洋。
火船就要靠近碼頭時停止了高亢的響動,發(fā)出了一聲嘆氣,隨后輕輕地撞在碼頭的石級上,火船隨著江面的浪花蕩了幾下終于停穩(wěn)了。火船從很遠的地方駛來,沿著長長的梅江水。
快看,那是你爹。娘的聲音帶點顫抖。
娘被擠得左右搖晃,隨著娘手指的方向,我在人群中左右探頭,伸長脖子去尋找爹的影子。
爹來了,從碼頭數十級的臺階走來,一手提著藤箱,一手拿著帽子,爹不穿褂子,爹真特別。
爹站在了我們的面前。娘的淚落在我的手背上。
爹一只眼睛裝著娘,一只眼睛裝著我。
快叫爹。娘抹了一把淚,搖晃著懷里的我。
來,爹抱。爹放下手里的東西,雙手伸向我。
爹個子高,我即便是在娘的懷里,也要仰頭才能看清他,爹的臉像菜園里阿婆新翻的菜地,黑褐色。爹的眼睛像陽光下的江面,閃閃的。我把頭埋進了娘的胸口,摟著她的脖子不肯松手。
傻孩子,這是爹。娘重復了一句。
來,我的兒。爹從娘手中接過我,我心慌了一下,沒能叫出心底那一句:爹。
爹哈哈笑了兩聲,拍拍我的屁股,走,回家。
從火船碼頭出來要經過熙熙攘攘的松口老街,沒走兩步迎面遇上挑貨郎,撥浪鼓咚咚在響。爹停下腳步問我:你要哪個?
我怯怯地看了一眼娘,娘笑了笑。我小聲地說:我要大的。
爹和娘都笑了,我也笑了。爹一手抱著我,一手給挑貨郎遞過銅板。我搖動著手中的撥浪鼓,風把鼓聲吹走,也把我的不安吹走。
爹抱著我穿過松口老街,走過糕餅店,走過打鐵鋪,一直走到王嬸的雜貨鋪門口,我掙扎著要下來。
我沖里頭喊了一句:二狗。
二狗是我的玩伴,那天我跟他說爹要回來,他玩著石子頭也不抬地說,說了這么多次,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氣得再沒找他。
二狗聞聲跑了出來,他就像對店里來來回回的客人一樣看了一眼我身邊的爹和娘,隨后就揮揮手中的彈弓,問我要不要去林中打鳥兒。
不去。我漲紅了臉,憋出這句,卻把:我爹回來了,給憋了回去。
爹拉著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走,爹的手又大又暖,包裹著我的小手,像冬天里阿婆烤火的火筒。要到家了,我掙脫爹的手,飛快地跑,一頭扎進家門口張望的阿婆的懷里。湊著她的耳朵說:阿婆,快看,那是我爹。阿婆掀起衣角擦著眼睛,摸著我的頭,笑了。
阿公坐在家門口的石墩上抽著水煙筒,和往常一樣,望著遠方,只是水煙筒咕嚕咕嚕的聲音比平時要響。
爹在家的日子不長。爹去上屋林伯家,下村王叔家,每到一處,我像個影子般跟在身后。聽著爹和別人對話,回來了?回來了。
爹又要走了,又要坐著火船離開,爹又要下南洋謀生。
我哭著不肯讓爹走,喊著也要去。爹一手抱著我,一手摸摸我的頭發(fā),太遠了,等你長大了,爹再帶你去。說完,爹的眼睛望向江面,望向遠方。
火船嘟嘟作響,那一刻,我的悲傷像江水那么長。
我把頭埋進了爹的胸口,摟著爹的脖子不放。娘伸手把我抱進了懷里,扭頭間,爹已經站在了船頭。
娘把我舉高,就像,爹回來那一天。
火船啟動,與身邊擠擠挨挨的人群聲混雜在一起。爹揮著手,喊著什么。風把爹的話吹走了。
我的淚止住了,可我卻聽到周圍有人在哭,伴著江面吹來的風。
爹坐著火船離開了,把我和娘留在了火船碼頭。江水很長很長,一直通往爹要去的南洋。我使勁揮手,用最大的聲音喊:爹。
風能捎去我的話,就像船會回來,載著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