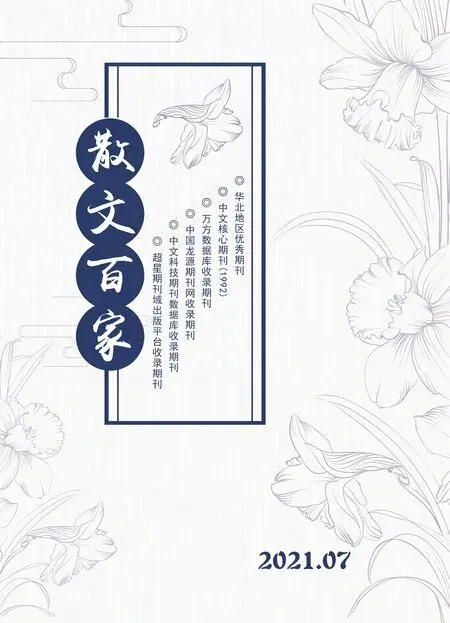迷失的自我
——運用拉康的鏡像理論分析《男孩去木星》
徐心宇
上海大學
《歷史修正辦公室》是一部小說集,其中包含六篇短篇小說和一篇中篇小說。每篇小說的主題都有所不同,并且故事中的主人公們都經歷了不同的痛苦、創傷和逆境。《男孩去木星》是該集的第三個短篇小說,主要講述了克萊爾--一個正處于青春期的“叛逆”女孩的經歷。小說以比基尼事件作為序幕開篇,在敘述過過程中,穿插了克萊爾童年經歷的倒敘。本文將運用拉康的鏡像理論來分析克萊爾的自我探索和構建,旨在分析出其身份建構出現混亂的原因。
一、鏡像階段中克萊爾的“自我”
在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中,自我形象的建立需要借助于鏡子的投射,而鏡子中的形象就是自我的原型。根據拉康的說法,主體可以在鏡子前認出自己;鏡子中的“他者”被主體誤認為是自我,而自我會如何呈現則取決于鏡子,因為不同的鏡子會反映出不同的自我。事實上,鏡像更像是一種隱喻:它可以是水,也可以是他人的視線等。除了在嬰兒時期形成的鏡像,人們還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形成不同的鏡像,并借此來構建自我。在《男孩去木星》這篇文章中,原生家庭是克萊爾構建自我的典型鏡子。
通過克萊爾對童年的回憶,埃文斯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看似溫馨,實則支離破碎的家庭。“克萊爾是孤獨的:她唯一的兄弟姐妹是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名叫肖恩,大她10歲,是她父親的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因此,年齡的差距注定了克萊爾與她的哥哥沒有什么共同話題,這也就意味著她只能獨處一室,自娛自樂。長此以往,孤獨感悄悄地進入小克萊爾的心里。正是由于童年時期的克萊爾缺少了同齡人的陪伴,她漸漸變得孤僻。
更可怕的是,“她的父親工作時間長,她的母親有某種形式感”。這意味著她甚至無法從父母那里獲得她所期盼的關心和愛護。一方面,克萊爾無法得到父愛,因為她的父親很少在她身邊。作為一名律師,克萊爾的父親忙于自己的生意,很少關注她的成長。另一方面,克萊爾能夠收獲的母愛也很有限。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孩,她愛她的母親,“但在她面前,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微型的成年人,為她六歲的欲望的愚蠢而感到尷尬”。對克萊爾來說,她的母親是一個有儀式感的女人,并且相當傳統和保守。因此,克萊爾害怕在她母親面前展示真實的自我。對于一個年幼的女孩來說,她尊重和愛她的母親,但同時她也害怕她的母親。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克萊爾內心十分孤獨,并漸漸失去了歸屬感。此外,她顯然繼承了家人的一些特征,比如不負責任、固執和叛逆。
二、想象界中的克萊爾
1953年,拉康第一次提出象征界、想象界與實在界是人類現實的三大基本轄域的概念,并首次把這三個截然不同的轄域對質起來。由此,想象界成為構成拉康思想中心的三維世界之一,與象征界和實在界相對。在鏡像階段形成的自我進入想象界后,在“他者”的影響下便有了最原始的發展和變化。克萊爾從小便受到家庭的影響,形成了孤僻的性格,這時所形成的自我,更像是對家庭成員的映射。自從霍爾夫婦搬進弗吉尼亞老街區的那天起,克萊爾的生活就發生了變化。從這時起,她遇到了第一個異于自己的“他者”,即霍爾夫婦的女兒安吉拉。有了安吉拉到陪伴,克萊爾從家庭中所感受到的孤獨和寂寞逐漸被消除。
“安吉拉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另一個自我”。對克萊爾來說,安吉拉是她“記得遇到的第一個聲音悠揚的人”。霍爾一家并不是克萊爾所遇到的第一個黑人家庭,但卻是她第一次與黑人親密接觸。顯然,對于一個白人少女來說,“克萊爾對他們的口音很著迷,而且,對他們皮膚的暗色調很著迷”。對克萊爾而言,“她渴望被人看見”,渴望從他人那里獲得在原生家庭中所得不到的關注和愛。因而,克萊爾和安吉拉這兩個膚色不同的女孩成為親密的朋友。為了紀念她們的友誼,克萊爾甚至寫了一首關于她們友誼的詩。“我判斷她的性格/所以我從不對她生氣”。這首詩被她們的老師看中,甚至被邀請“在學校二月的集會上表演”。毫無疑問,這次表演加深了她們的友誼。
想象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鏡像階段的誤認。“自我是被建立在整體性與主人性的虛幻形象基礎之上的,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維持著這種一致性與主人性的幻象”。對克萊爾而言,安吉拉的家庭滿足了她對于家庭的渴望;而安吉拉本人,更是她一直想要追尋的、理想中的另一個自己。一個被家人關愛,善良而又積極的女孩。在夏令營期間,即使她們被分在不同的小組,她們想盡辦法陪伴彼此。“當她們像小貓咪一樣躺在草地上時,克萊爾轉向安吉拉,依偎著她,摟著她的脖子”。兩個青春期的少女,深深地愛著對方,成為靈魂伴侶。無論是生活還是學習,在安吉拉的陪伴和影像下,克萊爾逐漸找到了全新的自我,獲得了快樂。
三、象征界中的克萊爾
象征界是支配個體生命活動規律的一種社會秩序。嬰兒通過習得語言的過程,與他人及現有的文化體系建立關聯,最終確立主體,由自然人變成文化人。“象征界的作用就是實現人的社會性和文化性,以及使人的性與侵略本能規范化”。在故事中,克萊爾母親和安吉拉的母親同一時期患病,安吉拉的母親最終痊愈,而克萊爾的母親卻不幸逝世,克萊爾獨自承受著這份痛苦,而她和安吉拉也開始漸行漸遠。然而,真正讓兩人的友情破裂的,是安吉拉哥哥遭遇的一場車禍。安吉拉的哥哥亞倫因為護送醉酒的克萊爾回家,而被白人青年誤解,最后導致車禍而慘死。雖然這次事故是一次意外,但卻使得安吉拉和克萊爾之間的關系決裂,甚至斷交。直到這時,克萊爾才意識到安吉拉對她而言只是一個虛幻的想象。此時的她渴望擺脫“他者”的束縛,追尋真實的自我。與自然界中的“想象”不同,象征界是充滿規律的領域。在拉康看來,象征界是一個規范主體欲望的領域。在經歷了尋求主體性的想象界之后,克萊爾試圖在象征界中建立一個新的自我。然而,盡管她努力嘗試,克萊爾仍然發現自己深陷追尋真實自我的困境之中。
在經歷了母親的離世后,克萊爾迎來了真正的自我覺醒。高中畢業后,她開始了在丹尼斯學院的生活。這一次,她選擇了自己住學生宿舍,而不是繼續留在家里。她渴望獨自生活,成為一個更加獨立的女孩。此外,她也渴望通過社交來遺忘曾經的痛苦。糟糕的是,她的父親剛剛失去了第二任妻子,便又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對克萊爾來說,在她母親去世后不久,繼母“已經以如此快的速度跨入了她母親留下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她對繼母的厭惡更深。為了表示她的憤怒,克萊爾經常和她的男朋友杰克遜獨處一室,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惹怒繼母,讓她“無法忍受”。
拉康通常將精神分析歸入語言的層面。在他看來,符號秩序的基本結構是語言。因此,正是在這個秩序中,主體開始成為說話的對象,并具有自我意識。在小說中,自從繼母闖入自己的生活后,克萊爾的家庭地位也受到威脅:她無法向父親表達她內心的真實想法。換言之,繼母的出現使克萊爾失去了話語權。從佛蒙特州到佛羅里達州的旅行,她經歷磨人的轉機過程,因為繼母“認為為直達航班支付兩倍的費用是一種浪費”。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她父親現在必須聽從繼母的話。顯然,話語權的缺失使得克萊爾在家里吃盡苦頭,因此他頁只能選擇與男友廝混來激怒繼母。她和繼母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克萊爾更加叛逆和迷失。在象征界中,克萊爾未能構建一個新的自我,反而更加迷失正確方向。
四、真實界的克萊爾
根據拉康的觀點,真實,即不可知的和不可模仿的,是無法想象的。首先,真實界經常與“創傷”這一概念聯系在一起,它指的是人們對深感痛苦或不安的事件的反應。在《男孩去火星》中,克萊爾也在比基尼事件中經歷了創傷。事實上,克萊爾想要的是用比基尼照來激怒她的繼母。相反,在她穿著印有邦聯旗幟的比基尼照片在互聯網上瘋傳后,沒過多久,這張照片就成了網友們激烈爭論的對象,網友們紛紛指責她是一個種族歧視主義者。克萊爾的個人信息也被人肉搜索:她的電子郵件地址被公開了,數百條憤怒的、支持的甚至色情的信息涌入了她的收件箱。甚至連克萊爾的同父異母的哥哥肖恩也“留下了一條憤怒的語音郵件,問她在想什么”。
毫無疑問,這一切都是因為克萊爾的非裔美國舍友卡門。對她而言,克萊爾的這一行為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的意味。于是,在她的轉發和語言煽動下,克萊爾的照片在各大網站被轉貼和轉發。面對外界對種族歧視的指責和謾罵,克萊爾再次迷失了自己。為了擺脫現實,“克萊爾關掉手機和收件箱,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在網上看唱歌的山羊的視頻”。[盡管她向校園自由主義者的主席羅伯特吐露了自己的感受,但她仍然被負面情緒所控制著。
此外,面對這個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卡門,她的非裔美國人的形象也克萊爾對于自己以前最好的朋友--安吉拉的回憶。顯然,這次比基尼事件激活了克萊爾曾經所遭受的創傷。在安吉拉的哥哥艾倫因車禍去世后,霍爾夫婦便帶著安吉拉搬出社區,此時的克萊爾“感到羞愧卻又松了口氣,具體什么她也說不清楚”。克萊爾的情緒很復雜,這次事故留在她心中的創傷無法通過語言來表達。當她面對種族歧視的指控時,她本可以利用自己與安吉拉曾經的友情來為自己辯解。但是,內心巨大的創傷讓她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沉默。
在故事的最后,即使克萊爾被憤怒的同學所圍攻,克萊爾仍堅持告訴自己“她仍然可以成為她想成為的任何人”。[雖然她身陷泥潭,但她仍然認為自己有可能成為她想成為的任何人,這也表明她正在建立一個新的自我的道路上。
五、結論
在拉康的三界的基礎上,克萊爾的成長歷程得到了剖析。由于受到家庭的影響,克萊爾在原始鏡像階段構建了一個混亂的自我。可以說,原生家庭的不和諧就注定了克萊爾自我構建之路的曲折和艱辛。進入想象界,克萊爾遇到了“他者”--安吉拉,從而找到了一個嶄新卻虛幻的自我。在象征界中,克萊爾因為繼母的出現而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這實際上加劇了自我迷失。最后,在現實界中,克萊爾經歷了比尼基事件,并因此而激發了她與安吉拉絕交的回憶。可以說,她經歷了雙重創傷。然而,克萊爾從未放棄尋找一個新的自我。她是一個樂觀的人,并始終自己才是人生的掌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