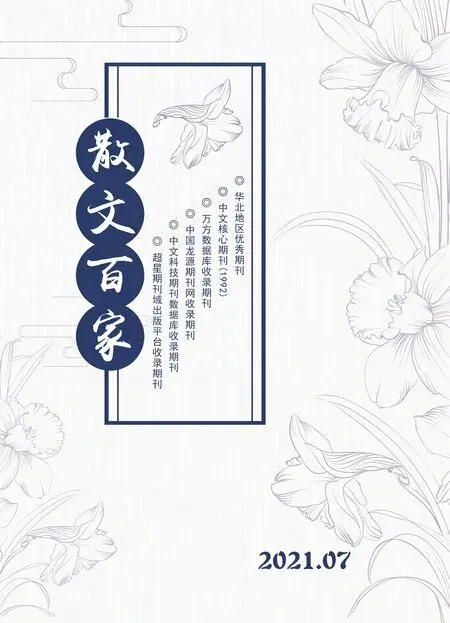淺議譚恩美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書寫
陳 蕊
河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譚恩美,英文名AmyTan,是當代著名美籍華裔女作家。她將華裔文學引入美國主流文學,被評論家們認為是湯婷婷之后美國華裔文學的又一高峰。她的文學作品包括六部小說,兩部兒童文學及一部散文集。譚恩美是第二代美國華裔,成長于中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因此她的文學創作離不開她獨特的中國文化背景和華裔身份,吸引她的讀者的也正是其小說中所呈現出的遙遠神秘充滿異域風情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故事。她的作品主要以女性為主題,以華裔女性敘事為主線,講述中國母親們的故事,并通過自己對中國的想象來書寫并重新構造中國形象。
一、中國——被否定的“他者”
曾有西方評論家認為:“譚對比了母親們和女兒們之間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念,表現了第一代移民向他們的下一代傳遞本民族文化的困難。”客觀地講,這種困難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因為在母女為代表的中西文化的對比中,女兒幾乎對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抱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匪夷所思的態度。
第一,這種描寫首先表現在飲食上,在《靈感女孩》中尤為突出。小說的現實背景是在20世紀的90年代,奧利維亞答應和離異的丈夫西蒙、同父異母的姐姐鄺一起去中國,而這一趟中國之行描述了很多中國人的怪異飲食。小說中的中國人不僅什么都吃,而且在作家的渲染下,中國人的宰殺行為也顯得異常的殘忍。
小說中,奧利維亞還透過攝像機詳細地記錄了中國人殺雞的過程。她看到杜麗麗“手里的雞鳴叫不停。……她把刀鋒壓在雞的脖子上,她慢慢用力,一股細細的血柱奔涌而出,我也仿佛挨了刀似地一抖。接著她把雞腿向上一提,血從脖子里流進了搪瓷碗中。我可以聽到后面的豬在尖叫,那是真正的尖叫,就像人在恐怖之中一樣。……大約有幾分鐘,我們看著它在無助地掙扎,最終翻起白眼,停止了抽搐。……西蒙向我走來,‘這簡直太野蠻了,你怎么還能拍得下去?’”
在中國,殺雞本來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中國的農村是食品加工業不發達的地方,自己殺雞是由老百姓的生活條件所決定的。透過對他者中國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到,譚恩美是在否定中國的同時肯定美國,是在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中國的落后,夸大中國飲食的弊病之處,而不是去選擇中國飲食的健康、營養等方面來描寫。這實質上是作家在有意拉開與中國的距離,宣告自己是典型的美國人,而中國人只能作為與之相對的飲食怪異的異類和他者來存在,反映出作家心理上對自己的華裔身份的下意識的排斥,也反映出作家是在用已經內化了的美國人的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眼光來看待中國。
第二,對典型的中國式家庭教育的否定。母親們成長于中國,她們顯然習慣于用中國式的思想觀念來要求和教育自己的女兒。母親們認為女兒應該聽從母親的安排,而且“做女兒的不應該有秘密瞞著母親”,但女兒們則反駁說:“我有隱私權,有權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活著不是為了滿足你的要求!”“別再對我管頭管腳了,我是我自己的。”母親身上顯然有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式家長制作風,而女兒們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她們更信奉自我的獨立和自由。
中國母親身上還體現了典型的中國式成功觀。她們將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為了女兒的成功她們可以去做清潔工,也可以做出更多的自我犧牲。她們認為女兒的成功是自己的光榮,是光耀門楣的事情;她們認為女兒不僅代表著個人,也還代表了家庭,這顯然與美國的個人主義的文化核心觀念是相沖突的。因此,女兒不能明白母親為什么非要拿她出風頭,女兒不想成為母親所希望她成為的那種人,她只想做自己。實際上,華裔女兒們正是在美國文化的教育下,“吸收內化了一套白人種族主義者貶低華人的陳規陋習,與母親們之間有了一道無形的屏障。她們嘲笑母親的語言,嘲笑母親的生活習慣,認識不到母親望女成鳳的良苦用心”。她們根本就沒有去試著理解母親和母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
第三,在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小說中的中國同樣是一個被否定的對象。小說中的女兒覺得中國母親“穿著領子硬邦邦地豎著緊箍著頭頸、前襟繡花的旗袍,樣子十分好笑”。她們認為在舊中國,一個大家族“二十幾口人擠住在一個屋頂下,大家庭里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地充滿了喋喋不休的爭執和抱怨”。中國人的房子的布局裝修也體現著太多門第家族的含義。小說里的中國人也總是言不由衷、虛假客套,嘴里說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兩回事。中國人還十分注意措辭和用詞,習慣講話要婉轉含蓄,用美國人的方式去理解,“這是中國式的文字游戲,一種措辭技巧的賣弄。——這其實是在混淆兩種根本相反的概念”。這一套在女兒們看來是她們永遠也學不會的。作為中國人“你總是要為其他人負責,不管什么事”,而“在美國——什么自由啦、獨立啦、個人的想法啦、干你想干的事啦、不必服從你母親啦”,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國人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就行了。實際上,作家是在對比中表明自己的看法:“中國人有中國式的建議,美國人也有美國式的建議,而一般情況下,我認為,美國式的見解,更合我意。”作家并沒有看到中國人行為方式的背后蘊含的文化淵源,也沒能看到中國文化的合理性存在,而只是單純地從一個典型的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和中國文化。
二、中國——被肯定的“他者”
細讀譚恩美的小說,我們發現她在作品中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傳統風俗節日的展示,二是對一些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象的大量使用。但是,我們還需要清醒地看待這種認同,作家文化認同的背后還有更復雜的認同動機。
第一,小說中展示了中國幾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和風俗,比如中秋節、新年,以及中國人傳統的婚禮習俗。《接骨師之女》中寫到中國的中秋節,茹靈的女兒露絲認為“中秋對中國人來說就相當于美國人的感恩節”,她希望家人和朋友們能夠在每年的這一天都聚在一起,覺得大家應該努力地去維持彼此之間的聯系。這些中國傳統節日風俗的描寫給西方讀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充滿了濃郁的異國情調,反映出作家對中國文化資源的利用。同時,因為美國社會人際關系的疏離,也因為華裔受到的種族歧視,小說中也反映了華裔女兒對中國傳統節日里蘊含的某些家庭觀念的認同,她們認為家族成員之間應該保持聯絡,應該維持親情。另外,對中國傳統節日風俗的積極展示不僅體現了作家對部分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是認同,也可以說還有部分的自豪或炫耀的成分在里面,因為作為華裔的譚恩美也需要通過對故國文化的認同來確認自我、認同自我。
第二,作品中著重使用了一些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象。在18世紀,歐洲出現過“中國潮”。那時候,中國玄妙高深的哲學、悠久的歷史、漢語、絲織品、瓷器、漆器、茶葉等就對西方人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凝聚著中國文化內蘊的意象成為了中國的代名詞,只要提到它們,人們就會想到中國。在譚恩美的作品中也有這樣一些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象,主要有中醫、筆墨、漢字、儒道思想等。因為它們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精粹,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象,所以西方人普遍對它們有一定的認知,也對它們有著濃厚的興趣。
小說《灶神之妻》中的中國母親得知女兒珍珠得了多發性硬化癥,而西醫治療又不見成效,她便馬上說要帶女兒到中國去進行中醫治療。如果說這只能表明是中國母親個人對中醫的信賴,那么另一個細節的描述則顯示了中醫本身的確是一種帶有神奇效果的治病方法。《喜福會》中提到華人生活的街區有一家中醫藥店,店主“老李把那種稀奇古怪的蛇蟲百腳的干殼,和著什么東西的枯葉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賣給病家。據說有一次,他就是用這種祖傳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國醫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
在《沉沒之魚》中,作家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大加贊揚。小說中寫道:“中國就像棵古老的松樹,需要慢慢地感受和領悟——古老又充滿活力,如五千年的歷史那樣無比宏偉。”作家對中國的儒道思想也是頗為贊賞,認為中國人不會隨意拋棄傳統,而是善于對多種信仰兼容并蓄,并會在修正和完善中保持自己信仰的主導地位。中國人的信仰里融入了多種成分,“從藏傳佛教開始,加入一些印度佛教、一些漢傳佛教,萬物有靈論以及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就像寬闊無邊的大海,能容納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這些寺廟是純中國的,如孔子般謙卑而典雅,這些混合使中國具有無窮的魅力。世界上所有的早期文明中,只有中國是連綿不斷地延續著自己的獨特文明”。作家覺得這些都是中國所獨有的文化深蘊。
當然,小說還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中國文化意象,它們與前文提到的那些典型意象在小說中一起構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征,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氛圍,滿足了西方讀者的異域審美趣味,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異國情調。同時,這些古老的中國文化意象積淀著一種寧靜、超脫的美感,甚至也能喚起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自省和內察。
三、結語
雖然譚恩美的中國構造多是根據二手資料,比如母親的講述,華人社區的影響,還有相關文獻資料的查閱等,但是從這些琳瑯滿目的中國文化的描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不管作家用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她的創作主題,中國文化背景對她的影響和烙印之深刻是不可否認的。另外,從作家的華裔身份這一實際情況出發,我們認為對這些古老輝煌的中國文化的描述正說明了作家譚恩美對自己文化之根中國的認同,進一步可以看出這實際上也是作家對自己華裔身份的認同。在種族歧視普遍存在的美國主流社會,美籍華裔需要首先找到并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夠自信而不彷徨地生活。譚恩美通過在其作品中肯定自己的文化之根——具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國去肯定自己的華裔身份,增強文化身份自信,反抗美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雖然譚恩美的作品不是為了認可中國而著,但作為其為肯定自我華裔身份而做的努力還是值得認可的,這是美籍華裔作家為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獲得與白人作家平等的地位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