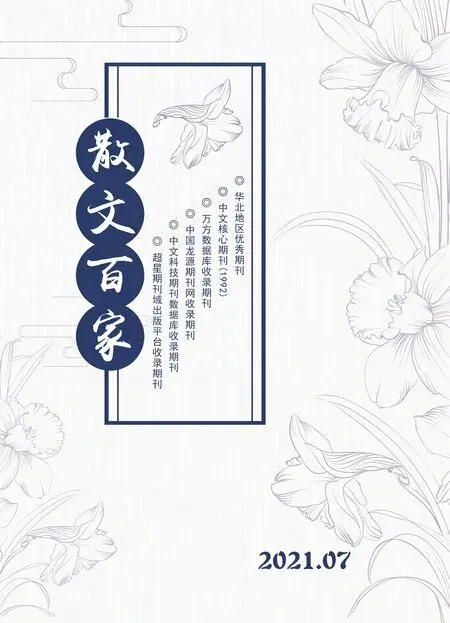重思柏拉圖“靈感說”
王昊宇
安徽大學
一、柏拉圖靈感說的時代背景
柏拉圖歷經古希臘的繁華到沒落,他將沒落原因歸結于“德性的淪喪”,也即“理性的淪喪”,人們借借宗教迷信來寬慰痛苦的生活。在當時,宗教觀念已密切滲透古希臘人生活當中,當時創作的詩歌與宗教亦存在共存關系。由此,柏拉圖不可能直接跨越當時存在的種種時代背景羈絆和局限,撇開神的信仰來單獨探討詩歌。
柏拉圖試圖對世俗概念中的宗教進行改造,他厭惡世俗宗教中的迂腐,而希臘宗教中的神性信仰,正是自然力與人的靈魂的人格化的顯現,是人的意志與神的意志高度統一。柏拉圖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對于理性價值十分重視。他將理性看作是人類認識世界、認識并實現自我的一個本質屬性,然而即便如此,因其“靈感說”的非理性色彩,頗受爭議。不可否認,柏拉圖的思想中確實有許多希臘神話的元素,但其“靈感說”實質是否是非理性的,要取決于他對于宗教的理解。
二、“靈感說”的理性內核
柏拉圖是首位對“靈感”概念進行較完整理論性論述的哲學家,在《柏拉圖文藝對話集》中有這么一段話:“科里班特巫師們在舞蹈時,心理都受一種迷狂支配……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不得到靈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沒有能力創造,就不能做詩或代神說話。”這里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首先,迷狂是詩人創作成功的必要條件,所謂“靈感”,也就是創作主體的一種迷狂狀態;其次,詩人的靈感,是必須失去平常理智的,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成功,陷入迷狂的狀態,由此體現了迷信、反理性色彩。實則,柏拉圖對于他的迷狂精神,是給予理性解釋和論述的。雖然柏拉圖眼中,神靈是遠高于塵世之上的存在,柏拉圖“靈感說”中“神賜靈感”論,諸如“神賜”“迷狂”等詞僅從字義層面上來理解,確實極具神秘主義色彩,但這些概念實質應是“理性賜靈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真理存在,而詩人創作靈感依靠神靈憑附,也是理性活動。
深入了解“迷狂”一詞的內在含義,我們需返回到《斐德若》篇中,“如果迷狂絕對是壞的,這話倒還可說;但是也有一種迷狂是神靈的稟賦,人類的許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從它來的。由此可知,柏拉圖的“迷狂”并非一種身體病理上的狀態,它是人類到達成功必經階段,這種神靈稟賦絕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件再好不過的美事。應該說,柏拉圖主張靈感是源于神力憑賦而帶來的一種獨特的迷狂狀態,對于靈感在文藝創作中的意義,“靈感說”“迷狂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揭示了創作靈感的心理特征的,只是當時他尚且無法用科學態度來之進行解釋說明,所以使用了“迷狂”這樣一個極具神秘色彩的詞語。若想剝出“迷狂”這個詞語中的合理因素,關鍵在于弄清前文所提及的“相對理智的狀態”,即“平常理智”的真正含義。為此,就要談及柏拉圖“靈魂不朽”和“靈魂回憶”的觀點。
柏拉圖將神靈憑附的靈感狀態,解釋為不朽的靈魂從前世帶來的回憶。在柏拉圖看來,靈魂依附在肉體身上,只是暫時的,肉體使得靈魂蒙上了一層紗帳,看不清真實。但靈魂的本質是積極向上的,在肉體死亡之后,靈魂會飛升至天神的世界,盡情的去觀照理式世界。待它再度重返人間時,人間的事物使它回想起那些在理式世界所見到的景象,這種高度的喜悅就是迷狂的狀態。詩人為了獲得靈感,陷入“迷狂”的狀態,必須舍棄這些凡間的欲望和規矩,打破這種“平常的理智”,才能夠超越肉體的束縛,體悟到“理式世界”的終極真善美。所以,在柏拉圖看來,這種“平常理智”狀態,才是一種不理性存在。
綜上可知,柏拉圖的“靈感說”不單單是反動的、迷信的。相反,他在屬于自己的哲學體系框架中建構了一個真正理性且豐富的世界。
三、“靈感說”下的審美啟示
靈感狀態是一種生命整體的升華,由此,人類意志不再受現實的道德所束縛,思想和感受亦不被現實的原則所圍困,情感想象仿佛被重新激發一般,在這種審美理想感召下,人們逐漸擺脫麻木和遲鈍,內心踴躍出一股極度的亢奮,伴隨著這種亢奮,人們的全部生理器官都仿佛變得敏銳起來。可以說,獲得靈感的狀態,就是對于現實生活中刻板規則的拋棄和對抗,柏拉圖“理式世界”中的“靈感說”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的體系下所建立的,我們常說,藝術不完全是直覺,但卻是有賴于直覺的,倘使沒有柏拉圖所強調的這種“迷狂”狀態,缺乏這種生理上的亢奮,感官上的敏銳以及血液里的激情,我們是很難對一個藝術創作進行單純的知和意層面上的展開的。
再者,柏拉圖的“理式世界”追求的是終極真理,但終極真理帶給我們最大的價值其實并不在于其究竟有多“終極”,其真正價值就在于它在每個階段,都拓寬了人類的認識局限,使得人類不斷超越現實,繼而實現個體有限生命和意義的超越,才有可能進入審美超越這個層面,使得每一個“相對真理”的階段都更加向“終極真理”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