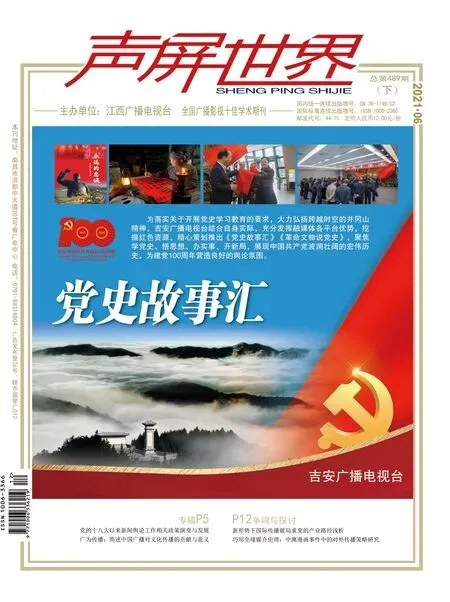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秀場(chǎng)直播:資本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的交織
□羅海嬌 馬夢(mèng)婕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網(wǎng)絡(luò)直播成了網(wǎng)民與外在世界建立聯(lián)系的重要方式,截至當(dāng)年6月,直播用戶規(guī)模達(dá)5.62億,約占網(wǎng)民整體的60%。網(wǎng)絡(luò)直播的發(fā)展如日中天,如影隨形的卻是層出不窮的負(fù)面新聞,如直播經(jīng)常涉及低俗媚俗、斗富炫富等內(nèi)容。哈貝馬斯認(rèn)為當(dāng)下社會(huì)亂象頻現(xiàn)的核心在于社會(huì)系統(tǒng)對(duì)生活世界的控制與干涉,因此,他提出通過(guò)合理化交往行為的方式達(dá)到生活世界中文化、社會(huì)和個(gè)人領(lǐng)域的均衡發(fā)展。在哈貝馬斯“應(yīng)然”規(guī)范指引下,本文觀察“實(shí)然”的秀場(chǎng)直播(表演、閑聊、送禮),期待重新認(rèn)識(shí)并驗(yàn)證生活世界理論的意義與價(jià)值,對(duì)生活世界與社會(huì)系統(tǒng)的關(guān)系有更深入的理解與認(rèn)識(shí)。
生活世界:重塑以語(yǔ)言為媒介的交往行為
在胡塞爾、許茨的基礎(chǔ)上,哈貝馬斯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二分:社會(huì)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社會(huì)系統(tǒng)是指基于工具理性建構(gòu)起來(lái)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體系,它的媒介是以行政效率、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為追求的權(quán)力和資本。生活世界是指基于價(jià)值理性形成的共同的生活背景和信念集合,它以語(yǔ)言為媒介,強(qiáng)調(diào)人們?cè)诮煌辛鲃?dòng)著的文化、道德和意義。在哈貝馬斯看來(lái),當(dāng)社會(huì)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并行不悖時(shí),工具理性與價(jià)值理性平衡發(fā)展,生活世界趨向合理化,人們實(shí)現(xiàn)真實(shí)、真誠(chéng)、正當(dāng)?shù)膶?duì)話,促成彼此的理解與認(rèn)同。若社會(huì)系統(tǒng)的力量超過(guò)生活世界,那么生活世界就會(huì)被控制。例如在文化知識(shí)方面,傳播范圍越廣遠(yuǎn),思想厚度越淺薄;在社會(huì)秩序方面,受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影響,社會(huì)價(jià)值觀念趨于片面物質(zhì)化;在個(gè)體同一性方面,現(xiàn)代的個(gè)人、權(quán)利意識(shí)與傳統(tǒng)的群體本位、等級(jí)意識(shí)發(fā)生糾纏等。具體而言,隨著社會(huì)系統(tǒng)的擴(kuò)張,原本通過(guò)知識(shí)儲(chǔ)存和理性對(duì)話建立起來(lái)的話語(yǔ)權(quán)會(huì)更多地屈從于權(quán)力和資本的表達(dá),使得文化公共領(lǐng)域越來(lái)越功利化和世俗化。網(wǎng)絡(luò)秀場(chǎng)直播的出現(xiàn)為觀察生活世界與社會(huì)系統(tǒng)的“對(duì)話關(guān)系”提供具體場(chǎng)域,當(dāng)社會(huì)系統(tǒng)占主導(dǎo)時(shí),它將與生活世界發(fā)生怎樣的互動(dòng)?這些互動(dòng)又是如何一步步生成、演變的?
禮物媒介的互動(dòng)可編織游離個(gè)體的意義網(wǎng)
認(rèn)知需求是用戶參與直播的五大需求之一,不過(guò)有近一半的用戶期待未來(lái)能繼續(xù)豐富直播的內(nèi)容與類型,可見(jiàn)用戶對(duì)直播的內(nèi)容并不滿意。盡管直播內(nèi)容的生產(chǎn)與流通無(wú)法實(shí)現(xiàn)文化層面上的傳承與融合,但“禮物”媒介的創(chuàng)制卻使得游離個(gè)體之間實(shí)現(xiàn)了共同意義的快速生成與理解。首先,秀場(chǎng)直播創(chuàng)建了陌生人互動(dòng)的“交換物”——虛擬禮物。互動(dòng)的虛擬禮物越昂貴,禮物的視覺(jué)效果越壯觀,意味著送禮者越容易被“看到”。當(dāng)主播收到禮物后,他們會(huì)主動(dòng)為觀眾表演才藝;當(dāng)觀眾希望主播為他們表演時(shí),他們會(huì)主動(dòng)刷禮物。相比語(yǔ)言媒介,禮物媒介的意義和內(nèi)涵更為穩(wěn)定。禮物的贈(zèng)予意味著對(duì)相應(yīng)回饋的期待,這是陌生交往者都明晰的單一法則。其次,秀場(chǎng)直播為虛擬禮物的流通提供了以游戲?yàn)楹诵牡幕?dòng)機(jī)制。平臺(tái)會(huì)給主播安排每日、每周、每月要完成的任務(wù),并邀請(qǐng)觀眾進(jìn)入直播間刷禮物支持主播的“連線PK”活動(dòng)。平臺(tái)通過(guò)這種“玩耍”“競(jìng)爭(zhēng)”的方式為主播與觀眾創(chuàng)造了持續(xù)交流的可能,在直播間,參與個(gè)體共享同一的傳播信息甚至參與整體的信息生產(chǎn)過(guò)程,或許在某一刻產(chǎn)生同樣的情緒,這種情緒氛圍是游離個(gè)體向往的共同意義與體驗(yàn)。但意義生產(chǎn)、流通的過(guò)程充滿了為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服務(wù)的氣息,短暫的活動(dòng)環(huán)節(jié)最大化地拼湊起觀眾的零碎時(shí)間,讓參與個(gè)體在感受到新鮮有趣互動(dòng)體驗(yàn)的同時(shí)自愿服從平臺(tái)的資本目的。在資本系統(tǒng)的規(guī)訓(xùn)下,陌生個(gè)體適應(yīng)了同一邏輯——贈(zèng)送禮物、情感回饋,再贈(zèng)送禮物、再情感回饋,循環(huán)往復(fù)的互動(dòng)程式使得參與個(gè)體的生活在“觀看”與“被觀看”中連接起來(lái),并在半封閉的直播空間中,從自我與他人的對(duì)話關(guān)系中確認(rèn)自我的存在,拓展自我的意義。
消費(fèi)性身份的確認(rèn)可獲得虛擬的親密關(guān)系
哈貝馬斯眼中的生活世界是指在社會(huì)層面上實(shí)現(xiàn)某種整合與團(tuán)結(jié),而資本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讓這一切分崩離析。認(rèn)同和歸屬感需求的滿足是網(wǎng)民參與直播的重要原因。一位行業(yè)投資者表示,如果觀眾“不用錢砸一個(gè)地位出來(lái)”是沒(méi)什么歸屬感可言的。隨著禮物媒介的流動(dòng),與資本深度捆綁的直播社群是如何快速營(yíng)造出親密氛圍的?首先,平臺(tái)售賣的社群身份是具體可感的。雖然社群身份是虛擬的,但身份賦予的特權(quán)是清晰可見(jiàn)的。研究表明,個(gè)體一旦知覺(jué)到分類會(huì)積極評(píng)價(jià)并建設(shè)自己所屬的社群,而特權(quán)的賦予使得觀眾對(duì)虛擬社群的想象愈加豐富、形象。身份越尊貴的觀眾越容易感受到被仰望、崇拜的目光,例如“尊貴年守護(hù)”(充值100元獲得的身份)比“月守護(hù)”(充值30元獲得的身份)擁有更多的特權(quán),獨(dú)屬于“尊貴年守護(hù)”的踢人、禁言等權(quán)力讓想象中的親密關(guān)系多了一層掌控與被掌控的快感。其次,平臺(tái)設(shè)置的暫時(shí)性身份需要觀眾不斷地投入禮物才能維持。無(wú)論是何種身份都需要觀眾持續(xù)地付出才可以保持,一旦停止投入黏貼在個(gè)人賬號(hào)上明顯的身份標(biāo)識(shí)會(huì)消失,相應(yīng)的特權(quán)也會(huì)失去。持續(xù)投入的觀眾對(duì)虛擬社群有著更強(qiáng)的責(zé)任感,他們作為社群的掌控人之一,意識(shí)到與主播在某些具體利益或議題上的共識(shí)與認(rèn)同。這種共同感黏貼起他們分離的身體與漂浮的想象,讓他們體驗(yàn)到作為交往共同體所擁有的積極信任與關(guān)系純粹的稀缺感受。但虛擬共同體的聯(lián)合是短暫的,它隨標(biāo)記的貼上而快速開(kāi)始,隨標(biāo)記的撕下而迅速消失,它不像真實(shí)的親密關(guān)系那樣沉重,因?yàn)樗倪M(jìn)出絲毫不費(fèi)力氣——個(gè)體的連線、離線,再連線、再離線,使得參與個(gè)體永遠(yuǎn)不會(huì)隸屬于某一特定社群,而是如同流水般無(wú)常形地游走。
物化的社交關(guān)系讓個(gè)體陷入矛盾與焦慮
在“直播+社交”的模式下,游離的個(gè)體得以聚合,陌生的個(gè)體得以親密,但嫁接在資本之上的關(guān)系模式也給個(gè)體帶來(lái)了新的痛苦。首先,在秀場(chǎng)直播“沒(méi)有消費(fèi)就沒(méi)有社交”的邏輯下,渴望通過(guò)社交活動(dòng)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以排除孤獨(dú)或焦慮的觀眾顯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們排斥秀場(chǎng)直播充斥的資本邏輯,在他們看來(lái),靠禮物媒介“續(xù)租”的情感關(guān)系似乎帶著“污點(diǎn)”,親密關(guān)系淪為資本的附庸——關(guān)系不再純粹、可靠。另一方面,他們享受著禮物消費(fèi)帶來(lái)的身份與地位,因?yàn)樗⒍Y物滿足了他們?cè)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無(wú)法企及的對(duì)“紙醉金迷”生活的想象與渴望。例如價(jià)值600元的“蘭博基尼”禮物可以讓他們徜徉在自己作為頂級(jí)富豪的暢想之中,價(jià)值1元的“玫瑰花”禮物可以讓他們有機(jī)會(huì)表達(dá)或收獲兩性浪漫關(guān)系中的愛(ài)與被愛(ài)。他們期待在消費(fèi)中獲得他人的尊重與肯定,但這種尊重與肯定又被他們認(rèn)為不夠真實(shí),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言的資本系統(tǒng)控制生活世界的后果——摧毀了人們溝通的共同背景和信念,讓人際關(guān)系充滿懷疑。其次,秀場(chǎng)直播的社交關(guān)系是一種商品,作為商品一部分的主播陷入無(wú)法掌控自我生活的物化焦慮中。主播為了讓虛擬關(guān)系更穩(wěn)定,他們被迫選擇延長(zhǎng)直播時(shí)間,一周直播七天、每天八小時(shí)以上是非常普遍的,他們認(rèn)為只有像機(jī)器人一樣不停地運(yùn)作,才能消減在休息間隙時(shí)被其他主播淘汰、取代的不安全感。此外,為了讓直播內(nèi)容更具“賣點(diǎn)”,主播被迫公開(kāi)個(gè)人私生活,直播場(chǎng)域出現(xiàn)“非道德事件”的道德化傾向,曖昧、私密、炫耀、虛榮的言語(yǔ)和行為在直播間時(shí)有發(fā)生,且顯得相當(dāng)平常。主播最大的痛苦在于他們被迫將“私人屬性”與“表演屬性”長(zhǎng)期糅合在一起,他們認(rèn)為只有出售自己的全部,將自己的所有“商品化”,才能掌握主動(dòng)權(quán)。但實(shí)際上,在主動(dòng)把自己變成商品的同時(shí),也把自己變成了活生生的消極客體,自己的一切受到他人目光的控制,貶損著自己作為主體的道德、審美與尊嚴(yán)。
結(jié)語(yǔ)
受制于資本邏輯的秀場(chǎng)直播雖然導(dǎo)致個(gè)體的物化,但同時(shí)也在原子化的社會(huì)中為游離的個(gè)體提供聚合的空間,為陌生的個(gè)體提供親密的體驗(yàn)。當(dāng)資本系統(tǒng)的力量超過(guò)生活世界時(shí),生活世界也會(huì)有所應(yīng)對(duì),例如借助禮物媒介“贈(zèng)予——回饋”邏輯幫助個(gè)體實(shí)現(xiàn)意義“聯(lián)結(jié)”,借助消費(fèi)性身份幫助個(gè)體獲得具體的情感體驗(yàn)。社會(huì)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的關(guān)系并沒(méi)有那么簡(jiǎn)單,二者不僅相互對(duì)抗而且相互滲透,正如秀場(chǎng)直播在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控制下借助資本邏輯找到新的社交空間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