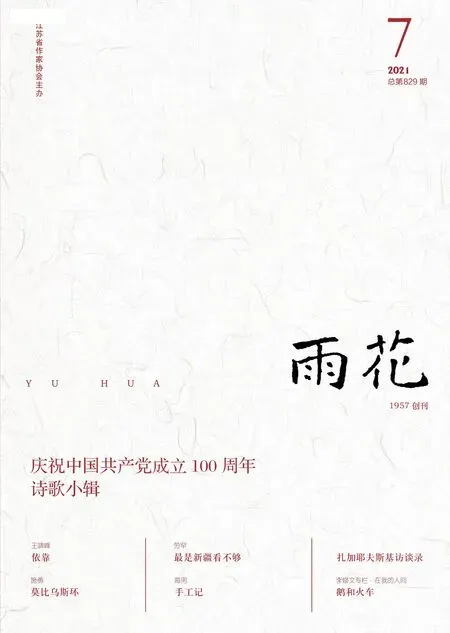迷樓
汪夕祿
二十歲的時(shí)候,我曾經(jīng)短暫地做過一段時(shí)間倉庫看管人。
我從家鄉(xiāng)來到這個(gè)城市,沒有一雙皮鞋,第一次上街閑逛,穿著母親新做的黑布鞋,踩到一塊西瓜皮,摔成了骨折。好在年輕。在醫(yī)院里躺了一個(gè)月,一分錢沒有掙到,把半年的生活費(fèi)都用在了醫(yī)院里。我不敢告訴父母,怕他們擔(dān)心。我一個(gè)人住在醫(yī)院里,沒有一個(gè)朋友,那雙闖了禍的布鞋,一正一反趴在床下。看到布鞋,我特別想念母親。我掙扎著起來,走到衛(wèi)生間,坐在馬桶上,痛哭了一場(chǎng)。那時(shí)候,窗外新千年的夜空正亮,一個(gè)個(gè)長著尾巴的焰火,刺破黑暗,升入高空,很快消失在暗夜當(dāng)中。
在醫(yī)院里,我認(rèn)識(shí)了一個(gè)老頭。他是市博物館的館長,酒喝多了,摔斷了小腿。我們躺在同一間病房里。他是個(gè)孤單的老頭,姓黃,除了單位里有人來看過他,沒一個(gè)家人來過。后來聽說他有一個(gè)女兒,在外面讀書,他沒敢告訴女兒。妻子平時(shí)在女兒那邊,也沒有出現(xiàn)過。我喜歡看書。他也喜歡。所以我們的病房平時(shí)很安靜。我看的是從原來學(xué)校圖書館順出來的一本小說,書名叫《綠衣亨利》。我看得很入神。他帶了一本漢語詞典,每天都看。我不喜歡和陌生人講話,他主動(dòng)跟我說話,問了我年齡、家鄉(xiāng),我一一作答。后來陷入沉默。看到我手上的書,他問,你喜歡讀書?算是吧。我回答他。平時(shí)看什么書?亂看,主要是小說,外國的。我指指手中的書。聊著聊著,我算是對(duì)他有了一點(diǎn)興趣,于是問,您每天看詞典?他解釋道,小說、散文,包括學(xué)術(shù)著作,都帶著作者的體溫,主觀性強(qiáng),只有詞典最誠實(shí),所以我只看詞典。我答不上話,覺得他很牛。
就是這個(gè)很牛的人,知道了我的情況,幫了我一把,出院后,他讓我到博物館的一個(gè)庫房里看門。你主要是去讀書。他這樣對(duì)我說。我很感激他,拎了一瓶酒去他家看他。他把我的酒放到一邊,從柜子里拿出一瓶茅臺(tái),我們喝掉了一瓶。我的酒量一般,卻沒有醉。他也沒有醉。我們剛想喝第二瓶,來了一個(gè)漂亮阿姨。黃館長趕緊把酒收了起來。阿姨沒有看我們,直接進(jìn)了房間。我還算清醒,趕緊起來告辭。他把我送到門口,送了我?guī)妆緯且惶自S國璋主編的英語教材。那時(shí)候,只要有點(diǎn)上進(jìn)心的青年,都在學(xué)習(xí)“許國璋”。我收下了,努力笑了笑。
市博物館總共有兩個(gè)倉庫,我看管的這個(gè)倉庫是老監(jiān)獄改造的,里面不知道存放了些什么。我雖然是看管人,卻不是管理員,什么都不知道,我的任務(wù)是不讓陌生人靠近。有一條大黃狗是我的伙伴,這條狗有點(diǎn)呆,個(gè)子很大,骨架結(jié)實(shí),就是腦子不行,遇到陌生人從來不叫,看到熟人就叫。白天還有一個(gè)姓羅的管理員,人們都叫他小羅。看年齡,他也有五十多了,都這年紀(jì)了還被人叫作小羅,總讓人難受。他自己好像毫不在意,我這個(gè)外人也就不需要多想了。到了晚上,就剩下大黃和我。大黃睡覺,我睡不著,像狗一樣瞎逛。更多時(shí)候,我到錄像廳消磨時(shí)間。有一天晚上,錄像廳人不多,看完了前面的正片,片名記不得了,港片,槍戰(zhàn),從開始打到最后,里面的演員都面熟,但一個(gè)名字都叫不出來。有人喊老板加片,老板就加了一部。極其香艷,看得我吞咽不已。正看著,忽然感覺不對(duì)。回頭一看,一個(gè)短發(fā)女孩,正瞪大眼睛看著屏幕。我嚇了一跳,這個(gè)錄像廳我經(jīng)常來,在看加片的時(shí)候從來沒有見到過女性。一般情況,老板說加片的時(shí)候,女孩們就自覺地走了。因?yàn)榧拥钠右词悄欠N片,要么是恐怖片,女孩子看了畢竟不方便。短發(fā)女孩沒有發(fā)現(xiàn)我在看她,還是看著電影畫面。時(shí)間不長,電影畫風(fēng)一轉(zhuǎn),兩個(gè)肉體糾纏在了一起,女孩好像忽然明白過來,站起來走了出去。
我有點(diǎn)失落,同時(shí)又非常憤怒。可是,我找不到失落和憤怒的根源,失落和憤怒本就是那個(gè)年紀(jì)的底色。我站起來,也走出去。沒有看到短發(fā)女孩。錄像廳外面就是小城的夜市,人來人往,一個(gè)攤位挨著一個(gè)攤位。逛夜市的漂亮女孩真不少。我想,以后不去看那種片了,沒意思,不如在夜市上看看漂亮女孩們。不過,這也夠無聊的。二十歲的日子,沒有人陪伴真夠操蛋的。我從夜市的東邊走到西邊,又從西邊走到東邊。小販們都在吆喝。在打氣球的攤位,我交了五塊錢,打了十槍,打爆了四個(gè)紅色的氣球。我喜歡紅色,專挑紅色打。打完之后,我發(fā)現(xiàn)一個(gè)熟悉的乞丐站在旁邊觀戰(zhàn)。我白了他一眼。他對(duì)著我做了一個(gè)開槍的手勢(shì)。我懶得理他,逛到了一個(gè)舊書攤。看到滿地的書,我的心才算平靜了一些,蹲下身子,挑選了五本,其中有劉以鬯的《迷樓》。有個(gè)女孩同時(shí)看中了它。我出手快一點(diǎn),已經(jīng)拿到手上了。女孩跟我商量,請(qǐng)我把書讓給她。我看她面熟,短發(fā),微胖,眸子特別黑,就是剛才從錄像廳逃出去的女孩。我很大方地把書讓給了她。她很感激,說要請(qǐng)我吃冷飲。我說,不吃冷飲,真要請(qǐng)的話,我們?nèi)ズ赛c(diǎn)啤酒。她很爽快地答應(yīng)了。我們抱起選中的十多本書,一起到路邊的大排檔喝酒。
大排檔很多,我們選了一家看上去干凈些的,點(diǎn)了毛豆、雞爪、酸菜魚,坐下來喝酒。老板是個(gè)小胖子,忙得腳下生風(fēng),啤酒送來,扳子卻找不到了。女孩搖搖頭,用牙齒輕輕嗑了嗑瓶蓋,瓶蓋應(yīng)聲掉地,熟練得不可思議。我不說話,為她倒?jié)M。兩人碰杯,干掉。我很少遇到這么爽快的女孩,也就放松下來,要知道我很少跟女孩打交道的。我們分別抓起一只雞爪啃了起來。
你知道《迷樓》嗎?她用餐巾紙擦了擦手問道。
知道一點(diǎn),是劉以鬯的小說集,里面有一篇同名短篇《迷樓》。
那么你知道迷樓這個(gè)建筑嗎?
也只是知道一點(diǎn)。傳說是隋煬帝建在揚(yáng)州觀音山上,專為享樂的地方。當(dāng)然,說法很多,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們又碰了一杯。兩人都不說話了,一杯一杯地干著。我的頭已經(jīng)暈了,膀胱脹得厲害。她不動(dòng)聲色,千杯不倒的樣子。我不好意思先上廁所,就憋著。
她好像看出來了,說你上下洗手間吧,你看你臉都憋紅了。我顧不得面子,問老板哪兒有洗手間。老板胖胖的小手指了指不遠(yuǎn)處的小巷子。我狂奔而去。
等我回來,女孩已經(jīng)走了,賬也結(jié)過了。我又坐了一會(huì)兒,晚風(fēng)吹來,酒已經(jīng)有點(diǎn)醒了,夜市漸散,馬路又像馬路的樣子了。回倉庫的時(shí)候,大黃對(duì)著我狂叫起來,我扔了幾個(gè)帶回來的雞爪給它。打開房門,倒頭便睡。
那次之后,好多天都沒有遇到短發(fā)女孩。我后悔沒有問她的名字,在這個(gè)城市,除了黃館長,她算是我可以聊一聊的人。有時(shí)候,特別是看到夜市上的大排檔,我會(huì)想起她。后來,就不再想了,她從我的腦海中慢慢消失了。那些天,我多了一個(gè)任務(wù)——帶著大黃跑步減肥。大黃又蠢又懶,體重極速飆升,走幾步就倚著墻根喘,就像個(gè)過度肥胖的老太太。我們繞著護(hù)城河跑。這個(gè)城市的河流多,護(hù)城河保留得比較完整,繞著老城曲曲折折的。政府搞了亮化工程,燈一開,夜如白晝,這樣一來,晚上散步的人越來越多。我?guī)е簏S,它艱難地跟在后面,一臉的困惑和不情愿。
我們沿著護(hù)城河跑,路過一處涼亭,似乎有人打架。我拍了拍大黃,讓它停下,擠過去看,懶狗正求之不得,停下來喘氣。我擠進(jìn)去才發(fā)現(xiàn)不是打架,有個(gè)女孩正對(duì)著簡易麥克風(fēng)唱《單身情歌》。
“抓不住愛情的我,總是眼睜睜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處有,為何不能算我一個(gè),為了愛孤軍奮斗,早就吃夠了愛情的苦,在愛中失落的人到處有,而我只是其中一個(gè)……”
女孩聲音高亢,略帶沙啞。等她抬起頭,我看清了,竟是和我喝過酒的短發(fā)女孩。她看到我,沖我點(diǎn)點(diǎn)頭,彈撥著吉他,繼續(xù)唱下去。有一個(gè)醉鬼——在這個(gè)小城每天都會(huì)產(chǎn)生無數(shù)個(gè)醉鬼——忽然闖了進(jìn)來,直直地看著短發(fā)女孩。跟我回去。他極力咬準(zhǔn)每一個(gè)字,可惜用力過猛,簡單的四個(gè)字碎成一地。女孩驚恐,收起吉他。醉漢強(qiáng)行去拉。我看不下去,想讓大黃上去嚇?biāo)幌隆;仡^一看,大黃不知道晃到哪去了。我攔住醉漢,問女孩,你認(rèn)識(shí)他嗎?女孩搖頭。圍觀的人也都覺出醉漢在撒酒瘋,紛紛指責(zé)。醉漢無趣,罵罵咧咧地走開了。經(jīng)此騷擾,女孩再無心唱歌。她拉著我的手說,我們真有緣,去喝酒吧。
還是大排檔。這次是擺在河邊的——亮化工程帶來的好處之一,是河流的邊上擺滿了小吃攤。在夜晚,人們安心地坐在簡易的塑料椅上,聊天喝酒,感覺真正地在生活了。
她叫李靜,中規(guī)中矩的名字。我們?nèi)允呛染啤F【疲械缺樱勘际且豢诟伞N业木屏亢孟耖L了,怎么喝也沒有醉意。李靜替我剝了一只龍蝦,放到我碗里,雖然隨意,我還是有些猝不及防,幾乎飄淚。離開父母近一年,先是摔斷腿,無人照料,后來在倉庫做看管,無親無故,三餐自理,何曾有此待遇?我將龍蝦塞到嘴里,滿杯舉起,鄭重地和李靜碰了碰,眼睛發(fā)亮,一飲而盡。
李靜長得漂亮,路過的,坐在我們旁邊的,只要是男的,都會(huì)有意無意地將目光投過來。我有點(diǎn)驕傲,雖然毫無來由。李靜不管,習(xí)慣了。她站起來,和我碰杯,高聳的胸部向我傾過來,我?guī)捉灒豢诤雀伞?/p>
我有點(diǎn)醉了,變得啰唆起來。我說,上學(xué)的時(shí)候我喜歡一個(gè)女孩,長得像你。那時(shí)羞澀,不敢當(dāng)面告訴她,就在課桌上刻她的名字。刻名字也不敢直接刻,而是把筆畫拆散了,這里一筆,那里一筆,完全是給自己看的。
李靜在聽。于是我繼續(xù)說。不過,估計(jì)那女孩早就知道,只是沒有點(diǎn)破。我不懂你們女孩,被人喜歡是不是很快樂?但如果被自己不喜歡的人喜歡呢?這些心理我摸不透。所以,我當(dāng)時(shí)非常希望自己像文學(xué)作品里寫的那樣,變成一只蜜蜂,或者另外的什么,在她周圍飛來飛去。最好能住進(jìn)她的心里,她怎么想的就全知道了。不過,現(xiàn)在想來,這也有風(fēng)險(xiǎn),如果看到女孩心里面都是別人,豈不是要傷心而死?
李靜笑了。我們又干了一杯。我繼續(xù)說道,我和她只有一個(gè)默契,就是放學(xué)回家的時(shí)候,我會(huì)遠(yuǎn)遠(yuǎn)地跟在她后面,她也是慢慢地走,偶爾會(huì)回頭,眼神對(duì)上,立刻轉(zhuǎn)頭。有幾次,我鼓起勇氣,幾乎要告訴她我的心意。可是,臨了又退縮,那時(shí)自卑得不行,連自己走路的姿勢(shì)都嫌棄。其實(shí)更怕被拒絕,沒有經(jīng)驗(yàn)。
李靜說,那你現(xiàn)在有經(jīng)驗(yàn)了?
還是沒有。我把這個(gè)小故事講完吧。女孩喜歡穿紅色衣服。有一天,我照例遠(yuǎn)遠(yuǎn)地跟著。走著走著,女孩忽然停了下來,好像在等我。我眼睛近視,平時(shí)都是跟著她的紅衣服走的,沒想到她停下了。我不好停下來,繼續(xù)走。等看清她的臉,我恨不得找個(gè)地縫鉆下,原來是隔壁班的生物老師,個(gè)子不高,也喜歡穿紅色,身材也差不多。我當(dāng)時(shí)臉熱得可以煮熟雞蛋,趕忙低下頭匆匆跑了。那個(gè)生物老師一臉愕然。后來,我心里就有了點(diǎn)小障礙。跟著女孩的時(shí)候,總疑心是那個(gè)生物老師。再后來我配了眼鏡,就沒有這樣的煩惱了。不久畢業(yè),上了三年技校,沒找到工作,流落到此。
我以為李靜要笑,可是沒有。她只是搖搖頭,又剝了一只龍蝦,看我吃下。兩人碰杯,喝干,各自回家。臨走,李靜說,我每天在這里唱歌,可以來找我,我們?cè)俸取?/p>
第二天醒來,我口干舌燥,喝了一杯涼水,吃了幾口面,胃里才舒服了一點(diǎn)。想起大黃,早上似乎沒叫,正常情況下,它和吊嗓子的藝術(shù)家一樣,早上會(huì)吼上幾句。到狗窩看,空的。城市很小,正常的狗應(yīng)該認(rèn)得家,可是大黃太笨,找不到家也在情理之中。我只好出去找它。我沿著昨晚走的路,走過了李靜唱歌的亭子,遠(yuǎn)遠(yuǎn)地看到大黃正對(duì)著一條穿著紅馬甲的小泰迪搔首弄姿,這方面它一點(diǎn)不傻。眼看就要勾搭成功,我一把拽住它的狗繩,吆喝一聲,很不人道地將它拖回庫房,關(guān)到狗屋,算是對(duì)它的懲罰。它也不反抗,嗚了兩聲,像確認(rèn)似的看了我?guī)籽郏刈哌M(jìn)狗屋,蹲下。
倉庫看管人的生活自由而沉悶,業(yè)務(wù)上黃館長并不管我,只是偶爾來看我。他喜歡背詞典,討厭一切言不由衷的作品。可是,他每次過來都帶書給我,從歌德到馬爾克斯,從盧梭到海德格爾,還有《金瓶梅》、“三言二拍”這些讓我看完無法入眠的古典文學(xué)。我發(fā)現(xiàn)這些書他基本上都看過,因?yàn)樯厦嬗兴墓P跡。他的字很有特點(diǎn),是胖一點(diǎn)的瘦金體,豎畫有特色,一筆而下,絕不拖泥帶水,就像冬天掛在屋檐下的冰柱,硬邦邦、直挺挺的。由此,我明白一個(gè)道理,如果想要否定什么,你對(duì)這個(gè)事物必須比別人更了解,否則構(gòu)不成那種無視一切的自信。黃館長只看詞典的自信,建立在翻閱無數(shù)書籍的基礎(chǔ)上。
在此期間,黃館長的女兒回來過一趟。他一高興,把我叫到他家吃飯。人不多,連我四個(gè),還有上次那個(gè)漂亮阿姨,估計(jì)是他夫人,另外一個(gè)就是他女兒,也是漂亮得沒話說。我仔細(xì)看看,其實(shí)黃館長也是個(gè)老帥哥。所以,這三個(gè)人坐在飯桌旁,就像偶像劇里的三個(gè)主角。我的出現(xiàn)就顯得尤其突兀,這同樣也表現(xiàn)在小黃小姐的臉上,她雖然沒有講話,可是五官還是很認(rèn)真地告訴父親,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帶?我如坐針氈,嘴里冒出的都是成語。我一緊張就說成語。我羞愧極了,感覺就像當(dāng)眾被剝了衣服一樣。黃夫人沒有講話,還禮節(jié)性地搛菜給我。不知什么原因,許是幾杯酒下肚,我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想到母親送我走時(shí)給我的那雙惹禍的黑色布鞋。在母女的注視下,黃館長也不說話,不停和我碰杯,席間幾次抱歉地向我看看,好像是他把我?guī)нM(jìn)了什么糟糕的場(chǎng)所。
吃完,我立刻告辭,發(fā)現(xiàn)黃小姐和黃夫人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也許他們只是不習(xí)慣在家里接待陌生人。打擾他們了,我真抱歉。出來后,我無處可去,錄像廳不想去,夜市也沒意思,于是跑到?jīng)鐾だ镎依铎o。她果然在,今天聽歌的人不多,她唱得有氣無力。聽了幾句,是劉德華的《忘情水》,她進(jìn)行了改編,聽上去就像一個(gè)小女孩在船上反復(fù)劃水。觀眾不太買賬,他們聽?wèi)T了劉天王,不喜歡劃水,聽完了也不鼓掌,煙頭扔了一地。我相信,要不是看在李靜漂亮又溫柔的份上,他們?cè)缟㈤_了。她看到了我,對(duì)我說,今天情緒不好,不唱了,我們?nèi)ズ染疲艺?qǐng)你。我說,我身上沒帶錢,想請(qǐng)你也力不從心啊。又是成語。我們?nèi)チ松洗魏染频牡胤健@习蹇吹轿覀儯f道,又來了啊。我很奇怪,這個(gè)老板難道過目不忘,竟然能記住我們?后來,我聽到他對(duì)每個(gè)來喝酒的人都這樣說,就明白了這只是他促銷的手段。
李靜負(fù)責(zé)點(diǎn)菜。我摸出一根煙點(diǎn)上。她點(diǎn)好菜,將菜單給了老板。我遞過去一根,她沒接,指指嗓子。菜很快就上了,雞爪、毛豆、鹽水花生米,還有一盆熱氣騰騰的毛血旺。她今天化了妝,眉毛描過,漂亮的唇線因?yàn)橥苛丝诩t而愈發(fā)好看。我們連干三杯。我在黃館長家已經(jīng)喝了些白酒,有點(diǎn)上頭,看東西開始發(fā)亮,話也多了起來。
你多大?我叫你姐吧。我對(duì)李靜說。我從小的夢(mèng)想就是有一個(gè)姐姐。本來我是有一個(gè)姐姐的,可是她十歲時(shí),下河摸河蚌,就再?zèng)]有上來。那時(shí)候還沒有我。這個(gè)姐姐沒了之后,爸媽合力把我生了下來。他們漸漸老了。人們都以為他們是我的爺爺奶奶。我不這樣想,他們雖然歲數(shù)大,但在我眼里,他們是最有力量的人。如果我遇到什么事,還愿意跟他們講,在外面實(shí)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他們會(huì)養(yǎng)我。說著說著,我覺得鼻子有點(diǎn)發(fā)酸。
李靜用手輕輕地?fù)崃藫嵛业念^,她的頭發(fā)搔到了我的臉,癢癢的,好聞的洗發(fā)水味道從發(fā)尖傳了過來。我想抱一下她,又不敢,即使喝了那么多酒,我也不敢,何況我剛剛叫了她“姐姐”。
我說個(gè)故事給你聽吧。李靜說。在很遠(yuǎn)的一個(gè)星球上,那個(gè)星球全被海水覆蓋著,生活著就像王小波《綠毛水怪》里描述的那種水怪。在那個(gè)星球上,水怪們,類似于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一樣,他們的生命可以無限延續(xù)下去。他們的繁殖方式和人類也無不同,主要通過男女交媾。可是,他們從不死亡。不過,水怪的星球也沒有人滿為患,他們有自己的淘汰法則。他們鼓勵(lì)個(gè)性,那些面目相似的,個(gè)性不突出的,容易隨大流的水怪,會(huì)在某一個(gè)明月(類似月球)皎皎的晚上徹底消失,不是死亡,而是消失。
所以,在這個(gè)星球上失去自我,就等于我們地球上的死亡。可以想見,這個(gè)星球盡管汪洋一片,但是多么豐富多彩。據(jù)說,從王小波的“綠毛水怪”開始,地球上經(jīng)常有人移民到那里。他們個(gè)性太突出,在地球上無法生存。所以,他們先把自己浸泡在咸水里,這些咸水主要是老祖母用來腌咸菜的鹵水。在鹵水里,他們身上漸漸沾上了一層綠色的熒光一樣的顆粒。然后,進(jìn)入第二道工序,將自己的身體攤到巖石上暴曬,沒有巖石的地方,可以用柏油馬路代替。暴曬的目的,主要是將皮膚曬裂開深深的口子,就像身上又長了一張張嘴。經(jīng)過一段漫長的修煉,在某個(gè)暴風(fēng)雨之夜,海邊會(huì)亮起一盞綠色的燈,有意者保持著在鹵水里的姿勢(shì),進(jìn)入海水。他們身上所有的口子都張著,吸收海水的能量,如果順利,他們就可以通過時(shí)空跳躍,進(jìn)入那個(gè)星球了。
我曾經(jīng)有幸見過這樣一個(gè)水怪。我不知道那是地球人變的,還是從那個(gè)星球過來的。她蜷伏在一段污水池里,起初我以為是一只鱷魚。我把手里的一塊磚頭甩了過去,激怒了她。她忽地站了起來,咒罵了一句。我這才看清了,那是一個(gè)女性水怪,兩個(gè)綠色的乳房挺在胸前。我落荒而逃。后來,就再?zèng)]見過了。
真有這樣的水怪?我問。
我也不是太肯定。其實(shí),我是想告訴你,我今天失戀了。但具體情況我今天不想說,下次講給你聽。你失戀過嗎?
我喝了一口酒,說道,有啊,沒有失戀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兩年前,我在上技校,曾經(jīng)交往過一個(gè)女朋友。她對(duì)我很好,我也愛她。但我們更多是以沉默的方式相處。我們就像兩塊立在山頂上的巨石,又像兩條潛伏在暗黑深海中的海龜,或者兩顆剛剛被傷過的跳動(dòng)著的心臟,也像風(fēng)雪中兩個(gè)人走過的漫長道路上干凈的腳印。我很享受這樣的感覺。因?yàn)槲覐男【褪莻€(gè)沉默的小孩。現(xiàn)在,她就在這個(gè)城市。我來這里,也是為了她。我父母不知道,以為我只是想打工掙錢。南方那么多城市,我為什么不去,而要到這個(gè)城市?因?yàn)檫@個(gè)城市有值得我來的人。
看不出,你還挺有詩意的,你找到她了?李靜問。
找到了。
她就是那個(gè)喜歡穿紅衣服的女孩?
是的。她叫王慧,有時(shí)候?qū)懗赏趸堋:芷胀ǖ拿郑墒菍?duì)我來說,這兩個(gè)字就是我的秘密。剛到這個(gè)城市時(shí),在我摔斷腿之前,我們見面了。那是我們分手之后第一次見面。我約她在誠品書店見面,其他地方我也不認(rèn)識(shí)。記得那書店有非常好喝的咖啡,我去過一次,是一個(gè)在這里上美院的老鄉(xiāng)請(qǐng)的。我到的時(shí)候,她已經(jīng)坐在黑色的沙發(fā)上。黑沙發(fā),很奇怪,她坐在上面,就像被黑暗吞噬了。她臉色蒼白,眼睛微腫,應(yīng)該是熬夜了。她已經(jīng)替我點(diǎn)了一杯咖啡。咖啡我不懂,拿起喝了一口,挺香的。
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她笑笑,看著她的臉,像要把她刻入我的腦中。你還是很美。我說。她好像對(duì)這話不感興趣,把玩著咖啡杯。我們不再說話,分別喝自己的咖啡。
還是她打破了沉默。我要走了,她說。
知道。我說。
你沒有什么要對(duì)我說的嗎?她問。
我又陷入了沉默。我情愿時(shí)間能夠靜止在這一刻。我不要回答,她也無須追問。
我忽然想起當(dāng)初和她分手的那一天。我像接受審判一樣坐在她對(duì)面,懇請(qǐng)她不要離開。當(dāng)時(shí)的對(duì)話,我印象深刻,可以復(fù)述。
我問她能不能重來。
她說,你說呢?
我說,不可以,但我想。
她有點(diǎn)不忍,說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你記得我們小時(shí)候上學(xué),經(jīng)常有同學(xué)從堆在七橋下的高草垛上跳下來嗎?有一個(gè)男生摔折了腿,參與的人后來被老師懲罰繞操場(chǎng)跑了十圈。即使這樣,每天還是有小男孩不停地從草垛上往下跳,好像那是他們的成人禮。你跳過嗎?
跳過,摔折腿的那個(gè)就是我。不過,不是摔折了,是崴腳了,一周不能動(dòng)彈。
如果你再跳一回,就可以。她說。
真的可以?
算是吧,但是,現(xiàn)在你到哪里找高草垛?草垛不是早就沒有了嗎?
這個(gè)你不要管。
我花了幾天時(shí)間,在郊區(qū)的一家廢棄窯廠找到了一個(gè)高大的草垛,并且從上面認(rèn)真地跳了下去。我去找她。告訴她,我跳過了,沒再受傷。
她很吃驚,像看外星人一樣看著我,你真的找了個(gè)草垛,而且跳了下去?天啦,我只是打個(gè)比方,你以為是真的?這就是我們一直走不到一起的原因。我要星星,我也相信如果你能做到肯定也會(huì)為我摘的。可是,你從來不想想其他辦法,而是扛?jìng)€(gè)梯子,試了又試,然后告訴我,梯子不夠長。其實(shí),哪怕你拿個(gè)破盤子,盛滿水,里面有了星星的倒影也可以啊。你從來不!
可是,你從來沒有跟我要過星星,我也沒有扛過梯子啊!我不可救藥地說。
天啦,再見吧。
真是痛苦的經(jīng)歷,在誠品書店和她再見面時(shí),這場(chǎng)景還是不管不顧地在我腦海中高速播放起來。我們品著咖啡,想著各自的心事。她要離開這個(gè)城市,我在這個(gè)城市的生活剛剛開始。后來,她起身離開,沒有親吻,沒有擁抱,也沒有握手。我坐在沙發(fā)上,后悔沒有平靜地和她說再見。
這就是我的失戀故事,乏味而可笑。我甚至懷疑自己的戀愛從一開始就是緩慢的失戀過程。我也思考過,自己為什么在戀愛當(dāng)中這么被動(dòng)。其實(shí)還是因?yàn)樽员埃碎L得一般,上了一個(gè)末流學(xué)校,普通話說不好,家里連電話都沒有,第一次在同學(xué)家打電話,將聽筒和話筒拿顛倒,聽不到聲音,我還以為電話壞了。
講到這,我將一瓶啤酒直接倒進(jìn)了喉嚨,憋著氣,沒有嗆到,一股清涼直竄至胃部。五分鐘后,我就什么也記不得了。第二天,醒來的時(shí)候,我躺在宿舍的簡易床上,地上放著一個(gè)水盆。我看了看,里面的水很干凈,我沒有吐。李靜伏在一邊的書桌上,睡得很熟。我沒有搖醒她。默默地看著她,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足足有一個(gè)星期沒有見到李靜了。這期間,黃館長又邀請(qǐng)我到他家吃飯,說他女兒要去學(xué)校了,想送一下。我不明白,這樣的場(chǎng)合,他為什么要叫上我。很顯然我不會(huì)成為他女婿的人選。我最不明白的是,在妻子和女兒的身邊,他為什么那么不自然。他那么驕傲的一個(gè)人,在她們跟前就像個(gè)作業(yè)老做錯(cuò),隨時(shí)準(zhǔn)備擦掉錯(cuò)誤答案的學(xué)生。因?yàn)檫@,我?guī)缀鯇?duì)家庭生活有了恐懼。我拒絕了黃館長,要煎熬讓他一個(gè)人煎熬吧。我在宿舍里背英語,我想自學(xué)本科報(bào)考古代文學(xué)類的研究生。電話鈴響了,我以為是黃館長,接通,是一個(gè)女孩的聲音,聽上去很遙遠(yuǎn),她沒有讓我猜是誰。我是李靜。她說。我問她,你怎么會(huì)有我的電話?她說,是你上次醉酒后寫給我的啊。我完全沒有印象,喝完那瓶啤酒之后的記憶全部消失了。我記不得了,我還干了什么?我問。沒有干什么,說話清楚,思路清晰,一直堅(jiān)持到宿舍,然后倒下便睡。她說。真的?我問。真的,好了,不說了,我在誠品書店,你快過來。我掛了啊。
我打車過去。一周不見,李靜的頭發(fā)好像長了不少,染成了亞麻色,束在腦后,看上去就像個(gè)文靜的小女孩。
是不是更像你的那個(gè)小女朋友了?她說。
像是像,可惜不是。是也不行,我不想又一次重復(fù)失戀的痛苦。你是不是想做我的女朋友啊?如果想,你就說啊,我沒意見!我說道。
你也學(xué)會(huì)油腔滑調(diào)了。她說,可以啊,不過,你還是要叫我姐姐。
我張大了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你不要當(dāng)真啊。她點(diǎn)了一杯美式,替我點(diǎn)了一杯拿鐵,又叫了一份甜點(diǎn)。
我問她有什么事。她說,我欠你一個(gè)失戀故事,今天不知什么原因,特別想說給你聽。想聽嗎?
當(dāng)然。我說。
這個(gè)要從頭說起。戀愛前史就不談了,我這么漂亮,從初中開始,就有男生不停地追我。甚至還有一個(gè)女生,為我折了一千只紙鶴,那時(shí)候流行。這些我都不說了。我講講剛剛過去的那場(chǎng)戀愛。一點(diǎn)也不浪漫,現(xiàn)在想來甚至有點(diǎn)惡心。他是我大學(xué)里的導(dǎo)師。你知道的,我是學(xué)生,他學(xué)識(shí)淵博、風(fēng)度翩翩,是全系女生的偶像。開始我以為是愛情片,后來發(fā)現(xiàn)是恐怖片。他是個(gè)渣男,同時(shí)和幾個(gè)女生交往,而且可能是因?yàn)閷W(xué)者的嚴(yán)謹(jǐn),或者是特別的癖好,他將跟每個(gè)女生的交往都細(xì)致地記錄了下來,也有可能這是他的時(shí)間管理法。女生們毫不知情,都以為自己是他的唯一。最可怕的是,那個(gè)筆記本,被他的夫人,一個(gè)機(jī)關(guān)里的女處長發(fā)現(xiàn)了。我的名字赫然在內(nèi),而且據(jù)說是篇幅最多的一個(gè)。女處長有手段,悄悄地跟自己的父親說了。他父親是那座城市的權(quán)勢(shì)人物。父女二人找了導(dǎo)師,下了最后通牒:只要如黃藥師一樣盡驅(qū)座前女弟子,既往不咎。導(dǎo)師的情況其實(shí)和黃藥師不具有可比性,不過傳言他們就是如此談判的。我其實(shí)不太傷心,自從知道他是這樣一個(gè)人,我就不傷心了,不值得。只是覺得惡心,就像吃進(jìn)了一只蒼蠅,怎么也吐不出來。明明白白地,那只蒼蠅就躺在自己的胃里,卻一直吐不出來。她一口氣講完。
我聽后無言,把咖啡喝掉,說,姐,我們?nèi)ズ染瓢桑@次我請(qǐng)你。
我們?nèi)チ撕舆叺睦系胤剑窡舸蔚诹疗穑鞘械牧硪恢谎劬Ρ犻_了。我在城市生活的這些天,想清楚了一件事,城市是擁有許多眼睛的怪物,什么時(shí)候睜開哪只眼,什么時(shí)候閉上哪只眼,從來不會(huì)錯(cuò),井井有條。如果誰自不量力,想打破這種規(guī)則,就只能被城市擠壓,難以喘息。
老板和我們打招呼。這次是真的認(rèn)識(shí)了,估計(jì)我上次醉酒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還是點(diǎn)了之前的老幾樣。毛豆和花生米必須有,雞爪也是,啃起來有生活氣息。酒還是啤酒。看著那些金色的液體,我心情變得有點(diǎn)好了。李靜因?yàn)閷㈩^發(fā)扎了起來,原先被頭發(fā)遮住的地方都露了出來,特別是耳朵和耳朵下面的皮膚,我真的想不出詞語來形容。我總覺得人類的語言無法形容自身的美,比如此刻李靜的白,我就想不出合適的語言,我想贊美,可是無從說起。
為你漂亮的耳朵干杯!我這樣說。
她笑了,為你難得的漂亮話,干杯!
那天我們喝得很多,卻沒有喝得人事不省。由于酒精的作用,我很激動(dòng),在大排檔的燈光下,我流著眼淚,仔細(xì)盯著李靜看。她也是,臉上掛著幾滴淚,遲遲不掉。我已經(jīng)記不清我們是怎么開了房,怎么擁抱到了一起。想不到她的動(dòng)作和我一樣笨拙。可是,當(dāng)我脫掉她身上的衣服的時(shí)候,我還是震驚了。那幾乎是一具完美的身體,潔白如玉,全身沒有一處瑕疵,胖瘦也恰到好處。我們接吻,她的嘴唇濕潤而柔軟,她的舌頭溫暖而甜蜜。
后來,我們躺在床上,我用中指在她漂亮的胸前劃著,就像劃過一段帶著溫度的絲綢。她說,默烏,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相遇時(shí)的那本書嗎?對(duì),是《迷樓》。后來我一直在想這本書。歷史層面的意義我就不說了。我重點(diǎn)想的是“迷”和“樓”這兩個(gè)字。我們每個(gè)人是不是都曾在迷樓里呢?迷惘、迷戀、迷失,我在導(dǎo)師的虛假溫暖中迷失了,他更不用說,在變態(tài)無節(jié)制的欲望中迷失了。你年輕,愛過,但迷惘,或許你還迷戀。你說的那個(gè)黃館長也是,看上去活得通透,可是,在妻子女兒的跟前,他還是沒有自我,只有躲到某個(gè)角落,比如病房,比如博物館,你可能也是他認(rèn)為的某個(gè)角落,只有在你的跟前,他活得才像自己。
停了一下,她又說,默烏,你記住,我們這樣,并不證明我就屬于你了,也不證明你就屬于我了。如果你迷戀我,就偏離了事情的初衷。記得我說的那個(gè)關(guān)于水怪的故事嗎?我們不一定要做水怪,但心里一定要住著一個(gè)水怪。你記住了嗎?
那天,我陷入狂喜,以為自己重新開啟了愛情的旅程,我愛李靜,我愛她的身體,也愛她展現(xiàn)在我面前的靈魂。可是,我不確定她愛不愛我,不過那時(shí)候,幸福沖昏了我的頭腦,我沒有聽出她話里面的深意。她其實(shí)把我當(dāng)作她的弟弟,或者把我當(dāng)作曾經(jīng)的她。她和我做愛,是給自己一個(gè)交代,也是給我一個(gè)念想。可是,我畢竟不是她。她不知道,我對(duì)什么都容易當(dāng)真。就像王卉說的,我把什么都當(dāng)真,而不去想表面之下的異質(zhì),哪有什么水平如鏡,每一個(gè)泛起的水紋都可能藏著另一個(gè)世界。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有些東西是當(dāng)不得真的。李靜不知道,那天是我二十歲生日,如果她不叫我出來,我將一個(gè)人過。我感謝她。
那天分別之后,李靜就從這個(gè)城市消失了。我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她的地址,沒有她的電話號(hào)碼,我只知道她很漂亮,她叫李靜。她去了南京,可是南京太大,我無法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