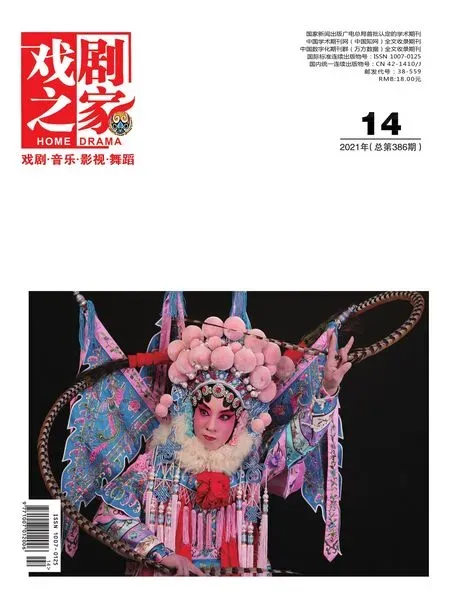從《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談古元的視覺敘事
潘艷飛,夏 強
(1.東北大學 遼寧 沈陽 110819;2.魯迅美術學院 遼寧 沈陽 110004)
1947 年間,古元先后創作了多幅反映土改的作品,題材直接來源于他在東北農村下鄉的經歷。1947 年7 月,東北局動員一萬二千名干部組織工作隊,下鄉開辟群眾工作,古元到哈爾濱五常縣周家崗參加土改,這里是土地改革的重點村,在這里,古元跟村民一起生活勞作、朝夕相處將近三個月,創作了一系列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品,其中反映東北土改的作品有《抓地主》、《起槍》、《發土地證》、《燒毀舊地契》以及《七斗王把頭》和《暴風驟雨》插圖等,這一系列土改作品反映了東北村民們面對土改時的不同心態,以及在不同土改階段群眾心理上的騷動和生活上的變化。本文將從這一系列土改作品入手,并主要以《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這兩幅作品為比較對象,解讀其題材內容、表現形式,探尋其視覺敘事的話語方式和意義的存在語境,及其隱含的精神理念。
古元一系列反映東北土改的作品主要創作于1947-1948年間,1947 年9 月初《東北日報》刊載配古元插圖《七斗王把頭》的故事,這個故事同《暴風驟雨》一樣也是以周家崗為原型,描寫了周家崗村民七次斗地主王把頭的過程,以及從中得到的教訓。這個故事刊發的時間較《暴風驟雨》早了三個月。古元以木刻的形式創作了該故事的插圖,其中一幅描述了“金牌子回到了群眾的手里”,古元并沒有落了窠臼地去畫村民們的笑臉,而是以小圓刀刻畫了手部特寫:近景處一只粗糙的、溝壑遍布的、經年勞作的手,小心翼翼地將一個八角星形的金牌子捧在手心,金牌子熠熠發光,遠處村舍、田地、馬匹安靜祥和,這種象征的意味加深了畫面的凝重感、分量感,更好地表現了文章的內容“周家崗群眾血汗制成的金牌子,又光華閃耀地回到了群眾的手里”;另一幅描述了“請財神爺上車”,這位“財神爺”處在畫面中心位置,蔫頭耷腦、神情沮喪,無力地倚靠在驢車欄桿上,表現了“財神爺”即將失去財物的心情,畫面上方光屁股的小孩子跑在驢車最前面,畫面右邊是負責押運的、握槍的民兵看著“財神爺”,左邊是村民意氣風發地走著,和“財神爺”沮喪的表情形成鮮明的對比,車夫則在前面回頭用手指著“財神爺”,似乎在說“活該,你自作自受”,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財神爺”這個典型地主身上,突出了土改工作批判的重點。
《暴風驟雨》插圖的創作也是在同時期展開的,當時住在老鄉家的古元遇到了下鄉深入生活的周立波,周立波邀請古元為自己的小說配插圖,于是就誕生了反映我國土改運動的長篇名作《暴風驟雨》,該書反映了東北農村封建勢力的垮臺,以及農民中間新人物出現的復雜曲折的過程。他們在合作的過程中,都住在農民家里,除了參加農會的各種活動以外,周立波就是趴在住戶家的一個三條腿的半圓桌上整理稿件,隨后把文稿交給古元,古元坐在土炕上點著油燈畫插圖,最后周立波的小說完成了,古元的插圖也隨之誕生了。他們都是土改運動的參加者,親身經歷和感受過土改中的人和事,加之對生活環境的細致觀察,使畫面人物栩栩如生,動勢、姿態、表情豐富準確,對細節的刻畫深入到位。古元作品中農民穿的靰鞡鞋以及爬犁、苞米樓子、磨盤都極富有東北的特色,使整體和局部有機結合而趨于完美的統一;《東北日報》于1947 年12 月25 日始圖文連載《暴風驟雨》這部長篇小說,并于1948 年4 月由各東北書店發行。
作品《起槍》發表于《東北日報》1947年8月23日第四版,描述了村民斗敗地主,被壓迫的農民翻身做了主人,把曾經壓迫他們的地主看押了起來,從地主家院子里挖出好多槍支和財物,圍在被挖出來的槍支周圍的人們興高采烈,而地主則扭頭偷眼窺視,面露不甘。《起槍》反映農民從曾經受壓迫的地主那里奪過來斗爭的武器,開始翻身作斗爭,他們從思想上開始覺醒起來。
如果說《抓地主》、《起槍》是反映了農民群眾的覺醒和抗爭,表現農民翻身,那么《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便是徹底推翻了壓迫的象征。《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兩幅作品的背景都安排在象征封建堡壘的城門樓附近,留給在場的村民們的空間狹窄逼仄,正如村民被壓迫的、艱難的生活。作品的視角是從側面俯視,在高墻的對比下,人顯得矮小,只占據畫面底部的部分,《發土地證》圖中如龍卷風般的云和《燒毀舊地契》圖中升騰的火焰象征著翻了身的農民打破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內心的渴望就像沖天的火光,心里翻騰的巨浪猶如滾滾濃煙,這一切都宣告了背負在農民身上幾千年的封建壓迫走向滅亡。
《燒毀舊地契》與《發土地證》都描繪了村民們的群像,不同之處在于人們的觀看狀態。在《發土地證》中,畫面左邊有一人背對著我們,光著上身,太陽照出他黝黑的皮膚,他高舉著土地證滿意地看著,順著他的視線方向往前又看到有一小群人在討論著什么,其中一個面對觀眾的人手中拿著土地證,側頭和旁邊的人說話,畫面中間一人上臺領土地證,古元刻畫了其接土地證的瞬間,點明了主題。還有幾個人蹲在近景處的樓角附近在觀看,其中離城門樓最近的一個女人則倚在樓墻邊,雖然我們看不到她的臉,但能感覺到她探尋的、若有所思的眼神,在畫面上方,即城門樓的上面,一個背槍的士兵在巡邏,士兵旁邊立著一個警鐘,土地證的頒發在政府的組織下井然有序。
而《燒毀舊地契》表現的是農民翻身的狂歡場景,不同于《發土地證》中有探尋、猶疑、觀望的態度,《燒毀舊地契》中每個人都是狂歡的一員,都參與其中。畫面近景處有敲鼓的四個人,邊敲邊舞,動作各異,專注投入,他們平分在畫面上,互相之間的距離相等,形成了一個半圓弧,而沒有畫出的另一半則是留給觀眾,觀眾仿佛被一種吸引力牽引到畫面中,就站在村民們的身邊,和他們一起舞起來。在四個舞者之后,位于畫面中央的是一個站在高處的、戴著草帽的赤膊農民,他雙手高舉舊的地契,欲將其投入火中,他黑色的背脊在熊熊火光的映襯下特別顯眼,也特別有分量感,所有人都睜大眼睛,目光都看向燃燒的舊地契,屏息凝神,面露崇高和堅毅。在面對觀眾的位置,一人揚起手中的長叉,將一張正在燃燒的地契高揚起來,與畫面右邊振臂高呼的人共同加強了畫面的動感。
通過兩個畫面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古元刻畫了農民群眾在其中不同的參與狀態,我們可以了解到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農民群眾的反應與政治環境和東北的歷史情況息息相關。
東北與延安的環境有很大的不同,東北沒有延安相對穩定的環境,日本侵略奴役東北十四年,期間進行了嚴酷的壓制和奴役文化的宣傳。日寇的統治通過原有的封建勢力延伸到農村。縣、村、屯的警察、特務以及協和會、興農會、合作社、配合所等統治機構,都由地主掌握。當時東北農村的土地,除了經日寇強占的約為東北耕地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開拓地”、“滿拓地”,及日本人的“私有地”之外,余則仍操縱在地主階級的手里。農民終年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生活。此種土地集中的情況,在蔣軍控制的地區,除將“開拓地”、“滿拓地”變成“‘國’有地”外,并無絲毫的改變。長期以來封建及帝國主義的壓迫,使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更加復雜。“八·一五”東北光復后,1946 年“七七”,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了實行土地改革的決定,批準了農民收回土地的要求,隨后動員一萬二千個干部,組織數百個工作團,深入農村,協助農民進行翻身斗爭。
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面對復雜的情況,出現了“斗爭運動不徹底,還嚴重存在著‘夾生飯’的狀態”這一現象。究其原因,一則是日本投降后,仍舊是“缺乏主見,甚至是彷徨的……含著毒素的……這個毒素包含著日本的奴化思想的殘余,以及傳統的封建思想,頑固的、退步的、腐敗的、迷信的、盲從的、奴性的等等污穢的成分”。二則是“領導不敢大膽放手,沒有貫徹群眾路線,犯了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毛病”。因此不同的人所持態度不同,有真正動員起來的、有觀望的、有陽奉陰違的,甚至還有“地主狗腿冒充積極分子,篡奪運動領導權的”。
土地改革的初期,村民們心里是有顧慮的,他們長期受著深重的壓迫,對于地主存在害怕的心理,將政府派來指導土改的工作隊視為“新鮮物”,沒有從心理上承認接受,因為自己“從未這樣密切地跟政府的人打交道”,群眾沒有發動起來,因而零敲碎打,每次因為一個問題,斗斗就算了。結果,群眾和“王把頭”二十多年的血海深仇無法得報,因而就不能打消群眾的顧慮、滿足群眾的要求,也就無法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所謂“翻身”,顧名思義是身子翻過來,而實際斗爭中更重要的是“翻心”,也就是改變自己的思想情感,成為一種革命主體,這對于經歷十四年雙重壓迫的東北群眾而言是很困難的。這從《七斗王把頭》歷時一年五次斗爭都失敗,以及群眾對斗爭感到疲乏、不感興趣中可見一斑。第七次斗王把頭,欲逃走未成的王把頭依然頑抗,問問題假裝不知,滿嘴胡扯,這時“有人上去就是打幾個嘴巴,說:‘老雜種操的,到這個時候你還敢拐著彎子罵窮人呢?誰是群小鬼兒呀?王八犢子!’一腳把他踢倒在地下,幾十根皮帶棍子沒頭沒腦地打起來,直到他大聲喊叫著‘我說,我說,我有金牌子。’又三天以后,全村一千多人,男女老少,每人都手拿一根棒子或皮帶浩浩蕩蕩地把王把頭拉出來就打,群眾吹著號、打著鼓,高聲叫著‘打元寶’、‘打漢奸’、‘給窮人報仇’的口號,從村南頭一直打到操場上,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公審斗爭”,⑦這個時候群眾才徹底翻了身,又翻了心。
面對土改人們的心態是不同的,廣大貧苦的農民群眾,感到有了生存的依據,有了得到土地和財富的希望,以及有了脫離貧困和災難的希望;而中農出現了動搖和疑慮,他們想到自己的土地會不會受到威脅;至于地主富農則會覺得震驚,他們會感到借以剝削的工具將要喪失了而負隅頑抗。東北局發現存在的問題后,在《東北日報》上發文《平分土地運動中的幾個問題》,在文中詳細闡釋土改運動中“雇貧農路線”和“團結中農跳出圈子”等幾個重要問題,并一再重申滿足群眾需要的重要性。后期,經過從上至下的政策指導及實際斗爭中的經驗總結,沒有了“兩面光”的思想,不存在“明分暗不分”的現象,分配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確實到了農民手里,土地改革才徹底取得了勝利。“據松江省五常、珠河等六縣七月中旬不完全統計:起初浮物(金銀、衣服、雜物)共值二百億元,其中金子一項,即達一百零五斤之多。群眾追回這筆血債之后,完全解決了生產中的糧食、牲畜等困難,安下了家底。”
上面提到的松江省五常縣正是周立波和古元所在的土改重點推進的地方。古元作品《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是于1947 年下半年在《東北日報》刊登出來的,東北局的發文是于1948 年年初刊登在《東北日報》上的,古元的土改作品給了東北其他地區可以借鑒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正因為東北土改的成功,中共才掌握了廣袤的農村基層,使征兵、征糧工作擁有了穩定的渠道,為后來的中共全面反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東北古元是第二次參加土改,在延安時期他就參加了土改并于1943 年創作了作品《減租會》,對于土改他有一定的經驗,他敏銳地捕捉到了人們心態的變化,并體現在他的作品中。《發土地證》和《燒毀舊地契》這兩幅作品中的圍觀者就是他根據畫面的需要構思設計的,這兩幅畫中圍觀者的不同表現了土改斗爭不同階段人們心態以及生活上的變化。他的目光始終在群眾中,他不是在一旁觀看,而就是群眾中的一員。《燒毀舊地契》中的場景,是一個帶有集體狂歡性質的慶祝儀式,也是對“翻身”帶來的解放力量的盛大展示,更因村民們凝聚著的集體意識和民族認同而深刻與雋永。
古元作為一名版畫戰士,將延安的優良傳統帶到東北,在這塊荒涼的土地上傳播中共的方針政策,闡明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激起東北人民翻身解放的信心和斗志。古元以刀筆為斗爭武器,始終堅持一切為群眾的創作方式和藝術道路,與廣大人民群眾情感相融、骨肉相連,這是他作為文藝工作者自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將心血付諸刀筆,創作出富有激情、戰斗力的作品,達到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對當今社會仍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注釋:
①關寄晨(文)古元(圖):《七斗王把頭》,《東北日報》1947 年9 月9 日第四版。
②周立波(文)古元(圖):《暴風驟雨》,《東北日報》1947 年12 月25 日。
③曹江,古安村:《刀筆激情——回望古元在東北》,《美術》。
④古元:《起槍》,《東北日報》1947 年8 月23 日第四版。
⑤古元:《燒毀舊地照》,《東北日報》1947 年7 月4日第四版。
⑥醒華:《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概況》,《群眾》1948年第50 期,13-14 頁。
⑦關寄晨(文)古元(圖):《七斗王把頭》,《東北日報》1947 年9 月9 日第四版。
⑧社論:《東北日報:平分土地運動中的幾個問題》,《正報》1948 年第2 卷第25 期10-11 頁。
⑨醒華:《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概況》,《群眾》1948年第50 期,13-1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