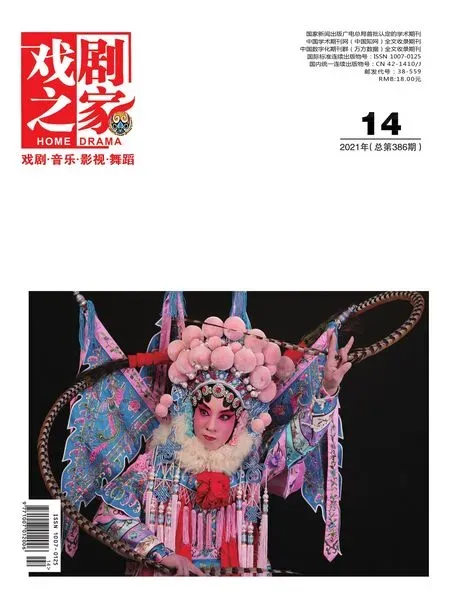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夏季》中女主人公悲劇命運成因解讀
畢世穎
(沈陽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0)
作為19 世紀末女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伊迪絲·華頓的經典作品,《夏季》描寫了長年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性角色切麗緹在成長過程中性意識的覺醒,她反叛現實,追求理想,結果卻又被困于殘酷現實的人生經歷。《夏季》最初出版時反響平平,但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重新受到了評論界的關注。
小說的主人公切麗緹出身于新英格蘭的一個貧困之家。生母是名妓女。五歲時,她被羅亞爾收養。當切麗緹18 歲時,羅亞爾闖入切麗緹房間試圖與其發生關系。盡管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育,切麗緹仍然靠著羅亞爾的幫助獲得了鎮上圖書管理員的工作。工作期間,她認識了建筑師哈尼。兩人發生關系后,哈尼許諾會與切麗緹結婚,卻轉身與另一女子訂婚。切麗緹在懷孕中被哈尼拋棄。最后,迫于當時的生活壓力,切麗緹不得不與養父羅亞爾結婚以獲得穩定的生活。本文將從幾個角度出發,分析切麗緹是如何走向最終的人生悲劇。
一、挫折的愛情
在切麗緹與哈尼的交往中,哈尼承諾過日后會與切麗緹結婚。在兩人的關系中,切麗緹總是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當中。哈尼會時不時地消失許多天,毫無音信,留下切麗緹在困惑中等待他的出現。不久,切麗緹得知哈尼已與他人訂婚,她最終明白哈尼根本不屬于自己。而對于哈尼來說,切麗緹的主要魅力來自于她的美貌,并非內在。換句話說,切麗緹只是他玩弄的工具而已,他根本沒有對切麗緹付出任何真心。哈尼的隱瞞與欺騙讓切麗緹處于無助的狀態中,而且她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加殘酷的現實:她懷孕了。身份的差距無法跨越,而腹中的孩子更是沒有任何力量去幫助挽回兩人的愛情,她清楚地明白哈尼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她給哈尼寫信告訴他她會放棄兩人的愛情,哈尼接受了切麗緹的善意。哈尼的出現激發起了切麗緹對于異性的愛慕,但是她對兩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深刻的理解。兩人之間巨大的身份地位的差距注定了愛情一定會以失敗收場。
切麗緹的經歷不僅反映了女性在當時社會環境中的卑微地位,也展示了作者的女性主義觀點。年輕女性的成長總是伴隨著女性自身對愛與性的認知過程。在切麗緹的成長過程中,她一直在追求愛的蹤影。當她遇到了哈尼,她將全部信任與感情都寄托在情人身上,但是卻遭遇到了對方的欺騙與背叛。即使已經懷孕在身,她也無法逃離被深深信賴的愛人的拋棄的命運。在伴隨著種族主義的封建主義社會中,無論切麗緹懷孕與否,她都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在與男性的交往中,她總是處于非常卑微與低下的地位之中,可以說,她的被拋棄的命運根本無法避免,她注定是被命運和男性玩弄的工具。
二、無奈的婚姻
小說中,切麗緹是一個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她不知道父親是誰,而母親僅僅是個妓女,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暫時的。五歲時,切麗緹被羅亞爾收養,羅亞爾在她的命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年少時,切麗緹想要上學接受教育,但是羅亞爾堅決反對。出于對孤獨的羅亞爾的同情,切麗緹放棄了上學的想法。然而,切麗緹的善意卻被羅亞爾理解為是她軟弱的表現。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像切麗緹這樣地位地下的女性根本沒有權利接受教育。即使羅亞爾不阻止她,她也無法順利地接受教育,因為這不會被身邊的人理解與接受。除此之外,對于羅亞爾來說,切麗緹如果接受了教育,很有可能會進入社會并被社會“污染”,那樣的話,切麗緹將就不會再屬于他了。父權的壓制使得切麗緹這樣的女孩完全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被外界操控著走向悲劇的命運。
小說中,羅亞爾是典型的父權制的代表人物。作為切麗緹的養父,他給切麗緹取這個名字的原因是希望能夠將她當成私人財產并永久地占有她。然而,“慈善”的面紗并不能掩蓋他的父權制思想。妻子死后,羅亞爾認為切麗緹是他的私人財產,并應該履行一個妻子的責任來表示對他養育的感激。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他宣揚的“慈善”的真正含義。事實上,他的所謂“慈善”不過是對切麗緹精神和肉體的占有而已。
切麗緹18 歲時,他想通過與切麗緹發生性關系而完全支配她。所以當他發現切麗緹愛上了哈尼時,他非常嫉妒哈尼,他告訴哈尼切麗緹卑微的出身,這使得哈尼在得知真相后從某種程度上疏遠切麗緹,并最終棄她而去。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像切麗緹這種出身的人,曲折的命運似乎生來就已經注定了。
與哈尼分手后,切麗緹的墮胎失敗了,她決定上山去找她的母親,對她來說,這似乎是生活的一線希望。然而,來到山上她卻發現母親已經去世。她再一次失去了依靠。同時,她審視著母親和祖母的生活環境,發現她們只是像動物一樣茍且地活著,并沒有任何尊嚴可言。而想到自己的處境,切麗緹明白她根本沒有任何能力能給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環境,而是極有可能回去重復母親和祖母的生活。這種想法讓切麗緹感到恐懼。同時,她開始理解母親的選擇。即使她是個妓女,但她并不是壞女人。在沒有任何經濟能力與話語權的社會中,母親只得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換取自己和孩子的穩定與幸福。這種選擇是極其無奈的。切麗緹開始理性地審視自己的處境,她權衡利弊,最終決定向現實妥協,和母親一樣成為一名妓女。因為作為母親,切麗緹也絕不能讓自己的孩子過如此悲慘的生活,即便她將不得不忍受著身體和精神巨大的摧殘。這是她唯一能夠撫養孩子的方式。然而下山途中,繼父羅亞爾及時趕來,再一次向切麗緹求婚。這一次,切麗緹沒有拒絕。因為對于當時的切麗緹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選擇。切麗緹在懷孕中與養父羅亞爾結婚。表面上,切麗緹與孩子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孩子得以在更加舒適的環境中成長,實際上,這是迫于殘酷生活現實的無奈之舉,可想而知,兩個人的婚姻對于切麗緹不可能有任何幸福感可言。切麗緹一直在與命運苦苦掙扎與抗爭,然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她只能屈從于命運的安排。
三、被壓抑的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切麗緹與哈尼發生關系很大程度上是對父權制度的反抗。在傳統的道德標準中,女性被放置在神壇之上供奉,要求其必須冰清玉潔,她們沒有權利去談論“性”。在小說中,羅亞爾對于切麗緹的性騷擾沒有得逞后,切麗緹去尋找哈查德女士尋求幫助,希望能從她的身上得到安慰。她意識到了切麗緹的悲慘境遇,但是她卻拒絕在切麗緹的面前談及與“性”相關的任何話題。顯然她完全內化了主流的父權思想,認為未婚女性必須要保持純潔,對于她們來說,“性”是禁忌,會威脅到她們的貞潔。“切麗緹的心變得冰冷起來。她明白,哈查德小姐無法給她任何幫助,她必須獨自努力擺脫困境。一種更深的孤獨感征服了她;她感到無比的寒冷。”
當羅亞爾粗魯地干涉了切麗緹與哈尼的關系,切麗緹冒著流言蜚語的風險在夜晚跑去哈尼的住所與之幽會,這完全破壞了父權制中女性必須純潔的規則。切麗緹被描述成為了推翻父權制的的叛逆者。至少對于切麗緹來說,在這個時刻,她是勇敢的。傳統的父權文化不再是支配她的力量,相反,切麗緹成功支配了自己的情感和命運,她完全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這是對傳統性別和種族文化模式的有力回擊。然而,強大的社會力量下,切麗緹的舉動注定是以悲劇收場。
四、嚴苛的宗教
在傳統的文化當中,女性必須懷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以確保其純潔。小說中,切麗緹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并且忽視傳統的女性道德觀。這使得她成為了主流社會中的“他者”。切麗緹深知基督教的虛偽,她仿佛一名“代言人”去揭發宗教的偽善。切麗緹不能從牧師為其死去的母親的禱告中獲得任何的力量和共鳴,這更加確認了切麗緹對于基督教的懷疑。“如果上帝能夠緩解世界的痛苦,為什么人類要在死去之后通過牧師的禱告獲得靈魂的升華?”一系列諸如此類的問題反映了切麗緹對于宗教的疑問,她也無法理解為什么人們對宗教為何如此盲目相信。面對哈尼的拋棄、尚在腹中的孩子的未知命運與來自身邊人的譴責,切麗緹沒有尋找宗教的慰藉,因為她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去向上帝懺悔她的行為。宗教對女性權利施加了太多的壓力,她們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小說中的敘述充分展示了宗教思想的腐朽和嚴苛以及宗教對于女性權利的迫害與壓制。
五、結語
挫敗的愛情、無奈的婚姻、被壓抑的性、嚴苛的宗教是女主人公切麗緹悲劇命運的原因。她的出走、考驗、迷惘、頓悟和認識人生和自我是她思想和心理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變化過程。《夏季》女主在對社會的反叛和對愛情友誼、理想信念的追求中,經受迷茫、痛苦、掙扎和無奈,最終完成自我救贖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