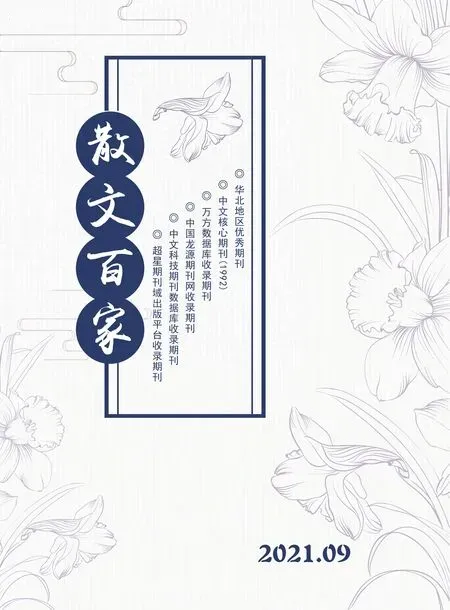淺析米爾佐夫《視覺文化導論》中的身份問題
胡 潞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一、視覺文化
米爾佐夫的理論研究涉及藝術史、政治學、哲學等諸多領域,作為藝術史學家及理論批評家,他界定“視覺文化”的學科邊界,并因此聞名世界。他認為“視覺文化是一種策略,而不是一門學科。是一種流動的闡釋結構,旨在理解個人以及群體對視覺媒體的反應,它依據其所提出或試圖提出的問題來獲得界定。”因此,視覺與文化相聯系,走出了一條文化迷宮的道路,伯明翰學派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指出,文化實踐成了人們參與并闡述政治的一個領域。視覺文化也便可成為闡釋身份問題的途徑。
二、視覺文化與身份問題
在文化研究中,“身份”乃是人與其所處在文化環境之間的被意識到的聯系,視覺文化中可窺見出視覺媒體中聯系的主體身份變化。身份問題為20世紀引發的文化研究思潮的浪潮而走入當代學術視野,在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論基礎之上,集合了女性主義思潮、后殖民主義思潮的因子,概念內涵為斯圖塔亞特·霍爾、佳亞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理論家所擴充延申,身份問題的闡釋領域是很寬廣的。從視覺文化的角度對身份問題的探討可以從米爾佐夫關于“視覺性”概念的探討出發。米爾佐夫指出“視覺文化是一種新東西,就因為它把視覺聚焦為一個意義生產和競爭的場所。”觀看從生理活動變成了一種社會性的事實,米爾佐夫稱之為“視覺性”,這一概念下將觀看過程視為一種社會化的權力文化和權力現象,承載了人為的呈現與遮蔽,成了特定歷史階段對視覺的壟斷和專權。于是,米爾佐夫試圖創建米歇爾·福柯意義上的關于視覺的譜系學,探析了媒介革命所牽動的視覺技術的沿革,從繪畫、攝影到電子虛擬,披露出依托媒介載體建構出的“視覺性”下所蟄伏著的主體間權力的牽制與博弈,力量的抗爭與制衡。由于視覺媒體成為了建構文化身份載體,是身份建構的一種表征符號,因此身份問題便得以從視覺文化的闡釋中從視覺圖像的背后來到幕前。
米爾佐夫認為圖像意義的生產機制可以分為:(1)舊制度時期的圖像刻板邏輯;(2)現代時期的圖像辯證邏輯;(3)悖謬的或虛擬的圖像的邏輯。這三種圖像意義生產機制因視覺技術更新帶來的圖像生產邏輯改變而改變,這三種視覺技術可分別以17世紀的古典繪畫、殖民主義時期的視覺藝術、以及后現代視覺影像為例。隨之帶來的身份認同模式可以表現出個體身份認同、集體身份認同和文化身份認同。
第一節,舊制度時期。
舊制度時期視覺文化的身份問題關乎一種個體身份認同。米爾佐夫指出17時期的古典主義繪畫的視覺表征系統中所采用的視覺元素,實則是一種現實政治權力的圖像化映射。在專制時期,肖像畫成為帝王宣誓權威的視覺表征,貴族人物形象被定格在畫面之中,視覺元素均服務于權利意識的表達,皇家趣味的需求。以視覺金字塔、暗箱理論的理論基礎之上透視法則為代表的視覺表征系統,透視法則在文藝復興時期應用得尤為突出,三維圖像轉化為平面二維圖像,滿足了人們對一種細致而真實的觀看效果的需要,除此之外,這也服從于一種權力規訓的思想,廣泛應用于西方古典繪畫中。例如17世紀法國路易十四的畫院的繪畫實踐,視覺圖像建構起與現實不同的秩序,帝王的身份差異得以凸顯,進而實現對帝王形象的贊美,至尊地位的歌頌。17世紀繪畫實踐中,畫院反對同時期笛卡爾的視覺理論,反對嚴格遵照幾何透視法則,因為恪守幾何透視的繪畫方法會造成帝王身體形象與其他人物形象的差異,形象上的差異可能會增加其統治動亂的風險。因此,畫院創造了新的透視法,建筑、背景在幾何透視的縱深感中可保留其宏偉的特點,人物卻按照古典比例來繪制,形象的尺度在衡量中得以建立起一種秩序觀。17世紀鏡廳的安排亦可以體現帝王身份的構想,臣民在鏡廳中關照到自己對于帝王的致敬,規范自己的姿態禮儀;帝王在鏡廳中也可以關照到自己對與臣民的統治,乃至最高臣子的主宰。這樣一種服務于政治統治的透視使得觀者在接受視覺規訓中界定自我的身份,透視規則的應用也闡明了藝術家的身份意識。類似于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了其主奴關系主體論,在這樣一種權力意識的表現之中,將權力差異視覺化予以表現,產生出不同主體對自身的認知和描述,形成一種個體身份認知。
第二節,現代時期。
現代時期視覺文化時期的身份問題關乎集體身份認同。瓦爾特·本雅明在其《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一書中提到:“在照相攝影中,展示價值開始整個的抑制膜拜價值。”照片作為歷史進程的見證,開始具有了政治意義。殖民時期,殖民者的攝影與被殖民者的雕塑作品呈現出了文化的對壘,雙方進行集體身份的選擇,可以在這時期的視覺文化中見出強烈的思想沖突。歐洲殖民者對剛果形象塑造的方式從文本走向影像記錄,攝影術的應用將殖民主義的暴行美化成為一項開化野蠻的正義使命,西方的“冒險家”和“探險家”們絡繹不絕地來到殖民地,在殖民地殖民局當局地安排下完成一個虛擬的剛果去體驗,這樣的體驗成為他們回到西方世界的談資。殖民地的剛果人被安排為構建殖民秩序的工作服務,這些工作通常是最苦最累的,而西方殖民者僅將殖民主義的“文明”成果,如鐵路、房屋等,成為他們堅持殖民,反對改革的正面例證。這一切殖民秩序的闡釋,都透過相機的鏡頭被定格下來,透過1909到1915年,赫伯特·朗拍攝的剛果地區芒貝圖人的生活方式中,可以洞察出霍米·巴巴所謂的對殖民秩序的模擬,即“當地人”應該怎樣生活,當地的建筑應該是什么樣。芒貝圖人照片中記錄的部落才是殖民者口中的剛果,與真正的文明的歐洲人身份相區別,因此攝影成為一種西方殖民者鞏固其在非洲殖民統治的工具,也是塑造其優越身份并獲得集體共情的手段。殖民地人民亦會在自身的視覺文化中予以強勢的殖民文化以反擊。象征物“命可司”被殖民地者視為有神力的東西,當它被一個熟練的操縱者——即“恩甘嘎”(nganga)——召喚而至時,就會站在懇求者這一邊,和他(她)的敵人或惡魔對著干。剛果人在殖民時期制作了大量的“命可司”,歐洲人也對這樣原始文明延續下誕生的雕像具有敬畏的心態,對這樣的宗教物品定性為“物神”,歐洲人對之展開大規模的圍剿。正是由于這樣的象征物的存在,非洲的被殖民者得以把自己想象成殖民體系內的主體,而不只是仆從或客體。在這樣的殖民文化的介入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以視覺媒介為載體,表征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并視之為一種集體文化,而將對方的文化視為他者,從而建立起相對立的集體身份。
第三節,后現代時期。
悖謬的或荒誕的圖像邏輯可洞察出身份問題事關文化身份,蟄伏在思想浪潮的涌動中,具有后現代時期的去中心化、多元化的特征。正如芭芭拉·克魯格的作品所揭示的那樣:“你的身體就是戰場。”這使得激進的女性主義浪潮中,女性的身體成為身份的符號。南·戈爾丁后攝影中,鏡頭直接目擊私密的場景,直白冷酷地表現青年一代在日常生活經驗方面的激進實驗,攝影中對自我形象的記錄也擺脫了追求自身理想化形象的動機,探求女性身份問題。藝術中技術工具的推進與文化思潮的雜糅,催生出當代美國影視作品《獨立日》、《星際迷航》、《異形》等科幻電影,虛擬世界里生物、宇宙、科技多元素的生發與粘合投射性、性別、階級身份的關注,以及對于青年文化、亞文化、后人類時代文化下的身份焦慮。在構建出的賽博自然中,以賽博格為主體的賽博朋克形象是人類在信息社會主體性文化的表征,如唐娜·哈拉維所述:“這(賽博格)是一個有關生命權力和生物社會性的故事,也同技術科學相關。”賽博格為主體的賽博自然是建立在虛擬身份理論基礎上的,是如雅斯貝爾斯所述第三軸心時代人類解放“智之力”的產物,賽博格形象的構建打破了人文限制,個人身份的數字化是其核心意義,個人也成一種技術上的概念,女性主義寄生于賽博格之上,誕生賽博女性主義,推進了女性主義的演變。賽博格所依托的虛擬性滲透到人們生活,觸發了一些新的性問題形式和性別身份形式,米爾佐夫提到泥巴(MUD)社區用戶構建的在線角色,通過塑造出的角色可見出異性雙方的性別身份認同。對創造虛擬身份的興趣愈發濃厚,人們創造了用于賽博空間的互動人造身份。后現代的視覺文化中身份問題圍繞性、性別、性向、種族等主題的探討后現代視角下的身份是非本質主義的,是一個策略的身份,是一個位置性的身份。這說明身份的背后隱藏著構建身份的目的性,以及位置身份中構建的權力關系。對身份政治的探討不再圍繞某一主題,不再認為身份是受某一核心變量的支配,而是在共性中存在著差異,走向去中心主義的文化身份,提倡變動多樣化的身份觀。
三、結語
依據米爾佐夫的觀點,將視覺文化視為一種闡釋結構,對特定歷史時期“視覺性”中統一的視覺機制進行揭露,對不同形式的“視覺性”進行譜系學的分析,可見出不同視覺技術中不同文化以及文化內部的權力差異,可見出身份是在與他者的對立與權力規訓中建立完成的。隨著視覺技術變化帶來的圖像意義生產方式發生改變,身份構建也呈現出從個體到集體,從統一到碎片的特征,服務于特定的話語體系,身份的建構逐漸走向一種去中心化的文化身份。如今,視覺文化中的身份問題還在被提及,米爾佐夫后續的學術論著《觀看的權利》《怎樣觀看世界》圍繞“視覺性”,貫穿了其對身份構成和身份政治的探討。在米爾佐夫的理論體系中,實現了其將視覺文化視為一種闡釋結構的預期目標,視覺文化也呈現出跨學科的特征。
注釋:
1.(美)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P5.
2.(美)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P7.
3.(美)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P8.
4.(德)本雅明著;王才偉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01.12.P23.
5.劉介民,劉小晨,哈拉維賽博格理論研宄:學術分析與詩化想象[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