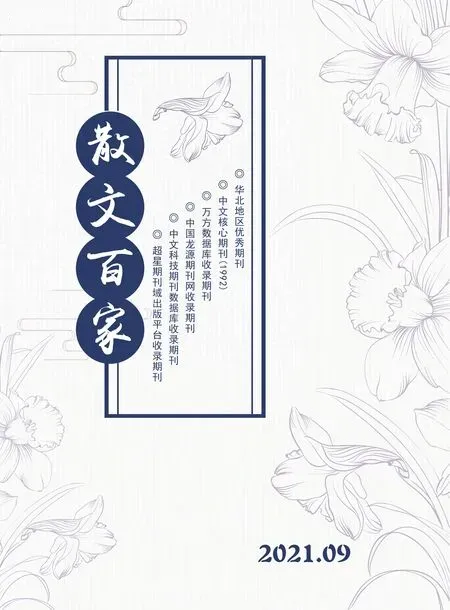清麗與焦慮交織下的“故事新編”
——論劉以鬯《蛇》的創(chuàng)新寫作
朱蓓佳
華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白蛇傳》是中國古代民間故事,講述了許仙與白蛇變成的白娘子相愛卻不斷受到法海阻撓的凄美愛情故事。劉以鬯先生的《蛇》以《白蛇傳》為原型,是當(dāng)代作家對“故事新編”的再一次嘗試,但作者不滿足于復(fù)述歷史、復(fù)活歷史,而是以現(xiàn)代人的視角重構(gòu)歷史。
一、對歷史的重構(gòu)
劉以鬯在《蛇》中很好地保留了《白蛇傳》民間故事平易近人的特點,整個故事像潺潺溪水一樣流暢優(yōu)美而又富有節(jié)奏。劉以鬯在保證作品整體架構(gòu)大體與《白蛇傳》一致的情況下對作品的情節(jié)以及人物進(jìn)行了創(chuàng)新。作者將白素貞妖怪的身份改為了普通的平民女子,讓她與許仙之間人與妖的隔閡化為烏有。
劉以鬯對歷史重構(gòu)的核心在于他創(chuàng)新性地賦予了白素貞與許仙更加豐滿的人物形象也充實了故事情節(jié)。在《蛇》中,白素貞與許仙的形象都是十分清晰的。從白素貞給捕蛇人三兩銀子、白素貞懷孕仍喝下雄黃酒等情節(jié)可以看出她對許仙真誠的愛意以及她對自己感情的勇敢捍衛(wèi);而劉以鬯描寫許仙則注重用心理分析的法進(jìn)行寫作,如:“一個可怕的印象占領(lǐng)思慮機(jī)構(gòu),他感到極大的不安”,以此凸顯許仙內(nèi)心的焦慮、懷疑、害怕。同時,劉以鬯也更新了《蛇》的主題,講述了一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故事,展露了人類復(fù)雜的心理。小說歷史重構(gòu)的目的不僅是求新,更是讓歷史改寫服務(wù)于人物的塑造,進(jìn)而呈現(xiàn)文章的主題。
二、清麗的詩化小說
劉以鬯先生曾經(jīng)在《不是詩的詩》中寫道:“我常在詩的邊緣行走,審看優(yōu)美環(huán)境的高長寬,我寫過一些不是詩的詩。”他也提到自己寫作《寺內(nèi)》是想要實驗“不是詩的詩”的寫法。試看《寺內(nèi)》中的一個像詩一般的片段:那份感情,濃得必須加水。那份感情,熟得太早。從夢中踱步而回的,名叫“現(xiàn)實”精短的句子與凝煉的詞語,再加上單句成行的排版,使得小說也成為了別樣的詩。《蛇》中也有這樣精短的句子與優(yōu)美的語言,“落日的余暉涂金黃于門墻。許仙的靴子仍染昨日之泥,”文言詞語的運用和整齊的格式讓這樣的句子有了一種古詩對仗的感覺。清麗的語言與中國傳統(tǒng)民間故事相輔相成,在《蛇》中塑造了一個世外桃園般的世界。兩人初遇時的景象平淡卻美得攝人心魂,“他說:‘雨很大。’她說‘雨很大。’艙外是一幅春雨圖,圖中色彩正追逐一個意象。風(fēng)景色彩原是濃的,一下子給驟雨沖淡了。”簡單的重復(fù)、白描的手法,二者的默契不言自明,明凈的景致與純凈的愛情兩相對照,這樣清新質(zhì)樸的語言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和翠翠、儺送二人的真摯愛情。再看二人的相伴之景,“燭光投照在酒液上,酒液有微笑的倒影。”詩一樣的語言讓此情此景更顯優(yōu)美動人,也為文章增加了行云流水般的韻味。
縱觀整篇文章,一種清麗動人之感撲面而來。白素貞與許仙相遇的清明之美、洞房花燭之美、白素貞悉心照料許仙之美。《蛇》的語言藝術(shù)之美是一種整體性的美,不是作者去適應(yīng)這種語言形式,而是詩一般的寫作形式符合作者的寫作需要。作者以精簡、考究的語言重構(gòu)了《白蛇傳》這個凄美的民間故事,讓“凄”更“凄”,“美”更“美”,體現(xiàn)出極強的藝術(shù)功力與審美價值,這也是作者對于寫作方式創(chuàng)新的一種追求。
三、焦慮的內(nèi)心探索
《蛇》一方面對小說的語言形式進(jìn)行了創(chuàng)新,一方面也反映了當(dāng)代作家對于“內(nèi)在真實”的關(guān)注。當(dāng)代小說有著比較明顯的“向內(nèi)轉(zhuǎn)”特征,作家們開始更多地關(guān)注人的心理,注重展現(xiàn)人的內(nèi)心世界,從人物的內(nèi)部情緒出發(fā)描繪外部世界。在這個階段,文學(xué)不再像過去那樣成為政治的“武器”,它轉(zhuǎn)向了人的內(nèi)在真實。魯樞元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是比較清晰的:“小說心靈化了、情緒化了、詩化了、音樂化了。小說寫得不怎么像小說了,小說卻更接近人的心理真實了。”伍爾芙在《論現(xiàn)代小說》中也表達(dá)了相似的觀點:“一切都是恰當(dāng)?shù)男≌f材料,每一種情感,每一種思想,每一種大腦和心靈的特征都是取材的對象。”我國文學(xué)評論家提出的“向內(nèi)轉(zhuǎn)”與西方作家提倡的“關(guān)注人的精神世界”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它反應(yīng)著一種整體性的文學(xué)發(fā)展趨勢,《蛇》一文就表現(xiàn)了作者對內(nèi)心世界的關(guān)注。
雖然《白蛇傳》是古典小說,作者卻采取了當(dāng)代的寫法,這一點突出地體現(xiàn)在了許仙心理的刻畫上。《蛇》與《白蛇傳》很大的區(qū)別在于,劉以鬯孜孜以求地探索著許仙焦灼病態(tài)的內(nèi)心世界。與許多西方現(xiàn)代小說家一樣,劉以鬯也把探求人的“內(nèi)在真實”作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他的心中,所謂“內(nèi)在真實”是“人的內(nèi)心沖突”,是“靈魂斗爭”……潛意識對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所產(chǎn)生的影響,較外在環(huán)境所給予他的大得多。按照榮格的分析心理學(xué):總體的心靈包括三個層次:意識、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意識是心靈中唯一能夠被個體直接感知的部分,而個體無意識是一個容器,蘊含和容納著所有與意識的個體化機(jī)能不相一致的心靈活動。“我親眼見到的,那條蛇游入亂草堆中。”“那蛇……那條蛇……”許仙能夠感知的僅僅是他對蛇的恐懼(意識),而他內(nèi)心深處的自私、多疑、扭曲(個體無意識)卻是他無法感知的。許仙的意識與無意識無法統(tǒng)一,他在激烈的內(nèi)心動蕩中無法掙脫對蛇的恐懼,更無法信任身邊美麗而又體貼的白素貞。作者兩次有意地寫道:“院中無蛇,蛇在許仙腦中”更是證明了蛇留存于許仙的潛意識中,而他自己卻渾然不覺。小時被蛇咬的恐懼遲遲不能散去,造成了心理的創(chuàng)傷,許仙甚至不顧白素貞的感受,不顧孩子的安危在家中懸掛符咒,自私地逼迫白素貞和下雄黃酒。此時的許仙內(nèi)心已經(jīng)嚴(yán)重扭曲,而他荒謬可笑幻象的極致是那條在床上的“蛇”。作者在這里仿佛流露出了暗暗的諷刺,書中的人物好像出現(xiàn)了身份的倒置,作為人的許仙展露出了人性的弱點:懷疑、自私,而在傳說中作為妖怪的白素貞則展露出了她最善良、最勇敢、最堅韌的一面。
文中“蛇”的意象在我讀來是頗有深意的,在中國文化中,蛇的形象本身就與冰冷、可怖相關(guān)聯(lián),在《蛇》一文中,它代表著許仙內(nèi)心的焦慮、痛苦、多疑,它雖然來自于歷史故事,卻也成為了當(dāng)代人情感的“客觀對應(yīng)物”(即表達(dá)作者情感、情緒、思想的具體形象事物,這個概念由英國詩人艾略特提出,他主張“藝術(shù)情感是非個人的”,而在藝術(shù)形式中表現(xiàn)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觀對應(yīng)物”。)。本文中的“蛇”,也讓我想起了馮至先生的《蛇》一詩:“我的寂寞是一條蛇,冰冷地沒有言語──姑娘,你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莫要悚懼!”馮至先生就是以蛇來隱喻當(dāng)時自己的心態(tài)——寂寞,無人理解,冷冰冰的,無言語的,漫長的毫無盡頭的寂寞而自己內(nèi)心又是如蛇嚙一般在疼痛。馮至先生的詩歌是潛沉內(nèi)向的,他將自己的內(nèi)心借助詩歌表達(dá)出來,而劉以鬯先生也對許仙的內(nèi)心進(jìn)行了深入地探索,在這一點上二者是共通,這樣的現(xiàn)象反映了中國文學(xué)對于現(xiàn)代主義的接納。總之,劉以鬯對于許仙內(nèi)心的開掘是深刻的,在《蛇》我們隱隱能夠感受到一種有著現(xiàn)代性的焦慮和掙扎。
四、懸疑的寫法
《白蛇傳》本身是不帶有懸疑色彩的,然而《蛇》中白素貞和法海兩個人物都有著懸疑的色彩,不讀到故事最后讀者無法知道結(jié)局。劉以鬯有意在行文中增添了一絲模糊的色彩,使得小說后半部分的情緒更加緊張。許仙逼迫白素貞喝雄黃酒的那一段節(jié)奏尤其緊張,“他(許仙)將《鐘馗抓鬼圖》貼在門扉,以之作為門禁,企圖禁錮白素貞于房中。白素貞態(tài)度自若,不畏不避。于是雄黃酒成為唯一有效的鎮(zhèn)邪物。相對而坐時許仙斟一滿杯,強要白素貞喝下。白素貞說:‘為了孩子,我不能喝。’許仙說:‘為了孩子,你必須喝。’白素貞不肯喝,許仙板著臉孔生氣。白素貞最怕許仙生氣,只好舉杯淺嘗......白素貞將杯中酒一口喝盡。”許仙的步步緊逼與白素貞的毫不畏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了解除自己內(nèi)心的恐懼,他不惜采用逼迫的方式,這也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許仙極度病態(tài)的心理。當(dāng)然,此處情節(jié)的設(shè)置也不僅僅是為了突出人物的特點,也加深了讀者心中的疑惑,將故事推向了高潮。白素貞對雄黃酒拒絕的態(tài)度以及她喝完酒暈眩的姿態(tài)(白素貞讓許仙去看他人打牌也讓人生疑)讓讀者不得不懷疑白素貞是否真的是蛇妖變的。直到那條腰帶的出現(xiàn),讀者的心里才有了答案。
故事進(jìn)行到第九節(jié)就戛然而止了,關(guān)于法海的真實身份作者也沒有進(jìn)行明確的交代。小說中法海的獨白像是一個來自歷史的聲音,它虛無縹緲,推動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劉以鬯有意識地懸置了真實的世界,給故事蒙上了虛幻的色彩,在《蛇》中,許仙和其他人似乎并不知道《白蛇傳》的民間故事,所以第七節(jié)中的法海也有極大的可能是不知道白素貞的。我認(rèn)為,第七節(jié)中法海的獨白更像是盤踞在許仙內(nèi)心中的焦慮和恐懼,他已經(jīng)對白素貞產(chǎn)生了猜忌和懷疑,法海的一段話更像是許仙猜測的證明,這是一種由恐懼引發(fā)的荒誕的幻象,它只是因為披上了歷史的面紗所以顯得合乎情理。讀者的主觀歷史經(jīng)驗會對理解文本產(chǎn)生影響,在《蛇》中,歷史背景與許仙復(fù)雜心理的交融產(chǎn)生了懸疑的色彩,讓故事更具當(dāng)代特點也更具創(chuàng)新色彩,這也是作者寫作的高妙之處。
作者在小說的結(jié)尾寫道:“許仙走去金山寺,找法海和尚。知客僧告訴他,法海方丈已于上月圓寂,你遇到的一定是另外一個和尚。”讀完文章,讀者可能會久久地沉浸在一種恍然大悟與自省的情緒中,誰能保證自己一生中不出現(xiàn)一條“蛇”?誰保證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中沒有遇到一個“法海”?誰又能保證自己沒有懷疑過身邊的“白素貞”?作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世界與審視自身的視角。劉以鬯先生的作品揭示了現(xiàn)代人緊張、焦慮的情緒和對他人的懷疑、不信任,借助歷史故事開掘現(xiàn)代人性。
五、結(jié)語
很多學(xué)者將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與劉以鬯先生的故事新編進(jìn)行比較。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飽含著一種對現(xiàn)實的強烈批判,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味;而劉以鬯先生的故事新編則更注重寫作手法以及寫作語言的創(chuàng)新,更加直接地指向當(dāng)代人焦灼的內(nèi)心世界,是一種創(chuàng)新式的嘗試。如果說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是借古喻今的話,那么劉以鬯先生的作品就是以舊賦新。“我寫故事新編,最重要的是新”。
《蛇》雖然是劉以鬯先生的刻意求新之作,但它同樣飽含著作者對藝術(shù)價值、文學(xué)審美的追求,它將新與舊融合地天衣無縫,是一篇更適合當(dāng)代人讀的,更符合現(xiàn)代人心境的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