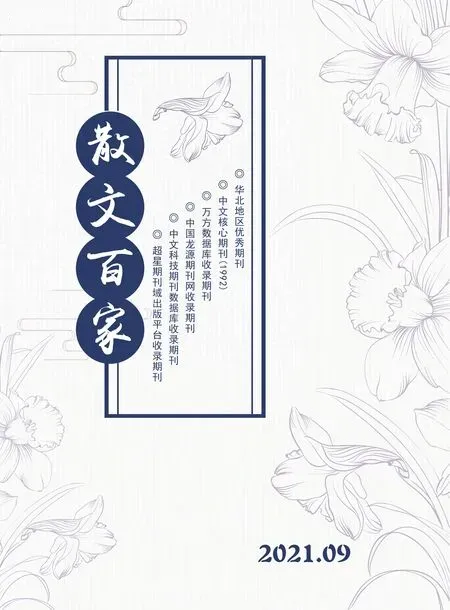彭斯詩歌《蘇格蘭人》中的格律與修辭探析
吳雅麗
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羅伯特·彭斯(1759-1796)是蘇格蘭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也是18世紀浪漫主義詩歌的先驅之輩。他一生勞作于田間,雖未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具有非凡的詩歌天賦,為后世留下了600多首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詩歌。彭斯的詩歌大多由蘇格蘭方言寫成,內容上真實反映了蘇格蘭農民的生活與情感,具有階級性與民族性。此外,受各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彭斯心中還燃起了自由與獨立的火種,他由此寫下了大量的愛國抒情詩歌,《蘇格蘭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蘇格蘭人》發表于1794年,由英語和蘇格蘭方言寫成,是彭斯游歷班諾可克本戰場遺址時的有感之作。全詩氣勢磅礴,具有宏偉的歷史感,它描寫了蘇格蘭國王羅伯特·布魯斯在班諾克本戰役前鼓舞士氣的場景,最終蘇軍大破英國侵略軍取得了勝利。此外,詩人還運用了獨特的詩歌語言藝術來加深其愛國情感的表達,詩歌中出現大量呼語、停頓、尾韻詩節及首句重復等語言現象。本文通過分析該詩的格律、修辭及各類語言現象,深入探討了《蘇格蘭人》中詩人彭斯的情感表達。
一、《蘇格蘭人》中的格律分析
詩的語言是詩人精心安排的結果,具有音樂性,這種音樂性體現在詩歌優美的韻律與格律當中。彭斯是土地與農民的詩人,勞作時常接觸民間歌謠,由此對民謠與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一生收集、改編蘇格蘭山地歌曲與民謠,詩歌《蘇格蘭人》便是他依據民間曲子自己創作的詩作。《蘇格蘭人》整體形式新穎、節奏鮮明且音韻和諧,詩人靈活地運用了呼語、韻律以及排比結構,使得全詩具有很強的音樂性,深受大眾喜愛。
音韻是通過重復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音素而產生的,是構成詩歌音樂美和藝術情趣的重要元素。詩人們為了使詩歌讀起來朗朗上口,常采用押韻的方式,安排詩句中某些具有相同韻律的音節按照一定規律重復出現,從而產生更和諧效果。押韻是詩歌的語言韻律的重要表現形式。常見的押韻方式有頭韻、行中韻以及尾韻,這三種韻式根據所在詩句中的位置不同而得名。在詩歌《蘇格蘭人》中,詩人靈活運用頭韻、尾韻等押韻手法賦予了詩句整體流暢、和諧的樂感。頭韻是指在一行詩中,兩個及兩個以上相鄰的詞起首輔音相同重復的情況。在詩歌第四節第三行,詩人使用freeman fa’來突出自由人毫無畏懼,為祖國英勇抗爭的獻身精神。freeman與fa’都具有相同的起首輔音,這里兩個連續/f/音的出現不僅能夠加強行內節奏感,形成悅耳的聲音韻律,還能夠引起讀者的注意與共鳴。尾韻又稱腳韻,指詩行與詩行之間行末的音節押韻,這類出現在詩行末尾規則的音素現象為詩歌整體的音樂性注入了靈魂,令讀者回味無窮。彭斯詩歌《蘇格蘭人》的創作形式新穎,韻律獨特,這首先體現在詩人采用了特殊的尾韻押韻形式—尾韻詩節。尾韻詩節一般由兩個單位組成,每一個單位之內有一個雙行聯韻體、三行聯韻體或四行套韻體,其后跟一個較短的詩行,即“尾行”。這兩個或三個聯韻體可以同韻,也可以不同韻,但較短的“尾行”必須押韻,例如:aabaab或aabccb,因此得名尾韻詩節(吳翔林,1993)。在《蘇格蘭人》詩歌中,詩人連用六個尾韻詩節,韻律上一氣呵成,大有史詩般恢弘的氣勢。以第一、二兩個詩節為例,在這兩個詩節中,單個詩節由一個三行聯韻體和一個“尾行”構成。第一節中一、二和三行末尾詞匯bled、led、bed中的元音音素/e/相同,其后的輔音音素/d/也相同,因此押單音節韻。第二個詩節中的每行末尾單詞:hour、lour、power也具有相同的元音音素,壓相同的尾韻。由此可見,兩節詩中前三行符合尾韻詩節中的三行聯韻體形式。此外,詩節中較短的“尾行”也相互押韻,第一節的尾行單詞victorie和slaverie末尾都壓/i/的韻,結構完全符合尾韻詩節的韻律形式。從詩歌整體來看,每個詩節都基本符合三行聯韻體加“尾行”的結構,第三節的前三行末尾詞knave、grave、slave壓單音節韻,第四節的law、 draw、fa’( fa’的英語對應詞為fall)也壓相同的單音節韻,五、六節可以此類推。與此同時,六節詩歌的六個“尾行”單詞victorie、slaverie、flee、me、free、die(die在古英語及蘇格蘭方言中讀[di:])都壓[i:]的單音節韻,完美地詮釋了尾韻詩行的形式與精髓。總體來看,詩歌整體韻律為aaabcccbdddbeeebfffbeeeb, 它不僅讀起來氣勢磅礴、激情澎湃,還將彭斯對于英雄的崇敬、祖國的熱愛情感融入韻律之中,這在英國詩歌史上是十分少見的。
詩歌不僅具有音樂美,還具有視覺美與形式美。彭斯的詩歌《蘇格蘭人》在詩歌形式做到了大膽創新,頗具研究價值。從詩歌的視覺形式上來看,較為明顯的一點在于詩人并未選擇規范對齊的詩行形式,而是采用了“尾行”縮進的方式。在《蘇格蘭人》中,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每一單獨詩節的“尾行”縮進都是為了對前面的內容做出回答、解釋、總結或者表明目的。以詩歌第五節為例,詩人在第五節前三行描述了布魯斯國王邀請士兵們起誓,為壓迫與苦難,為子孫能夠不受奴役而血戰到底,而詩節“尾行”的But they shall be free則表明了前三行起誓的目的是“子孫必須獲得自由”。詩人采用尾行縮進形式進行創作的優勢在于詩歌的內容結構變得更加清楚、邏輯更加明晰,這不僅能夠給讀者帶來視覺上美的享受,還有利于號召人民赴戰反抗、激發民族奮戰情緒。在詩行內部,詩人還采用了句中停頓、呼語和首句重復的方法創新詩歌形式。停頓指的是語音流的中斷,句中停頓常以感嘆號、破折號、逗號等作為標記,以加強語氣,產生一定的節奏感,恰當地運用停頓可以增強語言藝術效果和渲染力。在詩歌《蘇格蘭人》中,彭斯多次在句中使用逗號和破折號表現停頓。在詩歌第一節前兩行中,詩人首先兩次使用呼語“Scots”加逗號停頓的形式來表達此刻澎湃的情感。他將自己置于班諾可克本戰場,想象自己就是面對著蘇格蘭士兵的布魯斯國王,想象著斗爭與勝利,于是他慷慨致辭!借助呼語“Scots”,詩人跨越了時間、空間以及生命的界限完成了與過去不在場的人之間的對話,直接訴說了守衛祖國、慷慨赴戰的愛國情感,這不僅渲染了布魯斯國王戰前動員士兵時的激昂氣氛,還增強了詩歌的抒情色彩與感染力。
可以看到,與當時英國詩壇的新古典主義詩風不同,彭斯作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先驅人物,開辟了頗具個人特色的新詩風。他從民間歌謠中汲取營養,從土地與自然中獲得靈感,為當時詩歌創作帶來了一股清新、新鮮的活力。民間歌謠本就自由,不拘泥于詩行固定音節與節奏的束縛,彭斯對傳統詩歌的視覺形式進行的變異,極大地拓展了詩歌意義的表現手法,豐富了詩歌的視覺形式,為后來浪漫主義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蘇格蘭人》中內容與修辭分析
《蘇格蘭人》是彭斯所作愛國詩中最著名的一首,許多人甚至將這首詩看做蘇格蘭非正式的國歌(王佐良,1985)。在這首詩中,彭斯模仿蘇格蘭國王羅伯特·布魯斯的語氣,向即將參與班諾克本戰役的蘇格蘭士兵們發起了號召。班諾克本戰役是蘇格蘭民族的自豪之役,蘇格蘭人在這場戰役中大敗英國侵略者,改寫了蘇格蘭的歷史。于是彭斯首節便呼喚勇士,那些跟隨華萊士流血戰斗的人啊,那些和布魯斯一起打敗英軍的斗士啊,起來!即使是倒在血泊里,也要奪取勝利。華萊士和布魯斯都打敗過英國軍隊,是蘇格蘭的民族英雄。詩人在這里緬懷了逝去的戰士們并直接號召蘇格蘭軍隊,為保衛國家做好準備,戰場的氣氛由此營造。值得注意的是該節第三行“glory bed”暗喻“犧牲與死亡”,這是因為對于詩人來說,為國赴死是一件榮耀的事。詩歌第二節如電影運鏡一般,向讀者提供了士兵的視角。前線戰爭吃緊,英王愛德華統兵入侵,如果放棄奮戰,只會帶來鎖鏈和奴役,這樣的創作手法十分新穎。此外,詩人還使用了重復的修辭手法,連用兩個“see”以強調嚴峻的形勢,加重情感的表達,引起讀者的注意。聯想到過去失敗的抗爭,詩人使用了首語重復法(anaphora),連用三個“wha”來譴責叛國者、膽小鬼和愿做奴隸的人。首語重復法是一種修辭手法,指一個詞、詞組甚至是從句在一段話中每句起首進行重復, 進而起到強調或加重語氣的作用。在這節詩中,三個“wha”分別質問三個不同的對象,表達了詩人強烈的憤恨之情,詩歌情感部分的高潮也由此而來。詩歌第四節遵循演講的內在邏輯,將重點放在描寫詩人理想中的蘇格蘭戰士。詩人在這里使用了對比的修辭手法,塑造了自由抗爭的人物形象并與第三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不僅能夠更加有效地號召人民英勇奮戰,還凸顯出了詩人本身的政治立場,那就是向往自由、追求民族尊嚴。為堅定士氣,彭斯在第五、六節中談論了戰爭的目的。他曾經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創作《蘇格蘭人》不僅受到古代那場“光榮的斗爭”的啟發,還有對當時“在時間上卻不是那么遙遠的同類性質的斗爭”—法國大革命的深刻認識(王佐良,1985)。因此筆者認為,詩歌的第五、六段具有普遍適用性,是為世界上所有面臨著侵略與壓迫的人民而作。從修辭角度上看,第五節中詩人使用夸張的修辭手法,“drain our dearest veins”表明詩人即便耗干血液,也要追求自由的情感。此外,詩人還在第六節中將Liberty進行了擬人化,生動詮釋了在痛擊中才能獲得自由。由此可見,彭斯的《蘇格蘭人》不僅做到了形式上創新,還大量使用了如暗喻、夸張、首句重復等修辭手法,將詩人對自由與祖國的熱愛之情展現地淋漓盡致。
三、總結
《蘇格蘭人》是彭斯愛國詩歌的代表之作,顯現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在這首詩中,詩人借布魯斯之口來書寫他作為蘇格蘭人的愛國之情,具有強烈的戰斗性和感召力。全詩共六節,采用了短音節詞和尾韻詩節的韻式進行創作,讀起來激情澎湃、氣勢磅礴、開口有力。此外,詩人還在詩歌形式上進行了創新,使用大量的修辭手法以展現詩歌內容,傳達熾熱的愛國情感。總而言之,《蘇格蘭人》韻律優美、形式靈活,可以稱得上是英國詩歌史上的杰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