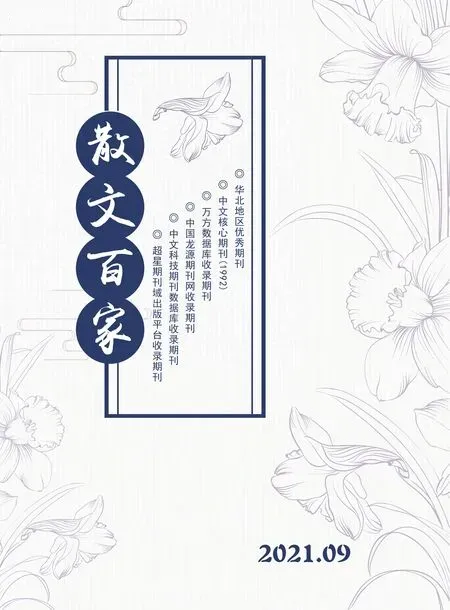讀柯璜先生《人生基礎哲學》
趙 濤
太原市晉祠博物館
柯璜先生是我國近代以來著名的儒學家、書畫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融會古今、博覽中西、傳道授業、心懷天下,頗受時人和后世所敬重,堪稱一代名儒。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在重慶期間,將其閱歷和感悟匯集成《人生基礎哲學》一書,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胸懷和擔當,試圖通過弘揚孔子之學,由內而外,由己及彼,教化世人,匡扶世道。即使今天讀來,不僅未覺陳舊,反而歷久彌新,裨益頗深。現將感受簡要述之如下:
一、集大成者,繼往出新
柯璜生活的年代大體來說是中華民族近世以來苦難最為深重、社會劇烈變化的時代,然而也是一個各種思想活躍、各路人才輩出的時代。柯璜先生所撰《人生基礎哲學》并不是一部闡釋儒家經典的研究性著作,也不是一時興起所為,而是在內外交困、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下,以其平生感悟積累而成、以闡發孔子之學于當時社會的一部語錄式著作。正如他在該書《自序》中開宗明義所指出的,“世間多少彰彰道理”,有些雖為前人所道,但是“未能十分透辟者”;更為重要的是,“又有多少事理,為新時代錯綜遞演而成,全為前人道未之及”。正因如此,柯璜先生決心以“平生所見所聞所身歷,于物我人己間,得其劇烈之刺激,大勢之競演,自然之變化,顯明之案例,擇其有益于人類人生,簡直明了,神味淵永者,筆其元要,以為立身立命,治國治家之公例”。該書通過節錄日常筆記,列出五百六十個重點議題,借用《大學》八目格式,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將這五百六十個小結歸納進八卷之中,由內而外、由淺到深,闡明了柯璜先生的人生態度,體現了他的人生境界。
《人生基礎哲學》一書,雖然以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為基礎展開,但是書中卻處處散發著時代的光芒,所謂“闡前人欲闡所未闡,言今人欲言未即言”。柯璜先生站在時代潮頭,以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和寬闊的世界眼光,現身說法、旁征博引,點化世人如何面對自己、面向外界。猶如茫茫滄海中的燈塔一般,試圖為迷蒙之世道點亮一盞明燈。他的很多觀點即使現在看來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這也成為該書最大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二、學貫古今,珍視孔學
柯璜先生出生于浙江臺州路橋桐嶼,祖父一生以教授為業,父親行醫,在路橋一帶頗有名氣。柯璜從小跟隨叔父和堂兄研習六藝經傳,由此打下了堅實的儒學基礎。他十八歲中舉,而后北上參加會試,在京城結識了康有為等一批社會名流。時值清廷北洋水師在中日海戰中戰敗,《馬關條約》簽訂在即。他積極響應康有為、梁啟超號召,同數百位在京舉人一起上書反對簽約。從此,柯璜先生個人和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也促使他更加關心國內外形勢,用時代眼光對待自己,看待世界。
自1840年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打開中國大門,中國人看到了西方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強大力量,開始轉向西方學習。然而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子遭受質疑。在救亡圖存的意識驅使下,一些人轉向全盤吸收西方的政治制度,徹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一股強大思潮。一批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斷攻擊柯璜,認為他是封建舊思想的衛道者,然而柯璜先生對孔子之學始終懷有堅定的認知。
《人生基礎哲學》一書始終貫穿著他對孔子之學和儒家精神的自信。他在“美國近時乃發明至誠二字”一節中說:“講機械,中國為世界后進國;講精神,中國實萬國先覺邦。然則吾人當講自國自家價值,不可過于輕看”。他在“精神修養,中國已到妙處”一節中進一步說:“講到形式學術,不可不至誠信仰西人,講到精神修養,吳國黃冠道服,亦多談到微妙之處”。這些論斷的提出不僅基于其深厚的國學內力和認知高度,也是基于其對中西方思想文化發展脈絡比較研究后得出的,更重要的是針對當時孔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形勢提出的。柯璜先生始終認為:孔學之所以能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并歷數千年而不絕,正說明了這種文化與中國社會相適應性。而弘揚孔子之學,正是上天所賦予他的神圣使命。
孔慶余在為該書所做序言中直截了當的指出了當時孔學的境遇。他說:“孔學云亡,而未嘗亡也。孔學云存,存而未敢云果存也”。在這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他認為孔子之學的傳道者和實踐者卻是寥若晨星。面對如此境遇,“黃巖柯定礎先生,盡然傷之”,于是才有了《人生基礎哲學》一書的橫空出世。柯璜先生一生研習孔學,“證之古代歷史、現今社會”成為該書的核心目標。柯璜先生在1946年為該書再版做序時進一步說:“孔子學說,是綜春秋以前,華夏三古百氏,行上人道之長,而集其大成”,“孔子學說,和平中正,不分時空,農市工商各界,莫不咸宜。故以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如日在長天,光臨大地,群生萬類,向榮欣欣。著書立說,宗主其理,故可俟百世而不惑者也”。以此闡明編撰《人生基礎哲學》一書的目的,體現出他對繼承和發揚孔子之學的使命擔當。
柯璜先生之所以不遺余力的推行孔子之學,是因為他堅信孔學有利于提振國人精神,能夠服務當下社會。他在“《孟子》最能醫今人痼病”一節中說:“讀《孟子》一書,振作自家自立志氣不少。士生今日,不好好讀古人振作精神之書,則必流于庸俗、卑污、脂韋、茍且、粗率而不自覺。不能自救,安能救人”。面對當時日軍侵華,民族精神不夠振奮,他提倡從儒家經典中汲取能量,找到振奮中華精神之要領,方能自救民族于水火。同樣是針對當時全國上下鼎新革故、學習西方反而不得要領的弊病,他在“撐起脊骨做新時代人”一節中說:“今者革新轟轟烈烈,服新式時裝者,仍有未能表現新時代之精神,此其責不可專歸咎三家村學究。此后青年、壯年、老年,非人人撐起脊骨做人,一切形式,都是皮毛”。撐起脊骨的不是外在的服飾,而是內在之精神,其來源正是持續數千年的孔孟之學,這正是柯璜先生在該書中所反復強調的。
三、洞察中西,預見未來
《人生基礎哲學》一書的價值,不僅在于柯璜先生身體力行的弘揚以孔子之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更重要的是這部著作將其日積月累的人生感悟和時代精神相結合,體現了柯璜先生的博學敏思和終極關懷,使得書中的格言警句煥發了持久的生命力。
柯璜先生長期以來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保持著自己的洞察。他在“其實發明發現不到萬一”一節中說道:“人每自夸其發明電視,豈知視聽嗅味觸五覺之最有限器官,耳目口鼻手意外,不知尚有多少無量數之色光香臭冷暖軟硬咸甜苦酸類之無量無限物質。學者用多少公式,多大多細之望遠鏡顯微鏡,多少理化試驗,多少寒熱氣壓,種種復雜精妙表計所求出著,實在不過只得其浮淺之萬一”,由此可知柯璜先生在當時不僅對西方科學技術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對現代科學的精神實質有著正確的把握。
然而,柯璜先生對科學技術并不一味盲從,而是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在“科學亦有穿鑿空疏,應辨別之”一節中講到:“人之尤吾國漢學穿鑿,宋學煩瑣,明清質藝試貼,拘泥空疏。殊不知各科科學,亦有借著顯微望遠諸鏡,及算術之推演,攝影之裝潢,自以為別有壺中日月,世外乾坤”。然后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說某人預測地球將于某年某月遇險,結果當然沒有發生。他說:“不特古來想象家不可信,即近世試驗派,亦有時有錯誤者”。從他辨別偽科學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科學技術的認知是謹慎的,是經過認真思索的。
柯璜先生對中西方文化的比較認知也是其思想具有時代精神的重要體現。在“耐人研究處”一節中,他說:“中西無論何事何語,能遺傳久遠者,必可耐人研究”,說明了他對西方文化的足夠重視。他在“好一塊他山石”一節中還比較了中西方對待家產的普遍差異。他說:“英人對于父兄無依賴性,人人自立自強。畢生所得財產,酌留十之一二,余悉布施社會善舉,公私兩利。我國習慣,金錢財產,以為傳家密寶,子孫若賢,損其自強獨立之精神;不賢,增其嫖賭吃喝惡習。愛之適以害之”。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他在“子女最良遺產”一節給了自己的答案。他說:“父母德行,子女最良遺產”。他在當時觀察到的這一現象,在今天我們看來幾乎盡人皆知,然而這一問題時至今日似乎并沒有被徹底反思。
正是基于其深厚的國學、寬闊的眼界以及對世界文明的深度思考,柯璜先生大膽提出了“孔子之學必為未來文明導線”的觀點。他在“自然趨勢之來不可失”一節中說:“凡震驚歷史之偉業,一呼眾應者,皆自然趨勢之新理想潛力為之也。今日百科日新,發揚大中至正孔氏微言大義,真確偉大之道德,實合人道最新之理想。莊嚴世界,可預卜也”。他還從中國文字“點畫變化,平直縱橫,文言醞釀,含宏微妙”的特點入手,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氣質特殊”的表現,中國文字“必為他日世界高遠博雅之士,極所推重,無可復疑。東方文化,大行世界,翹首可待”。
柯璜先生之所以認為以孔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能夠走向世界,即所謂“東學西漸”,是因為孔子之學在中國存在數千年,“集古今多數人心,以最完全試驗之成績——立為公式定例。故違反孔子教化意義,即違反華人生存原則”。世界各國,如果要長期和平發展,“若不向孔子教化中,尋求中和位育之出路,無論臻如何富強,不過造人類之恐慌,造人類懸殊之階級,彼此相嫉,彼此相競而已”。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就是要通過不偏不倚、各守其分的處事原則,來實現社會有序,進而達到世界和諧。因而柯璜先生自信的說:“世界學者,正研究造福人群,安得群來取法孔子人道,傳布各洲,早開真太平、真福利氣象”。他堅信天下大同,世界和諧的時代必將到來,儒家思想是關乎“人”的學說,不僅可為華人所用,也必將造福整個人類。
《人生基礎哲學》是一代名儒柯璜先生一生智慧的結晶。他深刻領悟孔子之學,并始終保持著高度自信,對孔學的熱愛和推崇幾近偏執。他站在時代前沿,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認知,把孔子之學推向了新的高度,認為孔學是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自身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他的許多思想和論述不論在當時還是在當下,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