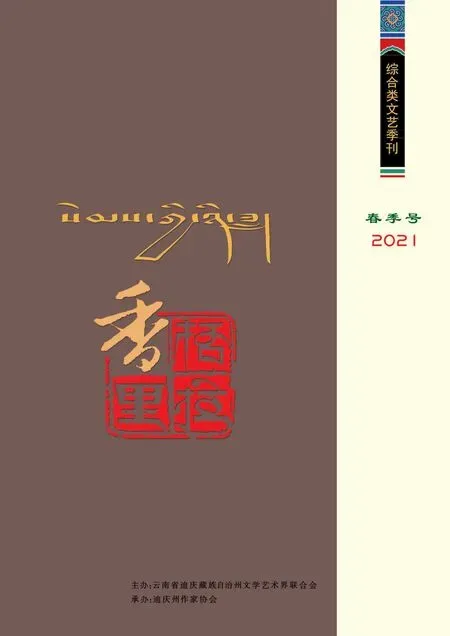遇見香格里拉的人
◎程健
遇見香格里拉的人
◎程健
作為久仰香格里拉卻初次到迪慶的我, 印象最深的還是有幸生活在這里的人。香格里拉一直是地球人向往的所在!文明越是發達,科技越是先進,文化越是豐富,人類越是向往一處文明不曾入侵的處女地,科技無法染指的地理坐標,世俗不曾污染的圣潔天堂。一時找不到就建些廳堂樓所命名之,比如全球聞名的豪華連鎖酒店集團——香格里拉;或者干脆撰寫一本書創造那樣一個人間奇幻,比如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以寄托心中的烏托邦。是的, 出發去香格里拉前,我再次讀了該書。越發羨慕能生活在地球上的香格里拉,那是多么幸運和難得!
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原名中甸縣,2001 年 12 月經國務院批準更名。許多年前,我還在香格里拉隔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工作時,曾因參加省級會議有機會與迪慶州的人同室相處一天到幾天不等。每次與初相識的迪慶人接觸幾天后都能成為很好的朋友,或者說他們都是理想的交談對象。我印象最深刻的經歷是一次省級培訓,會議安排我與一個迪慶的參訓者同屋。白天會議和休息間隙兩個人都在一起, 晚上臥談時,聽她講自己的求學、工作、生活經歷以及戀愛史。她本來有優先的機會留校發展,但是為了愛情她回到了故鄉迪慶與自己的心上人結婚生子育女。但是接替她留校的同學,或者說選擇了留校的兩個同學, 一個發展到了澳大利亞,一個去了日本。可是她馬上說:我一點也不后悔,就算我去了澳洲和日本也不會快樂,因為那里沒有我的“他”;我的他也說:就算澳洲和日本又有什么了不起,還不是在地球上,你還在地球上的香格里拉呢!哈哈!多么機智的回答。
時間過去了很久,久得我都忘記了她的名字和她當時的單位,卻無法忘記她和她愛人的對話。從此香格里拉種進了我的大腦! 我對每個后來見到的香格里拉人都預存了好感,事實也一再地驗證我的預存。這些年這種好感預存量一直在穩定地遞增。這次終于有機會來到香格里拉,更是讓我對迪慶人的好感上升到尊重,以致敬畏。像迪慶人對他們的信仰一樣,有信仰果然不一樣。
這次因工作原因來到迪慶,事先知道有人會來接我,卻沒有想到州文聯阿布司南主席會親自來。我太受寵若驚!主辦這樣的活動,作為東道主,更作為主要領導,他要操心的事太多了,最不重要的就是去機場接我。可他事無巨細,一視同仁,令我感動!所以說與人交接不是聽他說什么,是看他做什么。我初識阿布主席是在幾年前的一個采風活動中,那次活動有一場篝火晚會,晚會進行過程中,每個代表隊都要表演節目,輪到他們州, 他與自己的兩個下屬唱著藏族歌曲跳著鍋莊, 純粹熱烈而深情,和諧的舞步映著熊熊的篝火,說不上的“拉風”。人群中的我瞬間被他們實力圈粉,那個動感畫面恰似現在的電腦動圖永遠收錄在我的腦海里,碰巧遇到“關鍵詞”就會自動播放,比如現在。我們從機場到酒店的一路上,阿布司南主席不斷地給我介紹路過的景觀和建筑,談到香格里拉城市的布局和未來,口氣里都是驕傲和自信:我們整個迪慶區域環境好!雖然海拔高了點, 但是植被好,交通越來越方便,是全國機場離市區最近的城市,高鐵動車也將于明年底開通運行,屆時出入香格里拉更便捷了。別說香格里拉自己人,就是我聽了也期待那一天早日到來,那時我一定乘坐動車再來香格里拉。
到香格里拉的第二天,當地的作家詩人耶杰 ? 茨仁措姆開著她的私家車陪我去離城最近的高原濕地納帕海走走。清晨的迪慶整個隱身在重重霧靄中,我們的車子就在重重霧靄中穿行,車窗外是剛剛收獲過青稞并新翻耕的土地,肥沃、坦露;田野里隱約可見的牦牛三五成群,從容、壯碩;田邊路旁院落內晾滿青稞和其他農作物的青稞架,豐盈、誘惑。尤其是濃霧籠罩的晨曦中,晾滿青稞的架子飽滿立體像牧場或山民臨時的茅屋, 周圍是悠閑散牧的牦牛……此時此景是屬于詩人的。茨仁措姆突然說:去年也是這個季節, 我陪詩人于堅走這條路,他一路說就喜歡這樣的自然之美,這樣的風光,這樣的環境讓他激動,迎面而來的泥土氣息能觸動久違的心靈。看看,這就叫心有靈犀。只要走近給人類全部生存給養和生命的土地,看到熱騰騰的生活畫卷,無論在哪里都容易勾起我早年的生活記憶。我沒有種植過青稞,但我收割過小麥,看過老黃牛拉著犁翻耕土地,我也有過用農具手動松土的生活經驗,對土地的親近和熱愛,對農田苦累生活的記憶一齊化成淚水涌來眼眶。我真是等不及想看于堅對這土地和生命的書寫,我看過他對許多土地山川湖泊沙漠的書寫,看他的書寫最能理解什么叫與生俱來的才華,他用文學表達的能力就是。茨仁措姆接著說:不過于堅老師去年來的時候青稞也已經收割了。你知道青稞長在田里,這些土地和周圍的風光看起來更美,可惜了你現在來。好在過幾天青稞又該下種了,這里海拔高空氣稀薄,植物生長慢, 青稞幾乎是全年長在土地上……我知道啊, 世事難以兩全,如果給我選,我更愿意青稞一片金黃時和于堅老師一起坐在你的車子上呢。現在我也欣喜自己看到了休閑中的大地, 在迪慶一切都是有因果有緣起的,在這樣高原缺氧的環境里,能看到那么多高大威猛豪爽粗獷的康巴人總令我迷惑。原來是這些青稞吸飽來自土地和陽光的雙重養分,養育了康巴人的威武雄壯。
這樣撲朔迷離的半個小時后,我們到達了納帕海的湖邊,霧氣在漸漸上升,天色一點點變亮,我馬上要看到納帕海啦!心里真是激動得怦怦直跳。前一天在飛機降落的時分,隔著機窗玻璃居高臨下,看到地面是依山傍水的所在,一瞥間真是“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下來趕緊問阿布主席,才知道那是離城很近的高原濕地中的湖泊——“納帕海”,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行程。
茨仁措姆第一個給我介紹的點,湖邊有大叢美艷的狼毒花。她說,狼毒草有一定的毒性,是用來造經書紙的特殊原料之一,因為它的微毒性可以防蟲蛀,以保護經書千年不被蟲咬,也因為它的毒性注定不能用來造平常的紙張。這個季節的狼毒花紅艷如七八月份的毒菌子,你無法忽視對它的眼饞卻也不敢伸手去觸碰。在我拿個手機忙不迭地拍湖景山色,拍狼毒花的美艷時,眼睛的余光看到一輛大巴也跟著我們的車子后停下來, 大批人馬從車上下來,突然就想到王籍的《入若耶溪》中的“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他的耶溪需要蟬鳥來襯托安靜。空氣稀薄的高原納帕海連人聲都可以吸收掉,靜寂的納帕海湖邊瞬間的笑語喧嘩后復歸平靜,游人迅速散開各找拍照點位去了。我這么寫著就想起錢鐘書在《一個偏見》里說我們常把“鴉鳴雀噪”來比人聲喧嘩,還是對人類存三分回護的曲筆。常將一群婦女的說笑聲比于“鶯啼燕語”,那簡直是對于禽類的侮辱了。覺得自己有跟大師分證的不自量力。但他明說了那是“一個偏見”,何況在人類擁擠的城市, 在隔音效果不好的筒子樓里。這個“偏見” 并不算得偏見,簡直是生活的真理。而此處是天大地大空曠無垠的大山深處,是霧靄重重的高山湖泊的岸邊,熊聲豹語聽了都婉轉悠揚。有了人聲人影的湖邊平添了生機和活力。那些可遠可近的身影就是風景圖片里的動感地帶。三五成群的游人也跟我一樣一邊拍照一邊贊嘆,有人對著狼毒花叢里的大堆牦牛骨頭,猜是被什么動物襲擊后留下的…… 我聽著有趣就問:如果這里真有能襲擊牦牛的野生動物,你們還敢在這里拍照?怕不是跑得比兔子還快。哈哈!我們的笑聲驚動了正在跟大巴車司機交談的措姆,“這么快就交到朋友啦。”她邊說邊走過來。“這里是迪慶嘛!怎么聽著司機師傅在詳細地問路問景點,好像是初次到迪慶的游人,也跟隨我們興之所至的停車看景?”措姆笑得平靜自然,在我不啻驚濤駭浪……在這里真能遇到天下奇聞,我是一個人一車跟隨當地的朋友敢隨走隨停隨看,他拉著一大車的人也敢這樣沒有事先的攻略和計劃?這是對迪慶人和風景有著怎么樣的信心!寧不教人心服口服。
后來的幾天我們所有人到齊后,也是這樣一車人隨意停了看景,無論到哪個采訪地, 師傅都會跟我們說:東西不需要帶的都可以放在車上,放心!一樣也不會少,這里是迪慶!我們去香格里拉縣的尼西黑陶博物館參觀,了解黑陶的制作工藝。這種用精選的紅泥淘洗過濾晾曬后,和泥捏就的各種生活用品,燒制成功后會變成純黑色并有著金屬質感。這些黑陶生活用品在涉藏州縣非常實用并聞名,我們同車的涉藏州縣朋友無一例外都購買了各種用品。很少買易碎生活用品的我忍不住喜歡,選了一個別致的小酒壺,留下地址讓店家隨后寄來,所有在場的迪慶人都跟我保證,他們寄的一定會是我選的那個, 斷不會有其他手腳,完全可以放心。這樣對自己家鄉人的信任和肯定是得多少歲月證明。去年國慶節我居住的小區物業發通知提醒住戶:長假期間如果外出請務必關好門窗,家里不要放置貴重物品。那是“家”啊,貴不貴重都要放著,難道送物業給寄存不成?雖近荒唐也說明我們失去那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生存環境久矣。現在我買了這個用泥捏成在火里燒制出來的有著金屬光澤的小酒壺回到家后,要算得有貴重工藝品了。我長假再出去可放到哪里去呢?我要不要從現在就開始發愁?內心真是十二萬分地羨慕迪慶人,他們能生活在迪慶是多么幸運!
去納帕海的一路上,茨仁措姆給我介紹最多的還是路邊遍布的青稞架。北方的農村過去有統一的晾曬場院,專人護理,后來包產到戶,家家戶戶建有晾曬作物的水泥平臺。所以我在這里第一次見到青稞架,感覺十分新奇。智慧的藏族人家,順應當地的氣候, 把收割后沒有脫粒的青稞、苦蕎、蔓菁等作物, 碼在搭成 L 型架子的豎立面上,借助這里獨有的高原陽光和山風吹透晾干,就算是有雨, 雨也順著流下去不會讓收成受潮,很好地保護勞動成果,又節省了家里的空間或者晾曬的地面,在大山周圍,山角湖邊,寸土寸金, 實在是機智的設計。青稞晾曬好了,找個晴天又可以直接在 L 型平行于地面的架子上脫粒,架子下面鋪上塑料布,用來收集脫出的麥粒青稞粒等勞動果實,堪稱完美。
我還在前后左右地欣賞初次見到的青稞架,聽見茨仁措姆跟當地的老人開心地講藏語,我以為只是平常的搭訕,等我顧及時間不得不坐回車里才發現,那個老太太已經在車上坐著,要搭我們的車去前面的白塔處, 兩個人都體貼地沒有催我一句。現在會有多少人肯讓路遇的陌生人坐進自己的車子,我沒數據不敢妄下斷語,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會。迪慶人對彼此的信任就像他們信仰藏傳佛教一樣吧。我只能在心里再次感嘆信仰的力量! 到老太太下車,我剛好又看到此行最震撼的風景,夢幻般的納帕海邊,立著潔白的佛塔, 霧靄在慢慢散去,瓦藍瓦藍的天空浮著大朵大朵的白云,我把剛下車的藏族老人和她的同伴收進圖片里,這張圖片后來果然收獲微信朋友圈一眾圈友的贊嘆!
在后來的一處風景點停車,剛下車的茨仁措姆驚訝地發現地上居然那么多垃圾,她急急忙忙回車里拿塑料袋揀起地上的垃圾, 送到遠處的垃圾桶去;而我所有的眼睛都在湖水遠山和星羅棋布的青稞架及牦牛身上。我可以做到不在任何所到之處亂扔垃圾,但是堅持撿拾路上看到的垃圾,何況那么遠的地方的垃圾,我真沒做到過。她能快速跟公路邊農田里勞作著的所有農人用藏語打招呼拉著家常,熱烈親切像見到鄰居,我心里已經佩服贊嘆得不行。再看她能如此愛護她的環境,我就只有尊敬和仰慕!我知道自己無法看盡納帕海萬分之一的美。但是從次仁措姆的身上我知道香格里拉人有多非凡!
盡管我曾生活在怒江大峽谷許多年,對峽谷風光不陌生,也數次探訪峽谷深處,但巴拉格宗大峽谷還是深深震撼了我。隨著穿隧道、架橋梁等現代化筑路技術的發展成熟, 云南省全境內的交通條件在持續改善。像巴拉格宗大峽谷這樣上望壁立千仞下看萬丈深淵的盤山公路很少見了。膽怯或者恐高的都不敢坐在靠車窗的位置,眼睛不小心瞥出去都是魂飛魄散。別說沒路的過去,就是有路的現在,巴拉格宗大峽谷也是不容易通過的。我全程提著心,心里不斷念著佛,虔誠地祈禱著,佛教不能在這里弘揚才怪!在大自然面前,人類實在是太渺小。心中沒有佛,沒有佛法的護佑,真難想象巴拉村的村民如何生存!
是的,這樣的峽谷深處還有人居住。巴拉村過去曾經長期維持在 32 戶左右,巴拉村的村民在過去所有歲月里,走的都是那條只容一人或一馬單獨通過的,在懸崖峭壁間手工挖鑿出來的,寬只一尺半的馬路。曾經聽涉藏州縣“說古論今”的人講起當年走在涉藏州縣類似這樣的茶馬古道上,如果遇到對面來人牽著牛或者馬,或者拿著太多的東西, 都會導致無法同時通過,這樣的時候只有雙方比財富還是比體力,只有一方能活著繼續趕路。聽來殘忍卻佐證了這種路有多窄多危險。通過那條狹窄陡峭的山路,巴拉村與外界保持著有限的聯系,一般而言,嫁出去的女兒一生都沒有幾次機會再回娘家看看,有的根本就是生離;村民如果不幸有了急病想通過這條路出去求醫,熬不過五天的山路就只有死別了。我們想追問的,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經問過了:“為何不去之?”答案與《苛政猛于虎也》也許不同,但是留下總有留下的理由,走一次巴拉格宗大峽谷也許就理解了,為什么他們會留下。不但理解他們的留, 也理解了為什么有人堅信《消失的地平線》里的“Shangri-La”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就曾經存在于這里,只能存在于這里。
對許多外來人,甚至所有外來人,包括涉藏州縣的人,從巴拉格宗大峽谷的入口到達它目前公路通達的藍月山谷——《消失的地平線》里康威一行四人的飛機降落處,都要經過九死才得一生。你會被過于險峻的山路嚇死,被難以想象的急彎繞死;被驟寒驟冷的氣溫凍死;被強烈的陽光直刺曬死;被高海拔的反應折磨死;就算這些你都躲過了也會被無與倫比的風光仙死!被 5545 米高的格宗雪山醉死。等終于繞遍四季,突然看到“香巴拉佛塔”——一座天然形成的完美的圓錐形山峰(也是康威他們下飛機后第一眼看到的), 身披白雪像金字塔般巍峨聳立在天空下,所有的驚累苦怕都忘懷了。只剩下信服,相信自己真的到了“Shangri-La”——香格里拉。眼前的一切吻合得不可思議!
“你們順著我指的方向看過去:它旁邊的那座山像極了‘喇嘛蹲坐’著看前面那本打開的‘經書’,我們當地人尊稱這三座山為佛、法、僧三寶,它們在周邊的涉藏州縣也得到承認,它們就是佛祖釋迦摩尼成佛后所預言的天邊佛塔。”一路跟著給我們講解的工作人員格桑,就是這個巴拉村土生土長的孩子,現在也是孩子的父親了。他就在這個村子的企業巴拉格宗旅游開發有限公司里工作,他說過去走出去很自卑,不敢講話, 想不到有一天有人會花錢來看他們的神山, 聽他們講自己村里人的故事。他高中畢業會說漢語,普通話挺標準,也能簡單地說英語, 也許并不簡單,是他自己謙虛。反正他挺為此自豪和驕傲,藏語里有著標準的彈舌音, 他相信有機會學別的語言應該也不難。他詼諧幽默,很快跟全車的人打成一片,這種應答自如并隨時把自己拉進溶入一個臨時的集體里,讓這個臨時集體里的人都喜歡他相信他,就算是沒有專業的培訓也經過長時間的實踐了。
投資修通這條盤山公路的人就是從那條老山路走出去的孩子,現在是這個導游格桑的老板,是巴拉格宗旅游開發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因為修了這條路而走進了央視的《朗讀者》欄目,從而廣為人知,不但他自己被人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的巴拉村、巴格拉宗大峽谷和地球人都在尋找的“Shangri-La” 都被世人知道了——他叫斯那定珠。關于他修通這條盤山公路的故事,就像這條盤山路本身一樣,百轉千回,千難萬險。關鍵是他 13 歲從峽谷深處走出去闖蕩,對外面的世界所知寥寥,也沒有正規的學校教育,卻能靠自身的勤奮和天才經營能力擠身千萬資產富翁的行列。只能說是神山給了他靈氣,佛祖一路護佑著他。他在擁有了幾千萬的資產后, 動念回鄉修路,以一己之力協調說服各方關系,籌措資金修通村子通往外界的路,讓車子開進村邊開進家門口開到“格宗神山”的懷里。
我們沿著他修通的公路從“藍月山谷”到了巴拉村的老村寨,我相信這里就是當初Shangri-La 寺廟所在地。沒有公路的過去, 從那里要翻越非常陡峭的“半馬路”。村子中間有一山泉從村背后的山上湍流而下。看著這樣容易有的泉水,就理解為什么書中的Shangri-La 寺廟里那么容易修建有現代化的衛浴設施。老寨家家院落和窗戶都正對著巴拉格宗的最高雪山——格宗神山,你沒辦法不承認這里的仙境奇緣。格桑說:每當晨曦的霞光照耀到格宗雪山的山巔,整個神山呈現出金色光芒,太壯美了!他晃著頭微閉著眼先自陶醉著,我知道他為我們遺憾,因為我們并不能在這里留宿。就算留宿,神山要不要露出他的真容和佛面,也要看來人的佛緣。他拉著我到斯那定珠 13 歲前居住的老宅的客廳,現在這里是巴拉村歷史陳列館,指著墻上一幅日出時分的格宗雪山照片說:就是這個樣子,只是再好的攝影也沒有眼中看到的壯觀。這個我知道,我這一路都想把自己看到的拍下來,但是無論怎么努力呈現,都只是萬不及一。這就是為什么每個人都必須千山萬水地自己來。有些東西只能自己看自己經歷自己感悟。
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所描繪的藏族村莊寧靜祥和,在公路修通以前, 這里擁有的豈止是寧靜,那真是亙古的萬籟俱寂!
其實誰不說自己的家鄉好,何況迪慶的區域發展前景那么好!但是在平均海拔 3000 多米以上的雪域生存,其甘苦自知,說心里話,我們平原來的人真的隨時擔心高海拔反應,可是他們習慣成自然,甚至甘之若飴。我們全程遇到的每個迪慶人都那么熱情奔放, 既容易打開自己也容易接納感染別人。正是每個迪慶人讓迪慶成為香格里拉。
程健 女,文學創作二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云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作家協會,任《文學界》雜志編輯。1995 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在國家級、省級等報刊、雜志發表了大量的散文和文藝評論作品。2013 年出版個人散文集《情迷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