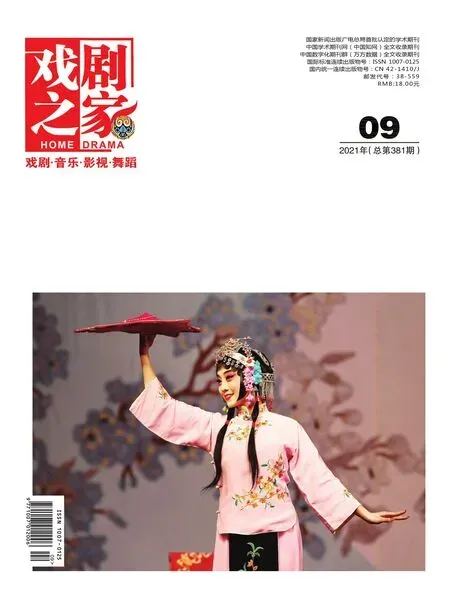巴赫金復調理論下的《安魂曲》
(云南藝術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復調”本是音樂術語,指具有兩個及以上聲部且各聲部都有自己的音調并與其他聲部相互依托,缺一不可的音樂,將這些聲部結合起來便形成了具有藝術效果的多層次整體。20 世紀20 年代,巴赫金在其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1963 年修訂版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首次將“復調”這一概念引入文論,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復調”結構,形成了“復調”這一新的文學理論。
復調小說理論主要是通過眾多的聲音形式體現出不同的思想意識,它們相結合后形成具有嶄新思想的立體式、多層次的整體結構,能更進一步體現作品主題。復調理論以對話為基礎進行建構,多聲部性、對話性和未完成性這三大特征相輔相成,互為裨益,增加現實感與復雜度。蘇聯學者索列爾金斯基提出:陀氏的創作“可以被看成戲劇的交響樂,因為戲劇有表演的過程和行為,戲劇中存在的不是一種而是幾種相互斗爭的人的意識,所以是多主體的交響樂。”復調小說理論雖然是基于陀氏創作提出的,但這一理論也存在著移植于戲劇創作、批評的意義。以色列卡梅爾劇團的話劇《安魂曲》就是一個可以用復調理論進行分析的典型戲劇作品。
以色列版《安魂曲》根據契訶夫的《苦惱》、《洛希爾的提琴》、《在峽谷里》三個短篇小說改編,是以色列偉大的劇作家、導演、詩人漢諾赫·列文患癌后在生命的末年所創作出的話劇。劇本以鄉村老棺材匠為核心,以他的行動串聯起了三個關于死亡的故事,與觀眾共同去探索生與死的意義。復調理論的多聲部性、對話性和未完成性在《安魂曲》中得到了完整貼切的體現。
一、多聲部性
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復調理論中的多聲部性主要指不同主人公發出的不同聲音,并通過“對話”來實現,這些對話平行展開,且沒有權威的控制性的聲音來主導。眾多平行的聲音構成不同的聲部,體現出不同的思想意識,將其結合后形成的具有藝術效果的多層次整體能夠更進一步體現、深化作品的主題。
三個看似并無聯系的故事,因為“死亡”這個繞不開的主題而聯系在了一起。面對死亡,人都感到了巨大的空虛和無所適從——不知自己從何處來,不知自己應當做些什么來擺脫這種恐怖的空虛,但是卻又在生命的推動下不得不行動。棺材鋪的故事、洗衣房的故事、馬車夫的故事三線并行鋪展,構成平行且平等的三個聲部,在這三個聲部進行演奏時,還穿插著赤腳大夫、馬車上的乘客和死亡天使的部分做間奏。
三個聲部都在發出對生命無力的拷問:母親發問孩子來到這個世界忍受這樣的痛苦又回去是為了什么;馬車夫多次開口想要談論兒子的死,因為他已無法忍受;老棺材匠笑稱死亡從理性而言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隨即卻大喊“雖然這想法是正確的,但無論如何還是痛苦的”。劇中乘馬車在兩地間來回的妓女與嫖客間的對話作為穿插在主要聲部中的間奏,也充滿這種無力:他們為了生存掙扎,被欲望驅使著徒勞奔波,同時又清楚自己終歸黃土;憧憬著想象出來的“巴黎”,談論著形而上的“必然性”,卻又永遠會回歸到“那話兒”還有死亡。醫生也是無力的,“真心發出的話語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他只能麻木地開著自己都知道沒用的處方。連那些穿得滑稽破爛的天使都是無力的:他們試圖給將死之人帶來短暫的歡笑與安慰,可卻總是徒勞。這些間奏,給各聲部增添了或詼諧調笑或冷漠荒誕或溫暖慰藉的色彩,呼應著“安魂曲”這一主題。
《安魂曲》中每一條線都是一個聲部,在同一個主題下每一個聲部發出不同的聲音,聲部間又有間奏加強張力,各個聲部組成合奏應和主題,這些聲部發出的聲音共同構成了“安魂曲”的合奏。
二、對話性
“對話”是巴赫金在復調理論中著重強調的部分,是不同意識存在、碰撞、沖突的基礎,巴赫金理論中主張多重獨立的聲音相互交流。“對話性”包含著四種對話關系: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自我”與客體的對話;不同思想者間的對話;創作者-主人公-觀眾的對話。《安魂曲》中對此也有明顯的體現,劇中對話充滿詩意,和大多數戲劇不同的是,這部戲看起來不像正在發生的劇情,更像是劇中人在另一個時空向觀眾講故事,或者說更像是一場交流。這正是復調理論中“對話”的呈現。
其一,自我與他者間的對話模式是最常見的,在劇中棺材鋪里老頭和老太太的對話,在醫館里老頭和十九先生的對話,老頭與姑娘的對話等等,都是這一類的對話。
二是“自我”與客體的對話,即人物的主體意識中不同思想的對話,表現這類對話往往是通過人物的獨白,老人與他的客體的對話就是通過這種形式:
老人:在路口……我沉浸在思考中,算了一筆賬,發現從死亡中我得到的只會是不錯的收益:不用吃飯,不用喝水,不繳稅,不會冒犯別人。因為人躺在墳墓里不只是一年的事情,而是成百上千年,所以可以知道從死亡中我渴望得到豐厚的利潤。生命等于損失,而死亡等于利潤。雖然這想法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這還是很壞的,痛苦的:為什么引導這個世界的是這么一個規則,生命只給人一次,兩手空空地就過去了。
而抱著孩子的姑娘從形式上說是借助與老人的對話最終找到了“自我”與客體對話的途徑。
老人:(在她面前站了片刻,不知道該做什么,觸摸她的臉頰)喏,我撫摸了你好讓你能哭出一點來。(停頓,她沉默)要是你哭出來,你會輕松些。(停頓)
母親:要是我哭出來,大叔,這世界就會輕松些。他們就會說:“是有不公,可是也有解脫。”我不要哭。要是他們問我:“你從沒有站在哪個十字路口嗎?”我就回答說:“我站了。在一個黃昏,我站在我孩子的墓前,我可以哭泣也可以沉默,我做了選擇。”
年輕的母親在完成了“自我”與客體的對話交流后她的思想也發生了改變:
母親:我的孩子!……誰說幻覺是謊言,我們的生活才是謊言,這個世界才是謊言,真實的世界是閉上眼睛的時候創造出來的,當你不能再向世界睜眼的時候,真實才在那里。
對話性中的第三類對話是不同思想者間的對話,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后,對于解釋事件的本質有著直接的促進作用。劇本中有最明顯的有兩處:
老人:一個問題。怎么會?大夫,我怎么會知道你要說的是什么?而你也知道我要說什么?我們從來沒發出過一句沒有料到的話,發自內心的東西……
十九先生:是……發自內心的東西是另外一個問題。發自內心的東西,眼角的淚珠這需要條件,這是特權,不屬于我們。
老人和醫生的這段對話,使觀眾突然意識到,原來醫生并不是完全陷入“醉”的狀態的。“醉”是他所選擇的生活模式,正如老人選擇了將生命的一切都以支出和盈利劃分。而令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正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的本質。
另外一處是老人告別醫生,回家等死時跟車夫的對話:
車夫:還在笑……
老人:讓她們笑吧。她們還不知道:在我們的世界里笑的意思就是還沒哭。
車夫:只要……(停頓,妓女們睡著了)
正如魯迅先生所寫“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這里的對話關系并不是表層的老人與車夫間的對話,而是他們與妓女間的對話關系。妓女們爆發出無意義的笑聲,又在一句話的時間內睡著,這是生者的空虛;兩個踏在生死交界的人苦悶卻無可奈何、無處可說,這是將逝者的空虛。
《安魂曲》本就是漢諾赫·列文作為一個將走之人對生命、對死亡的反思,將其搬上舞臺也正是創作者、角色、觀眾間對話的方式。契訶夫本就是描繪小人物、描述庸常的大師,而列文舍棄契訶夫筆下人物的姓名,讓這痛苦來得更日常也更震撼,每一個人都是一類人的符號,他們的不幸是人間的不幸,他們的苦難是世間的尋常。
與劇本信息一同傳遞的還有舞臺信息,如舞臺布景、燈光、音樂等都是創作者向觀眾傳遞的信息。舞臺非常簡潔,背景只是幾塊不同顏色的幕布和簡單的燈光,卻構成極美的意境,仿佛夢中才有的景色,短暫卻使人過目不忘。在老人等車的路口,一個演員提著長桿輕拍,簌簌抖落的雪花輕輕落在老人的頭發肩膀;劇末一個演員手舉飛鳥,從舞臺左端緩緩走向右端,與此同時開啟幕布的天使又徐徐拉上幕布。劇中的音樂也始終是寧靜悠遠的,尤其是老婦死去時和孩子母親在原野上奔跑時的歌聲,仿佛母親在哄孩子睡覺時哼唱的搖籃曲一樣溫和,觀眾在欣賞演出時或許會感覺到正是這部作品本身成為了那個在生命的虛無之中似乎有意義的、可以抓住的東西。這種創作者傳遞出來的且被接收到的信息,正是創作者、角色和觀眾間的對話。
三、未完成性
巴赫金在復調理論中倡導參與主體的對話和平等,他認為具有獨立意識的角色是具有不定性的,正是因為這種不定性,才能夠體現角色結局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正是不同的角色“人性”的體現,劇情不斷地發展,角色也隨之發展,“人性”不會到達終點,未完成性也由此體現。在這部劇結束的時候,棺材鋪的老夫婦和年輕母親的孩子都去世了,但是馬車夫和年輕母親的生活還在繼續,他們的生活會是怎樣呢?他們不僅是角色,也是存在于社會意識中的有獨立意識的人,他們會不斷地變化,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掙扎,也不斷爭取,不斷地延續自己的生命。
角色是作者創造出的獨立的“人”,角色的思想是與作者的思想平等存在并進行對話的,這種對話不會結束,關系也無法終結,并且是普適于任何時代的,只要人類仍在關注對話中探討的問題,那么未完成性將一直存在。
用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來分析《安魂曲》這部劇,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切入視角,讓我們從更哲學的角度來進行欣賞與反思,并主動加入創作者創造的對話關系中。借鑒復調理論來進行創作也可以豐富戲劇的形式,加深我們對戲劇的理解,戲劇能夠從文學理論中汲取養分,且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