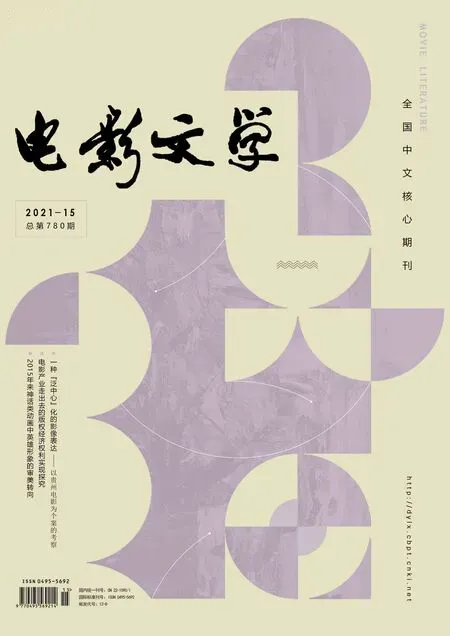中國主旋律電影對延安影像的再書寫
王 坤 王高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
延安文藝在20世紀的中國文藝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上與蘇區文學、“五四”文學,下與“左翼”文學有著緊密的聯系,又與“十七年”文學有著交集。何為延安時期?學術界對此有兩種定義:一種觀點認為,1935年10月長征順利結束后黨中央抵達瓦窯堡至1948年黨中央離開陜北的十三年時間;另一種觀點認為,1937年黨中央建立政府至1947年黨中央離開延安的十年時間。艾克恩在《延安文藝史》一書中將延安時期定為第二種,在該篇論文中,同樣以第二個時間段(1937—1947)為主論述。
延安文藝指“以延安為中心,包括陜甘寧邊區的革命文學藝術,是真正的人民文藝”。延安影像作為延安文藝的種類之一,它用拍攝照片視頻的方式見證中國的新生,延安影像成為新中國變遷的載體。不論是何種文藝作品,都無不表現出延安精神,同時展現出與國統區不一樣的精神面貌,影像中呈現出不懼困難犧牲、艱苦奮斗、為人民服務、與人民群眾緊密相連、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一、延安影像與延安文藝
延安影像作為我黨影視的起步點,在內容的呈現上煥然一新,但由于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技術缺乏,很多影片已散失,比較幸運的是留下眾多電影劇照和小部分影像素材,從保存的影像中依舊可以窺探出延安影像的新變化。
人物在影片中占據重要部分,抗戰影片同樣如此,在偽滿洲國影片中人物懦弱,受到眾多勢力欺壓,是日本統治下的“東亞病夫”;國統區中人物大多選取資產階級,底層民眾的形象不符合社會生活,但與“偽滿洲國”不同的是國統區電影中人物敢于反抗,不再懦弱,如《八百壯士》(1938),不足為影片中大多在歌頌某一階層,對于底層勞動人民的拍攝極少,人物刻畫范圍極其狹窄。
與偽滿洲國、國統區電影人物形成鮮明對照的為延安影像,延安影像體現軍民一家親的思想。如《邊區勞動英雄》,在這個故事中導演陳波兒將重大歷史事件融合在一起。以農民勞動英雄吳滿有翻身致富為線索,展示出在陜北,延安軍民共同保衛邊區的故事。故事的選取建立在真實事件之上,當時的延安由于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又是日本侵略者著重進攻的地方,國民黨對其實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等多種舉措,延安與陜甘寧邊區出現了極大的經濟與糧食危機。毛澤東主席曾在之后說道:“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迎向困難,進行大生產運動。影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以大生產運動為背景,以八路軍在三五九旅開墾南泥灣為素材。影片中人物選取人民軍隊,但巧妙的是并沒有將軍隊置身于戰火之中,而是將其置身于農田,展示出人民子弟兵“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思想,更能展示出自己雖處劣勢的大環境,但不怕艱難困苦的精神,塑造出“南泥灣”精神;《延安與八路軍》記錄八路軍與日本侵略者斗爭的場面,從戰斗的角度反映人民子弟兵不畏犧牲的精神;同時,在影片中展示出人民群眾對于子弟兵的支持,人民將親兒送戰場,幫助八路軍做后勤。
延安影像中所展示的人物更加全面,更加注重底層人物與軍隊的聯系,是軍如魚民如水的關系,這是在抗戰其他地區的影片中所不存在的。體現延安精神核心內涵,中華各地人民是一家,此時,影像中人物形象也有所改變,軍人人民緊密相連。
好的故事需要有好政策引導,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以來就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緊密扎根中國國情,緊密聯系群眾,實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策,延安影像在題材選取方面逐漸擴大。故事是影片的框架,可以反映時代的變遷,可以反映人物的精氣神,除卻“偽滿洲國”拍攝的《白蘭之歌》(1939)、《蘇州之夜》(1940)等,這些愛情片由日本影視公司導演,反映日本文化、價值觀,不符合我國傳統價值觀;戰爭片《黎明曙光》(1940)實質上依舊反映的是中國依靠日本才能強大,影片宣揚日本的價值觀;國統區影片以戰爭片為主,但故事較為脫離實際。在延安影像中,題材范圍擴大,《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延安與八路軍》以軍隊為大背景,展示人民軍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奮勇與敵人拼搏,在物質條件缺乏下,人民軍隊不甘于聽天由命,敢于運用人的力量來對抗自然。《邊區勞動英雄》展示底層人物在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土地革命、紅軍改編北上抗日、大生產運動政策的領導下農民翻身做主人的故事,反映農民新的精神面貌;此外,將鏡頭聚焦于國家大事,拍攝大量新聞素材,如《白求恩大夫》(1939)、《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這些都成為日后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片段。
在“偽滿洲國”、國統區內電影拍攝技術較為發達,影片中音效的使用也較為充分,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延安地區由于電影技術不發達,膠片等拍攝設備大多來源于友人捐贈。雖條件極為艱苦,但仍在不斷創新,《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首次采用聲音元素,利用留聲機、麥克風產生聲音,使用延安魯藝音樂系的留聲機、唱片;沒有電就采用手搖機發電,用兩個麥克風,一個解說,一個放音樂,《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將解說、音樂、郭蘭英所演唱《南泥灣》結合起來,使用輕快的音樂,旁白使用深沉男音,像極了南泥灣積極樂觀、不怕艱苦、就地取材的精神。
延安影像身處抗戰時代,雖然面臨眾多困難,但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在困境中尋找出路的精神,影像也不例外,通過描繪人物角色,反映人物精氣神;通過擴大故事題材,展示社會生活、人文習俗;通過聲音創新,將不怕困難,敢于戰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表現出來。
二、延安精神與延安影像
延安影像的組織雛形為1937年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抗敵電影社”。早些時期以外國記者拍攝記錄為主,用鏡頭記錄下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軍民生活的場景;記錄下了大魯藝、領導人的生活;之后蘇聯記者及越來越多的記者來到延安用鏡頭記錄下了延安的風土人情及政治生活,在此之后延安走向了國際舞臺。但此時,延安的拍攝主要以外來記者為主,在延安他們只進行單純拍攝,以拍照片為主,加之一些視頻,后期技術仍舊會回到影視行業發達區域,如北京、香港等。并且在此時,延安無專業影視行業人員參與,人們對拍攝、剪輯等影視技術認識匱乏,這一情況在更多的知識青年涌入延安后有了極大的緩解。在這批涌入的青年中就有袁牧之、吳印咸等影視專業技術人員,在黨中央的支持及專業人員的引領下延安影像逐步發展。
延安電影團成員于1938年到達延安,在之前,他們在上海等發達城市追逐自己的電影夢,因為熱愛電影,因為精神上的束縛,一大批有志之士萬里跋涉來到延安。正如何仲平寫道:“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革命的青年!”雖然延安在物質上匱乏,但是在這里卻能感受到民主自由、軍民一家親的思想,與國統區形成鮮明對比。即使條件艱苦,但眾人憑借滿腔熱情與黨的支持,于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延安電影團(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主要工作為攝制新聞紀錄片與新聞照片,人員有袁牧之、吳印咸等九人。
當時的延安電影事業與上海等發達之地差異較大,只有兩臺小型攝像機和較少膠片。事后團隊人員回憶到延安當時無電,也沒有拍攝電影的設備,電影之路極其艱難。在周恩來同志對電影事業的大力支持下,袁牧之賦予一項艱巨的任務,去香港購買攝影物資,此次購買近萬尺膠卷,開始籌劃拍攝《延安與八路軍》。此次拍攝十分順利,但拍攝結束后,由于延安無電,苦惱于無法后期制作的問題,最后只得求助于蘇聯影視人員的幫助,但不幸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此片丟失,只留下了短短的鏡頭。在延安,拍攝電影的每個階段都是重新開始、解決困難的過程,《南泥灣》的拍攝背后是重新選擇拍攝地點,開創手搖發電,開創聲音的首次運用,終于獲得新生。
在貧瘠的土地上、在缺乏技術的電影中,延安電影團眾人并沒有放棄,他們始終敢于正面困難,因為在電影的背后是中國共產黨對于電影事業的大力支持,同時,在拍攝電影中遇到的困難,都被一一化解,自強不息的延安精神在延安電影團得到了最大化的印證。
抗戰時期,拍攝電影本就是一項危險之事,尤其是在拍攝戰爭素材時,需要幕后拍攝人員深入戰爭中心,記錄真實畫面。如《記錄白求恩大夫》為徐肖冰等人冒著炮火沖向前線拍攝而成,白求恩在戰場上救助傷員,并拒絕轉移至安全地區,所以白求恩冒著炮火、不怕犧牲地在前線救助傷員,身邊、耳邊就是機槍掃射的聲音,就是在此種惡劣的戰爭環境下,拍攝也從未停止,但在此次救助中,白求恩大夫被刀割破手指,壯烈犧牲。不論是從影片拍攝,還是鏡頭里人物的選取,如白求恩大夫,他們都在親身闡釋著不懼犧牲的延安精神,他們敢與去拍、敢于去奉獻,敢于為黨、為人民付出一切。
西北電影攝影隊同樣不該被人遺忘,雖然他們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但是他們卻深入延安內地,拍攝表現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的影片《塞上風云》(1940)。該劇改編自同名話劇,講述蒙古族青年與漢族青年拋棄個人恩怨,團結抗日的故事。故事中的塞外風景攝制組選擇去往內蒙古進行真實環境拍攝,反映了內蒙古的壯麗風景、人文風俗等,但這一路上卻充滿艱辛。具體路程為重慶出發,翻越秦嶺,到達西安,北上洛川,之后進入陜北根據地,到達延安,最后到達內蒙古。這次的路線,據后來人回憶是由地下黨同志幫忙組織制定的。
出發時眾人全副武裝,但還是在洛川遇到了麻煩,在西安的胡宗南阻礙西北攝影隊的繼續前行,最后在應云衛的機智下化解,一行人終于排除萬難來到延安,他們耳目一新。“兩次途經延安,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是中國電影史上一次有開創意義的遠征。”雖然吃住都不如重慶,水里面有石子,米里面有爛米,用鹽巴下菜,住著窯洞,但是眾人卻感受到別具一格的延安氛圍。告別延安后,眾人向草原出發,由于語言不通,無法與他人交流,攝制組演員在困難條件下學習騎馬,拍攝同樣遇到困難。由于無電的原因,只能早晨、傍晚來進行拍攝,劇組人員只得順應自然,借助人力保證拍攝效果;其次是當地文化的差異,在拍攝中受到群眾的質疑,劇組人員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釋勸說;種種危險在拍攝中都有發生,但幸運的是,影片終于成功拍攝。
戰火紛飛的歲月,電影幕后人員用影像的方式闡述著自己對于國家的熱愛。如姜云川,曾在參加延安電影團之前參加過抗戰,1938年在白洋淀成功擊沉敵人的船,之后參加百團大戰,部隊休整之時,他與他所在的軍隊留在后方。正是此時,他加入延安電影團,開始識字,學習電影相關知識。姜云川是當時熱愛國家的眾多人員的一分子,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去熱愛著國家。
筆者認為延安電影團最重要的貢獻是將電影制作成功,并且進行放映,將先進思想帶給觀眾及更多的電影放映隊。在當時,上海等繁華城市的放映在黑暗影院進行播放,市民視其為高雅藝術,在延安放映隊呈現方式不一樣,為露天播放。延安電影團下設電影放映隊,進行政治性宣傳工作,隊長為余豐。放映隊經常使用蘇聯放映機,為余豐從蘇聯帶回,并且還帶回一系列優秀蘇聯影片,雖然放映條件艱苦,但是人民觀看電影的熱情卻從未消失,他們趕路看電影,下雨天冒雨看,在電影中他們感受到新思想、新政策、新世界,是放映隊的努力為觀眾打開了看世界之窗。擔任放映隊的隊員,認真對待每一次的放映工作,在實踐中總結出正確的工作方法。
熱愛國家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具有共性,那就是共同奉獻,希望國家在自己的努力奮斗下越來越好。
三、主旋律電影對延安影像的繼承與發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延安影像是中國主旋律電影的開端,在戰爭歲月中起到鼓舞人民、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延安電影團將其精神傳遍中國大地,如東北電影制片廠拍攝的《中國人民的勝利》(1951)、《泥人張》(1983)等多種類型紀錄片;21世紀,主旋律電影深受大眾歡迎,與延安影像相比,新世紀主旋律電影對于延安影像仍在不斷繼承與發展,是一個再書寫的過程。
主旋律人物角色繼承樂觀、不畏艱難、敢于戰斗的人物形象,如《中國機長》(2019)中的劉傳健在極限的條件下憑借自己頑強不屈、專業能力挽救人民群眾于危難之間,全心全意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和我的祖國前夜篇》(2019),故事中由于技術落后,對于首次電動升旗的新中國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林治遠并沒有選擇退縮,而是與他的團隊迎難而上,在克服了自己恐高的問題后,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終于成功飄揚在天安門上空。
巴拉茲表示:“每一部影片都應該有其特定的自然背景,這個背景必須對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產生影響。”同樣,主旋律電影對延安影像在繼承和發展的同時,還需要創新。
將小人物放置于時代大背景中,其一,雖然人物小,但他們是時代的見證者、親歷者。《我和我的祖國相遇篇》(2019)故事中將人物放置于核研制歷史背景下,展現高遠與方敏的愛情故事;《十八個手印》(2008)講述縣委書記在大時代潮流中為人民服務的故事,與此類似的為人物傳記電影,如《焦裕祿》(1990)等;《我和我的家鄉神筆馬良篇》(2020)中故事緊跟時代扶貧主旋律基調,將鏡頭聚焦基層,展現脫貧路上奮斗者的家國情懷。
其二,再現歷史的主旋律題材,尤其是從我黨成立至新中國建立,以抗爭為主題的主旋律影片,如《建黨偉業》(2011)、《開國大典》(2019)、《大決戰系列》。
其三,展示當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風貌。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在世界上擁有話語權的國家,展現中國敢于擔當的面貌是影視人的責任,如戰狼系列、《紅海行動》(2018)、《湄公河行動》(2020)等,題材雖不斷擴大,但依舊展示出延安精神,雖然時代在變,但是延安精神沒有被拋棄,而是越發閃亮。
主旋律電影的結構多元化,延安影像以畫面、人物、畫外音為主,如今主旋律結構更加多樣化,《建國大業》(2009)采用交織式對比敘事結構,使用共產黨與國民黨兩條線索;《建黨偉業》(2011)結構為因果敘事,通過歷史事件的成功或失敗引起下一段故事,敘事更加多元化。
21世紀主旋律電影對延安影像的繼承與發展不僅體現在故事題材、敘事結構的變化,更有技術的大跨步發展,如聲音、拍攝、后期等。
結 語
延安影像的內容為軍民共同創作,全面而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軍民一心進行斗爭的延安精神,塑造了一代革命英雄人物,將電影發展帶入更加輝煌的明天。21世紀主旋律電影中擴大的體裁、敘事結構的多元化,都是在展示何為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從延安發源,輻射至全中國,源遠流長。延安精神是熱愛祖國,不怕苦難,不怕犧牲,團結勇敢,自強不息,這些在我們的電影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同時,延安精神體現著文化軟實力,對內對外都有重大意義,回過頭看,延安影像所建構的延安精神對于21世紀不論是電影還是政治、經濟方面仍起到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