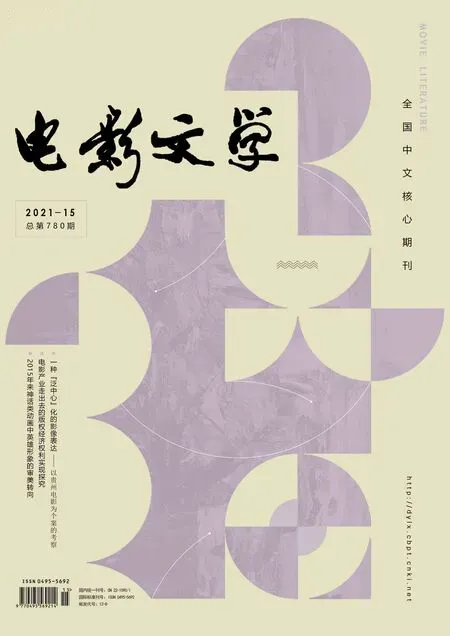罪與罰:《稻草之盾》的人性敘事
劉曉丹 (鄭州旅游職業(yè)學(xué)院旅游外語(yǔ)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0000)
近年來(lái),日本著名導(dǎo)演三池崇史不再拘泥于拍攝風(fēng)格前衛(wèi)的B級(jí)片,不斷拓展作品維度,濃縮其導(dǎo)演風(fēng)格特征,使其作品更加符合當(dāng)前商業(yè)電影市場(chǎng)的要求,三池崇史陸續(xù)推出的作品皆受到電影獎(jiǎng)項(xiàng)和觀眾口碑的雙重肯定。犯罪電影《稻草之盾》根據(jù)木內(nèi)一裕的同名小說(shuō)改編,導(dǎo)演三池崇史在保留自己的暴力美學(xué)風(fēng)格的同時(shí),著力將影片拍攝成一部指出社會(huì)問(wèn)題、諷刺社會(huì)心理、討論社會(huì)制度的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商業(yè)電影。影片主要圍繞五名警員押送殺人犯清丸國(guó)秀回東京的故事展開(kāi),在10億日元賞金的刺激下,人性的較量徐徐推進(jìn)全片的劇情發(fā)展,清丸國(guó)秀企圖利用法律自保,而每個(gè)企圖為了巨額賞金殺死他的人都有各自的隱情。
一、“罪與罰”命題的探尋與顛覆
“罪與罰”始終是犯罪類(lèi)電影的核心命題,伸張正義,懲治犯罪,幾乎是這些犯罪電影的不變的敘事邏輯。當(dāng)代日本涌現(xiàn)出多部風(fēng)格鮮明、內(nèi)容犀利的犯罪電影作品,這些電影在保留傳統(tǒng)的犯罪類(lèi)電影風(fēng)格特征的同時(shí),不拘泥于傳統(tǒng)的敘事主題,敘事主題進(jìn)一步深化與拓展,探索更多維度的主題內(nèi)容。中島哲也導(dǎo)演的《告白》用大量的慢鏡頭和特寫(xiě)鏡頭呈現(xiàn)了一個(gè)母親的復(fù)仇,人物的心理、意識(shí)和情緒統(tǒng)統(tǒng)被導(dǎo)演可視化,極富藝術(shù)美感的鏡頭之下是一個(gè)以暴制暴,顛覆法律的故事,單親媽媽森口悠子并沒(méi)因其教師身份就對(duì)兩個(gè)施暴少年加以寬恕,而是避開(kāi)法律對(duì)兩人加以徹底的懲罰。瀧本智行導(dǎo)演的《腦男》同樣將視角集中在正義、法律和人性之上,所謂的法律的正義究竟是否是真正的正義,個(gè)人行為的民間正義是否能夠代替法律的正義,罪與罰究竟應(yīng)當(dāng)以怎樣的方式處理和平衡,法律是否能夠代表絕對(duì)的公平,都在這部電影中得到了探討。
在三池崇史的《稻草之盾》當(dāng)中,“罪與罰”的命題再一次得到了深入探討。紅衣小女孩被殘殺并被棄尸下水道,而本案最大的嫌疑犯清丸國(guó)秀8年前就有相似的前科。三個(gè)月過(guò)去了,警方卻遲遲沒(méi)有偵破案件,沒(méi)能將其抓捕。警方的低效率甚至“無(wú)能”是促使這場(chǎng)殺人游戲爆發(fā)的導(dǎo)火索,擁有雄厚資本的受害者的爺爺蜷川隆興,在日本發(fā)行量最大的報(bào)紙上發(fā)表了懸賞啟事,傾盡所有財(cái)產(chǎn)舉國(guó)懸賞10億日元獵殺清丸國(guó)秀。頓時(shí),日本舉國(guó)上下陷入瘋狂,在巨大的利益誘導(dǎo)之下,馬上有人開(kāi)始行動(dòng)起來(lái),其中就包括知道清丸國(guó)秀藏身地的朋友。清丸國(guó)秀為了暫時(shí)自保性命主動(dòng)投案自首,本來(lái)應(yīng)當(dāng)對(duì)清丸國(guó)秀施加法律制裁的懲罰者和警察,卻因?yàn)槌袚?dān)將其押送東京送檢的任務(wù),暫時(shí)成為清丸國(guó)秀的保護(hù)者,當(dāng)越來(lái)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這場(chǎng)利益和所謂的正義驅(qū)使下的殺戮當(dāng)中時(shí),清丸國(guó)秀和警察的角色逐漸發(fā)生轉(zhuǎn)變。
《稻草之盾》中描述的極端事件的導(dǎo)火索是警察的不作為,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的審判是矛盾的核心。被清丸國(guó)秀殘殺的小女孩的爺爺蜷川隆興不相信警察的執(zhí)法能力,甚至對(duì)法律的制裁能力也感到懷疑,他用金錢(qián)將上下人脈買(mǎi)通,為的就是讓清丸國(guó)秀葬身荒野,一命抵一命,逃亡的恐懼感、被追殺的緊張感和死亡的痛苦感是蜷川隆興想要施加給清丸國(guó)秀的懲罰。然而礙于法律規(guī)定,警方需要將清丸國(guó)秀押送回東京審判。在押送過(guò)程中,越來(lái)越多的各色人等都為了不同的理由企圖殺死清丸國(guó)秀,越來(lái)越多的人因他而死,并且在如此極端的環(huán)境下,清丸國(guó)秀竟然對(duì)偶遇的小女孩再次起了殺心,殺人未果后甚至將保護(hù)自己的警察親手殺死,導(dǎo)演三池崇史不斷試探并摧毀人們的道德底線(xiàn),直至固有的道德觀崩塌,面對(duì)如此窮兇極惡的罪犯是否可以采取極端的懲罰,甚至脫離固有的法律限制,這也是導(dǎo)演三池崇史一步步引領(lǐng)劇中人物和銀幕之外的觀眾共同思考的。
二、人性的弱點(diǎn)作為悲劇敘事的驅(qū)動(dòng)力
三池崇史的電影中始終在探討人性的弱點(diǎn),人性中的善良、同情心、物質(zhì)欲望、性欲等都被三池崇史歸類(lèi)為人性的弱點(diǎn),在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最終成為悲劇的根源與悲劇敘事的驅(qū)動(dòng)力量。影片《稻草之盾》有悖于一般的犯罪電影,其中只塑造了一個(gè)極端的反面角色,即藤原龍也飾演的殺人犯清丸國(guó)秀,片中其他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這場(chǎng)殺戮游戲中的人,都被導(dǎo)演三池崇史歸類(lèi)為受人性弱點(diǎn)驅(qū)使的人,這也正是影片悲劇敘事的根源。
《稻草之盾》的敘事呈現(xiàn)套中套的環(huán)形結(jié)構(gòu),外層的環(huán)形敘事是10億日元懸賞追殺清丸國(guó)秀事件,內(nèi)層的環(huán)形敘事是五名“特選”的特警護(hù)送清丸國(guó)秀從福岡回到東京的事件。然而,兩個(gè)部分卻有著強(qiáng)烈的內(nèi)部關(guān)聯(lián)性,一方面五名特警要依照法律、擔(dān)負(fù)職責(zé)保護(hù)清丸國(guó)秀避免追殺,另一方面五個(gè)特警是被特選出來(lái)的,老人蜷川隆興作為幕后推手,收買(mǎi)了警察內(nèi)部的高層人員,挑選了五個(gè)有著不同背景的警察,他們有著各自的內(nèi)心創(chuàng)傷與內(nèi)心羈絆,都有不可忽視的人性弱點(diǎn),對(duì)于清丸國(guó)秀這樣一個(gè)極端的犯罪者,他們也有著模棱兩可的曖昧態(tài)度,相對(duì)于單純?yōu)榱私疱X(qián)而企圖殺死清丸國(guó)秀的那些民眾來(lái)說(shuō),這五名特警更像是老人蜷川隆興在清丸身邊安置的定時(shí)炸彈,隨時(shí)都有爆炸的可能。
無(wú)論是10億日元懸賞事件的殺機(jī)四伏,抑或是警察內(nèi)部對(duì)于清丸國(guó)秀的暗藏殺機(jī),推動(dòng)這兩條敘事線(xiàn)發(fā)展的根本動(dòng)因都是人性的弱點(diǎn),老人蜷川隆興的形象更像是一個(gè)具有上帝視角的旁觀者,在幕后監(jiān)視著、操控著,一切都在他的控制當(dāng)中,他對(duì)人性的弱點(diǎn)了如指掌,預(yù)測(cè)著事情發(fā)展的走向。當(dāng)代日本社會(huì)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占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人背負(fù)著各種責(zé)任和債務(wù),10億日元完全可以改變一個(gè)人的命運(yùn),蜷川隆興利用人們對(duì)金錢(qián)的極端欲望,驅(qū)使越來(lái)越多的人參與到這場(chǎng)所謂的正義的殺戮當(dāng)中。從福岡到東京短短5小時(shí)的新干線(xiàn)路程,從未顯得如此曲折和漫長(zhǎng),不斷有人慘死在這條路上,路上灑滿(mǎn)了血與淚。同時(shí),蜷川隆興又買(mǎi)通警察內(nèi)部管理者,精選出幾名具有正義感的警員,同時(shí)這些人又因?yàn)椴煌纳畋尘埃哂胁煌牡赖掠^,在這種極端的環(huán)境下具有懲罰清丸的可能性存在,所以這又構(gòu)成了一股潛在的力量。
《稻草之盾》的雙環(huán)敘事內(nèi)容都依靠人性的弱點(diǎn)推動(dòng)敘事進(jìn)程,接二連三的殺人襲擊導(dǎo)致護(hù)送清丸回東京的路線(xiàn)一再改變,從警車(chē)護(hù)送的高速路,轉(zhuǎn)到新干線(xiàn),再到劫車(chē),最后徒步回東京,以銘苅一基為首的特警小組從最初的五個(gè)人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人,同伴的接連慘死,清丸丑陋人性的暴露,一步步將他推向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導(dǎo)演三池崇史更傾向于將片中的特警神箸正貴、白巖篤子、關(guān)谷賢示塑造成為守衛(wèi)正義的殉道者形象,他們忠于職守,善良樂(lè)觀,剛正不阿。而銘苅一基是一名極端的法制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捍衛(wèi)者,可以說(shuō),老人蜷川隆興最初認(rèn)為銘苅一基會(huì)成為最終的正義執(zhí)行者,會(huì)在自己悲慘過(guò)往的驅(qū)使下殺死清丸,然而他卻捍衛(wèi)了自己的道德底線(xiàn)。影片結(jié)尾處,銘苅一基在道德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的掙扎,自己與自己人性弱點(diǎn)的博弈,將全片推向了高潮。
三、人性之惡的具象化與敘事張力的生成
《稻草之盾》塑造了清丸國(guó)秀極端的惡人形象,他出獄不久就再次殺人——將小女孩虐殺后殘忍地棄尸下水道,他看到美好的人和事物就想親手摧毀,對(duì)生命絲毫沒(méi)有敬畏感。影片幾乎將他人性中的惡淋漓盡致地呈現(xiàn)在銀幕之上,從影片開(kāi)始處他殺死朋友,渾身是血地出現(xiàn)在警察局門(mén)口,就奠定了影片的暴力基調(diào)。他仰仗法律機(jī)制不會(huì)馬上被審判處刑,在被護(hù)送的過(guò)程當(dāng)中不斷地挑釁周?chē)鷮?duì)他虎視眈眈的人,當(dāng)這些刺殺他的人被保鏢特警一一就地正法時(shí),他發(fā)自?xún)?nèi)心地狂笑,強(qiáng)烈地激發(fā)了他內(nèi)心的嗜血本性以及對(duì)于生命消逝的變態(tài)快感。他的內(nèi)心絲毫沒(méi)有憐憫之情,特警神箸正貴在列車(chē)上為了保護(hù)他中槍而死,死前的神箸正貴放不下自己的家人,在淚水、不甘與遺憾中死去,清丸絲毫沒(méi)有愧疚和憐憫,反而對(duì)他的死嗤之以鼻。
在押送的過(guò)程中,清丸國(guó)秀在特警的保護(hù)下一次次與死亡擦肩而過(guò),狼狽不堪,疲于奔命,然而在這種極度危險(xiǎn)的環(huán)境下,他卻在途中企圖逃走,并再次行兇。銘苅一基等保護(hù)押送他的警員絲毫看不到清丸有悔過(guò)的意思,直至清丸國(guó)秀趁白巖篤子不備,將她擊倒并奪走她的手槍?zhuān)z毫沒(méi)有感情和猶豫地開(kāi)槍打死了白巖篤子,至此清丸國(guó)秀的人性之惡的表現(xiàn)達(dá)到了巔峰。銘苅一基無(wú)法相信一個(gè)人竟然能夠兇殘、冷血到如此地步,毫無(wú)人性可言,此時(shí)的鏡頭以超近景聚焦在銘苅一基的臉上,彷徨無(wú)措、難以置信、憤怒至極、心痛如絞等多種復(fù)雜的情緒一時(shí)間全部出現(xiàn),清丸國(guó)秀卻表現(xiàn)得冷靜平淡,似乎奪走白巖篤子的生命就像碾碎一朵花一樣輕而易舉和自然,此時(shí)的清丸國(guó)秀彰顯的人性之惡徹底顛覆了銘苅一基的世界觀,摧毀了他的道德底線(xiàn),他一度舉起槍指向清丸,此時(shí)的他完全可以順理成章地以自衛(wèi)為理由射殺清丸。雖然銘苅一基在妻子去世后在悲痛中生活了幾年,但是妻子生前始終堅(jiān)信保護(hù)他人是銘苅的職責(zé),他始終銘記著妻子的愛(ài)與信任,最終,他戰(zhàn)勝了自己的心魔,戰(zhàn)勝了自己人性之惡、人性的脆弱。
毫無(wú)疑問(wèn),清丸國(guó)秀是影片中具象化的惡,如此極端的人性之惡作為影片敘事的動(dòng)因,勾連了敘事的各個(gè)部分,影片以此為軸線(xiàn),探討了程序正義、社會(huì)貧富差距、政府官員受賄、社會(huì)不公正、人性的弱點(diǎn)等多方面的問(wèn)題。進(jìn)一步來(lái)說(shuō),清丸國(guó)秀代表的極端的惡,并非是影片唯一描述的人性之惡,在金錢(qián)欲望驅(qū)使下,對(duì)清丸國(guó)秀虎視眈眈的各色人等都從不同程度上展現(xiàn)了人性之惡。企圖殺死清丸國(guó)秀的這些人,或是在社會(huì)底層掙扎求生,或是單純受欲望驅(qū)使,或是所謂的正義感使然,無(wú)論這些人是基于什么樣的理由,奪取他人的生命都是泯滅人性的行為。警察銘苅一基有理由、有武器、有機(jī)會(huì)殺死清丸國(guó)秀,甚至在身邊同伴接連慘死,僅剩下他和清丸二人時(shí),他完全可以殺死清丸,獲得10億日元賞金,同時(shí)又能避免法律的制裁,他也是老人蜷川隆興猜測(cè)最有可能殺死清丸的人選。然而,銘苅一基卻戰(zhàn)勝了自己的心魔,最終蛻變成為捍衛(wèi)法治社會(huì)與程序正義的英雄人物。
影片結(jié)尾處,最終受到審判的清丸國(guó)秀在法庭上直言:早知道如此,當(dāng)初就該多殺幾個(gè)人了。不禁再次引人深思,遵守程序正義的結(jié)果,是在浪費(fèi)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cái)力的同時(shí),很多優(yōu)秀的、善良的、勇敢的人犧牲了生命,而審判的結(jié)果是相同的,并沒(méi)有絲毫改變。
清丸國(guó)秀雖然罪大惡極,在10億日元賞金之下成為全民公敵,但導(dǎo)演三池崇史更傾向于將清丸看作是一個(gè)引子,在一個(gè)特殊的環(huán)境之中,審視社會(huì)的不公平問(wèn)題、社會(huì)貧富差距過(guò)大問(wèn)題、低效的政府職能單位,以及扭曲的人性。縱然清丸國(guó)秀是極端的惡人,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人性之惡,成為全民公敵,但在事件過(guò)程中逐漸暴露出來(lái)的各種問(wèn)題,更令人脊背發(fā)涼,發(fā)人深省。腐敗的政府、低效的職能部門(mén)、扭曲的社會(huì)現(xiàn)狀導(dǎo)致人們一步步走向極端,究竟什么才是全民公敵?導(dǎo)演三池崇史將答案留給了銀幕前的所有觀眾去解讀。尤其是影片結(jié)尾處,老人蜷川隆興手拄拐杖御風(fēng)掙扎前行,與之相對(duì)的是手持手槍的警察銘苅一基,這極具象征意義的一幕傳遞的不僅是老人復(fù)仇無(wú)果后的憤怒與無(wú)奈,更暗指?jìng)€(gè)人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的抗衡,也將影片的戲劇張力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