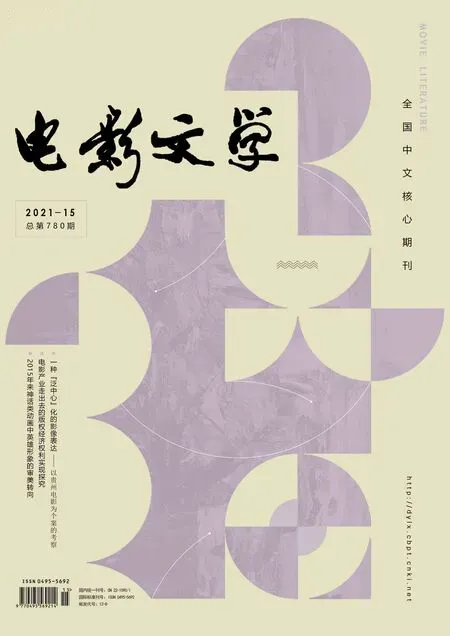詩意與超現實:慢鏡頭的觀看美學
張 清 (瀘州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慢鏡頭(slow motion,通常被縮寫成slowmo)也叫升格鏡頭,是電影攝影的一種技術手段,它通過改變正常的拍攝速度,在銀幕上呈現出動作變慢,時間延長的效果。早期這一技術的出現,僅僅只是吸引觀眾的“玩意兒”,但隨著電影工業的發展,慢鏡頭又不斷帶給觀眾富有詩意與超現實的審美震撼。
一、慢鏡頭的觀看新體驗
慢鏡頭呈現的動作如果以正常的速度展現,通常整個過程進行得很快,這樣用慢的方式表現快,其觀看性非常耐人尋味。蘇聯電影導演吉加·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
,1929)是一部集多種攝影技巧為一體的影片,其中慢鏡頭呈現的是擲鐵餅、跳高、撐桿跳、鏈球、沙灘排球、跨欄跑這六項競技體育運動,當這些動作以裸眼不能企及的速度投射到銀幕上時,觀眾不僅能看到人物舒展、優美的動作,還能看到平時不易看到的人物肌肉線條的擺動、運動員燦爛的笑容等細節。吉加·維爾托夫之所以把這六項競技運動用慢動作的方式呈現,和他的電影理念有著緊密聯系。他認為電影的主要基本功能是“對世界進行感性探索。把電影攝影機當成比肉眼更完美的電影眼睛來使用,以探索充塞空間的那些混沌的視覺現象”。每一項運動的慢鏡頭結束后,下一個鏡頭是單個或者兩個觀眾的近景鏡頭。這個鏡頭提示觀者,看的主體是這些觀眾,同時攝影機視點既是觀眾視點,但又超越觀眾的肉眼存在于時空中,“以一種與肉眼完全不同的方式收集并記錄各種印象”。眼睛作為造化的產物,天生是用來觀看的。但“人的視覺不僅意味著看見,而且還包含了對所見之物的理解,還包含了對看的行為本身的理解”。這就是人的觀看與動物的觀看最本質的區別,即動物的觀看是一種本能,目的是為了生存,人的觀看是有意識、有選擇的,人不僅能意識到自己在看,還能選擇看的內容看的方式,并且為看尋求意義。約翰·伯格在他的著作《看》中也提到“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人類具有以符號來思考的能力”。你可以訓練一只狗開車,但是你不可能教會它們看懂交通警示牌的意義。觀看需要一個過程,“‘看’這個動詞從語義上很容易解釋:‘使視線接觸人或物’”。因此,觀看過程的實現必須有一個可以看的對象,一旦視線投射到被觀看的對象時,累積在個人身上的情感、文化、記憶被瞬間帶動,觀看的意義便產生于心中。人就是在這樣的審美活動當中實現精神上的愉悅。
“美學”一詞源于希臘語,其本意是“感性之學”(aesthetics),在西方理論界,一般都把這個詞的現代用法追溯到18世紀德國唯理主義哲學家鮑姆加登。鮑姆加登用“aesthetics”這個詞為其著作命名,從而創立了一門“研究情感和對‘美’的感知的‘科學’”即“美學”。“藝術哲學本來就是根據感性知覺(感知)和我們情感性的感性特點,雙重意義上確定了感性的含義”。而人的感覺和動物的感覺又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在研究慢鏡頭時,一方面要體驗視聽畫面的直觀感受,另一方面,將感性的東西加以理性的思考,才能品味出呈現的美感。
二、慢鏡頭的視覺審美價值
蘇聯導演、電影理論家普多夫金在其文章中將慢鏡頭稱為“時間的特寫”。這是慢鏡頭給觀者最直接的視覺印象。時間仿佛被拉伸、延長,觀眾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被拉長的慢動作,原本看不到的細節被放大。隨著時代發展,慢鏡頭不再以炫技為目的,而是加入到敘事中成為影片組成部分,慢鏡頭的功效就不單是延長時間那么簡單,其中滲透的影片主題、導演的情感表達等,都需要通過觀看來體味。
法國導演讓·維果的劇情片《操行零分》中,一群寄宿學校的孩子因不滿學校非人性化的管制進而“反抗”。學生們撕破床墊,用枕頭互相打鬧,羽絨從床墊和枕頭中飛出,像雪花一樣紛紛飄落。一些學生手提自制的紙燈籠站在兩旁,反抗小英雄達巴爾做了一個后空翻,穩穩地落在了一個孩子抬著的椅子上,孩子們抬著他們的英雄開心地“出畫”。從達巴爾做后空翻開始,導演用一組慢鏡頭來渲染學生們“勝利”的氛圍。如果以正常速度來拍攝,不僅這一時刻很快流逝,而且也達不到詩意、浪漫的效果。這一詩意效果也很符合影片當中青少年的年齡特征,讓孩子們原本天真浪漫的個性通過鏡頭傳遞給觀眾。讓·維果采用了一種抒情的方式發表自己對權威的反抗和對學生敢于反抗權威的肯定與贊揚。
美國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1980年推出的影片《憤怒的公牛》,有一段很精彩的慢鏡頭組合,成功地將拳擊手的心理變化表現了出來。第一個鏡頭是杰西·拉莫塔(羅伯特·德尼羅)的對手,黑人拳擊手羅賓森的中景鏡頭,羅賓森看著鏡頭做出拳的動作,其實是杰西·拉莫塔眼中羅賓森準備出擊的主觀鏡頭。第二個鏡頭是拉莫塔的正面中近景運動鏡頭,此時的他已大汗淋漓,身體倚靠著邊繩,邊喘氣邊凝視著對面的羅賓森。和第一個鏡頭做對比,二人的氣勢、心理有明顯的變化,拉莫塔很明顯占據下風,迎接他的是如暴風雨般的拳頭。這兩個鏡頭的速度是正常速度,剪輯節奏很慢,也預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緊接著鏡頭切回羅賓森,羅賓森移動腳步,向鏡頭靠近,隨著他一記出拳,拉莫塔被打的特寫慢鏡頭和羅賓森出拳的正常速度鏡頭來回切換,這其中還穿插著正常速度的觀眾的反應鏡頭。瘋狂拳擊之后,羅賓森單人的慢鏡頭為這場比賽迎來結局,鏡頭從羅賓森的中景推到他高舉的拳擊手套上,其中還穿插著拉莫塔和拉莫塔妻子維姬的單人鏡頭(正常速度)。拳頭落下,打在拉莫塔頭上(慢鏡頭),大量鮮血緩慢地噴涌而出,落在臺下觀眾臉上。導演將慢鏡頭和正常速度鏡頭交叉剪輯,同時讓攝影機和被攝主體的距離以最合適的位置出現在銀幕上,血腥暴力的瞬間被放大,銀幕前的觀眾看到的遠比電影中現場觀眾看到的更加暴力。
慢鏡頭常常被用來延長暴力的時間,因此它也成為“暴力美學”的代表性語言。山姆·佩金法的影片《日落黃沙》(1969)中,大屠殺場景的剪輯模式堪稱暴力美學的經典,其中慢鏡頭觀看性更是意味深長。佩金法的暴力美學風格對吳宇森、昆丁·塔倫迪諾等暴力美學大師的影片造成了深遠影響。據統計,“最后廝殺的場面在短短4分30秒里集中了近乎270個鏡頭,平均每秒就是一個鏡頭。一些鏡頭持續了2到3秒”。慢鏡頭和正常速度鏡頭交替出現。通常鏡頭1是畫面中角色射擊正常速度鏡頭,鏡頭2是鏡頭1目標人物中彈倒地畫面,大部分畫面都是用慢動作呈現,也有一些是正常速度畫面。鏡頭3再回到鏡頭1中的人物,或者是另外一個開槍的主要角色,接著再開始下一個慢鏡頭或者正常速度鏡頭。經過快速剪輯,將這些鏡頭組接在一起。這樣一場長達4分多鐘的大屠殺讓人看得不免有些疲累,一個鏡頭接著一個鏡頭快速地出現,觀者一方面要緊盯畫面,避免錯過,另一方面還要承受著大屠殺帶來的視覺和心理的沖擊。盡管如此,這樣的剪輯模式已經被眾多暴力影片運用和發揚。但是《日落黃沙》最為人稱道的要數人物中槍流血的慢鏡頭,表現人物在中槍瞬間,子彈打中身體,鮮血瞬間噴出,隨即便是中彈者快要倒地,痛苦哀號的表情。這個過程帶來的效果,一是將血腥暴力擴大化,讓觀看者不得不看清楚整個過程,增加視覺沖擊力,也滿足了一些觀眾對血腥暴力場景的好奇;二是讓死亡的瞬間增添一種莊嚴、浪漫的美感。試想,如果以正常速度拍攝中彈瞬間,這種美感會被死亡的恐懼給抹殺不少。這就是慢鏡頭的觀看魅力。
吳宇森影片在風格上受到了山姆·佩金法的直接影響。這點從《喋血雙雄》中周潤發和一伙人在酒吧的槍戰戲可以得到印證。比如:鏡頭1,周潤發拿著兩把槍指著左右雙方對手,前景左下角是黑幫“老大”,中景是周潤發,后景是打手,三人成一條斜線站立,其中周潤發占銀幕主要位置,左右兩人被“逼”在角落,身體一半出畫,強調當前形勢是周潤發占據著控制權。鏡頭2,黑幫老大被周潤發的槍指著頭,槍是虛焦,主人公的臉是實焦,黑幫老大的面部神情十分緊張和害怕。鏡頭3,周潤發的反打鏡頭,周潤發的臉先是實焦,槍是虛焦。然后是很明顯的變焦,槍直指鏡頭,給人緊張、壓迫之感。隨著周潤發開槍,這種感覺得到提升。鏡頭在開槍瞬間切換。鏡頭4,黑幫老大中槍的近景鏡頭。鏡頭5,周潤發開槍射擊黑幫老大的中景仰拍鏡頭。鏡頭6,黑幫老大被打中身體的中景反打鏡頭。鏡頭7,回到鏡頭5,周潤發繼續開槍射擊。鏡頭8,黑幫老大被打中的中近景慢鏡頭。鏡頭9,黑幫老大倒在桌上的特寫慢鏡頭。從鏡頭4到鏡頭9,慢鏡頭把死亡的瞬間放大,把中槍的過程完整、清楚地展示給觀眾,將血腥暴力放大給觀眾。這和《日落黃沙》中中槍的慢鏡頭作用相似。不同的是吳宇森還把主人公射擊的慢鏡頭和對手中槍的正常速度鏡頭剪輯在一起。比如周潤發雙槍射擊從吧臺跳出的對手,鏡頭是以放慢的速度展示周潤發的“英雄本色”,鏡頭回轉是中彈者身體擺動、表情猙獰的正常速度鏡頭,導演用一慢一快兩種速度,將雙方的敵對狀態和誰“贏”誰“輸”的態勢投放在觀眾眼前。
在科幻電影中,慢鏡頭似乎回到它最原始的“吸引力”意義。美國著名學者湯姆·甘寧把還沒有建立起敘事意識的影片稱為“吸引力電影”。這類影片著重展示細節、動作,讓觀眾產生各種復雜的快感。科幻電影中一些慢鏡頭的動作毫無疑問是此類當代“吸引力電影”的例證。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黑客帝國》中的“子彈時間”。當子彈出槍時,電影中的時空被撕裂繼而又重建。一系列的動作呈現幾種不同的時間狀態。尼奧開槍的瞬間,影片中的時間處于人類正常感知范圍;子彈達到特工布朗時,影片中的時間被加速,繼而布朗的動作呈現出快的形式,不在人類正常感知范圍;尼奧面對子彈時,情形又與前者對立,影片中的時間被放慢,超出人類可感知的范圍;從空間上來看,特工布朗躲避子彈時,因動作變化造成空間層堆積疊壓在一起;尼奧躲避子彈時,攝影機圍繞他進行360度拍攝,子彈從尼奧身邊滑過,速度表現為慢速,攝影機的速度則相對快于子彈速度。時間的不統一性創造出了不同于現實可感知的空間形態。在傳統的慢鏡頭效果里,時間和空間在同一場景中被凝固下來,“子彈時間”的出現,不僅把細節放大,更為觀眾呈現超現實的視覺奇觀。此后眾多科幻電影中,類似“子彈時間”的應用層出不窮,并且也越來越多地應用在其他類型的影片中。
結 語
慢鏡頭的出現,最初只是電影創作者吸引觀眾的手段,在敘事電影還未成熟的階段,這種奇觀性的視覺效果,并不承擔推動情節發展的敘事功能。當電影的敘事越來越成熟后,電影創作者不只是看到它的奇觀性,更多的是借助這種技術的奇觀輔助敘事的連貫性,從而造成一種模糊的“藝術性”。隨著電影工業的發展,各種數字技術的進步,電影創作者又挖掘出更多潛在的可能性,慢鏡頭技術創造出的視覺效果的奇觀性又被放大和發展,它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意義。但這絕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一次偉大的創新,它讓我們看到電影的發展、進步,呈現給觀眾一次又一次的視覺震撼和心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