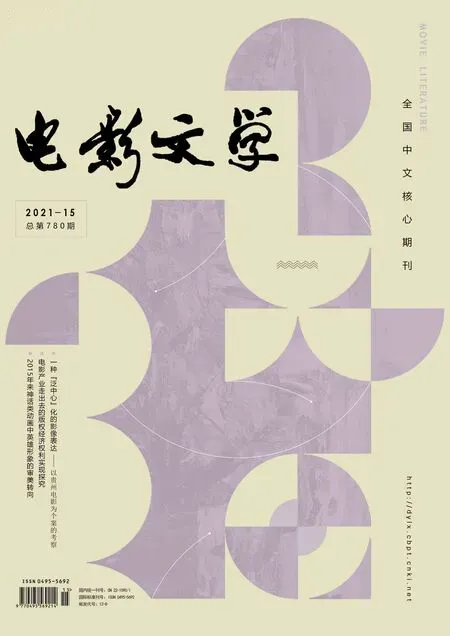中國“私影像”的藝術特色
劉 喆 (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
“私影像”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又被稱為“私紀錄片”“第一人稱紀錄片”“日記電影”等。在歐美國家,“第一人稱紀錄片”和“私人紀錄片”運用較為廣泛,而“私紀錄片”的說法則源于日本的“私小說”概念及其發展。在國內,不少學者傾向于“私紀錄片”概念的使用。相比于“第一人稱紀錄片”的稱謂,“私紀錄片”更加強調了拍攝對象、拍攝內容和拍攝空間的隱私性。日本學者那田尚史最早提出“私紀錄片”的概念,是指視覺藝術家直接拍攝自己或者記錄私人環境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紀錄片進入DV時代,更加重視主體化的表達。邊緣題材的興起,拍攝設備的便利為紀錄片拍攝提供了方便,也促進著紀錄片獨立精神的探索。2000年,王芬導演的《不快樂的不止一個》首次用主觀的方式探尋家庭矛盾根源,這具備了“日記電影”的特點。緊接著,唐丹鴻導演拍攝了首部“私影像”——《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這既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對“私影像”的重新發掘,也標志著“私影像”在中國的初步發展。2005年前后,誕生了一批始終堅持“私影像”創作的新銳導演,私紀錄片作品也呈現出井噴式增長。他們的作品有著較強的形式感和主觀性,但在價值觀的表達方面相對小眾,因而不容易為大眾所接受,更加難以進入院線。如胡新宇的《男人》、吳文光的《操他媽的電影》、李凝的《膠帶》、曹斐的《父親》等。2010年,吳文光的“草場地”工作站邀請日本“私影像”導演原一男一起探討,從此開始中國紀錄片的“私影像”自覺追求時期。2019年,陸慶屹《四個春天》院線上映,“私影像”開始進入大眾視野。
通過梳理“私影像”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筆者認為“私影像”將成為一種新的創作趨勢。一是傳統紀錄片信奉的“觀察美學”滿足了人向外看的愿望卻不善于表現人向內走的深度,這使得直接電影方法的焦慮成為創作的焦慮,“私影像”成為中國紀錄片突圍的一種嘗試。比起直接電影“作壁上觀”的美學訴求,“私影像”突破了攝像機界限的同時,也試圖突破具象和抽象、現實和內心的界限。比起純粹的觀察美學,“私影像”融入更多的主觀意識,但又傳達了紀錄片最根本的真實訴求,實現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平衡。二是隨著邊緣題材的過度挖掘,人文關懷的主題逐漸普遍化,這類題材的關注度正被逐漸消解。人們終將把目光對準自身以及同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上,而這種主觀的視角也更能引起觀眾的共情和共感。三是媒體傳播模式的改變與社會思想的變化使得人們更加關注自身并且樂于分享私人生活,這為當下“私影像”創作提供了土壤。
基于此,筆者結合具體作品,針對中國“私影像”的藝術特點進行分析。
一、主觀的視角
“第一人稱紀錄片”的命名顯示了“私影像”作品的主觀性特點。由于拍攝題材與拍攝對象的特殊性,這種主觀因素的存在并不影響紀錄片的真實性。在“私影像”的創作過程中,導演有兩重身份:鏡頭后是導演和攝像,鏡頭前則是拍攝對象或者拍攝對象的親人和朋友。正是因為第二種身份的存在,無論創作者出不出鏡都讓紀錄片帶上了主觀的色彩,他們是講述的主體同時又是被言說的對象。
(一)主觀的鏡頭語言
“私影像”的鏡頭如同導演的眼睛,影像既是他們書寫自己的材料,也是他們目光所至之處。當拍攝對象是與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人和事的時候,每一幅畫面都是“以我之眼看世界”,這些“第一人稱”鏡頭構成了最直接的主觀視角,這是鏡頭形式上的主觀性。在《夫妻不是同林鳥》中,作者將鏡頭分別對準自己的父母,父母對鏡頭的訴說和情感的流露就是對作者的訴說和情感表達。作者用目光凝視父母的同時也用鏡頭記錄下了父母對于婚姻生活的心聲。《四個春天》中父親母親偶爾會在鏡頭中同鏡頭后的導演進行交流,這種銀幕外的交流打破了鏡頭的壁壘,也增強了鏡頭的主觀性。
而當創作者把鏡頭對準自身,鏡頭就變成了心靈的窗戶,這是鏡頭內容上的主觀性。唐丹鴻在《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中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的生活,這是生活的記錄,也是內心的整理。
(二)主觀的情感表現
由于“私影像”作品的拍攝對象是作者本人或是作者私人環境中的人和事,作者的主觀情感就會在影片中或直接或含蓄地表現出來。在私紀錄片拍攝中,創作者的身影無處不在。他們中的有些人選擇在鏡頭之后拍攝,有些則選擇站在鏡頭前訴說自我。但無論是何種方式,都是對于自身或是同自身一樣的群體的情感訴說。在《家庭錄像帶》等“私影像”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在鏡頭后不斷地發問,作為一條線索貫穿整部片子。導演沒有出現在鏡頭中,但整個對話過程是在他的主觀引導下展開的,導演是隱性的發聲者。另一方面,導演作為環境中的一分子,他的發問是真實而合乎拍攝邏輯的。《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中,作者拍攝了自己與兩個藝術家朋友的生活。通過自述,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表達個人的情感。而當鏡頭轉向崔鶯與尹曉峰時,他們的生活自白也正是作者本人所試圖表現的生活與精神狀態。又如《男人》中,導演胡新宇借由朋友老蘇之口表達了對女性的看法。此外,一部分更加克制的“私影像”創作者則選擇單純用字幕、解說詞、音樂、剪輯等手段含蓄地表現主觀情感。
(三)主觀的剪輯表達
“私影像”所強調的是對于個體經驗的探索、個體回憶的探尋和個體生命體驗的記錄,相比傳統的觀察式紀錄片,“私影像”創作者在后期剪輯方面有了更多的主動性。在敘事邏輯的安排、節奏的控制、蒙太奇手法的運用等方面創作者能夠融入更多的主觀意識。《四個春天》全片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線性的敘事展開,四個春天依次鋪敘。但在姐姐因病去世之后,原本的時間線出現斷層,倒轉回20世紀90年代,姐姐再次出現在影像之中。這種時間重構的安排打開了觀眾情感的閘門,也從側面體現了創作者對姐姐的不舍與懷念。從《四個春天》《夫妻不是同林鳥》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私影像”創作者不約而同地選擇將過去的家庭錄像帶剪輯進自己的作品,這種做法使他們的作品更加豐滿完整,也表達了他們對過去對家庭對自我的一種態度。新舊素材的對比能夠直觀地展示時間的厚度,這得益于“私影像”創作者們豐富的素材積累。李有杰用6年時間創作《阿佬的村莊》,其間數次更名,幾度更改片子的結構。整個創作過程也是李有杰不斷認識自我、認識家人、認識家鄉的過程。這種對素材的選擇和剪輯,直接地反映了創作者的生活旨趣與表達訴求。
二、真實的介入
不同于其他獨立紀錄片的沉浸式創作,“私影像”創作者面對的是原本就很熟悉的生活,因而拍攝者與他的拍攝對象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密。一方面這種親密的共謀關系是真實存在的,另一方面創作者也力求主觀與客觀的平衡,選擇性地介入和干預拍攝對象,這使得“私影像”作品具有更加鮮活的靈魂。
(一)觀察式的拍攝
魏曉波的《生活而已》系列拍攝了其與女友從畢業同居到結婚之后的日常生活。生活小事和日常對話堆疊在一起,創作者試圖告訴人們,這并不是一部紀錄片,這就是生活。鏡頭像一只眼睛,代替他本人審視他的生活。這種拍攝手法使創作者暫時抽離自我的身份,以一種相對客觀的視角觀察自我和生活,使作品真實逼人。自述式的“私影像”是面對鏡頭的自我觀察和剖析。當鏡頭對準生活中的其他人,創作者使自己自然地融入私人空間中,且無須擔心在鏡頭之前暴露自己。《四個春天》中,作者用鏡頭深情地凝視父母。母親哼著小曲做飯、踩著拍子縫紉和即興唱山歌跳舞;父親用電腦學習歌曲、翻看影集、演奏樂器;而作者大部分時間則在鏡頭之后安靜地拍攝。這種觀察式的拍攝并非完全地不介入,而是一種自然的交流。作者很少出現在鏡頭之中,但并沒有隱匿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通過自然的介入實現真實的傳達。部分中國“私影像”創作者深受直接電影的影響,有刻意淡化自身存在痕跡的嫌疑。在“私影像”創作中,觀察式的拍攝是“私影像”創作者認識自我和周圍環境的另一新奇角度,創作者實在無須刻意隱瞞身份。此外,這種觀察式的拍攝得到的結果是狀態的記錄多于可組成故事的事件。“私影像”創作者普遍的觀點是希望通過真實的深度狀態記錄表現某種私密的情緒。相比之下,事件的串聯是否能夠構成完整的故事、乃至表達某種主題是不重要的。我們看到的“私影像”作品大都呈現出一種散文式的敘事。盡管“私影像”作品普遍按照時間順序鋪陳敘事,作品的故事完整性和連貫性仍是較弱的。
(二)平視的敘事角度
“私影像”創作者作為故事的參與者,視角是受限的,故事在創作者自我探尋的過程中不斷地展開。在未來不可預知的語境下,作者與拍攝對象、觀眾的視角是平等的,這種平視的敘事角度使“私影像”作品保持了一部分的客觀性。傳統紀錄片為了維護真實性總是避免穿幫,避開鏡子,不讓被攝者看鏡頭,營造一種攝影機不在場的假象。而自我反射式的電影把拍攝過程展示在觀眾面前,把判斷真實的權利交還觀眾。《家庭錄像帶》中,作者在鏡頭后發問,觀察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反應,嘗試尋找父母多年前離異的真相。父母、弟弟作為當事者,對當年的事件認知不一,使《家庭錄像帶》成為一部紀錄片版的《羅生門》。創作者本人是當事者的同時也是提問者與觀察者,在主觀參與的同時也在客觀地觀察。雖然過去的真相難以呈現,但在平視的敘事角度下,每個家庭成員的主觀反應共同構成了客觀的現實存在。美國學者林達·威廉姆斯認為,“真實沒有被‘保證’,無法被一面有記憶的鏡子透徹反映出來,而某種局部的和偶然的真實又始終為紀錄電影傳統所回避。”紀錄片中單純的客觀真實難以成立,主客觀同時存在才更接近生活的原貌。不同于傳統紀錄片極力避免主觀意識的參與,當“私影像”創作者將鏡頭對準自己的生活,向觀眾坦白一切,就實現了一種真實的介入。中國“私影像”創作者多采用平視視點的線性敘事,堅持維護“私影像”的紀錄片底色。日本“私影像”創作者的創作思維則更為大膽。他們敢于虛構,甚至突破了紀錄片這一體裁的邊界,將自我記錄與其他電影體裁相結合,呈現出濃厚的實驗電影特點。
(三)赤裸的聲畫
紀錄片一貫追求真實,而“私影像”則將真實銳化了。褪去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人際交往偽裝,“私影像”展現出一種近乎赤裸的聲畫。胡新宇在《男人》中曝光了兩位密友的隱私生活。在鏡頭里是雜亂的布滿啤酒瓶的房間,充斥著男人們關于女人的尖銳直白的談話。這些直接而裸露的聲畫使《男人》一經面世便引發極大爭議。一是因為《男人》不追求“詩意或者藝術的德行”,暴露了赤裸的人性;一是因為過于真實的影像或許不是觀眾需要的而是創作者所追求的。這種赤裸裸的聲畫正是真實介入的結果。鏡頭曝光的不只是被攝對象的生活,也是導演本人的生活。因此,攝像機可以沒有阻礙地進入私人空間,窺探到客觀存在而又不顯于世的畫面,這是空間世界的真實介入。影片中的對話不僅反映了拍攝對象的觀點,同時也是導演裸露的心聲,這則是內心世界的真實介入。
中國“私影像”創作者們大多關注自身和與自身一樣的人,他們的創作靈感也都發源于此。他們關注自我成長的地方、關注家鄉、關注日常的生活瑣事,如《阿佬的村莊》《俺爹俺娘》《生活而已》《老張》《四個春天》等;有的關注自身成長傷痛、暴露痛苦希望得到療愈,如《不快樂的不止一個》《日常對話》《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家庭錄像帶》《哀牢山的信仰》等;有的關注社會中同自身相似的群體,借世俗小民之口表達對社會的看法,如《男人》《最后的棒棒》等。同日本“私影像”選材相似,中國“私影像”不只是對日常生活的記錄,亦有暴露自我、記錄人生絕境的作品。但相對而言,在暴露的尺度上,中國“私影像”創作者始終是有所保留的。這種區別或許緣于中日兩國對家庭與個人認識的文化差異。比起對日常生活的記錄,日本“私影像”創作者更傾向于暴露禁忌。這與“私小說”在日本的風靡是分不開的。
三、內心的傳達
(一)以自身見他者,個體引發共鳴
“私影像”不僅是創作者的一幅自畫像,從更深層次來看創作者更像是一個典型人物和一個窗口。一個典型人物是指創作者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他的身上既存在個性的部分也必然存在共性,即最根本的人性。“私影像”則善于暴露人性。觀眾會因為人性的陰暗面的暴露而感到不適,同時也會因為人性中的閃光點而產生共情共感。如《父親》中表露的父女溫情,《四個春天》中所傳達的詩意達觀的人生態度,《治療》中作者對母親的深切思念等。這些個體的情感蘊含的能量是巨大的,能夠引發社會的共鳴。“私影像”創作者又是一個連接個人與社會的窗口,而窗口必然是雙向的。以自身見他者,他者也將以此見我。觀眾透過這個窗口能夠看到作者內心的表露,創作者透過這個窗口實現與自我的對話;社會透過這個窗口看到真實的人性,創作者透過這個窗口探尋社會與自我的真實距離。
(二)聲音承載內心情感
聲音是電影中最直接的情感載體,對“私影像”來說更是如此。一部分“私影像”導演選擇將自我的聲音化為環境音的一種(如《生活而已》系列、《四個春天》《家庭恐懼》等);一部分導演引導拍攝對象發聲(如《家庭錄像帶》);一部分導演選擇借由同自己相同的群體發聲(如《男人》);一部分導演則選擇自己面對鏡頭講述內心故事(如《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在一部影片中,導演有時會結合多種方式表達觀點,抒發情感。在紀錄片《最后的棒棒》中,導演何苦也作為拍攝對象之一參與其中。除了同期聲之外,大量由何苦親述的畫外音將紀錄片的片段章節聯結起來。何苦的自述與畫面相互補充說明,又填補了一些信息的空白,細微之處的描述生動真實。《最后的棒棒》給了“私影像”創作者以啟示:或許我們可以吸收借鑒一些“傳統的方法”(格里爾遜式的解說記錄)。在“私影像”創作中,創作者本人的畫外音和解說詞也許能夠讓內容更充實,使作品更貼近觀眾也更貼近創作者自身。
(三)隱喻的手法
“私影像”創作者為了到達意識的彼岸常常要借助隱喻的手法。隱喻的手法包括隱喻的語言、隱喻的空間和隱喻的意象等。唐丹鴻在《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中有這樣一段自白:“生活還在繼續,在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我看到了我的宇宙,看到了地獄在我里面,看到了五顏六色的霧靄和光芒,看到了一只紅色的受傷的大鳥想起飛,看到了天堂幼兒園,生活還在繼續。”詩人唐丹鴻用詩一樣的語言向鏡頭描述著她的精神花園,語言足夠隱晦,但能使人直觀地感受到作者的心靈受到了傷害,并在自我療愈的過程中。《不快樂的不止一個》中,逼仄、清冷的訪談空間令人感到壓抑。而這種壓抑可看作拍攝對象心靈壓抑的外化。《四個春天》中,姐姐去世后飯桌留出來的座位暗示了家人對姐姐的思念與不舍。《男人》中數次出現電影《美國往事》的片段。導演胡新宇在某次訪談中坦承,《美國往事》的情節影射了片子的內容,片中的老蘇幾乎是《美國往事》男主角的翻版。隱喻的手法使“私影像”創作者找到了精神世界投射的途徑,使個人的內心世界得以通過影像直觀地展現。
綜上所述,在創作過程、表達方式及藝術加工方面,中國“私影像”導演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個人與個人表現之間不斷地探尋,每一次嘗試都旨在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主觀的視角、真實的介入、內心的傳達都是在私密語境包裹下的產物,而這種私密的表達既是個人隱秘情感的主觀傳達,同時也是小眾私密空間的客觀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