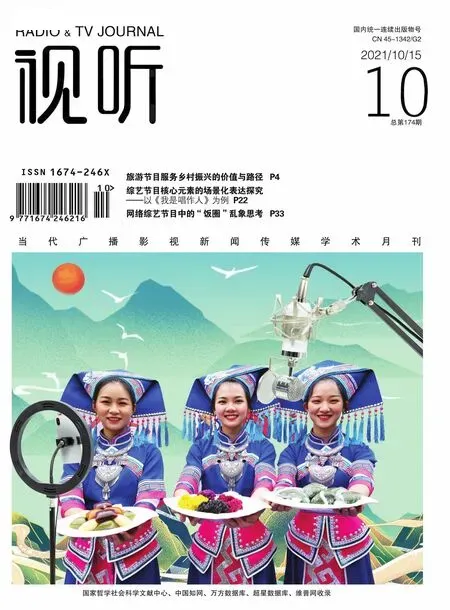活態傳承視角下“非遺”影像傳播機制研究
駱 楓 張永杰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此,要落實“以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推動傳統文化保護”的思路,建立常態化文化遺產普及傳播機制,通過“活態”傳承使“非遺”擺脫現實功效喪失、審美功能退化等生存困境。在媒介化社會日益轉向“以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的背景下,影像傳播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和手段,能夠助推“非遺”進入廣闊的社會文化領域,從而獲得全面、立體的傳播效應與價值認同。
一、“非遺”的本質及其傳播特性
(一)“非遺”的內核及其構成要素
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藝術、風俗、信仰、審美和價值觀念等深厚內涵,本質上是一種存在于特定文化空間的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然而,“非遺”在官方定義中更傾向于可觸摸的形式、實物或場所,這種誤讀易導致實踐中的“物化”行為。在哲學意義上,“非遺”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內核必然是觀念和精神,因為文化的本質只能是“觀念存在”①。因此,“非遺”中的“人造物”“文物”等是文化的產物(或附著物)而非文化本身,“非遺”保護必須將“無形”層面的觀念和精神文化作為核心,唯有如此,才能讓“非遺”具備“活態”傳承的生命力。
根據模因理論,某種“非遺”文化可解構為三個層次。其中,核心層涵蓋非物質的精神產物,包括核心理念、文化特質、價值訴求等;外在層是核心層的有形載體,表現為物質的、可提取的“非遺”元素,如題材、造型、質感等;而中間層則負責對核心層文化信息進行編碼、傳遞及解碼,將之轉化為外在的有形載體。因此,“非遺”傳承本質上是對“編碼——傳遞——解碼”程序的不斷重復,這一過程是否順利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非遺”文化元素是否具備遺傳、變異及選擇等內在特性,二是社會、經濟、文化等外在環境狀況。
(二)“非遺”的傳播特性:繼承與變異
“活態性”是“非遺”傳播的重要特征,在時間向度上表現為“非遺”的生成、傳承、創新和演化。換言之,“非遺”并非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它以現實的、動態的、不斷創造的方式構成不斷演進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盡管傳統具有內在的保守性,但會隨著時代變遷不斷變換其形式,“自從現代性到來,傳統就不再是自然意義上的了”②。同時,任何文化的傳承與延續,都不可能是純粹的、不走樣的復制,人們會根據自己的認知和信仰需求作出保護抑或改革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始終處于被變革、創造和重新建構的狀態。另一方面,雖然形式始終處于變化之中,但傳統文化的內核并不會改變,它能夠以新的形式繼續生存。霍布斯鮑姆指出,在社會迅速轉型或傳播者、機構載體發生主體轉變乃至消失時,傳統的重構或發明便會頻繁發生。根據這一觀點,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文化趨同等的沖擊下,大部分“非遺”必然會被邊緣化甚至滅亡。從實踐來看,“非遺”傳播會受到自然環境、社會認知、主體創新行為、傳播手段等因素的影響,總體上也會呈現既有繼承又有變異的特征。作為由多種模因組合而成的模因聚合體,“非遺”傳播效果往往取決于模因的結構特征、變異路徑以及復制頻率和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對那些失去了原生態環境就無法生存的“非遺”而言,最佳選擇或許就是送進博物館,因為我們不能為了保持傳統文化而要求民眾一直生活在“前現代社會”,“我們沒有辦法留住歷史、留住這些習俗,就像沒有辦法留住時間一樣”③。而對其他“非遺”來說,通過環境修整、土壤培育和形式創新為之創造新的生存空間,讓其文化內核能夠重煥光彩,不失為一種妥當的方式,可謂“理性的不理性”。
二、影像傳播與“非遺”保護的契合性
“非遺”通常以語言、技能、記憶等為手段,通過靜態的、儀式化的人際傳播實現傳承和延續。然而,這種缺乏自覺性的原生態傳承方式無力應對現代文化生態的挑戰,必須借助于新媒介手段——而“非遺”本身在全媒體、融媒體傳播中具有先天優勢——兩者可以實現一種“不完美”的“共贏”。
(一)本體性危機與傳播空間拓展
借助現代媒介已成為“非遺”傳播無法逃避的選擇,但這必然牽涉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即影像化的“非遺”是否能夠保持核心信息的完整性?顯然,種類繁多、千差萬別的“活生生”的藝術樣式,在“二次創作”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被損耗和分解,但這并不否定其影像化生存的內在價值。
本雅明將藝術品的獨特性概括為基于即時即地性的“韻味”,即使最完美的復制品也無法具備這一特性④。進入“后復制時代”,隨著藝術品的膜拜功能逐漸讓位于展示功能,其生存方式從模仿、復制轉向了虛擬,即“一個以現實之符號來取代現實本身的問題”。由此,一切現實都被符號模擬的超現實所吞噬,“藝術”似乎被蒸發了。但本雅明充分肯定了這一變遷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即現代技術手段賦予“藝術原作”以現實活力,拓展了生產模式、表達方式以及時空傳播范圍,從而使個體的“獨占玩味”演化為群體的共時性接受。因此,盡管影像化導致了一定程度的“韻味”衰竭,但有效拓展和發揚了“非遺”的新領地和生命力,這完全符合《保護公約》中的“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在一定意義上,這就是“活態”傳播的本質和價值之所在。
(二)“雙贏”之路:“非遺”的影像化生存
影像傳播之于“非遺”,是借之以傳遍寰宇、存之永恒的有效途徑;而“非遺”之于影視媒介,則是新藝術創造的源泉,更是張揚本土色彩、堅守“文化版圖”的有效策略。因此,“非遺”的影像化傳播堪稱一種“雙贏”。
一方面,雖然“非遺”不具備具體的物質形態,但其具有大量內嵌的語言和視覺模因,這些核心信息非常適于音頻、視頻、三維影像等新媒介傳播。事實上,視覺內涵建設在“非遺”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表現為視覺體驗形式隨時間推移而不斷轉換:平面化的原始巖畫——平面化與影像性交互的近代影像,集平面、影像、虛擬于一體的立體化交互性視覺造型。進入“視覺文化”時代,圍繞弘揚傳統文化這一核心議題,影像傳播和“非遺”傳承實現了雙向契合。
另一方面,“非遺”影像化存在兩個編碼層:直接意指層關乎“非遺”的本體層面,包括“非遺”項目以及被再現的表意情境;含蓄意指層則關注影像轉換的手段和技巧,如文本編輯、構圖、視角、剪輯等。對于注重“保真性”的“非遺”來說,其直接意指傾向于相對穩固,但并不排斥必要的技術處理和審美修飾。實際上,“非遺”并非是完全被動的,它與影視編碼手段是一種相互呼應、相輔相成、和諧搭配的關系。在實踐中,要避免兩種誤區:一是片面注重“影像化”而忽視“非遺”本體內涵的挖掘,導致文化深度不足;二是過度強調直接意指,但影像處理過于粗糙,無法喚起受眾的審美共鳴。
三、提升“非遺”影像傳播效應的具體策略
(一)“非遺”影像內容體系建構
作為一種工具和載體,“非遺”影像通過文本輯錄、記錄行為及影像結果來承載和傳播傳統文化信息,為“非遺”提供了更多創意、傳播和發展空間。就內容體系而言,可分為三類。(1)物質影像。作為人對視覺感知的物質再現,此類媒介具有物理層次的外顯性、符號性、具體性等特征,以手工藝類“非遺”流程與特質為主。(2)行為影像。與“非遺”相關的社會行為包括社會規范、禮儀、民俗等,有助于社區價值觀和凝聚力的形成。社會行為層次的“非遺”影像主要包括對個體行為、記憶的觀察與記錄以及基于地理位置、場所的共時性、歷時性活動。(3)心理影像。心理價值觀是“非遺”影像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旨在引導公眾實現跨時空的情感共鳴和文化認同。通過對“非遺”的深層次解讀以及信息重構,使心理影像具備超越“符號化”的人文和審美意蘊,從而實現了生態意識、生產認知、文化感知等核心信息的廣泛傳播。
(二)“非遺”影像創作理念創新
“非遺”影像是在非虛構原則下,通過對行為主體進行“深描”和理性記錄,多維度展現“非遺”的內在涵義,因此科學性與藝術性就構成了“非遺”影像的兩大基本特征。鑒于“非遺”本質是非物質的“文化”,應集合原生態素材與現代視覺理念為一體,通過要素提取、符號轉換、映像投射等程序重新建構一種立體化的影像系統,實現在當代媒介環境中的“活態”傳播。就科學性而言,必須通過充分的田野調查、符合邏輯的資料挖掘來還原真實的文化元素,以體現傳統文化的“保真性”和“差異性”。這符合“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主張,即只有“通過預先存在的各種本文化形式”才能把握歷史。“藝術性”則是“非遺”影像的靈魂,它注重發揮創作者的主觀性與想象力,通過藝術表現手段使“非遺”更加生動、獨特、富有活力。此外,要以當代視覺體系理念進行“非遺”內涵建設,從平面視角、影像記錄、虛擬交互三個緯度實現全新的動態化、互動式展示,以維護“非遺”視覺文化的內在統一性。
(三)提升“非遺”影像傳播效應的具體路徑
隨著我國“非遺”保護和傳承力度的不斷提升,“非遺”影像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創作機構和學界都要采取措施,切實提高“非遺”影像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首先,創作者要樹立正確的文化意識。在早期影視作品中,“非遺”成為文化性、審美性和藝術性的良好載體,但也出現了片面或錯誤解讀“非遺”甚至貶損“非遺”價值等現象,應引起創作者的警覺。其次,加大“非遺”影像創作力度。近年來,“非遺”題材影像作品雖然呈現快速增長趨勢,但總體數量上仍屬于“小眾”。因此,一方面,要針對不同群體創作科教、動畫、戲曲等多種類型的“非遺”影像作品,擴大受眾群體;另一方面,要通過“精耕細作”打造“非遺”影視精品,學會“講故事”“講文化”,以文化來提升故事的豐滿性、思想性和吸引力,努力做到“叫好”又“叫座”。再次,拓寬“非遺”影像的傳播渠道。一方面,要充分拓展影視屏幕、網絡流媒體、移動視頻客戶端等新媒體傳播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博物館展覽等傳統機構合作,利用虛擬現實影像技術實現全新的動態化、互動式影像展示。此外,還要加大對“非遺”影像創作與發行的政策扶持力度,破除資金缺乏、人才匱乏、“唯票房論”等因素對“非遺”影像創作和傳播的束縛。

四、結語
“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文本性”理論向我們闡釋了兩個觀點:一是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文本,人類就無法了解真正、完整的過去;二是這些留存下來的文本將再次充當文本闡釋的媒介⑤。“非遺”承載并延續著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維系著人類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也是我們認識過去的一個通道和窗口。在影像、記號和符號商品等“視覺文化”漸成主流的當下,要賦予“非遺”以全新的生命力和發展潛能,就必須借助現代影像傳播技術實現“非遺”的“活態”傳播。
注釋:
①蔡華.“文化”只能是觀念存在——關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核心概念的討論[J].民族文學研究,2015(03):47-50.
②[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紅云 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1.
③王娟.民俗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7.
④[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7.
⑤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批判[M].上海:三聯書店,1997: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