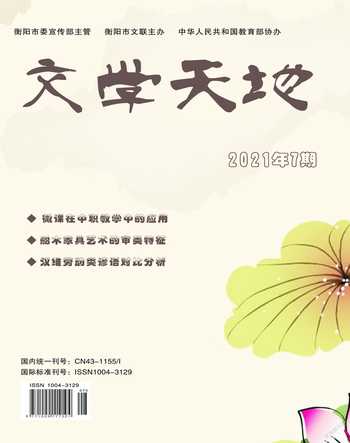明代繪畫中的耕讀精神
摘要:“耕讀傳家”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從中國(guó)古代農(nóng)耕文明的土壤中孕育而來(lái)的,耕讀文化也影響了中國(guó)的文化、農(nóng)業(yè)、制度、藝術(shù)等方面,這種精神與文化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通過(guò)對(duì)明代繪畫中有關(guān)耕讀題材的部分作品進(jìn)行鑒賞與分析,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耕讀精神。
關(guān)鍵詞:耕讀;文人;明代繪畫
一、耕讀的含義及關(guān)系
(一)耕讀,即利用農(nóng)耕之余,致力學(xué)問(wèn)的一種生活方式,中國(guó)古代一些知識(shí)分子既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同時(shí)又讀書教學(xué),過(guò)著勤苦而又恬淡的生活,他們以“耕讀傳家”為價(jià)值取向并逐漸形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
(二)關(guān)于耕與讀的關(guān)系,早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孔子就曾說(shuō)過(guò):“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xué)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意思是說(shuō),君子不應(yīng)該費(fèi)心思去求衣食,而應(yīng)該用心學(xué)道。即使你去耕田種地,難保也會(huì)有餓肚子的時(shí)候,用心學(xué)道,卻可以拿到俸祿。所以說(shuō),君子真正應(yīng)該擔(dān)憂的是能否學(xué)到道,而不是去擔(dān)憂貧窮。當(dāng)然,孔子所說(shuō)的不謀衣食并非真正地舍棄它,這句話背后所包含的其實(shí)是一種社會(huì)分工的意識(shí)。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也是同樣的道理。被孟子批判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農(nóng)學(xué)家與思想家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賢德的國(guó)君應(yīng)當(dāng)與老百姓一樣自己耕種糧食、自己做飯和處理國(guó)家大事。許行是反對(duì)不勞而食的。后世則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傳統(tǒng),一種把讀書入仕途當(dāng)作人生的最高追求,所謂“萬(wàn)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認(rèn)為其他行業(yè)都是低賤的,只有讀書致仕才是正途。另一種以耕讀為榮,提倡“耕讀傳家”,既學(xué)做人,又學(xué)謀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明末清初著名理學(xué)家張履祥在他的《訓(xùn)子語(yǔ)》中說(shuō)道:“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明確地指出了耕讀結(jié)合的重要性。
(三)古人在勞作中不斷體悟人與自然的聯(lián)系,逐漸形成“天人合一”與“知行合一”的宇宙觀與知識(shí)論,既肯定了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關(guān)系,又將知識(shí)與行動(dòng)結(jié)合起來(lái),形成了務(wù)實(shí)的作風(fēng),豐富了“耕讀”這一生活方式的精神內(nèi)涵。
二、耕讀精神在明代繪畫中的體現(xiàn)
(一)中國(guó)的耕讀文化不僅影響了農(nóng)學(xué)、科學(xué)與哲學(xué),也影響了文化藝術(shù)方面。下面我們主要從一些明代繪畫中來(lái)分析耕讀精神在繪畫中的表現(xiàn)。明代繪畫大體出入于宋元兩代之間,水墨山水與寫意花鳥成就顯著。明初的宮廷繪畫與浙派繼承了兩宋傳統(tǒng),明中期的吳門畫派繼承和發(fā)展了元代文人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至明末,徐渭完善了大寫意花鳥畫的畫法,陳洪綬、丁云鵬、崔子忠、吳彬等人開創(chuàng)了變形人物畫法,還有曾鯨“墨骨敷彩”的肖像畫,明末的繪畫呈現(xiàn)出獨(dú)特的新面貌。
(二)明代繪畫中“漁樵耕讀”這一題材最早見(jiàn)于明初浙派大師吳偉的畫作中,吳偉性格戇直而豪放,“獨(dú)樂(lè)于山人野夫厚”,筆下多漁樂(lè)耕讀等體現(xiàn)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內(nèi)容,其中《漁樂(lè)圖》便是這一題材的代表作品。只見(jiàn)圖中湖光與山色相接,漁艇稀稀落落地停靠在港灣,近處幾株老樹生于一片嶙峋山石之上,姿態(tài)各異,造型奇特。中景是一座綿延山巒,高低錯(cuò)落,幾點(diǎn)寒林襯托出高遠(yuǎn)蕭索之意境。山下港灣一艘艘漁艇停泊于此,還能看到幾個(gè)正在湖中垂釣的漁民,最遠(yuǎn)處是一片朦朧的群山,意境無(wú)限。S型的構(gòu)圖將近中遠(yuǎn)三處景色串連了起來(lái),顯得曲折迂回而又層次豐富,畫面營(yíng)造出一種雄偉開闊之意境。作品所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漁民生活非常真實(shí),圖中通過(guò)對(duì)人物造型與樸素衣著的描繪,勾勒出一個(gè)個(gè)形象淳樸厚實(shí)的山村漁夫,極具世俗氣息。此圖用筆勁健,水墨淋漓,有南宋馬遠(yuǎn)、夏圭之意境,形似“披麻”的皴法與清淡而層次分明的墨色乃是繼承了元人的風(fēng)格。吳偉開闊磅礴的繪畫風(fēng)格在這幅《漁樂(lè)圖》中很好地體現(xiàn)了出來(lái)。
(三)明代關(guān)于“漁樵耕讀”題材的畫作還有蔣嵩的《漁舟讀書圖》與陸治的《幽居樂(lè)事圖》。《漁舟讀書圖》中,近處一塊危巖巨石赫然聳立,高峻險(xiǎn)阻,巨石邊有樹盤出,灘頭幾叢稀疏的蘆葦。石下湖面潮平岸闊,湖中有一葉扁舟,舟中二人,一人撐竿,一人正坐在船頭讀書,神情悠哉,表現(xiàn)了文人士大夫閑適安逸的生活情趣。遠(yuǎn)處是綿延起伏的山巒,云霧彌漫,顯得畫面之境界十分清靜寒遠(yuǎn)。
(四)陸治的《幽居樂(lè)事圖》為冊(cè)頁(yè)形式,共十頁(yè),畫風(fēng)簡(jiǎn)逸,多描繪小村幽居之情景,如漁夫、放鴨、聽(tīng)雨、踏雪等村居樂(lè)事。“漁父”一圖中描繪了漁夫們?cè)谒写驖O的場(chǎng)景,其中一個(gè)漁夫在蘆葦叢邊撐船回望,一個(gè)正俯身收網(wǎng),另一艘漁船上,一人劃槳,一人靜坐,一人正在船頭張望著,湖面泛起漣漪,呈現(xiàn)出一幅生動(dòng)的漁獵活圖景。“放鴨”一幅中,河中鴨子形態(tài)各異,簡(jiǎn)練傳神,河邊一人微微抬頭,樂(lè)在其中。“聽(tīng)雨”描繪了大雨滂沱的景象,當(dāng)中一人低頭彎腰,艱難地在雨中撐傘獨(dú)行,整幅畫表現(xiàn)出了雨天的生動(dòng)。“踏雪”一幅頗有意境,畫面左側(cè)一塊禿石上挺著幾棵枯木,右側(cè)一長(zhǎng)者撐傘攜著書童行走于冰天雪地之間,遠(yuǎn)處群山疊嶂,一片雪白,畫境高寒,動(dòng)靜結(jié)合,畫面散發(fā)著文人情趣的氣息。
三、耕讀精神的意義
(一)明代繪畫中有關(guān)“耕讀”這一題材的繪畫并不算主流,但仍受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喜愛(ài),包括明代吳門畫派中的代表沈周與文征明,他們二人也鐘情于云游山林,以書畫自?shī)剩^(guò)著寄情山水的自在生活。他們對(duì)前人筆墨傳統(tǒng)的繼承相當(dāng)重視,也注重自身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追求。
(二)文人士大夫這個(gè)群體文化修養(yǎng)比較深厚,他們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同時(shí)也樂(lè)意走進(jìn)生活中去體驗(yàn)、感悟自然。東晉陶淵明詩(shī)風(fēng)平淡自然,無(wú)論寫物還是寫景,詩(shī)歌當(dāng)中流露出來(lái)的感情皆是濃厚真切,他所描繪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雖平淡,卻質(zhì)樸而生動(dòng)。這是無(wú)法通過(guò)技巧去拼湊的,只有詩(shī)人自己切身體會(huì)過(guò),才能做到在平淡中見(jiàn)真章。謝靈運(yùn)的山水詩(shī)精妙而準(zhǔn)確,對(duì)于山水的自然美,他能敏銳而細(xì)致地去感受與觀察,寫出來(lái)的詩(shī)常令人拍案叫絕。他們作品中的意境亦是他們生活中的感悟與審美追求的一種映射。“耕”與“讀”并非對(duì)立的關(guān)系,如果說(shuō)“耕”是“行”,“讀”是“知”,我們更應(yīng)該“知行合一”,立足于生活,寄情于自然,在自然中汲取養(yǎng)分,對(duì)于我們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與創(chuàng)作實(shí)踐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xiàn):
[1]薛永年.明代繪畫述要[J].中國(guó)藝術(shù),1995(01):3-6.
[2]孫鷺瑋. 明代浙派藝術(shù)特點(diǎn)及其傳承[D].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2019.
[3]袁澤宇. 儒隱與道隱[D].東北師范大學(xué),2020.
[4]馮瓊,張猛.張履祥“耕讀相兼”思想及其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J].嘉興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1,33(03):22-27.
作者簡(jiǎn)介:李大盈(1996—),男,漢族,湖北黃石人,藝術(shù)碩士,單位: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guó)畫學(xué)院,研究方向:中國(guó)畫藝術(sh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