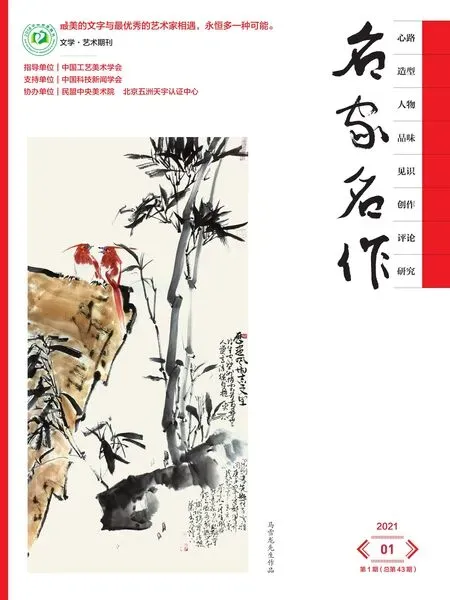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疾病解說者》的食物敘事與身份認同
林妮斯
裘帕·拉希莉是當代美國文壇著名印度裔女作家,1967 年生于倫敦,1969 年隨家人移居美國,幼年時常陪父母回印度加爾各答居住。《疾病解說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這部短篇小說集自1999 年出版后幾乎囊括了美國批評界的所有重要獎項,入選美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集,同時獲得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和普利策小說獎。小說敘事融入印度傳統習俗、宗教、政治、歷史等元素因而極具異域色彩,食物書寫就是其中一個維度。裘帕·拉希莉以其細致入微的寫實主義敘事和獨特的敘事視角反映了兩代印裔女性流散者在美國異質文化中的生存困境和身份流變。一、家庭關系與文化語境
食物被用來構成人物關系和文化語境,并構建作品中的社會關系體系。一次用餐就可能體現由語言、儀式、禮節等編碼構成的具有多重象征意義的符號組合系統。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闡釋,一次用餐除了能滿足用餐者的基本生理要求,同時還將用餐者置于復雜的關系中,用餐者和某一個人一起吃飯,就可能是在確認用餐者之間屬于同一個團體,又或是在履行用餐者之間的某種義務。
小說《停電時分》正是以食物共享為契機,反映一對在美國生活的印裔夫妻的家庭關系變化和女性在異域新環境中經營家庭遭遇的挫折困境。食物敘事離不開家庭中女性的身影,其中的女性形象尤為動人,而與女性生活最貼近的食物敘事和食物意象貫穿其中。作者通過第三人稱敘述視角展示人物的細微心理活動和真實的關系。丈夫蘇珂瑪負責烹煮食物,他內心矛盾,既期待每日的停電時分,又害怕兩人尷尬的共處。伴隨心理描寫自然回述了夫妻的甜蜜過往,倒敘穿插在敘事主線中,夫妻日常生活的今昔變化形成鮮明對比,反映了夫妻關系的變化,同時也因敘事的間隔拉長了時間軸,讓短時的相聚變得漫長而充滿回憶。
敘述看似冗長詳盡,食物一一羅列。蘇珂瑪每日從他們的儲備里挖取食物,他們早已是坐吃山空了,而修芭依然是無視所有生活所需,自顧自地忙,蘇珂瑪形容她:“可現在這個家對她來說跟旅館沒什么兩樣。”“現在蘇珂瑪喜歡上了做飯,正是如此她才感到有所貢獻。”蘇珂瑪內疚自己仍然沒有負擔家庭生活能力,擁有在讀博士身份,處境窘迫;妻子失去孩子的痛苦無處宣泄,選擇冷漠和逃避以掩飾不滿。
小說中食物敘事串聯成一條線,順時敘事為明,倒敘回憶為暗,此起彼伏,巧妙掌控故事的敘事節奏,出乎意料的結尾讓讀者不禁輕聲嘆息。丈夫從廚房食物烹飪中求得貢獻感以維持夫妻關系,透露出家庭關系的不平衡,展示了家庭權力的傾向性。食物是精巧的故事設計中必不可少的道具,娓娓道出這對印裔夫妻在美國偶遇、相愛,又因失去孩子而陷入婚姻困境的故事,證實了移居者在新環境求生存的困境和流散移居者家庭內部面臨的沖突與困境。
二、身份流變與思鄉之痛
《森太太》里的妻子同樣因為婚姻來到美國成了一個移居者,異域漂泊感和失根感始終伴隨著她。森太太迫切需要傾訴和陪伴,烹飪和分享印度傳統食物就成了她的生活寄托。“女性與食物天然就有一種親密的關系,因為女性是食物的準備者,也是家園和傳統的守護者。女性通過烹飪食物在向家人傳遞著濃濃的愛。”
在《食物與歸屬:異國廚房里的回家感》(Food and
Belong
:At
“Here
”in
“Alien kitchens
”)中,印度美國文化批評家柯圖·H.卡托克提出,充斥著思鄉情感的食物敘述常常操控著移民的記憶,使他們想象回家的感覺。離散者思念家園,把對家園和故國的渴望轉移到對傳統文化身份的堅守上。森太太兼職看護放學后的小男孩艾略特,每天都會為他準備不一樣的印度小吃。她一邊切菜一邊告訴艾略特:“在家里,你只要叫喊就行了。不是每家都有電話,可是你只要稍稍大聲點,不管是悲是喜,鄰居們都會過來看看情況,安排幫忙。”艾略特這才明白,森太太所說的“家”,原來指的是印度。小說通過“買魚”事件描述森太太在美國生存面臨的隔閡和沖突及她企圖融入新環境的失敗。森太太和森先生是典型的印度式包辦婚姻夫妻。森太太執意要求先生每周去海邊魚肆取魚,森先生從最初的配合遷就到不予理睬,既反映了森先生對妻子過于依賴丈夫和堅持印度生活方式的不認可,也隱含兩人感情根基不深無法相互理解的隱痛。買完整的魚是森太太對印度傳統生活方式的堅持,遠離家人的森太太并沒有在丈夫身上得到應有的關懷和尊重。作為新世界的“他者”,她既要面對在新環境中求生存的壓力,也要承受在不平衡的婚姻關系中流散家庭內部的疏離之痛,遭遇地域和心理上的雙重創傷。森太太是一個“失語者”,她的失聲源于去國離家者身份歸屬的困惑和流散人群越界后的雙重身份困境與異質文化中的邊緣處境。森太太對族裔食物的堅持即是對異域主流文化的默默抵抗。
小說在開頭以艾略特母親的視角描述,可以看作是“凝視”,以陌生化的視角打量一個印裔家庭在美國的安身之所,不管是室內裝飾擺設還是森先生、森太太本人,都讓這雙凝視的眼睛感到突兀與異常。這是兩種文化的首次碰撞,艾略特母親顯然對來自異域的文化和審美不甚認同,代表主流文化的權威凝視和批判。敘事視角迅速切換到十一歲的艾略特,孩子的觀察是天真純潔、不摻雜權力意識的。在艾略特看來,自己母親過于男性化和暴露的穿著以及對森太太拿出食物熱情招待的冷處理和警惕,那才顯得不合時宜。“拉希莉對食物的冷與熱的對比體現出她對食物的心理需求,即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她渴望親情、溫暖與關愛。食物的冷與熱也是兩種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精辟概括。”
三、食物敘事與女性族裔身份重建
理查德·瑞斯帕(Richard Raspa)教授曾指出:“小說中人物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烹食族裔食物,這種食物就能以一種紀念的方式或以某個舊風俗習慣的形式幫助進食者重建她們的族裔身份。”飲食可謂是文化的最佳觀察點。離散群體中的女性往往由于印裔原生環境的文化束縛,多局限于家庭生活,來到美國后,因語言和文化障礙無法自由獲得工作,就更難獲得主體價值和身份認同。重建身份意味著割裂過去,意味著她們必須克服性別、語言、文化、種族等多重障礙重新建立新的身份。像森太太一樣,通過準備食物的儀式感喚起家園記憶來撫慰心靈,通過保持民族傳統來延續族裔身份。這樣的例子在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一種敘事傳統,只是族裔文學一直處在被關注的邊緣,對這種敘事的分析也就更少見。
同是離散移居者族裔身份,森太太本質上仍是第一代移民;修芭和蘇珂瑪的父母都在美國居住,他們都在美國受教育,自由戀愛結婚,屬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對食物的態度反映出修芭和森太太不同的人物形象。修芭的獨立性是緣于她從小接受美式教育,是兩種文化影響下成長的新女性。享用傳統印裔美食顯示她對自己族裔身份的認同,外出工作表明她能夠很好地融入主流社會,有著身份認同的自信。對比之下,森太太的社會身份仍舊是家庭主婦。兩人的遭遇代表族裔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兩代族裔女性身份的轉變。流散者既需要在地理位移面前通過消除語言文化隔膜逐步獲得經濟獨立,又必須在心理上淡化對異域文化的抵觸并融入新環境。
四、總結
裘帕·拉希莉的現實主義書寫體現出優秀作家的世界主義人文觀和普世情懷。故事中“食物”這一符號被存入生存、欲望、身份認同、文化歸屬等一系列信息。食物敘事通過小說中飲食態度、烹飪過程體現不同人物或相同人物不同成長階段的自我文化歸屬。食物是流散者寄托鄉思、懷念家園的載體,食物也是對異國重建家園者邊緣處境的慰藉,食物隱喻人物關系親疏人情冷暖,是這寄居地重建身份的渴望與希望。精巧的敘事結構和巧妙的敘事視角為拉希莉筆下的人物增添光彩,為這浮世眾生相的孤獨傷痛抹上厚重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