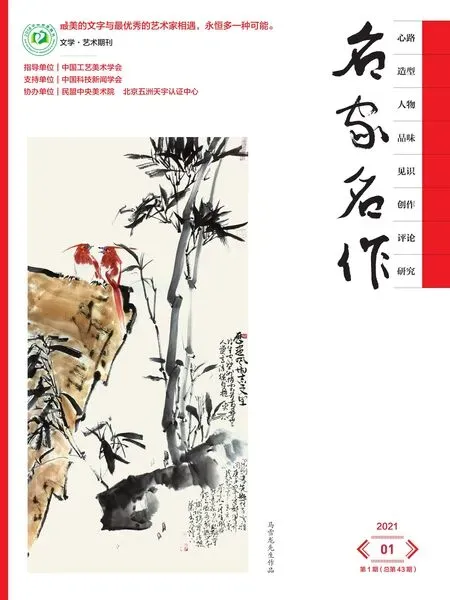從滬劇《羅漢錢》看趙樹理小說戲劇改編的特點
許 建
著名的小說家、“山藥蛋派”創(chuàng)始人趙樹理是20世紀30 年代至60 年代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代表。在趙樹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各類反映中國北方農(nóng)村生活的小說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些優(yōu)秀的、有著完整敘事結構的作品被改編成劇本,成為戲劇舞臺上二次創(chuàng)作的濫觴。本文將以改編自趙樹理短篇小說《登記》的滬劇《羅漢錢》為例,通過探究小說文本與戲劇舞臺呈現(xiàn)之間的異同等問題分析其改編的基本特點。
滬劇《羅漢錢》講述了解放伊始農(nóng)村青年男女李小晚和張艾艾自由戀愛的故事。二人互贈羅漢錢和戒指以表明心志,艾艾母親小飛娥顧忌村里人的閑話,又不忍自己年輕時飽受苦難的悲劇在女兒身上重演。在進步女青年馬燕燕的傾心相助下,二人的婚事逐漸得到理解與支持,并最終破除了封建觀念,響應婚姻法的頒布,成功登記結合,成就了人人稱羨的模范婚姻。該劇表達了對封建勢力束縛下“包辦和買賣婚姻”的批判,宣揚了自由戀愛的時代新風,展現(xiàn)了人們對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在這次改編之中,滬劇《羅漢錢》和原著《登記》有一定的出入,仔細審視內(nèi)在的嬗變將有利于揭示戲劇改編視閾下作品的審美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一、藝術設計與戲劇因素的承接性
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不成戲劇。滬劇《羅漢錢》的成功改編離不開小說《登記》情節(jié)的巧妙設計。故事中最主要的矛盾沖突聚焦在以小晚、燕燕為代表的年輕人和以村長為代表的守舊派之間。一方追求婚姻自由,一方固守封建傳統(tǒng)思想,這組矛盾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社會上的一些現(xiàn)象:許多民眾仍然存有濃重的封建思想,不認可新的婚姻制度和觀念,認為這是違背傳統(tǒng)的“造反”行為。因此,在改編之中主創(chuàng)人員宗華、文牧和幸之也是牢牢把握住這一點,將頑固不化的村長、重利輕義的五嬸、搖擺不定的張木匠乃至不通情法的王助理員等人刻畫成小晚和艾艾二人登記道路上的“攔路虎”。在雙方各自據(jù)理力爭、產(chǎn)生劇烈沖突的時刻,觀眾不免會思考:為什么小晚和艾艾這對年輕人的真心相愛始終打動不了村長等人?村長始終不肯給小晚和艾艾寫介紹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孤立無援的燕燕和艾艾等人又會想出什么樣巧妙的辦法去應對?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展現(xiàn)了作家高超的敘事能力,原著《登記》較為成熟的藝術設計為戲劇改編厚植了沃土,以矛盾沖突為代表的戲劇因素得以充分表現(xiàn)。
最有“戲”的還屬小飛娥的內(nèi)心矛盾。小說中原本不多的心理描寫被戲劇承接改造,以唱工、做工為主的演繹方式擴大了人物心理的表現(xiàn)空間。小飛娥偶然發(fā)現(xiàn)女兒艾艾的一枚羅漢錢,一聯(lián)想到自己的痛苦回憶,她就不由得為女兒重蹈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擔憂。在女兒的婚事問題上從不支持到最終認同,這也是小飛娥個人情感碰撞、思想斗爭的心路歷程。回娘家時路過相親男方家門卻聽見自己被人說成是不守貞節(jié)的女人,如今就連自己的女兒因為自由戀愛也被笑話,甚至還要斷了女兒回娘家的路,對人格的侮辱和摧殘讓迷茫的小飛娥漸漸地認識到舊時代的黑暗與罪惡,出于愛護女兒的母性,她開始向代表先進的力量靠攏。在陪伴女兒艾艾追求自由婚姻的同時,她受傷的心靈也得到凈化,為女兒來之不易的幸福感到欣慰,彰顯了新舊時代交點下女性形象對于自我生存價值的體認。故事中設置“羅漢錢”這一物件線索,既象征了母女兩代人的愛情,又自然地連接起馬燕燕和張艾艾、李小晚等青年男女為自由戀愛而奔走抗爭的故事主線。滬劇《羅漢錢》從故事中一枚小小的“羅漢錢”入手,通過易名來試圖淡化原作“登記”的制度儀式之感,更像是將一個淚中帶笑的愛情故事娓娓道來,揭示新的婚姻制度的可行性和觀念的先進性。
文本之中一些悲劇性和喜劇性的元素還為戲劇作品所繼承,增強了戲劇的表現(xiàn)力。前者即“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小飛娥的愛情悲劇是時代環(huán)境釀成的苦果。她與保安情投意合、傾心相付,卻對自己的婚姻大事難以做主,不得不遵從傳統(tǒng)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一個她不愛的男人——張木匠。如果說自己的心意完全任人支配已經(jīng)是莫大的悲哀,那么身心上飽受摧殘則是又一重的苦難與煎熬。小飛娥和保安難成眷屬,藕斷絲連的情誼被婆家人知曉,身為人婦的小飛娥更背負了不忠貞的污名,遭到丈夫無情的毒打。在挨打之后,小飛娥與張木匠實際上維持著一種畸形的夫妻關系,小飛娥見了丈夫就“好像看見了狼,沒有說話先哆嗦”,哪怕是為了不挨打而在丈夫面前強顏歡笑也是做不到的。丈夫?qū)λチ伺d趣而有了婚外情,婆媳獨處一個屋檐下的尷尬、夫妻感情的冷漠直到婆婆去世、艾艾出生才逐漸淡化、消解,可以說這二十年是小飛娥血淚交織的“苦難成長史”。“回憶”一段高度凝練地交代了小飛娥的辛酸往事,人們不由地對小飛娥的遭遇感到同情與憐憫并展開深思,小飛娥個人的悲劇影射出一個一去不返的黑暗時代,強化了作品扳倒舊婚姻制度和觀念的斗爭力度。在喜劇性上,在前往區(qū)上登記一段中添入了一個風趣幽默的小插曲。由于五嬸沒有向西王莊“那個孩子”說明白艾艾和小晚的事宜,導致那孩子直接遞上去了介紹信,結果新人們差點認錯自己的對象,鬧出了笑話。原文中張艾艾和李小晚二人來到區(qū)上登記這一部分的描寫較為細致,結婚登記這樣一個嚴肅的場合卻笑料頻出,在表現(xiàn)與王助理員溝通遇阻時,用輕松、詼諧的語句調(diào)劑了緊張的氣氛,讓敘事節(jié)奏有條不紊。另外,原著中五嬸的人物設定也成功移植到了戲曲中的丑角表演上。在滬劇《羅漢錢》中本不起眼的五嬸真正成為一個左右逢源、油嘴滑舌的媒婆形象,舉手投足間流露出逗笑的風情,讓人忍俊不禁。
二、文本風格與劇種類型的契合性
一次成功的改編離不開編創(chuàng)者對于原著整體風格的準確把握,從小說到戲劇的改編過程實際上除了要跨越藝術體裁的隔閡,還要在劇種的選擇上有所甄別。中國戲劇(即戲曲)是由各地方戲共同組成的“百花園”,由于自然地理和歷史文化的差異,各地方戲在各自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地域特色與藝術特征,如秦腔的雄壯悲憤、越劇的典雅婉轉(zhuǎn)、黃梅戲的載歌載舞等。發(fā)端于上海浦江地區(qū)的滬劇則是這偌大“百花園”中一朵耀眼的奇葩。滬劇《羅漢錢》一經(jīng)問世便好評不斷,重要的原因就是滬劇本身具有的藝術魅力為小說《登記》的飛躍提供了可行性。
首先,滬劇擅演現(xiàn)代戲題材的特征和趙樹理小說《登記》的故事背景相應,使原有的故事框架在移植創(chuàng)作之中基本完整地被沿襲下來,為改編提供了便利。百年滬劇中表現(xiàn)不同時期的現(xiàn)代戲?qū)映霾桓F,卻鮮有古裝歷史題材的劇目,這與上海的城市歷史文化有關。自開埠通商以來,上海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處于“先鋒”地位,民間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明的碰撞交織催生了滬劇的改革創(chuàng)新。在1941 年正式被命名為“滬劇”之前,其前身申曲已經(jīng)開始承擔宣傳時事政治、引介外來文化的社會功用。《黃慧如與陸根榮》一戲就直接取材于1928 年轟動上海的“黃慧如與陸根榮私奔案”;之后改編自美國電影的同名滬劇《魂斷藍橋》也別具一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樣板戲《沙家浜》更是移植了滬劇《蘆蕩火種》,成為革命題材的經(jīng)典之作。誕生于上海的滬劇堪稱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代表,是富有新鮮感的,是與時俱進、年輕而充滿活力的。而小說《登記》按照作者所注,故事發(fā)生在1950 年,恰逢新舊時代交替的關口,因此此次改編選擇與時代接軌更為緊密、反映社會現(xiàn)實更有經(jīng)驗的滬劇是再好不過的。
其次,滬劇樸實生動的曲詞唱腔和趙樹理小說《登記》的語言特色相應,有利于戲劇語言的轉(zhuǎn)化和受眾接受效果的增強。“從某種意義上說,滬劇的戲曲傳統(tǒng)和戲曲化就是滬語的話劇加唱。”縱觀全劇,人物對白基本是使用上海方言,簡短通俗,像“好稻不長荒田里,鳳凰不出在烏鴉巢”“青竹竿掏茅坑,臭氣越掏越難聞”的俚俗之語也為劇情增色不少;演唱上還采用了江南民間小調(diào),在原本規(guī)整的板腔體和曲牌體演唱之外擴大了戲曲音樂元素的使用。源于吳語之地的“紫竹調(diào)”在滬劇《羅漢錢》“燕燕說媒”一段中運用,呈現(xiàn)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平實之美。唱詞婉轉(zhuǎn)悠揚,如同白話,在二人來往對唱中完成了對馬燕燕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現(xiàn)了她樂于助人、機智聰慧的性格品質(zhì),同時也進一步解開了小飛娥顧慮的心結。極富農(nóng)民氣質(zhì)的小說家趙樹理的文字和語言迎合農(nóng)民的閱讀水平,是通俗化的、口語化的、趣味化的。就連他自己也說:“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nóng)村中的識字人讀,并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的。”由此可見,滲透了農(nóng)民思維的趙樹理致力于創(chuàng)作農(nóng)民喜聞樂見的故事,自然也將淺顯易懂的傳統(tǒng)寫法貫穿其中。加之滬劇說唱結合的基本體制本身也適合改編趙樹理評書式的小說,此次改編選擇了同樣充滿鄉(xiāng)土氣息的滬劇有助于傳播視域下作品價值的傳承。
最后,滬劇真切自然的表演風格和趙樹理小說《登記》的人物形象相應,小說中的人物走上戲曲舞臺,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重塑,也依舊能尋到原著的“影子”。閱讀趙樹理小說《登記》后不難發(fā)現(xiàn),文中對人物塑造的力度是不夠的,往往“其人物和情景描寫大都在故事情節(jié)的展開中進行,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和言語來展現(xiàn)其性格,少有靜止的景物與心理描寫”。這樣人物形象的塑造難免過于“扁平化”,欠缺人性的溫度,在滬劇《羅漢錢》之中對于張艾艾、小飛娥等主要人物的重塑就更加考驗演員的功底。著名滬劇女演員丁是娥對于小飛娥的演繹就極具代表性。小飛娥是封建舊時代迫害下的受害者、犧牲品,原著中她似乎只是一個符號化的配角人物,著墨不多。但在滬劇《羅漢錢》中小飛娥的戲份不僅貫穿全劇,而且對于她內(nèi)心的刻畫也更加深入,強化了其反抗性與斗爭性。“回憶”唱段中丁是娥飾演的小飛娥深夜坐在桌前聯(lián)想自己不堪回首的傷心往事,這段表演中丁是娥手扶桌臺,凝視著左手心的這枚羅漢錢,輕嘆一聲“羅漢錢”之后,隨著影視蒙太奇手法的轉(zhuǎn)場將觀眾帶回二十年前,唱罷淚濕眼眶,將人物情緒和心理的轉(zhuǎn)變表現(xiàn)得生動感人,一枚羅漢錢成為承載她悲痛、無奈、擔憂和恐慌各種情感的寄托。滬劇不同于其他傳統(tǒng)劇種對于程式化套數(shù)的大量展現(xiàn),它整體的表演風格擷取電影、話劇等新式藝術之華英,顯得更為清新脫俗、時尚自然。于是小說《登記》里天真純潔的張艾艾、正直機敏的馬燕燕、溫和敦厚的小飛娥、狡黠逢源的五嬸在戲曲舞臺上不僅沒有背離原著的風格設定,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各自形象的立體感,滬劇真切自然的表演風格也為人物塑造去璞存真。
三、主題思想與意識形態(tài)的呼應性
1950 年6 月,小說《登記》發(fā)表在趙樹理主創(chuàng)的期刊《說說唱唱》總第6 期,此時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實施僅僅過去一個月。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土壤卻依舊滋生著封建殘余勢力,對新政權法治建設與社會改造造成了阻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由于封建余毒的迫害,各省大量婦女被買賣、強嫁乃至受虐自殺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尖銳的社會問題向黨中央領導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發(fā)出了挑戰(zhàn)。為維護婦女權益、發(fā)展新型婚姻家庭關系而制定的《婚姻法》在各地貫徹執(zhí)行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法律條文在根深蒂固的舊思想觀念面前成為一紙空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呢?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新的司法體系,不少司法人員是從舊政權直接接收過來的,他們的民主思想淡薄;農(nóng)村基層干部,特別是在新解放地區(qū),大批基層干部來不及接受法治思想的教育,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和陳規(guī)舊習直接影響他們對案件性質(zhì)的判斷和審理……第二,不少群眾,特別是農(nóng)民因?qū)Α痘橐龇ā凡涣私舛a(chǎn)生恐慌和誤解。”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fā)揮文藝宣傳政治、啟蒙民眾的社會功能,及時推出適應時事的文藝作品就成為文藝界人士的首要任務。
時任北京市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會主席、文化部戲劇改進局曲藝處處長的趙樹理早在20 世紀40 年代就取得了顯著的創(chuàng)作成績。1943 年趙樹理通過創(chuàng)作小說《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等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解放區(qū)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被指定為一種代表歷史發(fā)展的新型文學代表,當時流行的“趙樹理方向”可以說是踐行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會議精神的優(yōu)秀典范。農(nóng)民、干部、民兵等底層人物在解放區(qū)文學中的大量出現(xiàn),實際上代表了一種大眾化的文藝發(fā)展趨勢,從政治的角度闡明了“文藝服務于群眾”的路線,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文化陣地建設上的戰(zhàn)略高度。
小說《登記》的發(fā)表正是為了宣傳《婚姻法》,在滬劇《羅漢錢》的改編中仍然保留了原著的基本精神。作為第一屆全國戲曲會演的重點劇目,上海市文化局藝術事業(yè)管理處改編《登記》的倡議明顯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原著中既有進步的青年戀愛男女,又有頑固的“老封建”村長等人;既有堅定政治信仰的黨員好干部,又有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抗法的政府機關人員。通過設計鮮明的立場分歧凸顯新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無意間渲染了一種階級斗爭的意味。另外在一些細節(jié)處也暗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社會風尚與政治運動,趙樹理此次創(chuàng)作也是他對當下時事有意識的回應,展現(xiàn)了他身為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擔當。滬劇《羅漢錢》在北京首演后得到他本人的贊賞,說明改編較好地體現(xiàn)了原著的精神內(nèi)核,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國家在有目的地推廣《婚姻法》的同時,游走于藝術與政治之間的戲曲自然是不能脫離社會功用化的范疇之中的。一方面,現(xiàn)實的需要讓它不得不“為政治服務”,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代言體”;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如果任由其走向極端也會淪為政治的附庸,喪失純粹的藝術價值。對于“戲曲服務于政治”的理念“不能做片面、狹隘的理解,特別是對于具體劇目,不能簡單地貼標簽,而要作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因而再次審視滬劇《羅漢錢》,它在當時是一部“活”的《婚姻法》,在法治建設日益健全的今天依然不失為一部佳作。
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思想在歷史的進程中有所變化,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相對和平的年代里“趙樹理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意識、思想意識、審美意識逐漸被主流意識縮所置換,趙樹理自由的文學創(chuàng)作被拉向了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文藝規(guī)范的監(jiān)督之下”。但從某種角度來說,趙樹理適應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其衍生的文藝作品對于當時整個社會具有啟蒙價值,趙樹理原本“為農(nóng)民發(fā)聲”的主體意識還是與官方話語不約而同產(chǎn)生了暗合。
四、結語
在趙樹理筆耕不輟的創(chuàng)作歲月中,小說《登記》以輕巧的姿態(tài)登上文壇,向社會大眾傳遞了新的婚姻家庭觀念,有力打擊了封建舊思想。20 世紀中后期,大量改編自趙樹理小說的戲劇作品接連涌現(xiàn),其中不乏諸如滬劇《羅漢錢》這樣的精品,它們的成功根本上要歸結于趙樹理本人高超的創(chuàng)作能力。多產(chǎn)的農(nóng)民作家趙樹理用他一生的心力講述著來自三晉黃土上的多彩軼事,從文本走向戲臺的過程也在引導著我們重新思考趙樹理作品的文學價值以及戲劇改編應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