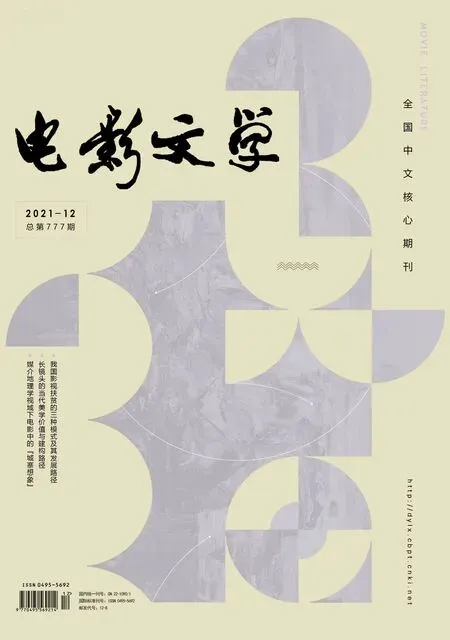媒介地理學視域下電影中的“城寨想象”
尤 達(南京藝術學院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從地理角度觀之,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后,百年歷史中香港儼然成為英國的一塊海外“飛地”,屬于英國殖民地但不與本土毗連;而曾經位于香港九龍,面積約2.67萬平方米的九龍寨城則成為英屬香港時期的一塊中國“飛地”。這個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幾經變遷,成為難民庇護地、三不管地區、記憶懷舊地等。由于身份復雜化、文化多樣性、空間奇觀化等,城寨頗具傳奇色彩,也成為香港電影中反復書寫的地方。然而,在1994年4月城寨拆除完成后,這種書寫非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許多香港導演不約而同地在電影中不惜工本重建城寨,海外導演也同樣鐘情城寨。這些電影中的“城寨想象”有著復雜的背景和多重的語境,從中既描繪出香港過去的圖景,又折射出社會轉型期的身份重構,更在全球化語境下成為一個文化符號。
媒介地理學,“以人、媒介、社會、地理四者的相互關系及互動規律為研究對象”,“從媒介生成,使用等基本關系出發,通過媒介呈現地理以及審視其中的人地關系,最終達到突破媒介與地理限制的目的”。立足該視域觀察,發現電影中的“城寨想象”,是電影媒介對九龍寨城這座背負特殊歷史身份、“所指”隱隱面向香港當下心態,且飄浮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城寨,發起的種種“想象的地理”。
一、“城寨想象”中的空間建構:從邊緣看中心的多元想象
“空間”指向了媒介空間與社會空間的關系,兩者“處于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之中,媒介空間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空間,同時又以—種‘想象’的能動性建構著社會空間”。關于“城寨想象”的空間建構便是媒介空間的形成過程。從社會空間審視,九龍寨城如同安東尼·吉登斯所言的城市“后臺”,即“被統一的空間實踐所排除或隱匿的部分”。這些“散落在統一空間之外的異質生活環境,正可以成為觀察城市的對立地點,成為城市之鏡”。換言之,從社會空間研究城寨文化可以反觀整個香港,其媒介空間的建構也如同一面“城市之鏡”,可以折射出媒介中的“香港想象”。福柯所言的“異托邦”指的是“由散布、并存于現實社會中的對立地點構成的鏡像”。以此出發,從這“邊緣”可以建構出通往“中心”的多元想象路徑,這些想象依托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構筑起城寨這一異質空間。
(一)“地方志”史傳想象:時代發展下的原型再現
“異托邦”的“地方志”所記錄的是“各式‘異質’的人在一個‘異質’的場所的生存景觀”。具體到城寨,香港電影中暴力的幫會、貪腐的警察、漂泊的難民構成了這個異質空間內的“生存景觀”,海外電影則更多是“賽博朋克”風格下末世的科學家、復制人、機器人或者游戲玩家等。“不同的‘記述者/口傳者’對于相關場景的‘復述’會有所差異,但包蘊在差異‘復述’之中的只屬于該地方的基本元素卻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因此,無論是真實或者再造的城寨,空間的基本構成不會改變。然而,“香港社會的官民結構基本由幫會成員與警察組成,正是這種特定的現實,決定了香港警匪片的盛興。”于是,在這個異質空間中,有一些出名的“外來者”警察與“居在者”梟雄構成的“生存景觀”被不斷提及,且“不同的記述者”復述差異較大。這一組組人物原型的再現,構成了時代發展下“異托邦”風格獨特的“地方志”史傳想象。
呂良偉主演的《跛豪》、劉德華主演的《五億探長雷洛傳》、劉青云和吳鎮宇主演的《O記三合會檔案》以及劉德華和甄子丹主演的《追龍》都在講述香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兩個原型人物的故事:“外來者”總華探長呂樂和“居在者”梟雄吳錫豪。這四部影片中,《跛豪》為吳錫豪傳記電影,全片氣勢磅礴地再現了一段黑幫血淚史,在那橫跨10年歲月的沉淀間,從城寨一隅觸碰著整個香港的時代脈搏。緊隨其后出現的《五億探長雷洛傳》,以呂樂為人物原型,既刻畫了人物的奮斗歷程,也描述了其顛簸半生的情感,總體觀之,戲說的成分多了些。全片淋漓盡致地渲染出城寨的舊時氣氛,令觀眾不由自主地沉浸入“城寨想象”。《O記三合會檔案》于1999年上映,片子以“阿豪”和“阿樂”指代的兩位原型人物,卻更像是城寨內兩個青年的奮斗發家史,與原型人物間關聯度略低。不過該片在開始部分用相當長的篇幅回顧了城寨的真實歷史。《追龍》于香港回歸20年之際上映,影片不再執著于個人傳記,而是聚焦香港人與英國人的對抗,深化反抗殖民壓迫的主題。
“在‘地方志’形態中,所有的個體都將以自主參與的方式成為其‘同質化記憶’的一部分,群體性的生存樣態是個體生存的唯一憑據,而個體對集體記憶的傳承也即是個體自身存在的有力證明。”從這個層面論及,上述四部影片無論是傳記或者戲說,抑或是兼而有之,都成為九龍寨城這個媒介空間“地方志”史傳想象中極為精彩的一部分。
(二)外來者的書寫想象:罪惡化與妖魔化
對于“外來者”“異托邦”的開放性和排斥性共存。一方面,“‘外來者’總是會攜帶其所固有的‘生存模型’來觀察和參與到‘異托邦’的空間之中”;另一方面,“外來者”“很難徹底放棄其原有的‘生存模型’而完全融入‘異在’的生存形態之中”。因此,“外來者”進入城寨的行為一般是暫時的,“并可能生成諸多的摩擦、不適應甚至矛盾”,最終任何改變現狀的嘗試都將失敗。具體而言,這些“城寨”中的“外來者”大多為辦案的警察、討回公道的復仇者、揭開真相的解密人等。
從1983年的《A計劃》到1993年的《重案組》,成龍飾演的警察兩度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城寨。在這種媒介空間設定中,城寨時而是警察與海盜勾結的藏污納垢之地,時而是綁匪藏身的庇護之所。“罪惡化”想象下,警察這種“外來者”很容易被城寨“‘拒絕’來自‘外來者’的任何試圖改變此種‘異在’形態的全部訴求”,于是影片往往以某一起犯罪被撲滅為結局,而非改變城寨這個異質空間的形態。同樣的影片還有《三不管》《低壓槽:欲望之城》等。海外電影中,《銀翼殺手》《環太平洋》均是“外來者”以警察的身份進入末世的城寨,此時不再為了消滅罪惡,而是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前者需要知道“復制人”的下落,后者則要得到“怪獸腦袋”。換言之,此類末世電影中城寨已經不是最大的危機發生地,而成為未來人類生活的日常居所。
2013年,黃秋生飾演的葉問在影片《葉問:終極一戰》中孤身闖入城寨,為友復仇,伸張正義。2019年,唐文龍飾演的葉問在《葉問之九龍城寨》中再闖城寨,為己復仇,自證清白。香港武俠功夫片中,俠客如同警匪片中警察,大多扮演著正義的角色,而城寨依然是罪惡的符號。兩部電影不約而同地將城寨寨主作為邪惡之源,進而讓主人公如游戲闖關般發起挑戰,直至最終勝利。如此“‘外來者’以自身生存形態去影響和改變‘異托邦’的嘗試”,得到了假想般的勝利。然而,武俠功夫片“所表現的那種草莽精神,和當代社會法制精神是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的”。事實上,此類影片在香港電影中已不多見,但這種囿于成見的罪惡想象卻在西方電影中一再上演,如尚格云頓主演的《血點》、克里斯蒂安·貝爾主演的《蝙蝠俠:俠影之謎》等。
2006年李心潔主演的《鬼域》和2015年張家輝主演的《陀地驅魔人》兩部恐怖片展開靈異想象,將異質空間“妖魔化”。九龍城寨的空間構造有著狹隘、破敗、壓抑、骯臟等特點,且已經消失在歷史之中,這些與“恐怖片中的古堡、廢棄而幽閉的老屋”等不謀而合。《鬼域》以此營造出一個被遺忘與遺棄的空間,一個充斥著怨念的世界。主人公是一個解密者,身處“鬼域”后發現,其實自己是一切的制造者。即便如此,作為“外來者”,主人公“改變‘異托邦’的嘗試總是會以失敗而告終”。《陀地驅魔人》則通過主人公驅魔尋找事情真相,然后如警匪片、武俠片般將魔王生前設定在城寨,以此凸顯邪惡。這兩部電影中,城寨的空間設計局部還原度較高。
(三)居在者的書寫想象:逃離情結與異樣歷史
“居在者”站在“刺激‘中心’自身的反思,其對‘中心’及‘外來者’而言,既是某種幻象,也是對其缺失的有效的補償。”空間層面論及,“異托邦”與“中心”互為鏡像,這使得來自“中心”的“外來者”與身處“邊緣”的“居在者”,兩者的書寫想象也互為鏡像。“城寨”中的“居在者”,往往是幫會成員、社會底層。“想象的目的絕不在于使‘異托邦’成為新的‘中心’,而恰恰在于以‘鏡子’的方式‘映射’出‘中心’所自有的‘缺失’。”
事實上,早期黑幫電影《白粉雙雄》《城寨出來者》和《省港旗兵》都通過幫會男性成員的視角看待著城寨。這些“居在者”“天然地擁有某種能夠直接感知‘異托邦’特性的優勢”,但無一不想“逃離”。換言之,這些影片對“城寨”的認同帶有一種悲劇性的色彩,于是逃離異質空間成為主旋律。以《城寨出來者》為例,探討的話題是從城寨出來的人會有怎樣的人生經歷與最終結局,最終的答案是:有且只有宿命性的悲劇。此外,《懵仔多情》中的脫衣舞女天嬌、《三不管》中的妓院老鴇阿玲和女兒、《三更之餃子》中的墮胎少女,都詮釋著女性社會底層的“逃離”想象。如此,在警匪片中“異托邦”與“中心”的互為鏡像體現為“居在者”幫會分子的“逃離”想象與“外來者”警察的“罪惡化”想象。從邊緣看中心,城寨成為香港這座大都市的“城市之鏡”。
另一方面,以原型人物創作的黑幫電影,如《跛豪》《三支旗》《毒。誡》等并無“逃離”想象,而是通過描繪異質空間內崛起衰落的奇特“居在者”,從另一個視角展現香港的異樣歷史。有意思的是,這種“異托邦”想象并非想“成為新的‘中心’”,但是由于“香港回歸之前一直處于殖民統治之下,沒有政黨,由社會各行各業自發組建的幫派(有的淪為黑幫)也就大行其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或多或少帶有幫派色彩,而維系香港社會秩序的主要是警察”,這便導致城寨梟雄成為風云人物,傳記電影憑借媒介的影響力,使得“邊地”歷史的地位超過“主流”歷史。時至今日,普通人記憶中的香港史往往會與這些電影發生聯系。
二、“城寨想象”中的時間建構:從過去到未來的多重符號
“時間”代表著“媒介地理系統的變化與流動”,具體指媒介想象的時間與現實時間的對應關系。由于城寨業已消失,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城寨想象”的時間建構呈現兩極化,即與過去和未來產生關聯。“電影中的城市時間坐標總體上是扁平的,‘過去’與‘未來’同樣被附著在空間符號之上,共同指向一種‘現在’的消費與狂歡。”于是對城寨過去的經驗和體認,以及對城寨未來的符號化處理,“都被轉化成碎片化、模式化、感官化的‘空間感’”。“城寨想象”正是以書寫不同的時代背景完成這樣的“媒介地理”的生產。
(一)存在于記憶中的過去
齊格蒙特·鮑曼指出:“面對充滿不確定的未來,人們越來越希望回到過去,由此進入了一個懷舊的時代。”城寨拆除前后,電影中的“城寨想象”密集地出現,甚至城寨拆除后對于過去的回望依然愈演愈烈,本質原因在于懷舊。正如詹姆遜論述懷舊電影,以電影《體溫》為例:“小鎮背景有關鍵的策略作用:它使電影用不著可能令我們聯想到當前世界、消費社會的大多數符號和參照。”
第一,孤城時代。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九龍寨城歸滿清管轄,直至20世紀40年代這里成為清朝軍隊的駐地。對于這段歷史,香港電影中表現較少。1983年的《A計劃》第一次表現“孤城時代”的城寨,成龍飾演的警察穿梭于城寨辦案,因為復雜的地形產生一堆笑料。在這里城寨不光提供了時代背景,更因空間造型為影片增色不少。2009年的《十月圍城》也出現了清兵把守的城寨,滿清是革命的對立面,城寨歸屬為邪惡的象征。由于當時真實的城寨已然拆除,該片也并未去搭景再現,只是將之作為故事背景一閃而過。
第二,圍城時代。抗戰期間,日本人拆除了城寨的圍墻。勝利后,露宿者開始在九龍寨城聚居,一堵無形的墻被建起,城寨與香港隔墻對望。有意思的是,反映這一時期的電影渲染的是一種溫馨記憶。1973年翻拍的《七十二家房客》,影片的故事背景定義為廣州市西關太平街的一幢破舊大院。實際上,該片是在邵氏的片場搭棚和旺角西洋菜街實景拍攝的,其中棚內搭設的房屋,造型參考的九龍寨城。《七十二家房客》站在20世紀70年代回望40年代的街坊情誼;2004年的《功夫》則互文了這種鄰里溫情,那舊日里小市民百態在“豬籠城寨”緩緩流淌。所謂“豬籠城寨”無非是粵語發音中“九”如同“狗”,以此解構演繹而來。這些影片都能透過溫暖彌散的光線,滋滋作響的油香,狹窄弄堂的穿梭,面目模糊的人影,讓觀眾回到過去,這便構成了對都市化香港的一種批判視角。當時代發展越來越快,人們唯有從媒介空間中去探尋美好的往昔。當然,對媒介本身,“這種‘回歸’的本質是追求娛樂性,所有和諧悠閑的生活并非歷史的本貌”。
第三,罪城時代。1948年城寨內的難民成功抵抗英國政府進入整頓,這里成為“三不管”地區。此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更是淪為幫會活躍地帶,成為非法行為的“溫床”。以《跛豪》為代表的一批帶有傳記色彩的電影,回望的便是這一時期的城寨。在這里,“城寨想象”的時間建構采用的是“回憶的模仿”,即“回憶不可能真正被仿造,而是可以對不同的回憶過程進行文學演示,以此產生一種模巧錯覺”。這是一種對“過去”的仿真重構,通過模仿真實人物的回憶而產生令人信服的效果。例如,《跛豪》從1990年11月赤柱監獄里的跛豪開始一段往昔回憶;《五億探長雷洛傳》讓功成名就的雷洛在煙霧繚繞中回眸昨日;《O記三合會檔案》從老年阿豪為警察講述三合會和城寨歷史夢回當年;《毒。誡》從1987年戒毒成功的陳華開啟回憶;《追龍》則以畫外音的形式開始,講述人物自己的故事。此外,講述同一時代的兩部葉問電影中,《葉問:終極一戰》采用兒子的回憶,講述父親葉問的傳奇故事;《葉問之九龍城寨》則未設置敘述者,以一段倒敘開始故事。
第四,清城時代。1974年廉政公署進入城寨清理之后,九龍寨城不同于之前的混亂,但“城寨想象”的時間建構并未因為情況好轉而停止“罪惡化”想象,而是開始根據真實案件進行改編。《省港旗兵》根據吳建東洗劫珠寶行案改編而成,《白粉雙雄》靈感來自真實犯罪新聞,兩作均聚焦70年代末的城寨;美國電影《血點》根據空手道宗師杜克·法蘭的經歷改編,表現了80年代初期的城寨;《重案組》則根據香港富商王德輝綁架案改編,描繪90年代的城寨。
(二)存在于擬仿中的未來
波德里亞認為,后工業時代的符號特征以“擬仿”為主,“和所謂真實一點兒關系都沒有,它是自身最純粹的擬仿物”。“擬仿”帶來的是“超真實”。“它不再是造假問題,不再是復制問題,也不再是模仿問題,而是以真實的符號替代真實本身的問題;這是通過重復操作制止每一個真實過程的行動。”波德里亞指出,消費社會中的大眾文化就是“擬仿”先行的文化,“既然超真實是一種以模型取代真實的新的現實秩序,那么模型就成了真實的決定因素,現實反而成為擬像的模仿”。根據該理論,以1994年城寨拆除完成為時間界點,此后的“城寨想象”中符號化的未來,是依據“模型”建構起由大量擬像組成的“超真實”世界,并以此引發現實中的效仿。
第一,浮城意象。1987年,我國政府與香港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并于原址興建公園。此后,城寨的“擬像”卻始終浮現于電影媒介的想象之中。香港電影中,2005年開始的兩部《黑社會》將幫派內部、幫派之間的斗爭或博弈一一展現給觀眾,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社會之龍城歲月》。由于城寨已經拆除,全片未出現九龍寨城景觀,但依然在用片名呼應著曾經的城寨。更重要的是,片中的城寨意味著曾經的道義正在幫會成員心目中消失。“以往的道德、理想在金錢的影響下不斷退縮,那個英雄的時代已經逝去,接踵而來的是對金錢的崇拜。”正如片中的臺詞,“時代不同了,談的都是生意”,這種“浮城意象”無疑充滿著對過去的緬懷,它通過對城寨這個符號的傳遞折射著當下社會人的浮躁。除此之外,九龍寨城在海外電影中成為“賽博朋克”風格的代名詞。“賽博朋克”(Cyberpunk)是“控制論”(Cybernetics)與“朋克”(Punk)的結合詞,指的是低端生活與高等科技的結合。早在城寨拆除前,1982年的《銀翼殺手》便將城寨“擬像”化,以此構建未來的洛杉磯,此后更是成為此類電影的標準。“賽博朋克”電影將想象引申到未來,急切需要現實的“擬像”來縫合“當下”與“未來”之間的裂隙,如此才能將超前想象與現實境遇相結合。九龍寨城無疑是一個絕佳的符號,城寨內不見陽光的黑夜、單一的冷色調、下著雨的街道、高樓下衰敗的小巷,以及底層人的掙扎、痛苦、叛逆和反抗,與“賽博朋克”風格天然契合。
第二,危城意象。21世紀之后,隨著內地發展態勢的大好,香港經濟轉入低迷,一種“危城意象”隨之誕生。反映到電影中,“香港被塑造成一個隨時崩塌、燒毀、炸毀、成為空城、危機四伏的都市”。這無疑“展現的正是難以言表的香港文化身份”,而城寨作為曾經“罪惡化”想象的象征,無疑成為“危城意象”中一個典型符號。2006年的《鬼域》帶有一種后現代的末世風情,城寨作為劇中人物大腦中勾畫出的一座“危城”,最終在萬物崩毀中重歸虛無,然后再一次填充那些被遺忘的人和物,永不停息。2008年的《三不管》,則把敘事的背景放在了2046年,城寨的混亂讓身處其中的人想要逃離。2015年的《陀地驅魔人》淡化了時間概念,但依然指向了未來,片中讓九龍城寨徹底崩塌,以此反映對未來的焦慮。“危城意象”,“以寓言的形式展現了香港人想要追尋新出路,改變現有狀況的迫切愿望,探討了人的去留問題,呼喚秩序的重建。”必須看到,這種意象在當下的香港電影中頗為常見,但也必然隨著內地與香港對話的持續推進而減少,香港的未來絕不是一座“危城”。
三、“城寨想象”中的地方建構:從凝固到流動的文化距離
“地方”是一個頗具情感的概念,“當人將意義投注于局部空間,然后以某種方式(如命名)附加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換言之,其與自我認同、集體認同相關聯,可被視為“認同的中介和歸屬感的來源”。更為重要的是,現有研究表明“地方”原為是一個凝固的概念,本土性與排他性是其特征;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地方”的概念,邊界在不斷打開。因此,考察“城寨想象”中的地方建構,無疑要從導演的認同,即他們與城寨本身文化的遠近入手,按照從凝固到流動的發展脈絡,描繪他們的想象路徑。
(一)寨內導演個體尋根的文化認同
寨內導演,主要指兩位有過城寨生活經歷的香港導演:吳宇森和杜琪峰。從作品總體觀之,他們的共性在于對城寨有著一種文化認同,即在一個地方生活所形成的對此地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自我存在的形成依賴于內生的、剝離了流動性與距離體驗的地方,其中自我的地方體驗式文化身份與認同形成的關鍵環節”。然而,兩人一者偏向浪漫主義,一者更多的是現實主義,代表不同時期香港黑幫電影的人物銀幕形象變遷。
吳宇森五歲來港,在城寨只是暫居,更多是在石硤尾貧民區長大,然而從他本人對兒時生活回憶看,記憶中的血腥與暴力與城寨文化如出一轍。“街上總有黑道的人拉年輕人入伙,你不去就揍你,我印象里流血是家常便飯,一出巷子口就遭到埋伏。”于是他的作品中將這種文化泛化為暴力的情緒符號,以代表作品《喋血街頭》為例,開場一幕,年輕人之間的打架斗毆,血腥復仇成為家常便飯。另外,這種城寨文化又被衍變成一種浪漫主義。“當時我一些鄰居小伙伴兒同樣有正義感,只是做的方式不同,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到,沒有絕對的善與惡,人都是兩面性的,后來我的很多作品中都會出現俠盜,我喜歡拍兩個性格背景完全不一樣的人成為朋友的雙雄片”。因此在電影里他將幫派人物進行銀幕英雄化轉換,《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便是從城寨泛化出文化之根的。
杜琪峰與吳宇森不同,他在城寨長大,17歲才離開,耳濡目染之下對這里濃濃的世態人情和江湖道義有著深深的情結。首先,他的作品偏向于現實主義。不同于吳宇森“義字當頭”的浪漫主義黑幫片,對杜琪峰而言,幫派不是美化的熱血傳說,而是隔壁的鄰居和路上的死尸,是暴力壓制下的沉默與秩序,是不明原因的仇殺或結盟。于是,他深受城寨文化影響,塑造出一個黑幫、警察、殺手共存的世界,且各方遵循著既定的程序和儀式,然后于其中人物走向必然的悲慘宿命。其次,在接受采訪時他曾說道:“我曾經住在九龍寨城……那里大多是屋邨,雖然人蛇混雜,但是充滿濃濃的人情和江湖道義。”于是他的影片有一種對城寨深深的依戀,那是對過去江湖道義的依戀。即便城寨拆除,這一風格依然在杜琪峰的影片中延續。正如《黑社會之龍城歲月》中僅存的誓死捍衛幫規的肥雪,盡管在其他人物眼里這已經是一個神經質人物。
(二)香港導演集體記憶的文化召喚
九龍寨城對其他香港導演同樣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因為城寨是20世紀香港社會底層生活的一個縮影。于是他們在影片中發出文化召喚,喚醒觀眾的集體記憶。
蕭榮、藍乃才和麥當雄是最早發出這種召喚的導演,《白粉雙雄》《城寨出來者》和《省港騎兵》用九龍寨城透射社會問題,“表現一群在港求生的小人物,無奈受盡黑社會迫害,而社會亦失去公義,他們憤而個人執法、以暴制暴,奮力掙扎反抗”。潘文杰的《跛豪》、劉國昌的《五億探長雷洛傳》等呼應的是吳宇森開啟的黑幫片英雄時代。黑幫電影之外,王家衛、張之亮、黃靖華等導演也在城寨中尋找著什么。王家衛要找的是城市的疏離與人的漂泊和無根,《阿飛正傳》對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投去驚鴻一瞥。折射的卻是90年代港人疲憊不堪的靈魂;張之亮想要找到底層人們生活中的溫情,《籠民》近乎白描般書寫方寸之地的人情味;黃靖華用故事里的逃離表達著留戀,《懵仔多情》發起城寨拆除后的第一次港式回望。
隨著城寨的拆除,集體記憶被再度強勢激活,當觀眾無法目睹現實中的城寨,唯有依靠想象去還原地理。于是文化召喚顯得更為有理有據,電影類型呈現多元化趨勢:既有黑幫電影,如霍耀良的《O記三合會檔案》、王晶的《追龍》發出深深的懷舊召喚;又有武俠功夫片,如邱禮濤的《葉問:終極一戰》、付利偉的《葉問之九龍城寨》,講述過去的武俠神話;還有彭氏兄弟的《鬼域》、張家輝《陀地驅魔人》這樣的恐怖題材,以及邱禮濤的科幻電影《三不管》等。
這其中,“城寨情結”最為深厚的導演是王晶,他是《五億探長雷洛傳》的監制、《O記三合會檔案》的編劇、《追龍》的導演。特別是2017年的《追龍》,他為了真實再現,花費數千萬元和兩個月時間實景搭建了一座九龍寨城:大到商鋪招牌,小到一張報紙,每個道具都經過認真的挑選,做舊。逼仄的巷子、擺放隨意的茶水攤、燈光昏暗的賭博及吸毒場所,將特有的生活場景精細呈現出來。更有意思的是,影片中以城寨內不時出現的飛機呼應敘事節奏,這既是生活場景的再現,也是故事中人物命運的隱喻。
(三)異域導演東方奇觀的文化圖騰
異域導演主要來自日本和美國,按照文化距離的遠近幻化出不同的關于東方奇觀的圖騰。
日本在文化上與我國有著同根同源性,加之歷史原因,始終在關注城寨。九龍寨城被拆除后,甚至還在神奈川縣原樣仿制,連里面的涂鴉都是一樣,據說材料都是直接從九龍寨城買下空運來的。因此,早在1977年野田幸男的《骷髏13:九龍之首》便第一次展開“城寨想象”。其后,這種想象大多在動畫電影中被描繪。1995年押井守在《攻殼機動隊》制作前,帶領團隊到香港采風,目的就是一睹九龍寨城風貌。2005年森田修平的《捉迷藏》、2013年木村尚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香港九龍財寶殺人事件》等則借用了城寨的概念。總體觀之,日本電影中的“城寨現象”是在東方思維下展開的,即站在東方的“地方”概念下,幾近真實地去還原。例如,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中未來都市的一部分,完全是真實的九龍寨城:破舊密集的筒子樓,鱗次櫛比的漢字招牌,遍地污水的狹窄通路,甚至“烏云壓頂”般轟鳴著低掠過房頂的巨大飛機也被再現出來。
與之相對的是,美國的“賽博朋克”電影是西方導演在想象“城寨”,不可避免地站在西方的“地方”概念下,將城寨轉化為一個異質性存在的“他者”。1988年紐維特·阿諾導演的《血點》,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概念的西方化讀解:城寨有著難以描畫的、只屬于香港的獨特風情。雷德利·斯科特、克里斯托弗·諾蘭、吉爾莫·德爾·托羅、斯皮爾伯格的“賽博朋克”電影,則將這種獨特風情指向未來,在對城寨的罪惡性、混亂性進行充分征用的同時,城寨本身的地域性、日常性未被保留。換言之,這些都是西方思維與城寨元素的簡單嫁接,以未來的名義將西方價值觀嵌入神秘的東方,其間城寨“地方”的概念如同其本身一樣消失殆盡。也許曼努爾·卡斯特“流動空間”理論解釋了這一現象,全球性對地方性的取代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的功能與權力是在流動空間里組織,其邏輯的結構性支配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
四、“城寨想象”中的景觀建構:從真實到虛構的變化演進
“景觀”,即“媒介對世界的描述和解釋”,“媒介本身既從屬于景觀社會……又反映和呈現景觀,并不斷地塑造和建構景觀社會。”媒介地理學關注地理景觀如何在媒介中呈現出來,置于電影維度思考,便涉及出品公司的選擇。具體而言,“城寨想象”中的景觀建構,大致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形態:借代詮釋、真實取景和靈感再造。
一是借代詮釋,即并非拍攝真實的九龍寨城,而是以城寨的空間造型為藍本卻借景拍攝講述其間的故事。如前所述,最早出現于邵氏公司于1973年翻拍的《七十二家房客》中。該片如此做的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地域相同卻文化迥異,香港人看待城寨人的心態有些復雜,非常希望展開電影想象;其二,城寨自身既有視覺特色,又具文化內涵,也適合展開電影想象,但貼著“生人勿入”的標簽,讓電影實拍并不現實。所以,邵氏此舉在將城寨作為“能指”,“所指”指向20世紀40年代社會小市民的眾生相。此后,大量電影中出現這種借代詮釋,如美亞電影等出品的《歲月神偷》,故事背景設定的是臨近的九龍深水埗永利街;Black Canyon Productions出品的《新難兄難弟》則講述春風街的故事,兩者的房屋造型都有著城寨的身影。有意思的是,這種借代詮釋在此后的香港電影中,九龍寨城不再作為“能指”,而是成為“所指”。特別是1994年城寨拆除后,這種現象因城寨的消失而大量涌現。例如2004年華誼兄弟出品的《功夫》,再造了一座“豬籠城寨”,2006年寰宇娛樂的《鬼域》、甲上娛樂的《三更之餃子》等影片中所出現的景觀,“所指”也為九龍寨城。
二是真實取景,主要為警匪片,此時的“所指”與“能指”合一。九龍寨城的存在為警匪片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臺,因此,第一次走進城寨取景拍攝的影片,是1978年恒發電影的警匪片《白粉雙雄》。該片客觀地描述出城寨內下層市民的生活全貌。1982年,邵氏出品的《城寨出來者》更是被譽為“不能重拍的經典”,也是迄今為止最全景、最直觀、最徹底展現九龍寨城生活景觀的影片。由于該片的實景拍攝占比較高,已經具有史料價值。此后,1984年寶禾影業的《省港旗兵》、1988年美國Cannon International的《血點》、1990年影之杰的《阿飛正傳》等一系列影片均在城寨內實景拍攝。1993年嘉峰出品的《重案組》成為最后一部留下城寨影像的電影,其史料價值已經遠遠超過電影本身。
三是靈感再造,指的是以城寨為藍本想象化地模擬出場景,此時的“所指”與“能指”斷裂。這指向的是“賽博朋克”電影,美國華納兄弟非常喜歡從九龍寨城中獲得靈感,以此完成此類影片。最早的是1982年的《銀翼殺手》,其后是2005年的《蝙蝠俠:俠影之謎》、2013年的《環太平洋》、2018年的《頭號玩家》等,都將城寨作為構建未來高科技控制下“賽博朋克”城市的靈感來源。香港電影中蘊含“危城意象”的幾部影片也在以城寨為想象藍本,擬仿著未來。
“城寨”想象中的景觀建構,是通過電影媒介完成想象中的城寨地理與或借用、或真實、或再造的場景相交會。無論這種景觀建構與真正的城寨相差幾何,但至少電影通過其技術手段,完成了媒介對城寨的描述和解釋。毫無疑問,“在用于表現和建構地理的媒介樣式中,電影是一種相對完美的手段”。
結語:“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構
“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構為空間、時間、地方、景觀四個維度的想象提供了標尺。從以上四個維度的研究發現,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圍繞“城寨”所發起的“想象的地理”,其背后潛藏著豐富的文化意義,且與香港城市的變革密切相關,更是指向了全球化。這便涉及“聯系媒介與地理最重要的兩個尺度”:本土性聯系著地方,全球性關聯著世界。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本土性在無差別的景觀和壓縮時空的傳播中面臨重重危機,體現地方個性和特色的內容逐漸被淡化,全球化對本土性的消解成為不爭的事實。”真實的城寨消失之后,關于城寨的本土化想象正在淡去。當《功夫》以“豬籠城寨”代替曾經的九龍寨城,當《十面圍城》無暇顧及城寨的真實外貌,觀眾唯有從《追龍》中隱約回憶起城寨的一草一木,可是這些回憶透出“虛假的歷史”。事實上,1994年之后唯有杜琪峰的影片中雖不見城寨但飽含情結,余下更多地或者走向“危城意象”,或者填塞“外來者”的“罪惡化”“妖魔化”想象。換言之,一方面,城寨的消失使得媒介的想象唯有向著“浮城”靠攏;另一方面,“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跨越地理邊界生產了一種‘無地方感’的社群,以及一種異化的感受和再現方式”,勢必消失的“危城”陰影當下正籠罩城寨。于是,“城寨想象”必然隨著全球化帶來的“地域的跨越和邊界的消失”而轉型。關鍵是這種轉型中文化的擁有者并不具備話語權,當城寨與“賽博朋克”相關聯,由此引申出的“全球化”想象讓人啼笑皆非。格洛利亞·安扎杜萊和凱利·莫拉加將由國際接觸的加速和增多而導致的文化稱為“混血”文化。從這一角度論及,不能為“城寨想象”所產生的“混血”文化一味叫好,畢竟這里的想象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存在。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已經將城寨重建完成,這是否意味著未來的城寨“全球化”想象該是從日本發起呢?
因此,從“城寨想象”中的尺度建構角度看,在本土化難以維系的當下,與其一味走入歷史,不如著眼未來。一方面,僅就香港電影本身論,“賽博朋克”風格早已出現。受到漫威風靡世界的影響,1993年杜琪峰導演的《東方三俠》便有著濃厚的“賽博朋克”混搭“蒸汽朋克”的味道。在中國科幻電影崛起的今天,融合內地和香港電影人的力量,發展有著城寨元素的“賽博朋克”電影,不失為一條新路。另一方面,建構起屬于自己的“城寨想象”全球化發展體系更為重要。這里漂泊者的人生故事沒有說完,多元化的景觀可以呈現,在城市急遽變遷中,提取城寨的新內涵,可以在歷史和未來、本土和全球間構建起通道。九一一事件中消失的“世貿中心”在美國好萊塢電影中至今熠熠生輝,這無疑為電影中的“城寨想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