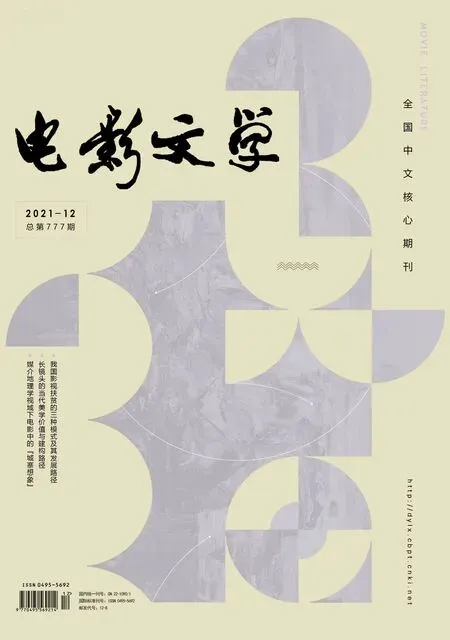新世紀初中國電影中農村女性的生存境遇與時代書寫
趙 浩 閆科旭
(1.河北大學藝術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2.重慶工商大學藝術學院,重慶 400000)
進入千禧年之后,在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中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蒸蒸日上。黨和政府在關注國家整體發展、建設的同時,注重協調好整體與局部之間的關系,統籌城鄉均衡發展,并將“三農問題”作為當前全黨工作的中心。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在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視之下,電影作為記錄時代真實性的影像媒介,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將創作導向聚焦于“三農問題”。“‘寓教于樂’的最佳載體,電影無疑必須在令人驚奇的光影敘事中,承載傳達主流意識形態、引導觀眾精神文化的歷史重負。”因此,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對“三農問題”高度關注,將農村女性形象的變遷作為“三農問題”的縮影與表達途徑,通過塑造豐富多元的農村女性形象來反映當前我國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的現狀。“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中女性形象的內涵承擔著遠遠大于她自身的現實責任與文化使命。農村劇中的女性形象經歷了農村社會與歷史文化觀念的變遷,被賦予了不同的歷史文化內涵。”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中的農村女性形象作為現實鏡像傳達的載體,可以窺見我國社會的發展動態與農村女性的命運走向,并以農村女性在生存、情感、成長等層面呈現出來的“弱勢”特質為橫斷面,展現農村女性在現代化語境中遭遇的不公待遇與生活窘境。
一、農村女童形象
“農村女童”一詞作為屬概念,其涵蓋農村留守女童、輟學女童、被性侵女童等種概念,作為種概念的農村女童形象皆在新世紀初期電影中得到呈現。影片《上學路上》講述了在我國西部地區輟學女童王燕想方設法籌集24.8元學雜費重返校園的故事,該片集中反映了農村男童與女童、中西部地區教育資源與發展機會不平等的現狀。“我國農村女性……在輟學、失學兒童中,女童占60%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僅為6.8年。”男童與女童在教育上的不公平待遇不僅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所導致的結果,而且還是農村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風俗習慣,貧困狀況、缺乏婦女身份認同等多種因素在教育上的共同體現。如影片中的王燕媽媽對男童、女童區別對待,讓兒子繼續上學,卻讓女兒輟學,并在當地早婚風俗的影響下,為王燕介紹相親對象。此外,男童與女童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問題,也是我國社會當前發展階段必然面臨的問題。“男女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是教育公平的難點,即使在發達國家,婦女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和機會仍然沒有保證,在發展中國家,男女受教育不均等的狀況就更為嚴重。”影片《上學路上》所反映的問題是我國中、西部地區存在的普遍問題,也是我國在發展階段現存且正在發生的教育問題,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我國在實現總體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的同時,也要注重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差距,努力協調整體與局部發展的均衡,從而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
影片《如果樹知道》講述了遭遇性侵的留守女童小蓮在老師的援助下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的故事,該片從留守女童與被性侵女童兩個維度折射出農村女童的生理、心理、安全等多方面的問題。農村留守女童一方面是城鎮化進程的產物。“預計2020年之前,流動遷移人口(包括鄉城流動、城城流動及新落戶城鎮的農業轉移人口)每年增長600萬~700萬人。”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城鎮化發展的特征之一,農村年輕人在面對農村貧困與城市“吸引”的情況下,選擇了進城務工,即這些年輕父母在照顧孩子與生活之間,優先選擇了生活,因此造成農村眾多留守兒童的存在。另一方面,農村留守女童是由于農村女童的性別差異所帶來的困擾,部分父母進城務工時選擇帶男童進城接受教育,女童則留在農村由老人照顧。正如影片中的小蓮弟弟就跟隨城里務工的父母生活,而小蓮卻跟隨年邁的奶奶在農村相依為命。“由于男女性別差異和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農村女童在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上大多低于男童,加之留守家庭結構不完整、功能不完善、力量不足,留守女童漸漸地處于劣勢的地位。”在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農村留守女童的數量激增,這些農村女童多跟隨老人一起生活。然而這些老人受教育水平較低、生活背景較貧困、對信息接收較為閉塞,并且在他們現有的認知中,只要保證孫輩最基本的衣食溫飽即可,從而忽略了對兒童心理、生理、安全等多方面的教育。也就是說,這些農村留守女童的生活得不到有效監管,因此處于社會的邊緣地帶,成為各種惡劣事件的受害人。“2017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4歲以下)案件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其中受害者為農村地區兒童的有112起,占比29.63%。2017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問題案件中受害人超過606人,女童遭遇性侵害人數為538人,占比為90.43%。”但由于此種案件的特殊性,在傳統“貞潔觀”思想的影響下,對于關乎女童聲譽、家庭名聲的事件,這些農村父母多選擇沉默,放棄訴訟,導致性侵女童未被發現的案件也不在少數。正如影片中的小蓮,在“性”知識匱乏與法律意識淡薄的情況下,被性侵之后產生的恐懼與蒙羞的心理,以及家人為了小蓮的名聲,一再選擇隱忍,導致犯罪嫌疑人長期逍遙法外。最后小蓮在老師的幫助下,公安機關才得以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
農村女童問題關系到社會基礎教育問題與基礎安全問題,“女童問題既是兒童問題,更是婦女問題和性別問題。女童是處于女性生命周期初始階段的特殊群體,女童的權利是婦女權利的重要內容,女童的生存發展狀況是婦女地位狀況的重要表征。”因此,新世紀初期電影中對農村女童問題的關注,即對新一代農村女性的生存與成長、命運走向等問題的關注,這也是不容忽視、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二、被拐賣的農村女性形象
中國電影對于買賣婦女犯罪行為的揭露,早在“十七年”電影中便初見端倪。“十七年”電影中塑造了諸如《白毛女》中的喜兒、《祝福》中的祥林嫂、《武訓傳》中的小桃等被男人“物化”的農村女性形象,她們成為男人的私有財產自由地進行出賣和轉讓。“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啟動,買賣婦女的犯罪活動開始浮出水面,90年代隨著社會轉型和人口流動,買賣婦女的犯罪活動一度猖狂,甚至出現職業化、集團化的傾向。”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5—2018年公安機關立案的拐賣婦女兒童刑事案件分別為9150起、7121起、6668起、5397起,而實際被拐賣婦女兒童人數遠遠不止這些。新世紀初期的中國電影繼續聚焦于被拐賣農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創作出諸如電影《盲山》中的白雪梅、《喊山》中的紅霞、《嫁給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等被拐賣的農村女性形象。
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塑造被拐的農村女性形象,呈現出如下特征:
(一)物化的私有物品
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塑造的被拐女性是貧困社會下的犧牲品,她們淪為宗族繁衍的生殖工具,作為一件明碼標價的商品被出售,并在男權社會的背景下淪落為男人的私有物品,成功被男人所物化。“男女在社會權利和經濟地位的失衡卻導致‘物化’在兩者之間是不平等的——男性可以成功物化女性,將其作為個人物品進行自由買賣,但在這個以男性意識形態為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女性卻難以物化男性。”在這一男女雙方共同參與交易的活動中,主動權操控在男人手中,雙方的交易地位不對等,當且僅有男人對女性進行買賣時,這場交易活動才可有效完成,并達到交易目的。因為這些被拐的農村女性在男權制社會中才能被物化,成為自由買賣的商品,可見,這種“物化”是單向的,是不可逆的,是男人對女性的“物化”。如影片中白雪梅被人販子以7000元的價格賣給黃德貴,白雪梅為了40元車費與小賣部的老板進行身體交易。山菊被人販子以3000元的價格賣給鐘老漢,被人販子拐賣的紅霞也是買賣雙方進行交易的物品。在這一過程中,只有女性被出售、被交易,而男人則扮演著物化女性的買方。在這種境遇下,這些農村女性不僅成為男人的附屬物品,而且逐漸喪失話語權,甚至被剝奪了自由生育與婚姻自主的權利,主動讓位于男人并沉溺于男人構建的二元對立世界之中。
(二)封閉的道德空間
被拐女性的生存空間,無論是在電影影像的表達中,還是現實生活的境遇下,她們多生活在封閉的道德空間之內,并且不能逾越身體和世俗的紅線。“村子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成員和親屬之間,族長或長輩所代表的父權在那樣一個封閉的空間中無處不在,并成為一種凝視的眼光和規范婦女言行的道德話語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當權力把身體和情感納入一種體系化的規訓體制中,這種社會空間就成為一個道德空間。”因此,這些被拐婦女在失去人身自由與剝奪話語權之后,牢牢束縛于由男人構建的農村道德空間之內,男人所構建的道德空間只是針對女性的生存空間而言,對男人的生存空間不會產生任何威脅,他們依舊是道德空間、生存空間的主導者,維護著自我男權社會與男人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但這些被束縛的農村女性卻把這種道德空間當成既定的規范與行為準則,她們依附、順從,維護男人構建的道德空間秩序。如《盲山》中的白雪梅與鄉村教師黃德誠相遇,白雪梅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這個男人身上,但是黃德誠面對表弟對表嫂的“錯愛”、表弟對表哥的愧疚、自責、兩個家族之間潛在的矛盾等傳統的道德秩序,最終未履行將白雪梅帶離山村的承諾,而是默認了山村陳舊的倫理與道德秩序,將白雪梅拋棄在大山之中,自己從農村出逃。這也暗示著男人永遠掌握著主動權,他們可以沖破道德空間的網絡,選擇逃離、出走,掙脫道德的束縛,將所有的指責謾罵留給女性——像白雪梅一樣的女人。同為被拐婦女的陳姐在男權中心的威懾之下,逐漸認同并且屈從于男權社會的生存規則,尤其是陳姐有了孩子之后,逃離的愿望逐漸消失,成為男權游戲規則的守護人,并勸說白雪梅留在山區。“而對不愿意接受規訓的人,謾罵和否定首當其沖,甚至沒有人愿意去改變這種狀況,因為她們的存在破壞了空間中的某種道德持續,對權力形成一種挑戰。”福柯認為規訓是現代社會權力的核心,發生作用的對象是身體,被拐婦女白雪梅、紅霞長期遭受暴力、虐待與侮辱,男人對她們進行肉體與精神的控制,這些男人通過暴力完成對被拐女性的身體控制與身體懲罰,將她們幽禁在男權主義的道德空間之內。
(三)被看的欲望表達
電影敘事是根據男人意志進行的敘事,因此,在電影的敘事中男人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正如女性主義理論的先驅者勞拉·穆爾維所說:“電影的凝視是男性的,電影以男性欲念建立敘事,導致女性的缺席。”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對被拐農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凸顯了“看”與“被看”的欲望表達。在《盲山》《嫁給大山的女人》《喊山》等電影中所塑造的被拐農村女性形象,電影導演將她們置于男人“看”的視域之中,尤其是電影中某些大尺度鏡頭的呈現,如白雪梅被黃德貴父母按在床上,由黃德貴完成對白雪梅的暴力強奸行為,導演在這一敘事過程中,對女性身體的“看”具有雙重意義,一是犯罪現場中當事人對女性身體的“看”,這種“看”是在銀幕幻覺當中,角色彼此之間的看;二是影院里的觀眾對女性身體進行“看”的二次重構,需要將自身從銀幕中剝離出來,從而獲得視覺快感。勞拉·穆爾維認為:“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看的快感不平衡地分布在兩性之間,形成男性=主動和女性=被動的兩極化模式。決定性的男性凝視(gaze)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到女性人物身上。”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地位不對等是與生俱來的,正如女性身份與性別均以男性身份與性別為參照系而得以確立,“看”與“被看”也是以男人視域為中心形成的不對等凝視,使男人的窺淫癖與性欲望得到滿足。男女雙方也正是通過看與被看、凝視與被凝視的方式,將這些被拐的農村女性繼續放置在男人的視域中心,歸屬于男人構建的社會秩序之內。
三、女性農民工形象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農村女性的自我意識與獨立意識逐漸覺醒,為了實現家庭與個人的發展,農村女性從原住地流動至城鎮務工,流動比例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2018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較上年增長0.6%;其中女性比例34.8%,較上年提高0.4%,女性農民工總量持續增長。”中國電影對于女性農民工形象的塑造,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便初露端倪,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在農村地區出現了勞動力過剩而沿海及發達地區勞動力資源不足的問題,這一時期大量的農村人口涌進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助力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時期電影中塑造了諸如《黃山的姑娘》中的保姆龔玲玲,《公寓》中的保姆秀娥、小琴、玉芬和惠芳,《給咖啡加點糖》中的補鞋妹林霞等女性農民工形象。“這一時期的電影對于改革開放帶給農民工的機遇與挑戰做了較為客觀的反映,真實地再現了改革思潮下的農民工主體對鄉下封建婚姻的逃離、對繁華都市的向往以及打工過程中所受到的猜忌與不信任。”而在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塑造的女性農民工形象相對前一時期的女性農民工形象而言,更能反映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女性農民工的邊緣地位與弱勢形象,在現代性語境中女性農民工的種種焦慮與失意。
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對于女性農民工形象的塑造,一方面,體現了新世紀農村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自我意識的獨立,開始改變依靠男人實現救贖的歷史地位,她們不再局限于農村狹小的生存空間,試圖逃離男人中心主義的生存困境,她們積極實現自救。例如影片《碗兒》《安居》中塑造了碗兒、珊妹吃苦耐勞、積極奮進的女性農民工形象;影片《所有夢想都開花》《女模特的風波》中塑造了林芳、春杏積極向上、與命運抗爭的女性農民工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農民工受到現實困境與心理困境等因素的影響,遭遇性別歧視、職業隔離等不公平待遇,并且缺乏一定的生存技能,她們在面對城市燈紅酒綠、車水馬龍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時,隨波逐流,從而在城市沉淪,迷失自我。“當她們面對‘我是誰’‘我是怎樣的’的問題時,社會生活經驗重建的考驗、‘顯著性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影響讓女性農民工難免陷入身份的焦慮。”在這一背景下,女性農民工從農村出走之后,在缺乏生存技能與生活保障時,只能憑借自己年輕的資本與肉體姿色將自己標注為可交易的物品。“在市場經濟時代,任何東西都被貼上了可交易標簽,長期作為男權文化下的凱覦者的女性很容易被標的為欲望投射的對象,成為被消費和玩弄的對象。”這里的“物化”不再是前文所說的男人對女性操縱下的物化,而是農村女性在城市生活的激流之中自我貼上“物化”的標簽,雖然在這一交易活動中,男人依舊扮演買方角色,但是和男人強迫女性“物化”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一個是暴力操控原則,一個則是自愿原則。如電影《租期》中在欲望都市中出賣自己身體的農村女孩莉莉;《泥鰍也是魚》中的男泥鰍說服女泥鰍“晚上一起睡覺做個伴”,從而兩人組成“臨時夫妻”關系;《蘋果》中在酒店做服務員的劉蘋果,被老板性侵懷孕,并以此為籌碼和老板進行金錢交易;《工地中的女人》中來自四川的打工妹玉蘭,是包工頭杜昆包養的眾多情婦之一。這些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農民工將身體作為代價與男人進行交易,從而成為她們扎根城里、賴以生存的籌碼。
新世紀初期電影塑造的女性農民工形象初具女性意識形態,如:不甘駐留農村,不屈從于男人構建的社會秩序。“這是一種相當清晰的反抗意識,一種決不甘居‘第二性’的姿態;但它又無疑是一種謬誤與臣服的選擇:它不僅仍潛伏在地接受了男性文化的范本,內在化了一種文化、社會等級邏輯,而且它必然再度成就了對女性生存現實的無視或遮蔽。”影片中的農村女性并未意識到逃離農村之后,在城市里卻闖入更堅不可摧的男權社會。如影片《不許搶劫》中楊樹根的老婆梅花跟城里人離開了貧困的農村;《上車,走吧!》中的打工女小辮子離開了農民工高明,坐上了有錢人的轎車。楊樹根與高明代表女性逃離的農村空間,城里有錢人則代表更堅固的男權話語中心,牢不可破的男權統治秩序。同時,以上影片所塑造的女性農民工形象折射出當前女性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傳達出女性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迷茫與無奈,無所適從與格格不入的生存危機,這些女性農民工的出走之路也反映了魯迅筆下娜拉的出走之路,不是墮落,就是回家。
四、農村老年女性形象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與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農村年輕人口大量流入城鎮,空巢家庭將成為我國農村老年女性主要的生活模式。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5歲及以上年齡的老年人口中,共有空巢家庭1495.79萬戶,占農村家庭總戶數的7.68%,合計老年人口約為2179.39萬人,占農村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數的32.69%。”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對農村老年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反映出當前我國存在的“空巢老人”現象以及農村老年女性的養老與贍養等問題。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老年人口高齡化,高齡人口女性化,將成為未來社會人口發展的重要趨勢”。在這種趨勢下,農村女性的養老和贍養問題也隨之而來。農村老年女性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而存在,其他年齡階段的農村女性較老年女性相比尚且有反抗與逃離的意識,而農村老年女性只能固守在土地之上,沒有反叛的勇氣與出走的能力,在生活上完全依附子女。由于子女多外出務工,因此,這些農村老年女性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產生一系列農村老年女性的贍養問題。
電影《喜喪》中子女對林郭氏的贍養問題,采取了子女共同承擔、輪流到各家暫住的方法。林郭氏的養老問題以家庭為中心,“家庭成員的活動往往圍繞著女性老年人展開,農村女性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成為家庭內部各種矛盾的中心”。在商討被贍養人和贍養方式的過程中,無人征求林郭氏的意見,林郭氏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聽之任之。全權由男人(兒子)來決定,女人(兒媳婦)也試圖參與其中,爭奪話語權之時,卻被男人拒之于外,家庭之間的矛盾沖突隨之產生。英國社會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指出:“話語與社會結構存在一種辯證關系,一方面話語被社會結構所構成,并受到其限制;另一方面話語又在身份、關系和觀念層面發揮社會建構作用。”影片《喜喪》中的林郭氏便在老年女性身份、母子、婆媳家庭關系之間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觀念的共同作用下,成為悲劇人物,最后孑然一身,孤獨終老。在《黃土地的守望》中空巢老人林奶奶的兩個兒子在城里打工,林奶奶不僅得不到兩個兒子的贍養,還要因為大兒子在城里誤傷別人的事情奔走操勞。影片中空巢老人林奶奶的生存困境是眾多農村老年女性生存現狀的縮影,主要受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快了農村年輕人口流動的速度。“由于流動而產生的空間上的隔離,在客觀上也削弱了子女所能提供生活照料的質量和頻率。”造成了農村老年女性獨居留守、“養兒防老”贍養難等問題,影片對農村老年女性的養老與贍養問題的關注,也折射出當前農村貧窮落后的現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立政之本存乎于農’。解決農村空巢老人養老困境的首要之舉就是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改善其生活水平和質量。”因此,解決農村老年女性乃至一切農村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本方法,就要采取發展農村經濟、平衡城鄉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優化農村環境等舉措。
結 語
通過梳理新世紀初期中國電影農村女性形象的類型,深入解讀塑造農村女性形象的社會化意義。“中國婦女生活的社會化使她們擔負著雙重任務,一是在與傳統觀念的決裂中證實自己作為‘社會人’的價值,二是在男女角色的沖突中證明自己作為‘女人’的意義。”這個時期電影中所塑造的農村女性形象,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新世紀初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與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并通過影像的形式記錄、展現,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農村女性形象的變遷過程可以看作整個中國女性的發展縮影,以小見大,從點到面剖析了中國女性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的生存現狀,引人深思。歸根結底,男女在生理結構上的差異是導致她們不平等地位的關鍵因素,也就是性別因素導致她們不能享受平等的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農村女性要實現自我發展,掙脫男人設置的牢籠,必須進行自我身份的認同,最重要的是對自身社會性別的認同,從性別的角度出發去爭取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機會平等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身份的認同是以女性自身為主體,是自發的,而不是由男人和社會所賦予女性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