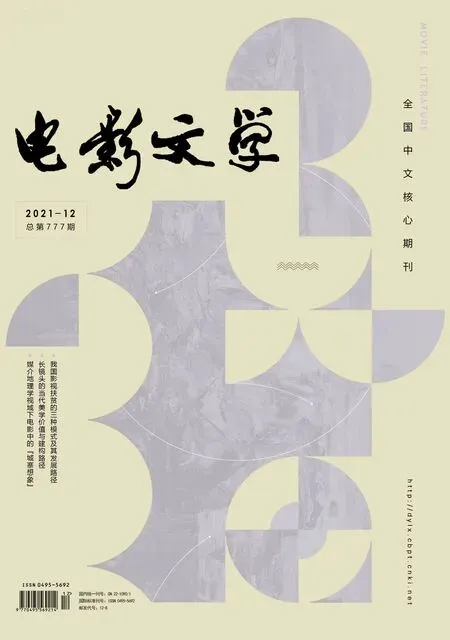文化的指向: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建構
周祥東 鄧 靜(.河北地質大學藝術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四川傳媒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四川 成都 60000)
電影藝術作為一種影像媒介,將其放置于少數民族文化記錄的視野下無疑讓是讓它成為窺視民族文化、記載民族風俗的有效載體。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充滿了書寫民族記憶、觀照族群歷史的文化意味,然而,彝族題材電影在中國電影藝術創作中始終處于一個“似是而非”的尷尬局面,作為擁有自身文字、語言、風俗、建筑風貌特征且擁有5000年歷史的一個民族,其影像創作卻呈現出了與民族發展面貌、其他樣式藝術發展速度不協調的現象。新中國成立70年來,彝族題材電影創作在中國電影創作格局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對促進民族團結、宣傳民族文化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但是近年來,彝族題材電影并未在電影創作格局中形成如蒙古族、藏族等其他少數民族一般的繁盛局面,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文化樣貌在影像中的記錄、復刻面臨“失語”之態,且在現有的彝族題材電影中,以“民族”為奇觀之外衣而缺少內核的影片比比皆是,故此,從空間建構角度去解讀、探析彝族題材電影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影像對“民族性”的把握。
空間不僅是自然的、地理的,也是社會的和心理的。電影中的空間復現,不是簡單的地理選取,而是對蘊含著政治的、文化的一種社會空間的擇取。“通過現有電影藝術畫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所描繪的生活內容以及故事發生地界——中國西南和蒙藏地理環境的結構特征,影響甚至制約著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總體特征,進而影響到其電影藝術品格的獨有風貌。”彝族題材電影中的空間選取蘊含的則是彝族文化中最為直觀的體現。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選取、空間建構對于彝族題材電影的創作而言具有著重要意義。選擇何種空間、如何運用本民族獨有的空間進行敘事,是構筑彝族題材電影獨特民族化視聽風格的首要保證。
一、彝族題材電影的敘事空間選取
從1955年《神秘的旅伴》開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彝族題材電影已然走過了60余年的光輝歷程。當電影藝術將創作的視野聚焦于彝族文化之時,彝族題材電影就勢必是一種“在地化”的審美在場,彝族民眾生存的空間場域成為展現彝族風貌、傳播觀念的重要載體,彝族群眾的聚集地、生存空間就成為一種具有在場“象征”意味的符號。然而,當代表科技力量、現代文明的電影同彝族傳統文化進行聯姻之時,彝族題材電影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多元空間”聚集地,成為一種指向文化在地的樣態,最終現代、傳統空間相互融合形成了彝族題材電影的敘事空間。
(一)傳統生活空間
空間不是一種絕對物化的外在地域性定義,它始終以一種固定的形式存在,因為空間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容器,它同人類的社會實踐息息相關。在中國少數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各民族歷史的、地理的原因早已形成了較為固定的一種生活空間,這種棲息空間的選取讓民族族群形成了獨特的生活習慣、民風民俗。事實上,從文化地理學角度去辯證地看待少數民族世居的空間,不難發現他們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間業已成為他們文化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傳統的世居空間呈現出了其與其他民族的顯著特征,這正如邵培仁所說的那樣:“即便是以文化為核心結成的空間系統,也能夠通過民族以及地理景觀的差異而呈現出具有差別的外部形態。”“彝族題材電影”這一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則就是“文化原則”,也就是說只有以彝族民眾生活為取材對象的、反映彝族文化的影片才能夠被稱為彝族題材電影。從這個原則上說,彝族題材電影堅持的就是文化秉性。
大眾對世界的認知離不開對空間的指認,因為空間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烙印!對電影藝術而言,空間是影像敘述內容發生的容器,故此彝族傳統的生活空間不可避免地成為影像選擇的重要內容。彝族題材電影對于傳統生活的空間選取主要是鄉村、山谷、山林,這些極具辨識度的地域空間配以彝族特有的民俗、服飾等文化符號再融合現實為觀眾勾勒出彝族文化生活的面貌。在諸如《奴隸的女兒》(1978)、《舞戀》(1981)等彝族題材影像中,茅草屋、雪山、寨子、藤索橋成為構筑彝族民眾生活空間重要的能指。從這些意象符號的外觀來看,這些帶有彝族文化特色的場域符號成為“彝族”題材電影的標志。因為這些傳統的空間、傳統的符號是彝族人民在千百年生活棲息的過程中運用自己獨特的生產方式產生的結晶,它既是見證、說明彝族題材電影的裝飾,又是彝族題材電影本質核心的文化心臟。
可以說,彝族傳統生活空間的擇取,是電影導演寫給觀眾的一封“情書”。影片將鏡頭對準了彝族民眾生活的周圍,用視聽解讀彝族人民文化生活的變遷,用畫面直接呈現彝族歷史與現實,最終構筑了本民族文化變遷的影像世界。雖然,這些傳統空間的擇取在某些觀眾看來是一種“浮夸”或者“臆造”的符號,但是對更多的彝族大眾而言,這些內容是他們回望曾經歷史的、傳統的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同樣地,這也是非彝族人民體認彝族傳統文化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窗口。
(二)現代生活空間
全球化的到來讓世界越發地成為一個整體,地理空間的區位界定越發模糊,傳統的生活空間勢必被強大的全球化所裹挾,傳統生活空間也勢必被現代工業文明所蠶食。傳統與現代似乎成為一個硬幣的兩面,然而事實上在真正的影像空間中二者并非一種真實的事物,只有二者相互對照、解釋的時候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才有了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意義。更多的時候,大眾目力所及之處見到更多的是一種“灰色”地帶,即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的空間,二者的相互交融讓本土文化逐步同現代文明進行了不同程度上的聯姻,本土文化也逐步呈現出了區別于原始文化的一種轉化趨勢。
電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映演,伴隨民族在現代文明中的境遇,電影中現代的生活空間隨處可見。對彝族題材電影而言,純現代化的、都市化的影像并未出現;相反,一些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交融地帶——“小城鎮”“小縣城”出現的頻率更高,小城鎮成為彝族題材電影中現代生活的空間能指。《深谷尸變》(1985)《茶花彝女》(2011)等影片就多次出現“城鎮”“縣域”,這些現代生活的空間構筑了彝族群眾在現代都市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處境。現代生活空間——小城鎮、縣域在某種程度上構筑了區別于其他類型電影的獨特韻味,這些現代空間的應用已然成為影響、推動彝族題材電影發展的核心要素。畢竟在彝族題材電影中,現代生活空間有著多重的文化指涉。一方面,現代都市文明的侵襲讓傳統的彝族文化無所適從,這是眾多導演目光投射的重點;另一方面,現代工業文明急速發展過程中的彝族人民所處之尷尬境遇、現代都市空間中彝族人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習慣的變革也是導演關注的焦點,二者都成為現代生活空間選取的重要原因。
從建構民族形象的角度而言,現代的、文明的、都市的現代生活空間,更多的是從民族處境的角度進行空間敘事的,它沒有以一種宏大的、歷史的敘事方式進行電影講述,也沒有沉浸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可自拔,而是將鏡頭對準了彝族民眾、文化學者所關注的社會命題——現如今彝族民眾的處境。用現代意識側目之窺,挖掘、剖析彝族民眾的心理,這體現了彝族題材電影創作者的責任擔當。另外,關注現代生活空間的彝族題材電影,無疑是對彝族文化進行了影像“編碼”,在保持了彝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之時,實現了同其他文化、工業文明的融合共通,挖掘出了充滿時代特征的彝族記憶!
二、彝族題材電影空間文化表達與主題展現
馬爾塞·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中指出:“電影是空間的藝術。”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電影空間,是逃脫了傳統意義上“地域”限制的,它不是一種客觀實在的自然環境、一種物理學意義上的物質空間,它是一種承載文化內涵、一種精神隱喻、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方玲玲認為:“地理學在城市景觀的展現過程中,已經不再僅僅糾纏于物質的、自然的環境地理,而是深入精神與經驗的層面。媒介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中介。”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選取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與精神隱喻,每一處空間的選取、應用都充滿電影導演的目的,自然這些空間的選取都成為電影觀眾洞察彝族民眾文化的重要維度。
(一)彝族身份的隱喻
空間是承載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它是本土性的直觀體現。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擁有一方文化,文化的體現勢必要加注于空間之上,而電影文本的空間選取,呈現是地方意識、民族意識。故此,電影的拍攝擁有了一定的特殊價值,它運用強大的光影藝術手段將地域空間放置于銀幕空間之上,運用空間所固有的風景、民俗、風俗為觀眾構筑了一個異國異域景觀。用謝爾慈(R.Sheilds)的話來說,這些仿制的地方給人制造了一種“他鄉別處”的感覺,它們使遙遠的地區和時代魔幻般地出現在人們眼前。彝族傳統、現代空間的選取讓影像成為一種充滿異域情調的文化地域。
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選取,無疑是凸顯“彝族身份”重要的符號能指。一方面,在彝族題材電影中,導演的文化身份或其他原因導致所有的影像并非都植根于厚重的彝族文化之土的,一部分電影是運用一種“移植化”的手段將故事生拉硬套至彝族生活中,希望憑借“奇觀化”“陌生化”的影像風格完成敘事。可以說,彝族文化中神秘的、民俗化的元素成為大眾文化語境下一場消費的場景,影像對彝族人民生活的描摹、空間符號的選取或曰是為了借助彝族的“他者”文化身份而引起觀眾的“窺探”欲望,彝族群眾被奴隸主壓迫、參與抗戰反特務的面貌有時是一種“他者”化的書寫,彝族空間就單單成為一種淺層次的、僅為觀眾講述影像是彝族故事所運用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值得肯定是:對于真正講述彝族文化的電影來說,彝族空間的符號選取是塑造、展現彝族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些影片成為表現民族認同、傳播彝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例如《別姬印象》(2006)等影片都將彝族空間的文化隱喻功能最大限度地進行了發揮,另外《彝文之戀》(2012)從民族文字的視角出發極大地渲染、傳播了彝族文化,彝族的文化身份與民族意識在空間的加持下得到了明顯呈現。
(二)“國族一體”與時代認同的表現
作為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我國至為重要的社會政治資源,中華民族認同的程度及其建設水平,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穩定和發展。電影藝術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它必定涉及民族團結、家國建設等問題,通過少數民族電影講述民族文化、中國故事、時代境遇是擺在電影藝術創作者面前不可避免的創作題材。從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內蒙春光》上映初始掀起的波瀾而最終毛澤東主席將其更名為《內蒙人民的勝利》來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在民族團結、國族一體、時代氣息的創作上無疑是受到多方矚目的。
“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群體對中華民族的認知、情感和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歸宿感、責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便是中華民族認同。”少數民族電影反映的是少數民族群體的生活已經成為電影創作者共同的觀念,在6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彝族題材電影也必定同時代呼吸、與歷史同行,以“國族一體”“祖國建設”為主題的影片也層出不窮。而空間是體現民族特色的有力載體,故此,彝族民眾生活的空間成為電影構筑“國族一體”社會認同的重要能指。影片《神秘的旅伴》(1955)就講述了彝族民眾同邊防軍指戰員攜手同行、同敵特勢力做斗爭的故事,“盤大媽”等彝族群眾形象的塑造無疑是彝族群為祖國解放、建設貢獻力量的生動描摹,彝族小伙朱林生最終實現自己的愿望當上邊防戰士更是凸顯了彝族群眾在時代語境下的同祖國站到了一起共同建設祖國的美好愿景。個體敘事的書寫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的是族群的記憶,是具有族群“共同體”敘事的特征的。故此,在這樣的影片中,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內容就被賦予了一種使命、一種構筑多民族國家認同的使命。除《神秘的旅伴》之外,還有《金沙水拍》(1994)、《彝海結盟》(1996)等影片都是將空間的選取當作國族一體故事講述的重要敘事載體,另外《姑娘寨》(1987)等電影是講述彝族民眾在時代背景下走向脫貧致富道路的故事,起伏的丘陵、美麗的薩尼村寨就成為影像敘事的重要空間,成為講述時代背景下彝族人生活的背景。電影是一種能夠再現、臨摹社會的媒介,能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時代語境下民眾生活的狀態,側寫時代語境下群眾的面貌,而彝族生活的空間就是反映時代語境下彝族民眾真實面貌的場所。
(三)民族文化的反思與堅守喻象
“文化”一直是電影導演在創作中秉承、堅守的原則之一,然而文化同樣也是一種易受影響、并非一成不變的生命樣態。工業時代的到來讓傳統的文化在影像中越發呈現出一種澆漓之態,中國在大跨步邁入現代化的大門之時,傳統風俗、文化語態的處境似乎處于一種尷尬的局面,暗淡與退卻、光明與重提成為文化學者不斷論述的話題。電影因為其媒介身份的因素必定涉及這樣的一個話題,即傳統文化在時代的快步躍進中要何以處之、本民族群眾堅守的民族文化究竟應當何去何從?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呈現,無疑是表現急速發展的現代工業文明同少數民族人民堅守的傳統文明之間相互影響、交融的最好手段,自然,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也因為其文化身份讓影像多了幾分“詠嘆”的色彩。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選擇永遠同文化相連,呈現出一種“人類學家”的冷峻目光,凝視著民族文化。
在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大量的民俗元素、空間景觀都不是一種簡單的民俗風情展覽,一地一物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意味。在大量的彝族題材電影中,空間不是那個為觀眾營造奇觀化、符號化的消費能指,而是一種真正的敘事符號,彝族浮光掠影的異域景觀成為探尋民族文化處境的重要載體,《花腰新娘》(2005)、《走山人》(2018)等影片就是秉承這樣的一種姿態。《花腰新娘》(2005)以愛情為敘事外衣,將彝族文化的風俗習慣、文化特征表現得一覽無余,體現了創作者對于傳統、現代的一種別樣的彝族文化思考。《走山人》(2018)更是如此,彝族人民對于大山的崇拜在影像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是對民族文化的又一次深刻問詢、頂禮膜拜。可以說在彝族題材電影中,無論是傳統生活空間的選擇還是現代空間的展現,其核心都體現出創作者在現代都市文化視域下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復雜感受,退守、前進成為創作者內心飄忽不定的選擇。對彝族文化風俗與民族信仰的深度刻畫強調的是民族文化的異質性、是對本民族傳統特色文化的一種堅守。彝族題材電影雖然并非在工業化、現代化的今天在電影市場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是憑借空間選取與文化隱喻成為電影史冊上堅守民族文化的一種鉤沉,給予了彝族大眾以精神快慰和身心滿足。
(四)民族神話與史詩傳統的復刻
“少數民族的史詩被馬克思稱為‘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的’史詩。在我國少數民族的口頭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是少數民族神話還是英雄史詩都波瀾壯闊地呈現在了大眾面前,原本早已泛黃的故事伴隨著書籍、紙張、互聯網得以再次呈現,這些史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之林中最為亮麗的一抹色彩。伴隨影像技術的更新迭代與中國電影行業風馳電掣的發展,“古老”的少數民族史詩藝術得以以“視覺”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彝族神話、史詩成為彝族題材電影重要的展現內容。若涉及此題材則必定涉及電影的空間選取,彝族傳統生活空間成為講述民族神話與史詩的重要載體,成為影像一個重要的、可見的、可辨識的內容。
一方面,文化市場的廣博胸懷讓彝族神話、史詩有了生存的空間,畢竟吸納民眾、以饗消費是電影創作的動力;另一方面,對民族神話、事實的記錄是影像作為一種媒介履行一種工具職能,即當作開展學術考察與文化表達的影像記錄和書寫工具。無論怎樣攝制這樣的電影必定離不開彝族傳統空間,《我的圣途》(2016)重復展現彝人史詩《勒俄特依》,“影片由20多年前的劇本《山神》改編而成,以一位年輕的畢摩‘尋找圣途’為主線,圍繞家族、血統、習慣法等元素再現了涼山彝族地區的民俗文化;故事情節的張力與彝族民俗密切相關;彝族的史詩傳統貫穿影片全程,對‘圣途’理想之境的探尋發人深思。”大涼山雪域高原的空間景象在影像中一覽無遺,河谷淺談、綠樹青山等地域空間成為影像有力的敘事載體。而作為少數民族神話電影代表作的《阿詩瑪》(1964)更是如此,電影《阿詩瑪》的敘事空間就是云南石林地區,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事項成為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火把節上的阿細跳月讓人看到了別樣的民俗風情,而美麗勇敢的阿詩瑪也成為彝族形象的新代表。風光旖旎的邊地空間讓彝族題材電影讓彝族傳統神話與史詩進行了復調呈現,這樣的空間選取與呈現無疑也是符合大眾審美期待的。
三、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建構路徑辨析
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讓地域直接的界限越發呈現出一種消解的態勢,地域文化場景與民族生活空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地域空間的打破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古老的、傳統的、原先的文化情境與文化規則被顛覆。在“消失的地域”這樣的語境之下,彝族題材電影必須選擇、構筑出一個真正屬于彝族人民的生活空間、突破和超越地理空間帶來的限制,在銀幕之上構筑一個屬于彝族人民的精神空間。可以說,在現如今的這種錯位與失語的空間塑造過程中,彝族題材電影必須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方能迎來自己的創作盛筵。
(一)用民族特色構筑獨特視聽符號空間
在電影這樣一個碩大的名詞里面,各類型、各民族電影一如炫目的燈光一樣閃爍著萬丈光芒,但是其中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有屬于自己的“特色”韻味,且這種具有文化身份的特色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地理空間界限的消弭以一種翩然而至之態出現在大眾面前,對于彝族傳統生活空間而言,這無疑是一種猝不及防卻又無可奈何的事件,彝族大眾也在都市化與商業化的過些中被擁躉進入城市,傳統生活空間諸如木屋、村寨一般的美麗世界逐步也被納入商業化的氣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彝族題材電影需要用影像的視聽語言構筑出新時代、獨具彝族特色的符號空間,而不是所有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選取都指向古老時期,去重現、重制彝族原生態的生活空間。
電影是影像的、視聽的藝術,故此選擇何種畫面符號、何種聲音語言是構筑電影空間的重大選擇。彝族題材電影在創作過程中必須嘗試用民族特色構筑獨特的視聽符號空間,這是電影本體創作的基本要求。在彝族題材電影中,首先要從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上進行把握,其一顰一笑是否符合彝族人的生活習慣、文化態勢,就如同《走山人》(2018)、《我的圣途》(2015)一般的彝族題材電影就是從人物入手進行把握,主人公舉手投足間體現的就是彝族文化,如果人物形象僅僅是被貼上彝族人民的帽子而沒有彝族人民的生活特性,那么這個電影是否能夠被稱為彝族題材電影尚值得深思。其次,要善用民俗文化符號。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同民俗文化進行了多維度意義上的聯姻,電影不停地從民俗文化中汲取養分,多重符號的同樣特質能夠構筑出一個獨特的銀幕空間指向,這種指向恰恰就是構筑電影類型的重要元素。彝族人獨有的服飾、建筑、風俗等都是構筑彝族生活空間的重要能指,諸如木樓、大煙斗、火把節等這些內容能夠為觀眾在銀幕上構筑一個彝族空間,這是彝族文化身份的表述方式與力證。彝族題材電影必須堅持在銀幕上構筑獨特的民族文化銀幕空間,在人物、民俗的加持下,用獨特的光影藝術與聲音特質書寫當代彝族文化的符號,這樣才是對當代彝族文化本質的折射和呈現。
(二)將“奇觀化”轉為注重影像文化空間的建構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近年來似乎是處于一個獨特的歷史年代,本民族原本的文化特質在如今都成為大眾文化語境下的一種消費冠能。民族風俗習慣成為影像中競相出現的“奇觀化”鏡像,這無疑是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的悲哀與無奈,電影創作者試圖借助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風俗與面貌撐起民族文化這桿大旗,而創作過程中則夾雜著一些“羸弱”的特質,即注重當下“利益的”投注,即展現少數民族文化特質,挖掘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色的“點”的同時不惜進行“偽文化”的創作。
當電影的鏡頭投向現代生活時,不能呈現一種“偽”現實的特質,彝族題材電影在創作的過程之中絕不能為了民俗化而奇觀化,可以說現在的彝族文化元素在電影中是脫離了原本的彝族文化面貌的,部分電影只是將少許彝族元素貼片到影像中,將火把節等彝族文化元素當成是一種獵奇符號,為了展現民族風情而運用彝族符號。自然,電影創作者為了市場票房不得不滿足觀眾的一些觀影欲望,這是可以理解、能夠認同的。但是在這樣虛幻的奇觀景象即便取得了票房,贏得了市場,但是對于民族群眾而言絕對是個人記憶的一次絕望,原本希冀遠去的民族文化能夠在影像媒介中得以再現,卻未承想影像造就了一個虛幻的民族夢境。
的確現在的電影市場成為一個“虛懷若谷”的天堂,一切能夠消費的奇觀化、獵奇化的點都被資本進行了深入挖掘、爆炒,以待大眾為之買票。但是彝族題材電影不妨將“獵奇化”“奇觀化”的影像創作態勢轉向關注電影真正的文化空間、向彝族文化更深處漫溯,就像彝族群眾獨特的質樸、詩意、豐富的生活方式都是彝族題材電影創作者可以馳騁的空間。《茶花彝女》(2012)、《彝文之戀》(2012)、《支格阿魯》(2013)等電影都在為觀眾展現不一樣民族文化風情的同時,更是關注著彝族人的文化動向與歷史內涵。這樣的選擇方式無疑是成功的,彝族文化并未成為影像奇觀化的一點,電影將整個彝族文化納入一種影像的訴說中,以一種客觀、平實的態度冷靜訴說彝族文化的文字、神話、茶文化。
(三)建構具有寫意性的彝族題材電影空間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電影的故事空間和空間敘事分別是敘事中介和敘事方式,簡單地說,敘事空間是電影中直接呈現的用于承載故事的視聽空間形象,而空間敘事是指利用空間來進行敘事的行為過程。”少數民族電影的空間選取與展現與其他電影相比是具有顯著特征的,無論是生活的地理空間還是生活器物,抑或是民風民俗都有顯著的文化特征。但是在具體的影像創作過程中,彝族文化的體現被呈現出了一種“塊狀”的狀態,即將彝族文化按照類型特點硬性植入影像中,這樣的創作模式無疑給觀眾一種疏離之感,在60余年的創作歷程中,彝族題材電影并非形成自己的類型,也沒有自己獨有的美學風格。故此,在彝族題材電影未來的創作中,要營造一種彝族文化獨有的影像空間,將彝族文化的特性凸顯于整部影片之中進而呈現出一種寫意空間,最終形成彝族題材電影獨有的美學風格。
新時期以來的彝族題材電影,無論是山林形象還是村寨風格,都在某種程度上呈現了一種彝族文化的寫實空間,這值得贊嘆與發揚,但是彝族題材電影還應當進行“寫意空間”的營造,在傳統的寫實空間之外營造一種獨特的含蓄性、隱喻性的彝族文化之美。比如《走山人》中巍峨秀麗的圣山、《茶花彝女》中唯美的夕陽,彝族民眾生活的空間躍然紙上,呈現出了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空靈之美。再如影片《我的圣途》(2015)將大涼山一帶的雪域高原同彝族民眾的信仰朝圣之旅進行融合,也就是說電影將寫實空間與寫意空間緊密地進行了結合,晨昏處處裊炊煙、牧童牛羊共悠閑與彝族民眾的信仰靈魂的融合讓觀眾無比悸動!這樣的寫意空間營造無疑是讓影片更深層次地充滿了彝族文化的氣息,這樣震撼的寫意空間也能夠讓觀眾進一步對影片進行一定思考。
彝族題材電影是中國電影藝術史冊中不可或缺的一筆,《阿詩瑪》《奢香夫人》《花腰新娘》等經典影片對于今天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依舊有著深刻影響。新中國成立70年來彝族題材電影創作的數量并不多,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來賈鐵、張蠡等人創作的彝族題材電影在今天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電影是空間的藝術,電影空間的選取有著重要的文化依據!在今天,電影的空間早已成為敘事的重要因素、成為敘事的中心,彝族題材電影的空間如何進行選取、建構,是擺在所有彝族題材電影創作者面前的一大問題。只有通過對電影空間的合理化建構,用真誠的態度、質樸的情感去關注彝族民眾歷史的、現代的生活空間,才能更好實現電影對彝族民族文化的把握,才能建立起一種彝族文化獨有的寫意空間,才能夠讓彝族題材電影創作進一步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