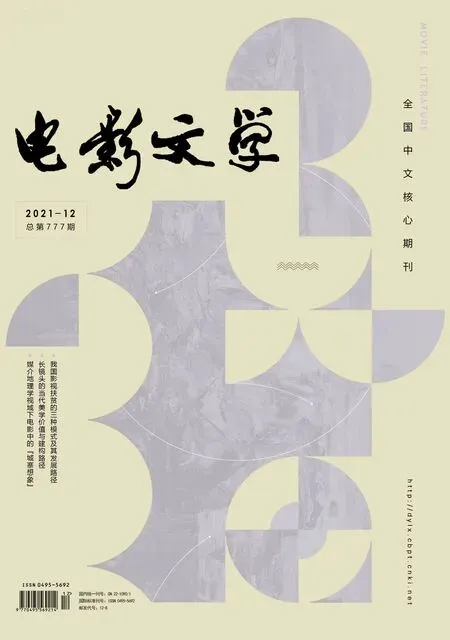論張藝謀的晚近創作
鄭 敏(山西傳媒學院表演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1)
一、色彩的詩學:由多彩的絢爛走向黑白的沉靜
作為中國重要的導演之一,張藝謀導演在中國電影創作的歷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作為電影攝影出身的導演,張藝謀的電影創作幾乎可以用顏色來進行分析和理解。從現有的作品來看,他的作品幾乎都包含著鮮明的顏色對比手法,這一手法不僅為他的電影創作打下了特殊的藝術印記,同時也代表著一種彼時電影創作的潮流。
色彩之于電影文本主要有兩種作用,首先對電影而言,影像的基本內容不可控制,因為它只能取材于現實世界,即使在視覺技術突飛猛進的當下,影像語言依舊難以擺脫真實這一要求。而對于創作者而言,能試圖改變的也就不是這一基本的語言內容,而是附加在影像之外的非現實因素,比如配樂、鏡頭效果以及表現對象等方面。而影像表現中所使用的顏色就是一個重要方面。除內容外,顏色對于電影文本的表達還在于為有限的影像賦予更深刻的隱喻意義。
從張藝謀早期作品來看,鮮明且突出的色彩是表現環境和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諸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自不待言,晚一些的《一個都不能少》更是如此。從色彩運用的創作方法看,2010年上映的《山楂樹之戀》應當是張藝謀電影創作在色彩使用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部電影中色彩的使用主要通過明與暗間的對比來強調外部環境的陰郁與主人公即將面臨的苦難,鏡頭在表現主人公形象時多用淡藍色或白色的純潔色調,加上山楂樹本身的白色花朵,更加能夠表現出主人公的愛情底色。這部電影主要創作的就是一種純潔的戀愛故事,從故事情節的客觀概括出發,這段感情并不完全是一種美好的悲劇,但是影像通過色彩的重新加工,成功回避了大多數源自日常生活的駁雜成分,最終在觀眾眼前留下了純凈、不帶有世俗浸染的感情氛圍。
從這點看,張藝謀濃烈的色彩風格在此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雖然他之后的作品也有眾多色彩明艷的例子,但《山楂樹之戀》之后,他的電影呈現出了更多含蓄內斂的抒情風格。他晚近的力作《影》與《一秒鐘》都是這種類型的作品。在這兩部作品中,灰暗的色調與光線并沒有使影片產生晦澀與壓抑的情感體驗,相反,不同顏色的運用所得到的敘事效果為正常的影像敘述提供了全新的感情內涵。
以電影《影》為例,從敘事的內容和策略上看,這部電影文本并沒有給人帶來難以磨滅的印象。故事實際上是一個失去自我身份的主人公以暴力形式重新賦予自我意義的過程。按照當下流行的商業電影敘事邏輯,這部電影只是在敘事策略之外同時實現了復調的人物塑造,并不能真正在敘事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績。但是這部電影對色彩的探索,卻使得這部商業電影獲得了更重要的藝術地位。這部電影的主人公一明一暗,雖然外貌相似,但是所背負的仇恨與堅持的立場卻毫無關聯。從身體上看,一個重傷羸弱一個強健英武,而這種身體的區別毫無意外地同時體現了兩個人物的性格特質,前者深居簡出,性格陰鷙;后者則感情細膩,忠厚果敢。人物塑造法已基本決定兩者的結局。但這部反復以復仇作為敘事線索的電影文本,其實暗藏著對自我存在的發現與確認。這種確認放置在由黑白兩色構成的影像中則構建出了完全不同的情感氛圍。黑白兩色為這種情感的外放尋求了一種沉靜的氛圍,強調人物黑與白的同時也側面說明了黑與白在人性中的混織。
顏色在電影文本中的作用有限,它通過加工影像的內在風格來營造處于某一特定環境中的人物特性,并借以營造帶有感情的敘事氛圍。但是顏色的意義非常重要。在張藝謀的電影中這種重要超出了一般電影在組織影像時色彩發揮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色彩超越了對內容的影響轉而成為結構上的某種要素。舉例來說,在《一秒鐘》這部電影中,黑白的色調并不算多,但是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戲劇沖突即主人公看到女兒的影像后被捕就是在相對色調單一的環境下交代的。在這一部分中,整體的客觀環境是夜晚,周遭光線比較昏暗,加之在電影院這一昏暗的環境中,影像的基本色調幾乎是黑色的,而銀幕上偶爾投射出的電影光線又為這一環境賦予了簡單的光亮,而放映電影本身又是黑白的,所以在這一部分的影像色調基本同樣由黑白構成。這種黑白與混沌又在敘事方面與主人公之間的和解、全片的高潮實現重合,事實上構成了這部電影的敘事高潮。
二、文化與個體:由歷史的語境走向個體的掙扎
鮮明的色彩運用除了在內容與敘述結構上具有重要作用外,也往往會與張藝謀電影作品中的中國特質聯系在一起。張藝謀的大多作品都可用一種明確的民族性特色來概括。他早期電影創作如《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和新世紀之后的《山楂樹之戀》都與中國式審美密切相關。我們可以從他的電影中找到屬于中國民族歷史的審美特性,它在張藝謀的創作中雖以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延續下來,但是從這種承續的內里來理解,張藝謀創作中的中國民族傳統間或呈現出一種非本土的眼光。
就如《影》,這部電影毋庸置疑是中國古典社會題材,影片的大部分元素與表現手法都屬于典型的中國故事,但從敘事文本的核心來看,這部電影似乎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性作品。很多接受者都把電影中最富有闡釋空間的“傘”與“刀”理解為女性的陰柔與男性的剛猛,并進一步將之理解為以傘為盾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女性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這種理解符合導演的創作意圖。以傘為盾所表現出的女性視角確實是很重要的文本特色,但是在這部電影中作者所要表現的人物不僅只有這一個,或者,創作者所努力表達出來的不是在這個歷史語境下某一個人物的生活,而是在這個歷史洪流的小支流上,一組人物群像的命運。我們可以發現電影的核心矛盾是作為“影武士”的小人物與實際掌握權威的權臣之間的身份之爭。但是電影為這典型的現代性迷思提供了一種非常古典的解決過程,首先阻礙兩者身份發現的直接阻力是古典政治權威的爭奪,這種爭奪不僅對主要矛盾的雙方產生影響,在電影文本中圍繞這一核心矛盾還有很多衍生問題亟待解決。如都督重傷無法繼續完成軍事野心與將軍之間的矛盾;又比如與皇權間的權力斗爭問題;甚至是公主對自己生活自由的爭取等,都可以構成電影敘事過程中的重要矛盾。之所以可以得到這一結論,除了在文本敘事中可以明確發現這些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敘事的高潮部分——兩國的決戰時刻,以上問題都基本得到了解決。這意味著電影所關注的問題不僅是在傳統的歷史語境下發現和解決專屬于中國民族的古典命題,而是進一步提出了更具現代意義的多元問題。這些問題圍繞著某一個人的生存提出,并且圍繞這個人物的具體生存體驗逐步地進行解答,因此作為電影當中的人物群像,每一個人都在影像構成的社會形態中尋求自我的慰藉和意義。從這一點上看這部電影所關注的就不僅是某個人的身份問題,而是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各自解決自我問題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電影中的傳統特性就逐漸被剝離了,轉而對人以及人的現代性境遇進行了反思。
文化的逐漸退場與個人生活的逐漸出現在張藝謀的電影創作過程中不是一日之功,但是他晚近的兩部作品卻可以集中體現出他作品中的這種轉變。如果說《影》中的個體書寫還存在于較為含混的語境中的話,那《一秒鐘》則完全掙脫了群像的書寫方式,僅僅就某個個體的生存進行了書寫。主人公的個體生命意識實際上也是隨著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人的關系以及對這種關系的人性的反思得以確立的。
三、表現到再現:由浪漫的意象走向現實的審視
張藝謀鏡頭中的藝術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鄉村構成的,或者說對于成熟于20世紀90年代的作者和導演來說,中國鄉村一直是他們創作的重要經驗來源。對這一類導演來說,文學與電影文本創作密不可分。當時很多小說家都以最終能被改編成電影來衡量自己小說的價值,相對應的,電影導演對電影文本的選擇也慎之又慎。在這一時期小說和電影之間借助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種非常奇妙的聯系。這一時期,文學界普遍以重構當前的鄉土社會為主要的書寫對象,其中以尋根文學為代表。但這種鄉土書寫不僅在于重現中國的鄉村特性,而是在面對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時本民族所應當做出的思考層面著力。
照此邏輯,張藝謀早期作品幾乎代表性地展現了當時文學界對中國鄉村以及民族性的探尋。如代表作《紅高粱》,就是典范的文學文本改編的電影作品,回顧其文本基礎,可以發現莫言筆下的《紅高粱家族》本就是融合了一種現代性的符號化書寫,其中對中國鄉村的描摹充滿了魔幻的意象。而在電影當中,張藝謀成功地將這種意象通過影像化的語言表達了出來。比如影片最后,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后,陽光照向山關,隨著主人公的遠走,鏡頭慢慢延伸,最終在一片紅高粱前留下一個長鏡頭。這個別有意味的長鏡頭將紅高粱這一意象強調出來。這種情況在他的作品中屢見不鮮。鄉土性與民族性通過影像語言構成了充滿闡釋空間的意象,并一道構成了張藝謀電影創作的主要風格。
但從《一秒鐘》來看,除電影影像并未使用色彩強烈、對比鮮明的手法之外,電影文本所描繪的中國鄉村相比之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就是在鄉村這一場域所代表的意義上,《紅高粱》等其他作品中的鄉村社會就如前文所說因為文學創作風潮、社會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發展產生了獨特的內在意蘊。而反觀《一秒鐘》這部電影當中的鄉村社會,鄉土更類似于一個故事發生的平臺和處所,它的故事開展有著明顯的環境要求,而鄉土社會本身有沒有對主人公產生影響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從環境與人之間的關系來看,電影中的鄉土環境并沒有直接對主人公的個體生活產生影響,真正產生影響的應當是存在于這一鄉土社會中的人。換言之,真正促使主人公在這一文本中產生改變的不是鄉土而是“社會”。
對于這部電影當中的鄉土環境與主人公之間的關系而言,主人公并沒有對這一空間環境產生過多的留戀。按照身份來說,他是一個外來者,為了追蹤自己女兒所在的電影片段輾轉多地。這一輾轉的過程當然不會使他發生個體生活的改變,文本中他脅迫放映員反復播放電影,或許是舐犢情深,但是也恰恰說明了他與當地生活所保持的距離。而導演為這個人物安排的轉變則是以他與女主人公相遇開始的。從內容上看,我們可以很明確地將這部電影歸類到父女親情等家庭類的電影類型作品中,并且主人公在文本中的主要人生意義就在于對女兒的思念。但是從電影結尾的處理上看,主人公最珍視的女兒照片已經遺失于沙漠中,那么此時主人公的生存意義已經遭到了否定,但是他重新尋找到的就是在尋找女兒的路上所結識的另一個孤兒,按照這種情感邏輯的變化上來看,主人公所追尋的人生意義從個體的親情走向了更博愛的人性的感情。在這一過程中,與此前的創作不同的是,作者為這一人性感受的獲得提供了很多來自鄉土的消極因素,這些消極的方面自然不同于早先創作時對民族性的表達,甚至在文本中并沒有過多地對此進行批判和渲染,人性的問題在這里被沉淀下來不僅進行著反思,更多的是一種觀察的角度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