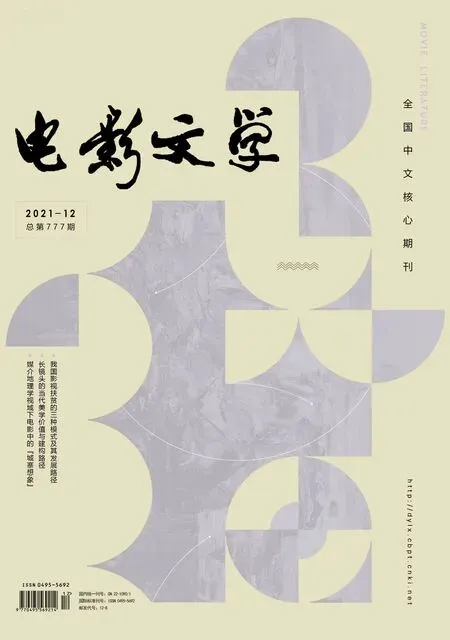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八佰》中的“圍觀”視覺話語建構
潘萬里(廣西藝術學院人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7)
應云衛(1938年)和丁善璽(1975年)均以《八百壯士》為名,將四行倉庫戰役搬上過銀幕。《八佰》作為華語電影史上第三部改編四行倉庫戰役的影片,相對于前兩部影片,其突破主要體現在對該戰役的獨特性即世界上第一次被全球錄播的精準把握上:它不僅以多目光交織、多視角交叉敘事的方式來凸顯這種“被觀看”性,而且還試圖以對戰爭的“觀看”本身作為影片的敘事母題和劇情發展動力。由此來看,我們就不會覺得奇怪,為何影片中會充斥著大量的、各式各樣的視覺媒介,如望遠鏡、攝像機、照相機、探照燈等。這些視覺媒介不僅是作為一種視覺工具,而且它們“在引導和講述關于四行倉庫的英雄敘事。并且整個南岸百姓的眼睛及他們的視覺工具,還決定了北岸敘事話語開啟的時間、入場的觀眾以及參與的道德必要性”。可以說,這些視覺媒介背后代表著不同的敘事視點、敘事立場以及由此建構而來的視覺話語。本文將以影片中存在的不同類型的視覺觀看為突破口,來探析《八佰》中存在的“圍觀”視覺話語,也即“目光詩學”。
一、遠點互視:“看與被看”中的啟蒙救亡
在中國長達十四年的抗戰歷史中,曾發生過難以計數的著名戰役,為何規模相對不大的四行倉庫戰役卻成了導演們競相改編的題材?四行倉庫之戰的獨特魅力或者說魔幻之處在于,它是全球第一次被現場紀實錄播的戰役。而這種近距離的觀看和拍攝之所以可能,主要得益于當時上海作為半殖民地狀態的地緣政治空間:以蘇州河為界,北面是四行倉庫及日軍攻陷區即戰役發生地,南面則是被歐美各國瓜分且實際掌控的租界區,也是日軍暫時不敢進攻的區域。
《八佰》巧妙地將這種地緣政治空間轉換成了帶有魔幻色彩的影像敘事空間,影片開始不久就運用了一個無人機拍攝的360度大全景俯拍鏡頭,該鏡頭在表現兩岸不同境遇時有意識地在畫面色彩和音效方面制造了強烈反差,拍攝南岸時呈現的是霓虹閃爍的燈火輝煌和舒緩曼妙的歌女悠唱,當鏡頭轉向北岸時畫面則變成了慘敗陰暗的斷壁殘垣,聲音也變得令人急促緊張、不安壓抑。鏡頭配合著謝晉元的那句臺詞,“那邊是天堂(租界),這邊就是地獄”很好地建構了影片的敘事空間。
這種基于地緣政治建構起來的敘事空間,為蘇州河兩岸的相互觀看提供了可能性。并且影片還通過北岸戰役區和南岸租界區的遠點互視、“看與被看”實現了兩岸情節敘事上的巧妙互動和有機融合。這也是《八佰》與之前的改編所不同的地方,它并沒有將敘事的焦點完全定位在北岸四行倉庫,而是在完成戰爭敘事的同時,還“以租界宏闊的生活場景與眾生世相的情感轉變傳達并闡述著某種深刻的思想意義——對覺醒性的反思”。即是說,南岸租界區的圍觀群眾在影片中也成為“被觀看”的對象,觀看者則主要是被圍觀的南岸“八佰壯士”,他們“觀看”著自己的“被看”。透過戰士們的目光,影片見證了南岸國人在戰役推進過程中如何由麻木變得覺醒。
當四行倉庫戰役正式開始前,逃去南岸的國人目睹了國軍的全面潰敗,表現出了極度的冷漠。戰役開始時,南岸的國人因為擔心戰火傷及自身,而對“八佰壯士”的抵抗發出質疑和責難。甚至,當戰爭進入白熱化狀態,大部分群眾開始覺醒時,還有南岸的“看客”將戰爭的輸贏攢作賭局。顯然正是在這種對“看客”觀看的“回視”中,影片完成了對“國民性”的批判性寫照。
當然,影片聚焦南岸群眾的“觀看”的目的不止于批判,而是要在刻畫“國民性”的基礎上實現啟蒙救亡。南岸國人看到北岸戰士為阻止敵人爆破樓體而奮不顧身負與敵人同歸于盡時,內心無不受到震動。當“八佰壯士”抵擋住日軍的進攻,使得日軍三小時結束戰斗的企圖破滅后,又隨之而歡呼。直到最后戰士們在日軍的槍林彈雨中悲壯撤退時,原來圍觀的國人紛紛沖破封鎖去接應,最終實現了精神上的救贖和升華。
另外,通過兩岸之間的遠點互視而實現啟蒙救贖的不只是南岸國人,還有北岸的雜牌軍戰士,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和南岸旁觀的國人一樣,認為這場戰役與自己無關。而他們得以實現啟蒙的動因,不僅有來自長官的規訓引導和戰友們之間的相互感染,還有來自南岸投來的“凝視目光”。因為“觸發主體進入象征秩序的東西不僅有言語或他者的話語,而且還有他者的看或凝視,因為那在看我的人已經是象征秩序的一部分,他們對我的看是象征性的看”。
上述觀點,在“端午”和“小湖北”兄弟二人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驗證,最初當他們目睹了至親被日軍殘忍殺害后,依然對這場戰役存在著很多困惑。但是,當“端午”癡迷而凝望南岸歌女,逃跑時被后者投以崇拜的目光時,他似乎找到了要成為英雄的成就感。最終他在“山東兵”的規訓和引導下殺身成仁。而其堂弟“小湖北”在多次凝望南岸表演的戲劇《長坂坡》及目睹了兄長的離去后,在其想象的世界里面兩次出現了長坂坡趙子龍孤軍殺敵的場景。
無論是來自歌女的認同“目光”,還是戲劇《長坂坡》的表演,它們都是南岸國人受到“八佰壯士”英勇感人的壯舉之后的反饋,或者說前者對后者的“觀看”,使得其“目光”的回視被納入到了啟蒙救亡的象征界之中,并且它還反向刺激和召喚了雜牌軍戰士完成了同樣的啟蒙救贖。而且在這種“看與被看”的相互砥礪中,有的南岸國人還打破了這種遠點互視的關系,他們在愛國主義熱情的感召下,加入了北岸的抗戰之中。
顯然,《八佰》立足于歷史真實,巧妙地將地緣政治空間轉化成了視覺觀看的影像空間,不僅完成了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同時還在兩岸遠點互視的“看與被看”中建構了啟蒙救亡的視覺話語。
二、高點俯視:殖民他者的旁觀見證和無效救贖
如果說《八佰》對蘇州河兩岸的“圍觀”場面的視覺建構,屬于對歷史事實的真實改編。那么影片中出現的乘坐飛艇占據視覺制高點的西方軍事觀察團則屬于藝術虛構。當然,這種藝術虛構又并非完全的憑空捏造,因為在當時蘇州河南岸確實存在歐美各國的觀察員和新聞記者。他們利用手中的攝影機、照相機、望遠鏡等視覺媒介,在同步觀看和記錄著這場戰役。而之所以虛構出一艘承載西方軍事觀察員的飛艇橫亙在蘇州河上空,導演管虎的說法是“我們拍的畢竟不是紀錄片,我們需要構成一種魔幻感或者是荒唐感”。但其實,飛艇不僅可以作為影片精心打造的東方夢巴黎的代表,同時還具有很強的政治隱喻色彩,“將‘飛行船’斷為‘二十世紀之世界’的主宰,而且將其與‘殖民之地’相聯系,這一思路在晚清相當普遍”。顯然,這與西方軍事觀察員的身份也十分匹配。
虛構的飛艇不僅為影片營造了一種魔幻感,同時其背后的殖民者的身份隱喻,將西方他者的觀看和南岸普通國人的觀看進行了有意的區隔,并且還在無形之中建構了一種視覺等級秩序。其中“位置越高越掌有敘事話語權。如最厲害的就是高懸空中、360度視野的世界軍事觀察團,他們有決定這場保衛戰呈現價值的話語權。然后是有著專門席位的英美記者觀察團,他們有專業的觀察設備”。這兩類西方殖民他者的觀看因為占據了有利位置,可以同時從高點俯視北岸戰事和南岸“看客”。
這些位居高點擁有“上帝視角”的西方殖民他者,不僅是作為第三方的旁觀者相對客觀地見證和記錄著四行倉庫之戰,同時他們也是這場戰役的間接參與者,甚至還對這場戰役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四行倉庫戰役背后的政治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這些高懸于頭頂的西方軍事觀察團和河對岸的新聞記者們告訴世界中國軍隊還在抵抗著日軍侵略,從而能夠在布魯塞爾國際會議上爭取英美各國更多的支持。也如黃曉明飾演的特派員所說,這場戰役就是“表演”給西方人看的。
雖然我們看到處于南岸高點的西方媒體,它們在觀看和記錄四行倉庫戰役時保持了新聞報道的客觀中立態度。但是,當他們看到對岸“八佰壯士”的英勇壯舉時,內心一樣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再加上日軍將炮火引自南岸傷及平民時,他們更是義憤填膺。可以說,這些媒體在情感上更傾向于同情中方,只不過旁觀者的同情歸同情,他們無法兌現國民當局給予的期望,事實證明這個愿景在布魯塞爾會議延期召開時破滅了。因為“戰爭背后都是政治”,而政治背后則是利益的計較和考量,而非絕對正義。
如果說作為殖民他者的西方觀察團和新聞記者們的旁觀見證,無法實現對四行倉庫戰役乃至中國抗日戰爭的有效救贖。但是,他們卻在無意中起到了道德審判或者說“國民性批判”的作用。當西方軍事觀察員看到南岸群眾麻木圍觀北岸戰事時,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看看南岸這些人,就像在看戲一樣。”“看戲”一詞顯然是說南岸的國人是站在一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立場“觀看”這場事關民族生死的戰役的。而站在南岸高點的西方人也曾對售賣情報的方記者發出過類似的責問:“看起來這場戰爭和你一點兒關系都沒有。”很顯然這些話無論是對于方記者還是其他麻木的國人來說都是極具諷刺意義的。
顯然,位居高點擁有“上帝視角”可以俯視南北兩岸的西方殖民者,雖然在情感上更傾向于同情中方,同時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批判麻木的國人。但他們只是作為旁觀者“觀看”,無法實現有效的救贖。
三、散點平視:“小人物英雄”群像背后的國族認同
如果說上述遠點互視和高點俯視屬于影片內部人物角色的視線安排,那么整部影片在塑造人物角色時多采用了散點平視的多視點交叉敘事,也即是“大攝影機”的敘事視角。這里所謂的“散點平視”是指影片拍攝時不是以一個或兩個主角的視點貫穿全片,其敘事視角在不同的人物之間流轉,而且多以單機拍攝的形式和有限認知的主觀視點完成影像敘事,也即是說這類視點與人物之間是處于平等關系,攝影機和人物所知一樣多。這類視點和上述前兩類視點一樣,使得影片在影像敘事方面明顯不同于以往類似題材的影片,尤其是類型片。
《八佰》所采用的這種散點平視的敘事視點明顯是反類型化的,因為在整部影片之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碎片化的,這在類型電影中是極少出現的。因為這樣的反類型敘事會使“觀眾有不適感,帶來的人物是散點式的群像。每個人都要記錄特別難,沒有男女主角,全是各色人等”。而影片為何要冒這樣的風險呢?因為在管虎導演看來,他所要關注的“不是戰役,而是戰役中的人,普通的個體。……有溫度有人性的人”。所以《八佰》拋棄了一般戰爭類型片中頂著主角光環的個人英雄,選擇由戰役中占大多數的普通個體即“小人物英雄”群像來完成影片敘事。
那么,這種由眾多“小人物英雄”為主所構筑的碎片化的主觀視點,在戰役敘事的客觀性上會不會弱于類型電影的全知視點。從表象上來看似乎如此,但是從能否深入戰役內部肌理對其進行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人物形象的情感認同的角度來看,前者并不弱于甚至更勝于后者。類型電影中的全知視角多是以聚焦和塑造主角人物服務的,而且其情感認同也多集中主角身上。某種程度上這種全知視角反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情感認同也會顯得單一和獨斷。相反,散點平視的多視點交叉敘事反而能夠通過不同角色的視角來拼湊一個完成的敘事架構,同時“讓觀眾的眼睛受到限制,反而更接近真實生活中的視覺感受,更能產生身臨其境的效果”。這樣散點平視的敘事視角則可以通過不同人物視點展開多維度敘事和實現多面向的情感認同,更能深入到事件敘事肌理之中進行內部反思。
而電影《八佰》實現了對同題材類型電影的超越,它“通過還原歷史情境的影像質感、多重轉換的視點調度,以及柔和、寫意而富有沖突美感的光影處理,外化劇中人物的心理感受,從情感體驗的層面引導觀眾和影片敘事融為一體,將觀眾帶入影片所建構出的詩意的精神世界之中。觀眾不僅能夠從不同人物的主觀情緒中體會到戰爭的殘酷、壓抑和絕望,而且也能夠從多重視點的轉換中對這一場戰役及其背后的政治意義和復雜人性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
那么上述由散點平視的影像敘事所衍生出來的對戰爭中的人性反思和“詩意的精神世界”在影片中是如何落實的呢?其最終的目的是什么?
在影片中出現了不少肩扛或手持攝影的跟拍鏡頭,尤其是在表現戰爭場面時,整個拍攝基本上都是貼著人物進行的。不僅營造了一種代入感極強的緊張氛圍,而且還在這樣的氛圍中展現了眾多小人物不可預期甚至是毫無征兆的死亡,很好地展現了戰爭本身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在其威脅下的眾生相:大義凜然敢舍生取義的、外強中干且膽小懦弱的、滿腔熱血卻臨陣退縮的、成長蛻變后殺身成仁的等,絲毫看不出類型電影中刻意化的安排。
除此之外,有時候影片還會通過設置一些具有特定意味的象征意象來強化人物背后的情感觀念,如影片中幾乎貫穿始終的“白馬”意象。還有與之相比較為具象化的意象,如上文提到的“小湖北”的由對戲劇《長坂坡》聯想到的趙子龍孤軍奮戰的場景,它們寓意著一種家國民族的希望和力量。《八佰》以這樣的帶有主觀情感抑或詩意化的影像敘事,將觀者代入甚至沉浸到了眾多真實可信的小人物的精神情感世界之中。
然而,影片通過散點平視的目光流轉最終并不只是為了塑造多樣化的單個“小人物英雄”形象,而是要在實現對其情感認同的基礎上完成英雄群像的塑造,進而完成建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敘事。具體到“《八佰》中,導演管虎用對家國精神和民族情懷的集體性認同來替代對單個角色的認同構建,通過一些象征性意象,在潛移默化中給觀眾以心理暗示,強化觀眾對這場戰爭背后所蘊含的群體性、民族性的認同感”。
這在升旗和最后撤退兩個橋段體現得最為明顯,升旗時當謝晉元團長訓誡后戰士們喊出了“中華不會亡”的呼聲,引起了南岸觀眾的共鳴和吶喊。而撤退時,南岸的國人基于對中華民族家國觀念的認同,而向槍林彈雨中的“八佰壯士”伸出帶有“希望之光”的雙手時,他們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其后民族抗戰的“火種”。顯然,這才是影片進行散點平視敘事所要建構的視覺話語也即是最終目的。
雖然在《八佰》之前,《南京!南京!》就已經采用過類似的交叉視點敘事的方式,但是相比之下,前者的敘事視點和結構更為復雜。而且與之不同的是,《八佰》是以對戰爭的“觀看”或者說“圍觀”為切入點展開敘事安排,它帶給觀眾的視覺體驗是對“觀看”本身的觀看,這在中國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上都是一個大膽且有益的嘗試。基于此,本文嘗試提煉和總結了影片中大致存在的三大類型的“觀看”視點及其背后的視覺話語即“目光詩學”的建構。而對影片中存在問題,如煽情過度、“圍觀”背后的情感認同的機制的同質化以及敘事結構反類型化所帶來的風險等問題并沒有展開,對此可另行文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