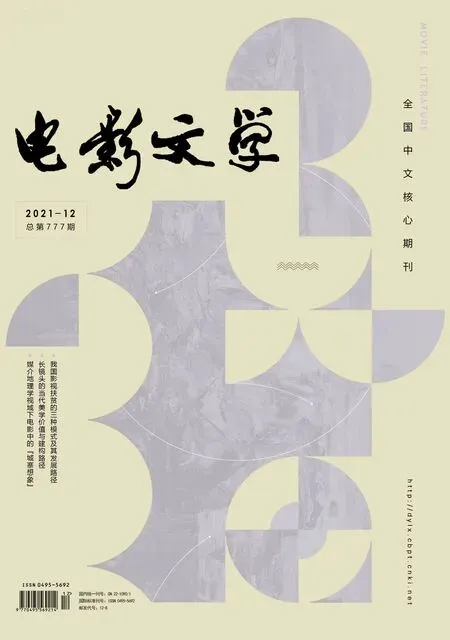論《盜夢空間》對現實的隱喻性構造
李慶麗(長春大學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1)
英國導演克里斯托佛·諾蘭的電影《盜夢空間》以精神分析為基本的敘述視角,融商業抱負、動作場景以及哲理性思考等現代電影的各種基本話語和敘事元素為一體,它內蘊的獨特的世界觀設定以及所呈現出來的創造性的敘事美學不僅極大地拓展和充盈著我們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感知,而且從根本上觸及了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和敘事話語對精神、實在甚至是整個現代世界進行思考時所可能達到的基本的思想邊界和本質性維度。從表面上來看,《盜夢空間》這部電影從頭至尾都圍繞著盜取、植入、構筑以及喚醒等各種關于夢和潛意識的話題展開,貫穿和攝取電影的各種敘事線條、情節脈絡以及人物定位的內在邏輯,也同樣以精神分析理論所提供的思想背景和思考框架為基本支撐,但是電影的真正主題和思想抱負卻落腳于對現實本身的哲理思考和藝術拆分。通過電影《盜夢空間》的美學觀賞和思想洗禮,我們正承納并踏入或者已經承納并踏入了一個全新的“現實”,本文意圖通過以下三個方面具體闡述和剖析《盜夢空間》所給予的這種全新的現實觀念。
一、現實與夢境:《盜夢空間》的世界觀設定
世界觀設定是一部電影展開藝術敘事的基本前提,它不僅作為某種前置的宏觀思想背景和感知的底層結構懸臨于整部電影敘事之上,而且是規制和整合電影敘事的內在邏輯框架。無論是情節的安排、觀念的呈現、人物的定位還是沖突的制造都離不開這種內在邏輯對電影敘事過程的攝取和整合,“被理解為敘事人物的人,是不同于其‘體驗’的存在同一體。恰恰相反:它分有了敘述故事自身的動態的同一性體制。敘事通過構建敘述故事的同一性,構成了人物的同一性,我們可以稱之為他的敘述的同一性。正是敘述的同一性造成了人物的同一性”。因此,澄清《盜夢空間》的世界觀設定應該成為本文具體分析這部電影的敘事邏輯和觀念指涉的首要目標。
《盜夢空間》這部電影的世界觀設定基于由弗洛伊德開創的精神分析理論。電影的主人公柯布是一個極富天分、技藝高超的“盜夢者”,他擅長潛入他人的夢境去獲取他人內在的真實想法,通過一種精神的同步介入實現對他人思想和行為的真正干預和塑造。這個觀念設定的有效性就源于精神分析學說對夢和潛意識的全新界定和闡釋。弗洛伊德認為“夢是一個(受壓制的或者被壓制的)欲望的(偽裝)的滿足”,“夢的內容乃是欲望的滿足,而夢的動機卻是一種欲望”,從根本上來說“夢是一個人與自己內心的真實對話,是向自己學習的過程,是另一次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人生”。在弗洛伊德這里,夢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雜亂無章的意象、觀念和情緒之碎片,而是有其內在的邏輯和意義,這種意義可以通過對人的心理或者意識結構的重新發現和認知得到澄清,這個人類心理或者意識的本質性結構就集中體現在他的潛意識理論之中。通過夢的解析所敞開的這個潛意識領域就為《盜夢空間》這部電影的觀念設定、情節推進以及人物解說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藝術敘事空間和內在的敘事邏輯。
具體而言,如果以傳統的意識或者心理學為背景設定,則“盜夢”的設定就失去了意義和有效性。這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對于傳統意識或者心理學來說,夢是完全無意義、無邏輯的意象、觀念、情感之碎片,通過盜夢獲取別人的真實想法并無可能;其次,以理性觀念為主導,傳統的意識或者心理學認為對他人觀念和行為的認知和獲取可以通過對普遍的意識和行為結構的分析得到澄清,如此一來,則“盜夢”也毫無必要;最后,傳統的意識理論和心理學基本的思維邏輯必然導致內在和外在、心理和現實的主客分立和對峙,在這種分立和對峙之下,夢和現實、內在和外在之間的關系或者歸結于完全內在性的理性燭照,或者歸結為完全外在性的行為歸納,兩者之間缺乏相互侵越、相互映射之本質性關聯和內在性路徑。在《盜夢空間》這部電影里,卻時時體現出現實和夢境之間的相互牽連、相互侵越之基本情狀,這也是電影對“盜夢”并通過“盜夢”實現對他人行為的內在介入和干預這個敘事邏輯之設定的基本前提。在電影里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筑夢、偽裝還是喚醒過程中,對夢境與現實的對設以及相互纏繞狀態的指涉時時閃現,并且成為“盜夢”得以可能的前提以及左右“盜夢”成敗的最為根本的因素,這一點將隨著電影中“盜夢”之具體過程的展開呈現出來。
二、盜取與植入:潛意識的譯寫與呈現
《盜夢空間》這部電影采用的是非線性敘事,采取這種敘事手法與電影主題息息相關,正因為夢境與現實的相互侵越之情狀,所以“盜夢”敘事不能采用依據故事情節現實進展而推進的線性敘事。電影對某現實事件按其發展邏輯、時間進展、自然結構敘事時,稱之為故事再現;而經過一系列的藝術重組后的結構化事件,稱之為情節。由于這一特性,電影的意義生成和生產都是面向現實社會開放的,一方面電影的情節安排源于現實,另一方面正因為電影源于現實,其隱喻意義也能在現實中找到映射,甚至可以利用情節和敘事安排掌控整部電影的精神與意志表達。從根本上來說,電影采取的敘事手法主要依于夢境的不同層次和“盜夢”的不同面向展開的,這就涉及電影里所說的夢的盜取和植入這種“盜夢”過程的相互疊合、相互詮說的雙重結構。無論是盜取還是植入都涉及對他人潛意識領域的侵入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他人夢境的構筑。
正如電影中所言,如果所構筑的夢境過于光怪陸離則會導致他人能夠易于辨識夢境和現實,從而導致盜夢失敗;如果所構筑的夢境過于逼真則會導致盜夢者易于迷失于夢境之中,增加喚醒之困難,同樣容易導致盜夢失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盜夢”過程的相互疊合、相互詮說的雙重結構正是夢境與現實的相互指涉、相互侵越的世界觀設定符合邏輯的結果。在電影中,為了解除自己的被通緝狀態,柯布接受了齋藤關于侵入全球最大能源公司繼承人費舍夢境的“盜夢”指令,與單純的夢境侵入不同,柯布提出了通過在費舍的夢境中植入某種夢中之夢的想法,并且通過新的盜夢團隊實施了“盜夢”過程。我們在這里暫且不分析柯布自己的私人性考慮,而把思考集中在盜取與植入這一雙重結構之上。拋開具體的盜夢過程來說,這里對夢中夢以及夢中夢中夢的層級設定和套接,本質上是對通過釋夢過程實現的對精神和心理底層的潛意識結構不斷開掘和沉潛過程的隱喻性指涉。在精神分析看來,既然潛意識領域不能依據理性原則實現完全外在的澄明和獲取,那就只能通過夢的解析實現向自我的潛意識的、本能性的原始欲望的敞開來展現,正像弗洛伊德所言,精神分析的本質是與自己內心的真實對話和敞開。
《盜夢空間》對夢主潛意識自我防衛機制的說明以及對筑夢師自我精神映射的敘述,實際上正指涉著意識自身的自我防御機制以及由于壓抑所導致的創傷性情結固著化,筑夢師對夢境的創造和人為干預正指涉著分析師對夢之解析和破譯,所以夢的盜取和植入雙重性結構是對心理或者精神的意識——潛意識之動力學結構的隱喻性指涉。雖然電影圍繞著對他人潛意識領域同步性介入和主動性塑造為主線推進情節的進展,但是從結果上來說都是最終要達到精神的自我平衡和自我治愈。以潛意識領域“真相”自我呈現為開端,以精神的自我平衡和自我治愈為結束,這完全符合精神分析的內在邏輯。正如電影里所展現的那樣,柯布與費舍最終都達成了各自所企慕的生命之救贖和精神之平衡,可以說這部電影完美地詮釋了精神分析的經典格言即“與自己內心的真實對話”。
三、夢的套接和搭建:現實的隱喻結構
電影《盜夢空間》是關于現實本身的內在結構和情態的隱喻性指涉。電影中各種夢的套接和層級正是關于現實自身的疊合、褶皺結構的隱喻性表達。通過電影采取的這種獨特的敘事技巧和藝術視角,在精神與實在、自我與他人以及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內在關聯域中嵌入夢和潛意識這種隱喻性的思考維度,能夠破除這些經典的二元結構自身的穩定性,從而藝術性地引發它們之間內在的、動態性關聯,使它們之間固有的相互牽引、相互侵越的本質性情狀向觀者呈現出來,從而啟發并拓展我們對這些議題進行感知和思考的全新維度和視域。隱喻的基本特征在于超越具體的現實關聯和物理結構,建立物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概念與概念之間的意義和邏輯關聯。隱喻能夠將兩個不同的“表象”帶入一個互動的關聯之中,這種關聯由一個詞或一個短語體現,其意義則是兩個表象互動的結果,也就是說,隱喻能夠成為一種人類觀念和生活經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語言學構型,隱喻不再是某種修辭手法,而是表征著人類思維特征和生活經驗的基本圖式。在《盜夢空間》這部電影里,夢與夢的套接及其形成的夢境的層級構造相對于現實世界與夢想世界之間的相互疊合、相互侵越情狀之間具有某種超現實、跨語境上的隱喻性關聯,因此通過盜夢和植夢過程所構筑的夢境的開放性關聯和套接本身就意味著現實通過思想或者精神之間的同步介入和內在勾連所展現出的層級化、褶皺化隱喻性結構。
由此,電影《盜夢空間》通過它的世界觀設定以及以筑夢為主線的情節推演和以精神分析的基本邏輯為津梁的敘事技巧的運用,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和關于現實的可能設想。正如我們上文所言,這個隱喻性的現實觀是以精神分析理論為邏輯構型,以“盜夢”為基本的敘事主線,既能容納各種新奇的想象和大膽的設定又具備嚴格的邏輯性和闡釋的自洽性,是藝術與哲思、想象與邏輯的完美搭建和銜接,展現了電影藝術對現實進行思考的內在深度。更為可貴的是,電影并沒有一味沉迷于對潛意識領域的獨特的呈現和對新的世界觀的抽象編織,而是最終指向對個人生存的深度思考。在電影結尾處,柯布被通緝狀態的解除不僅意味著主角與現實世界緊張關系的解除,而且意味著主角與自己生命和精神的最終和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陀螺是否停止,主角是否回歸現實并不是那么重要。因為,清醒本質上并不依賴于理性對現實的指認,而在于精神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容納關于現實自身的全新設想,精神分析的真相也不能僅僅止步于對潛意識領域的不斷沉潛和開掘,而應該指向個體與自己生命和精神的最終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