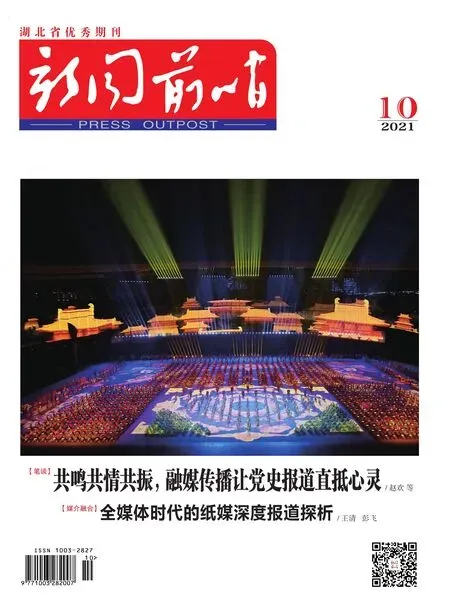互聯網媒介的功能建構及影響研究
——基于媒介環境學派的視角
王修君
一、媒介決定論與“人性化趨勢”
麥克盧漢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開篇就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認為“媒介的影響之所以非常強烈,恰恰是另一種媒介變成了它的‘內容’。”保羅·萊文森認為技術越來越像人,技術在模仿,復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他提出“人性化趨勢”理論,強調人在媒介技術中的自主能力,技術的發展是根據人的需要所決定的,人工智能的出現也是在人的需求中逐步進化而來。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媒介技術是人思維的延伸”。他認為在工業時代,“人類的延伸部分是技術元素”這種思維理解世界是很容易的,動物的延伸外殼是來源于它們的基因,人類卻不是這樣。我們的外骨骼結構產生于我們的思維……如果說科技是人類的延伸,那也是與基因無關,而是思維的延伸。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技術學派的媒介理論與網絡的現實發展做個歸納總結:網絡媒介基于人為主體而不斷進化發展的事實是不可改變的,人類與技術未來應該是呈現共同演化,共同進步,共同需要的狀態。
二、“媒介延伸論”與“新新媒介”
媒介環境學派從誕生之初就在探討技術在社會層面的影響,該學派認為人類總是處于一個象征性中介的世界中,這意味著,我們無時無刻不身處一個社會建構的價值觀、等級制和意識形態的世界。麥克盧漢甚至將“新媒介”、“新技術”稱為社會肌體的集體大手術,如廣播沖擊的是聽覺,照片沖擊的是視覺。今天的互聯網媒介以文本、圖像、視頻的形態沖擊著人類的綜合感知覺。
從政治層面來看,作為媒介環境學派的鼻祖哈羅德·伊尼斯認為“媒介的形態對社會形態、社會心理都產生深重的影響。”他指出,紙張與印刷術始終對空間感興趣,國家通過戰爭實現領土的擴展,這對西方社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互聯網媒介則使國家間的戰爭由物理的空間轉向了信息資源的掠奪,正如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今日簡史:人類命運大議題》中所提到的,“從亞述帝國和秦朝開始,各大帝國通常依靠暴力征服而建立”;然而,到了21 世紀,世界戰爭早已不再依靠占領實物資產,而轉變成知識與信息,國家之間的戰地也已從實體戰場轉向互聯網。互聯網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概念,使國家網絡安全成為重大議題。
從社會結構的維度來看,媒介環境學派認為,“在社會層面,印刷術這種人的延伸產生了民族主義、工業主義、龐大的市場、識字和教育的普及。”而互聯網媒介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比印刷術更為深遠的影響,正如網絡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在他的著作《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所指出的那樣,網絡社會對全球經濟、網絡企業、文化制度、經濟組織、就業結構、虛擬文化、流動空間、永恒時間等都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網絡社會’以全球經濟力量,徹底動搖了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或所有組織的既有形式。從知識變革的視角來看,與印刷術之于文藝復興與文化產業的影響相比,互聯網不僅改變了文化的表現形式與文化基礎,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真理、理性、倫理等文化觀念的改變,互聯網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超文本的網絡技術奠定了互聯網數字化閱讀的可能,此外,知識經濟已成為互聯網媒介環境下的重要變革。
從人際社交的維度來看,作為媒介環境學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保羅·萊文森指出互聯網媒介最大的屬性便是社交屬性,“新新媒介發明了一種線上友誼,人類擁有的家庭關系與朋友關系都能通過網絡媒介從真實世界遷移到數字世界。”萊文森還以Facebook 為范例(網站提供“朋友”、“密友”、“熟人”三個選項),指出線上交往存在著圈層化現象。這種圈層化特征在當下互聯網媒介環境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今天的幾億人利用臉書、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聯網工具聯系,兩者都是雙向的交談環境,信息沿社交關系網從一個人橫向傳給另一個人,而不是由一個非人的中心來源縱向傳播。”人類天生具備社交屬性,人際關系的建立與發展與媒介的作用密不可分,網絡圈層的產生正是基于人際之間對網絡社交工具的使用與信息的交互傳遞。
三、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術
“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中,哈羅德·伊尼斯直接將媒介變革與文明變遷聯系在一起。這位原本研究加拿大經濟學史的經濟學家,卻將目光轉向文明史和傳播史,甚至成為技術學派的創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地經歷讓他切身體會到,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擴展的文明,在研究過程中,他逐漸發現信息技術傳播除了影響社會經濟外,它還影響整個文明。
在這個基礎上,伊尼斯從整個世界文明史、傳播史出發,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他將傳播和傳播媒介分為兩類:口頭傳播的偏向與書面傳播的偏向、時間的偏向與空間的偏向。偏向時間的媒介表現在它對文化制度所產生的影響,即宗教組織;偏向空間的文明則側重于地域擴張及個人主義,即軍事政治。他指出穩定的社會需要這樣一種知識: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維持恰當的平衡。
從這個視角來看待當下互聯網傳播偏向,我們會發現網絡是具有雙重偏向的。一方面,根據伊尼斯界定的“空間偏向” 媒介特征——輕巧易運輸,互聯網通過各類PC 終端、移動終端等開始脫離媒介的物理屬性來進行符號傳輸,無疑是倚重空間的;另一方面,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將研制并普及更多耐久且永恒延續的信息存儲介質。云時代的到來已使大數據的存儲成為現實,網絡媒體也因此有了明顯的時間偏向。
伊尼斯作為“媒介技術主義范式”的先驅,從文明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媒介的偏向和強大影響。他認為文明的相對穩定性受制于社會中傳播媒介的性質和占比,就信息的組織和控制而言,每一種媒介都有一種偏向,傳播媒介的發展是社會變遷的關鍵因素之一,傳播媒介有助于文明保持時間上的持續或者空間上的擴展。
隨著互聯網對社會形態、基礎結構、心理建設等都產生深刻的影響,媒介的社會作用與歷史影響也開始成為人文社會學科主要研究范疇。在人類文明轉型的歷史中,印刷術就如同今日互聯網般掀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然而關于印刷術在歐洲普及之后的影響卻鮮有研究,關于印刷術產生的傳播革命對歐洲變革帶來深刻影響的研究還要起源于1962 年,馬歇爾·麥克盧出版的《谷登堡星漢》一書,他宣告線性展開、條塊分割的歷史研究已經過時,應該將研究重點放在印刷術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心理影響上。
總之,互聯網產生的變革影響是全球性,突破了印刷術所催生的“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歷史視角。在歷史上,作為印刷術的發源地——中國卻因當時的內在制度、文化傳統、生產方式、社會需求等多重因素而使印刷術在歷史進程中沒有成為決定性的變革動因。
然而,產生于西方社會的互聯網在傳入中國的三十多年間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互聯網對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產生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首先,在互聯網的規模效應上,西方偏向“去人化”,而中國固有的人口基數使得互聯網在人與社會的影響力上更加凸顯;其次,在互聯網受眾接納程度上,西方接受早,無疑互聯網的影響已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雖然中國處于轉型期,但受眾在接受網絡這一外來事物時規模影響呈現了裂變之勢。從媒介技術論的視角來看,搭乘網絡媒介的這趟列車將有利于實現人民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而避免印刷時代曾錯失的機遇。
以網絡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已成為21 世紀的 “太空競賽”,人工智能不僅是一次技術層面的革命,未來它必將與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教育變革、思想變革、文化變革等同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上做出了重要判斷,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新的時代意味著新的歷史機遇,就目前形勢而言,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可以說中國正在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會實現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著作《文明的沖突》中的預言——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 年或20 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 年以前東亞的霸主地位。當然,在伊尼斯看來,一切文明的興起都與媒介的使用息息相關。
結語
互聯網與人之間的關系從互聯網誕生之初就成為重要議題被討論,當下的人工智能雖然超越人類的智慧存儲與運算速度等,但它畢竟是基于人類主體的發明創造,媒介環境學派給我們提供了“樂觀”與“悲觀”的雙重視角,但我們不妨采用凱文?凱利宏觀視角上的媒介技術觀,即人與技術將共同進化,網絡的發展并不能控制人類的思維與實踐。互聯網在社會歷史進程、文化形態上產生了全球性的變革影響,且這一影響是遠遠超過印刷術的。因此,如何利用網絡媒介來實現中華民族的文明復興在新時代下仍有重要意義。
注釋:
[1](美)凱文·凱利:《科技想要什么》,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2] [7] [8][9](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
[3](以)尤瓦爾·赫拉利:《今日簡史》,林俊宏譯,中信出版集團2008 年版
[4](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譯林出版社2019 年版
[5](美)曼紐爾·卡斯特爾:《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
[6](美)保羅·萊文森:《新新媒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
[10]華進、陳伊高:《媒介環境視閾下傳播的“媒介偏向論”探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 期
[11]崔林:《變革動因與背景范式——對互聯網與印刷術社會作用與歷史影響的比較》,《現代傳播》2014 年第5 期
[12]包政:《西方為什么沒有“互聯網思維”?》,《中外管理》2015 年第9 期
[13](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新華出版社201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