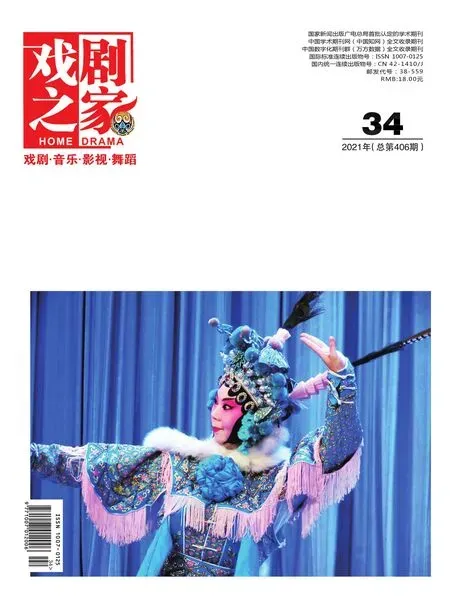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價(jià)值意義與問(wèn)題挑戰(zhàn)
艾 玲
(豫章師范學(xué)院 江西 南昌 330103)
傳承人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要載體和傳遞使者,他們以獨(dú)具匠心的技藝與強(qiáng)記博聞的記憶,掌握與傳承著我國(guó)優(yōu)秀的民間文化藝術(shù)。以口述的形式記錄生活、傳習(xí)的歷史也成了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這是因?yàn)槊恳粋€(gè)個(gè)體的記憶,都是一份獨(dú)一無(wú)二的人性檔案。這份人性在每個(gè)非遺傳承人身上表現(xiàn)為個(gè)人生活、情感經(jīng)歷、語(yǔ)言特性、心靈歷程、個(gè)性心理、社會(huì)關(guān)系、身心狀況乃至記憶方式等。
2005 年,著名學(xué)者馮驥才先生首提“傳承人口述史”的概念,并把它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和保護(hù)的新型學(xué)科領(lǐng)域和方向,廣受學(xué)界關(guān)注。2015 年,原文化部啟動(dòng)“國(guó)家級(jí)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作”以后,傳承人口述史更成了非遺保護(hù)工作中的牛鼻子。“沒(méi)有傳承人的口述史工作,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所傳承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沒(méi)有傳承人的口述史工作,我們就不可能獲得一些遺產(chǎn)中最有價(jià)值的資料,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此遺產(chǎn)的技術(shù)精髓。”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擬以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料的采集實(shí)踐為例進(jìn)行價(jià)值與意義的探究,并對(duì)一些問(wèn)題與挑戰(zhàn)進(jìn)行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橫峰木偶戲傳承現(xiàn)狀
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之中的橫峰木偶戲,俗稱“橫峰傀儡戲”“吊戲”,也稱“平安戲”,其最晚在明清時(shí)期就已存在,屬于木偶戲中的提線木偶種類。大多熟悉橫峰木偶戲的老藝人們都認(rèn)為:橫峰木偶戲雖然發(fā)端于江西省上饒市橫峰縣司鋪鄉(xiāng)牛橋莞草池自然村,但木偶戲文化在傳入橫峰之前,最初是由浙江通過(guò)陸路和水路分別傳自近鄰玉山縣和鉛山縣,然后再傳入橫峰縣的。這個(gè)觀點(diǎn)也得到了橫峰縣左瑋館長(zhǎng)的認(rèn)同。但令人遺憾的是,玉山和鉛山的木偶戲現(xiàn)在已經(jīng)絕跡,只剩下橫峰木偶戲仍在延續(xù)傳承。筆者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了解到:橫峰縣政府2006 年開(kāi)始進(jìn)行縣非遺普查,無(wú)意中發(fā)現(xiàn)了這個(gè)文化寶藏,并及時(shí)對(duì)木偶戲進(jìn)行了搶救性挖掘。橫峰木偶戲現(xiàn)有傳統(tǒng)劇目80 余個(gè),由于橫峰木偶戲至今仍留存著江西古宜黃戲(又名二凡,即京劇的二黃)和南戲弋陽(yáng)腔連臺(tái)大戲的原始唱腔與抄本,這為研究我國(guó)二黃腔、弋陽(yáng)腔的衍變與發(fā)展提供了活性形象資料,因而引起學(xué)界為之駐足。當(dāng)時(shí),能演唱木偶戲的只剩下黃歪仔、丁黃炎、方炳亨等三位老藝人。
1.黃歪仔(1937-2015),男,上饒董團(tuán)鄉(xiāng)紙坊村人,第一批橫峰木偶戲省級(jí)文化傳承人。從小接觸木偶戲,但直到43 歲才開(kāi)始跟其舅舅正式學(xué)習(xí)提線木偶表演技藝,能唱80 多出完整戲目,尤其是《西游記》的故事,能從“黑水河”唱到“小西天”,完整唱25 出戲目。
2.丁黃炎(1934-2014),男,橫峰縣蓮荷鄉(xiāng)藤橋村人,第一批橫峰木偶戲省級(jí)文化傳承人,擅長(zhǎng)橫峰木偶戲、傳統(tǒng)戲劇表演。
3.方炳亨(1936-2017),男,橫峰縣司鋪鄉(xiāng)司鋪村人,第二批橫峰木偶戲省級(jí)文化傳承人,擅長(zhǎng)橫峰木偶戲、傳統(tǒng)戲劇表演。
發(fā)現(xiàn)橫峰木偶戲的時(shí)候,鮮有文字,所有的唱腔和故事都保留在了上述三位老人的記憶之中。縣文化部門為此專門聘請(qǐng)攝像人員對(duì)黃歪仔等傳承人所表演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劇目進(jìn)行了搶救性攝像和錄音,同時(shí)也對(duì)劇本文字和音樂(lè)曲譜進(jìn)行了搶救存檔。2014 年,僅木偶連臺(tái)戲就留下了1 萬(wàn)張照片和1000G 的影像資料存檔,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木偶戲的珍貴資料。
雖然,橫峰木偶戲的傳承與保護(h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筆者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目前橫峰木偶戲傳承也存在一定缺憾。如戲班僅有的三位省級(jí)傳承人黃歪仔、丁黃炎、方炳亨均在2015 年前后陸續(xù)去世,由于當(dāng)時(shí)在傳承人口述史方面研究經(jīng)驗(yàn)不足,以致都沒(méi)有來(lái)得及采集三位省級(jí)傳承人的口述史,這不能不說(shuō)是橫峰木偶戲文化歷史的一大缺憾。為了彌補(bǔ)缺憾,木偶戲戲班在當(dāng)?shù)匚幕块T的幫扶下,在司鋪鄉(xiāng)牛橋莞草池自然村開(kāi)辦了傳習(xí)所,并由林必河、周就峰、周園等三位市級(jí)傳承人代表分別帶領(lǐng)著一批年輕人維持著木偶戲的傳承工作。
二、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價(jià)值意義
通過(guò)兩年多來(lái)對(duì)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的采集實(shí)踐,筆者深感其價(jià)值意義重大。
(一)口述史為探究文化密碼提供了較好的史料線索或佐證
由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基本上靠傳承人口傳身授而傳承,其文化密碼,一定會(huì)沉淀在傳承人的記憶之中。盡管在口述史記錄中,有的傳承人記憶會(huì)有一定的偏差,但這并不影響其文化的純色,反而說(shuō)明了歷史的色彩不僅有黑白,也有七彩之色,這些色彩至少為探尋其文化密碼提供了較好的線索或者佐證。
筆者在對(duì)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的采集中,就探尋到了橫峰木偶戲傳承人許多鮮為人知的傳承經(jīng)歷與傳承脈絡(luò)。如原有口述史料在對(duì)歷代橫峰木偶戲紫鴻班傳承人的傳承脈絡(luò)梳理上有三種版本,在新聞?dòng)浾叩膱?bào)道中,有的記者一直把黃歪仔認(rèn)定為戲班的第四代傳承人,筆者通過(guò)資料查詢還發(fā)現(xiàn),原浙江師范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生黃文婷在其2013 年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江西橫峰提線木偶戲田野調(diào)查與研究》中,有一段對(duì)黃歪仔本人的訪談文本整理記錄,黃歪仔認(rèn)為:橫峰木偶戲紫紅戲班的第一代傳承人是嚴(yán)富盛;第二代傳承人有嚴(yán)文顯、黃忠生、嚴(yán)邦清;第三代傳承人有周春芳、林傳金、黃歪仔、丁黃炎、周美興、嚴(yán)國(guó)成;第四代傳承人為周舊福、徐紹紅、林必河。
但2021 年4 月,筆者對(duì)傳承人周就峰口述訪談時(shí),周就峰認(rèn)為:“結(jié)合我爺爺、外公在世時(shí)的回憶和我知道的傳承線索,周添興是橫峰木偶戲紫鴻戲班的第一代傳承人;周德彪和嚴(yán)福盛是戲班第二代傳承人;周春芳、嚴(yán)文顯是戲班第三代傳承人;嚴(yán)邦茂、嚴(yán)邦清、嚴(yán)國(guó)成、林傳金、周美興、丁黃炎是戲班第四代傳承人;黃歪仔和林必河是戲班第五代傳承人;周就峰、周就云、黃園屬戲班第六代傳承人。”
面對(duì)三種版本的不同說(shuō)法,筆者雖然當(dāng)時(shí)也無(wú)法考證橫峰木偶戲紫鴻班到目前為止究竟有幾代傳承人,但至少這些線索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問(wèn)題和線索。后來(lái),筆者通過(guò)訪談橫峰縣文化館左瑋館長(zhǎng),佐證了周就峰所提供的記憶線索接近真相。
(二)口述史研究還原了傳承人的生活本質(zhì)
馮驥才先生認(rèn)為:“只有底層小百姓的真實(shí)才是生活本質(zhì)的真實(shí)。”傳承人作為“民間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者,多半是生活在社會(huì)底層的“文化”人。他們的社會(huì)認(rèn)知,最容易反映和揭示社會(huì)生活的本質(zhì)。從田野考察的情形來(lái)看,歷屆戲班傳承人都是草根百姓出身,表演木偶戲的地方都是在偏僻的農(nóng)村,傳承人學(xué)習(xí)木偶戲的主要初衷也都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使得木偶戲具有典型的草根性。
在傳承人周就峰收藏的祖輩抄唱本中,筆者發(fā)現(xiàn):雖然民間手抄唱本是用普通話的形式記錄整理的,但在橫峰木偶戲戲班演員表演時(shí),基本上都是使用濃郁的鄉(xiāng)音演唱唱詞和念白,幾乎不太使用普通話表達(dá),因?yàn)橛眠@些方言表演的效果比普通話妙趣得多,同時(shí)也充分表現(xiàn)出橫峰木偶戲民間藝人的真實(shí)性和生活性。
(三)口述史研究提升了傳承人的話語(yǔ)權(quán)
目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與保護(hù)的牽頭者是政府,當(dāng)然還有歷史學(xué)者、社會(huì)學(xué)者以及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者,但長(zhǎng)期以來(lái),受精英文化的影響,傳承人長(zhǎng)期處于文化話語(yǔ)權(quán)的底端情形并未得到有效改變。如果要徹底改變這種情形,只有通過(guò)傳承人口述史的不斷深入研究,來(lái)逐步提升傳承人的影響力和話語(yǔ)權(quán)。
三、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問(wèn)題挑戰(zhàn)
在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中,筆者認(rèn)為,作為研究者,要經(jīng)得起如下問(wèn)題的挑戰(zhàn)。
(一)研究激情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生存的土壤一般地處偏僻鄉(xiāng)村,交通往往不便。如筆者所在的城市南昌到上饒市橫峰縣司鋪鄉(xiāng)牛橋莞草池自然村車程約220 公里,單程就需耗時(shí)約3 小時(shí),來(lái)回則需6 小時(shí)以上。如果沒(méi)有濃烈的鄉(xiāng)土情懷,沒(méi)有對(duì)傳承人口述史的研究激情,研究項(xiàng)目往往無(wú)法順利進(jìn)行。
(二)語(yǔ)言交流
通過(guò)對(duì)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周就峰的訪談,筆者感悟:良好的主體合作關(guān)系是研究者與傳承人在訪談過(guò)程中的一種互動(dòng)式的交流理解過(guò)程。這個(gè)過(guò)程處理好了,往往口述史訪談會(huì)比較順利。如在與周就峰傳承人交流的過(guò)程中,筆者首先站在傳承人的立場(chǎng)設(shè)計(jì)了訪談內(nèi)容,并以目前傳承人所普遍關(guān)心的待遇問(wèn)題、生活問(wèn)題為切入點(diǎn),在訪談過(guò)程中充分尊重傳承人的表述權(quán)利,哪怕表述有時(shí)與真相出入很大,只要把話語(yǔ)權(quán)交給傳承人,做一個(gè)真正的傾聽(tīng)者,傳承人一定也會(huì)吐露真心。另外,非遺文化傳承人往往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藝人,文化層次相對(duì)較低,再加上口語(yǔ)表達(dá)、方言等語(yǔ)言障礙,更需要訪談?wù)吣托膬A聽(tīng)。所以,對(duì)訪談?wù)邅?lái)說(shuō),如何溝通和交流順暢確實(shí)也是一種考驗(yàn)和歷練。
(三)文本整理
在對(duì)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訪談錄音進(jìn)行整理的過(guò)程中,筆者主要采取了將訪問(wèn)者的言行全部記錄其中,然后再整理文本的步驟。由于在交流的過(guò)程中,一般采取的是聊天的形式,所以在文本整理時(shí),也會(huì)習(xí)慣于夾雜著自己的語(yǔ)言和觀點(diǎn)。在撰寫(xiě)文本的時(shí)候也會(huì)糾結(jié),口述史文本究竟是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來(lái)整理表達(dá)。面對(duì)上述問(wèn)題,筆者的建議是自覺(jué)秉持“吹盡狂沙始到金”的職業(yè)操守,盡量真實(shí)記錄現(xiàn)場(chǎng),還原歷史。
四、結(jié)語(yǔ)
總之,通過(guò)對(duì)橫峰木偶戲傳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傳承人口述史無(wú)疑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文化保護(hù)工作的深度推進(jìn)開(kāi)辟了新的視角和領(lǐng)域,但需要進(jìn)一步指出的是,對(duì)類似橫峰縣木偶戲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人進(jìn)行口述史研究,一定要有與時(shí)間賽跑的意識(shí),因?yàn)樗袝r(shí)間里的事物,都永遠(yuǎn)不會(huì)再回來(lái),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