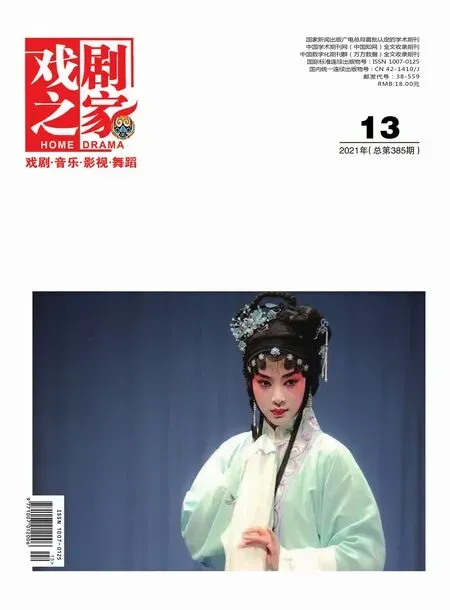角色·情節·主題: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敘事美學分析
劉也鈴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興起,許多動畫作品開始從衰落的紙質媒體轉向更加自由便捷的網絡新媒體平臺,如快看漫畫、騰訊動漫、嗶哩嗶哩漫畫等。從2015年起,《大圣歸來》、《大魚海棠》、《大護法》、《風語咒》等動畫電影的熱映,讓中國傳統文化故事改編而成的國漫IP電影掀起了觀影熱潮,大量的動畫作品涌現出來,國漫開始從小屏幕走向大銀幕,而它所激發出的強大生命力,使我國的動畫產業飛速發展,也讓整個動漫產業鏈條在完善過程中有了巨大的發揮空間。
改編自中國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上映之初便好評如潮,累計票房更是達到2019年榜首,一舉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不折不扣的“黑馬電影”。這部電影不僅展現了中國動畫電影產業在動畫制作技術上可以與高水平技術相媲美的實力,而且基于自身的文化語境和審美精神構建了一個觸動觀眾心靈的敘事,使這部電影不僅具有賞心悅目的視覺美感,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電影中的東方文化和美學精神不僅支撐著電影的內涵,也訴說著它崛起的力量。這部電影在敘事上的傾注最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也為國產電影找到了方向。國產動漫也以其具有的亞文化特質逐漸養成“主流化”意識,更加符合現代審美與現實價值,以經典創巔峰,用敘事傳文化。
一、角色的顛覆與改編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設計是基于劇本需求的突破,符合時代的審美需求。電影中的哪吒、敖丙、李靖、太乙、申公豹的角色塑造和表演邏輯與觀眾熟悉的完全不同,而李府家丁、結界獸等配角則借鑒了國內外優秀動畫電影的諸多元素。可以看出,這部電影的人物塑造既有繼承性又有創新性。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塑造中,對“哪吒”這一家喻戶曉的人物進行了改寫,重構了其在人們頭腦中所產生的固有印象,整個設定既有對傳統人物的顛覆性變化,也在影片角色形象上加入了不同形式的改編。在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它還對人物進行了三維刻畫,使人物更加真實、堅韌,將“夜叉神”與“萌頑童”兩種身份融合進了新文本中,由此來拉近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讓角色的境遇更加牽動觀眾的心。
(一)繼承發展傳統
作為一個發展勢頭迅猛、與人們日常生活聯系日益緊密的行業,國家越來越重視對電影市場的規范,以期通過人們對電影消費市場的熱衷,引導全社會的價值觀朝著更加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中國本土電影一直受到觀眾的喜愛和追捧,但隨著外國文化和其他電影產業相對成熟的國家的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本土電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人們更愿意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畫電影、印度電影等。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80后的導演餃子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致力于挖掘中國電影元素,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所傳達的民族精神。影片中有大量三星堆的青銅器和馬家窯的彩瓷。瓷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以其代表性的符號傳播著傳統文化,滲透著民族意識。餃子是一個在周星馳的電影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在周星馳的電影中,許多普通人都有一種可笑、懶散、嘲諷和諷刺的電影風格。餃子沿襲了周星馳電影風格,許多經典元素也在電影中呈現出來。通過展示角色情感外化和行為夸張的細節,這種對社會小人物的描述更接近觀眾的真實生活,也感受到了從關注個人命運的成長到家族興衰的過程中命運和人性力量的束縛。
(二)打破傳統認知
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中,一直不乏對哪吒這一形象的解讀和運用。在人們的固有印象中,哪吒是機智、勇氣和正義的象征,哪吒和父親李靖的關系,不同于當今社會的父子關系。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被設定為一個“妖氣”的頑童,黑黑的眼圈、鍋蓋似的發型、大蒜形狀的鼻子,笑容中透露著一絲邪魅。這種形象與充滿正義感和英雄氣概的原有形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片中不僅顛覆了主角哪吒的形象,龍三太子、李靖、太乙真人、申公豹等經典形象都被改寫,講著一口四川方言的太乙真人更是帶給觀眾無窮盡的歡笑與回憶。這些角色都是對傳統的顛覆和極具創造力的改編。
在這個大力呼吁創新的年代,“不破不立”在很多時候都成為一條黃金法則,但如果依然是傳統的表現形式,很難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無法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當今社會發展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電影藝術應該跟上時代的步伐,甚至超越時代的眼光,打破一些局限,探索不同的發展道路,有更高的標準和前瞻性,這也是現當代電影觀眾對電影藝術和事業的基本要求。當傳統與現代相互交融時,社會需要多元化的價值觀。如果電影中的傳統敘事打破了一些界限,這也將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避免生活困難的一種慰藉。
二、情節的改寫與重構
故事情節是一部電影的核心,缺乏令人興奮的故事情節,很難被大部分觀眾認可和喜歡。市場上成功的電影,我們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可以挖掘社會的文化核心,挑動人們敏感的神經,真實地呈現人們經常接觸到的事物、人物的情感、價值觀和道德觀。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故事情節將父子關系、大小宿命、人性兩面等主題用創新性的手法予以呈現,帶給人們更強的共情力與感染力,也在多線情感交織中尋求著自我認可。
(一)“魔丸”與“靈珠”的設定
在中國古典著作中,哪吒是智慧和正義的化身,特別是在《西游記》、《封神演義》等作品中,都將哪吒演繹地敢為人先、出神入化,帶給觀眾深刻的印象(刪掉)。但是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是一顆魔丸轉世,陰差陽錯地來到了人間,受盡了人們的恥笑和欺辱,他的內心無比苦悶,沒有朋友也沒有人理解他,別人都把他當做妖怪。但他并沒有因為眾人對他的恥笑和命運的不公而在心中種下惡的種子),而是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留下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名言。隨著劇情的推進,當哪吒與敖丙變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時,善惡便難以分辨。導演試圖在這個矛盾中找到兩個性格互補的人之間的契合點,人物命運和是非之間的徘徊和對抗也使整個情節更加戲劇化,同時給觀眾帶來更多真實的反饋和哲學思考。人性的善與惡的問題在哲學領域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無論人性是善還是惡,或者善與惡兼而有之,電影中關于人性的變幻無常和復雜的情感給觀眾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讓他們在理解人物時找到相似的情感,從而尋求一種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二)父子關系
就傳統文化中的父子關系而言,父親是兒子的行動綱領,父親說一,兒子不二,而哪吒對他父親李靖的權力反抗的對立關系在每部關于哪吒的電影中都有呈現,父子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但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導演卻將李靖設定為一位慈父,社會上曾經引發激烈討論的原生家庭問題、代際關系問題、家庭秩序問題等,都在片中有突出的體現,并給與觀眾深入的思考,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片中的慈父李靖體現了父愛最深沉的一面,為了自己的兒子扛下所有百姓的指責,不顧一切地無私奉獻,教導哪吒做一個正直的人,敢于向不公正的命運抗爭。當哪吒受到天劫的詛咒時,李靖更是選擇用自身的生命換取兒子的生命,將父愛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此事被哪吒知道以后,哪吒決定和不公正的命運相抗衡,如他所說“我命由我不由天”,正是父親的激勵和愛護,讓他有了信心和勇氣去和命運抗爭。
哪吒從出生就被別人視為“妖怪”,即使他是在打妖怪救人,卻還是被陳塘關百姓誤解為搶孩子,用批評、指責的方式給他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于是無力抗爭的他便開始變本加厲地成為百姓心中所認為的那個樣子,做一個“反叛者”。但人終究是社會性動物,內心仍希望得到人們的理解與尊重,當哪吒開始被百姓的判斷束縛時,他無法認清自己的本質日漸消沉,于是在親情的強烈感召下與自己的生活境遇與個人命運抗爭,重新找回自己,不僅為宗族贏得榮譽,還從百姓嘴里也獲得了贊許,從見天地,到見眾生,再到見自己,哪吒最終完成了自我的成長蛻變,以“不認命”的方式成為了孩童英雄。《哪吒之魔童降世》利用經典的英雄敘事模式展開的故事劇情與人物命運,通過種種細節對其進行了成功的闡釋,使影片在敘事上處于有利的位置。
(三)反抗命運
哪吒從出生起就被人們嘲笑和鄙視,人們對他有很大的偏見。不管他如何解釋和努力,仍然不能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這個故事情節讓很多觀眾回憶起自身的經歷,面對誤解時應該作何反應?然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除了主角哪吒之外,還有一些角色也同樣受到了他人的輕視與不尊重。例如,敖丙的身世、申公豹的口吃等,讓他們在生活環境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人格的侮辱,這讓他們苦惱,卻又給他們勇氣,化悲痛為力量,將其內心的自卑與執念化作頑強努力,和命運作斗爭,用自身的實際行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愛戴。在影片中,海浪不斷沖刷海岸、人物落水后產生的水花、房屋倒塌和倒塌后產生的煙塵、石頭被撞擊和撞擊后產生的碎屑、以及打斗時揚起來的沙塵,讓天地之間的哪吒和敖丙,太乙真人和申公豹皆為一體兩面,萬物兩極和情感對立的交織顯現在故事中,再一次印證了該片對原著經典的顛覆和重構。這不僅是對現實生活中反抗精神的完美演繹,也是對無數觀眾和社會風氣的鼓舞與肅清。人人都希望獲得認可、實現自我價值,這種不懼困難的堅持,正是時代精神的導向,也是社會大眾的精神需求所在。
三、主題的互文與融合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形成了對過去文本的互文關系,電影通過拼貼、戲仿等方式與前文本產生呼應,所設定的情節中加入的新元素也為影片增添了不少喜劇色彩,也增強了內容的豐富性,而它透露出來的主題更是十分貼合時代所需和大眾審美,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關注點予以立體和完美呈現。不僅沒有讓觀眾產生與前文本的距離感,還以新形式將各年齡階段的受眾群體帶入這場視聽盛宴中,用一種寓教于樂的方式將影片價值觀傳遞給觀眾,并在笑聲與淚水中,還能產生出跨代際之間觀影所帶來的不同劇情角度、內容深度和思考維度的思考。
(一)表達普世價值
《哪吒之魔童降世》之所以能夠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歡和追捧,一大原因就是電影中蘊含的價值觀具有普適性,是觀眾能理解并踐行的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在電影中,人性的善惡表現和刻畫得淋漓盡致,人物的內心世界、現實境遇、親子關系等展現得出神入化。從社會學視角來看,這些話題皆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一直追思的問題。影片中,哪吒的父親李靖正和現實生活中的大多數父親一樣,是無奈工作與社會壓力身不由已,但是他們對孩子的愛卻一直沒有變過。哪吒在所剩不多的時間里,父母依然成為他思想上的引導,根據他的優勢讓他修煉仙術,給他建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為了他能夠更好地享受剩下的時光,便騙他說:“你是靈珠轉世,不是妖怪。”這個善意的謊言激發了本是魔童轉世的哪吒內心真實的渴望,才得以配合師父修煉兩年。這部電影的不同角色身上有著很多現代人問題的縮影,希望有父母、家庭庇佑,渴望有朋友陪伴和理解,期望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不論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在哪吒的時代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二)掌握命運訴求
敖丙的父親龍王對敖丙說:“我們龍族的命運就靠你了!”龍王及龍族所有的成員都把希望放在敖丙身上,將所有厚望寄予“好孩子”,卻使得他最后痛苦的爆發,這樣扭曲的價值觀不僅會消磨人對自身的關心,耗盡人對生活的熱情,還會喪失掉生而為人的天性。人終究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思維,有自己的人生,誰都不是誰的附屬品。父母給我們軀殼,那真正的“命”,是誰來掌握?《哪吒之魔童降世》給經典的傳統神話故事添加進了“掌握自己命運”的新的精神內核,不再以反抗強權與壓迫去替天行道,而是以個人成長的敘述方式,細致勾勒出哪吒面對不公命運時的心路歷程,也折射出現實生活中的各類社會心理問題。在保留了原型哪吒正義聰慧、智勇好戰的性格特點后,影片將主題濃縮為“自己對命運的掌握”,并貫穿一系列情節的發展,哪吒最終掌握住自己的命運,實現自我超越的價值,也使影片具有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內核。
四、結語
古代經典神話小說中的故事在被拍成電影時需要融合現實語境。只有這樣,電影才能反映新的時代和新時代人們的心靈,才能被當代觀眾所接受。這部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從傳統的物質文本中找到突破口,賦予它鮮明的時代特征。從過去的抵抗父權到當下的反抗天命,《哪吒之魔童降世》表現了哪吒與父母、與朋友之間的情感互動,藉由這種倫理關系的曲折前進引導了哪吒走向理性的、正向的自覺成長,在這種成長的背后實際上也是觀眾自身心理的投射。雖然電影名稱定為“魔童降世”,但不再是簡單的“鬧海”模式,呈現出的是哪吒的成長歷程,用當下的時代語言回歸社會,調動受眾最深處的情感以及價值認同,這一改編歷程既有效地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又能夠成功地實現對古典神話的現代化書寫。基于此,《哪吒之魔童降世》在自成一派的風格和新的敘事元素上對整個動畫產業創作進程提供了豐富的文本素材和優秀的實踐方案,利用好傳統文化資源,創新影像策略,在具有美學觀念的同時,賦予了它新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
《哪吒之魔童降世》呈現出極致的東方美學意境,將經典的神話故事與當代美學相結合,展現了具有時代審美特征的東方形象。東方文化對電影敘事的介入,不僅使電影突出了人文沉思,也使電影體現了深刻的人生哲學,具有重大的創新意義。該片突破了國產動畫電影敘事蒼白無力的困境,同時將傳統文化置于當代審美潮流的環境中。重構的敘事和不凡的東方視野都展示了當代國產動畫電影的最高制作能力,也為后來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