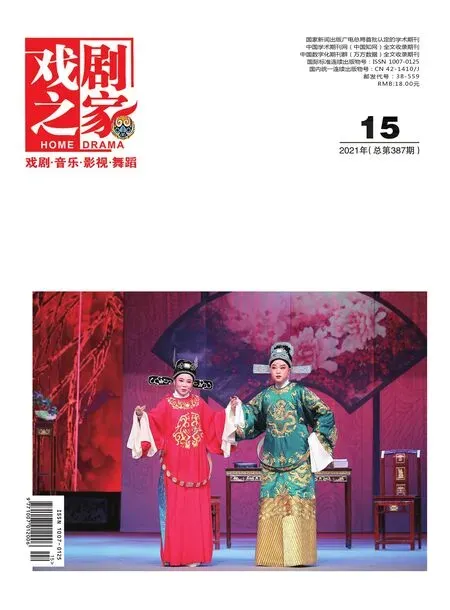本我與超我的多時空對話
——對讀《金鎖記》的舞臺與文本
(武漢大學 湖北 武漢 430000)
一、轉換原著基調:從冷眼到關懷
(一)翻案:七巧是如何成為七巧的
七巧是如何成為曹七巧的?無論是閱讀小說文本還是觀看戲劇畫面,思索“曹七巧如何成為曹七巧”都是重要的問題之一。在張愛玲那里,七巧的悲劇可以是舊中國的婚姻荒蕪,也可以是女性作家對于女性自身的殘酷打量,張愛玲在骨子里是冷的,《小團圓》里面,張愛玲以半自傳的形式書寫了自己和身邊女性的關系——與自己的母親、姑媽、女同學的關系,透徹又清冷。她以冷眼看七巧,所以七巧的悲劇是中國女孩的整體悲劇,這種悲劇形成一個集體無意識而積壓在全體中國女性身上——從女孩到女人,母親和兒女形成一種奇妙的怪圈。這怪圈便是,母親從原生家庭帶來的缺憾和從父親那里缺失的愛要從兒子這里滿足(似勞倫斯)、從女兒這里剝奪。同為女性,七巧對長安總是比對長白更苛刻。但這兩種愛,無一不是病態。回到戲劇舞臺,以七巧的一個夢作為開篇,在七巧的夢里,中藥鋪的小劉和自己組成的幸福家庭里,長白和長安都是幸福的,七巧活在自己的夢中,她同所有的女性一樣,對愛情和家庭抱有最質樸的夢想。中藥鋪里的小劉在張愛玲的小說里面只是一筆帶過,而到了戲劇這里,小劉在開篇結尾作為夢的化身,都充當了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在漆黑的老二的房間里,傳來咳嗽不止的聲音,舞臺燈光的明暗對比之下,七巧從虛幻走入現實黑暗中,咳聲似警鐘,黑暗似地洞。
(二)他者的婚禮:癔癥患者、欲望載體、欲望剝奪
七巧將丈夫的軟骨病造成的情欲不滿足轉向季澤,舞臺上的婚禮成為重點描摹的對象,七巧恰似一只游魂,穿梭在季澤的婚禮之上。而以這樣的方式參與到季澤的婚禮中,是張愛玲在小說中沒有強調的。秉承著為七巧翻案的宗旨,舞臺還給七巧一個變異的婚禮,這樣的婚禮變成兩個人和一個游魂的游戲。張愛玲之所以沒有給七巧一個婚禮是因為七巧的婚禮本是變態的婚禮,老二作為殘疾人本來就剝奪了一位普通女子對于自己所愛之人的幻想,所以張愛玲認為沒必要給七巧一個婚禮。舞臺上的七巧有三場夢中的婚禮。第一場是開場時對于自己和小劉的幻想,這是幻想中婚禮成功之后的結果,中藥鋪小劉成為她幻想之地最后一道防線,在她的潛意識里面,小劉代表著自己對家對美好的向往。舞臺劇《金鎖記》開篇結局都以小劉作為幻想的載體而出現,整個劇被嚴嚴實實包裹在虛幻的夢境當中,這是國光劇團給七巧最大的饋贈,相較于張愛玲的冷眼旁觀,國光劇團以自己的溫情關懷為小女子帶來了一場夢中的婚禮。第二場婚禮來源于季澤,這是七巧最大的欲望投射對象,她頭披紅巾,參與到本不屬于自己的婚禮中,似幽魂一樣,逡巡在季澤和新娘之間,季澤作為七巧最大的欲望載體,承載著七巧對于愛情最后的向往,可是身邊的男人一個個都離她遠去。第三場婚禮,是兒子長白和芝壽的婚禮,正如張愛玲在小說中形容的那樣,長白是可以留在身邊的人,因為長白是金錢的繼承者,但現在長白要被芝壽搶走,七巧在舞臺上又似一只游魂一樣在長白的婚禮上穿梭。季澤已經不是自己可以留下的人,因為她明白那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的錢,她生命的兩個男人,就這樣出現在他者的婚禮中,七巧作為自始至終的局外人以病態的方式“參與”著。
二、突出原著情欲:在場與不在場
(一)兒子與情人
關于這一段,張愛玲在原著中這樣描寫——這些年來她的生命里只有這一個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錢——橫豎錢都是他的。可是,因為他是她的兒子,他這一個人還抵不了半個……現在,就連這半個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親。國光劇團的演出舞臺上,七巧和長安對躺在床榻上,對食鴉片。七巧對兒子長白已經跳脫出母愛,從打探兒子的閨房之事開始;此時,舞臺上形成鮮明的明暗對比,明處,七巧和長白嬉戲打鬧似情侶,暗處,芝壽獨坐閨中,忍受著來自權力的擠壓——七巧在芝壽的年紀受到的是上一級權力的剝削,此時她已得勢,這樣的壓迫便傳到下一輩芝壽身上。在暗處,孕育著另一個似七巧的女性,她們對抗壓迫的方式是忍受、得勢、施壓。“京劇《金鎖記》對曹七巧的表現透著十足的張愛玲風,很得原著神髓,極大地考驗了改編者的智慧。此劇對曹七巧粗俗而又尖酸刻薄的講話方式基本是保持了原作風貌的,如第一幕曹七巧與哥哥曹大年及嫂子的對白,既揭示了曹七巧的出身、婚前的感情情況、又初步表現了她的性格特征,為后面的深入展現做了交代,又表現了她的刻薄”,在繼承原著的風貌上,舞臺做出了很好的把控,兒子與情人的情感的變態也全然張愛玲化。
(二)本我與超我:舞臺和小說的多時空對話
“這是她的生命里頂完美的一段,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她知道她會懊悔的,她知道她會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樣子,說道:‘既然娘不愿意結這頭親,我去回掉他們就是了。’七巧正哭著,忽然住了聲,停了一停,又抽搭抽搭哭了起來。”關于長安的愛情終曲,張愛玲給出了這樣的結束語,這樣的愛情終曲是一種變態且常態的中國母女關系的映射,變態之處在于母親將自己的不幸轉嫁到子女身上——自己得不到的幸福,也不會讓他們得到。常態在于,這似乎揭示了每個女性的成長歷程——被剝離幸福、掠奪別人的幸福。國光劇團戲曲改編中,創作者延續了張愛玲這種“害與被害”的模式和情感基調,兩方在悲劇的誕生上面具有一致性的認同感。七巧是家族和集體無意識的失落者,她的失落造成了子女的失落,這是一個圈套,牢固且愈來愈堅固。“戲曲現代化絕非挪用西方理論,古典記憶和現代感受之間的關系才是反復探索的主題。臺灣京劇曾高度強調教化意義,大陸樣板戲之后仍以崇高命題宏達論述為創作主流。此時此地,張愛玲筆下的市井欲望與脆弱人性(甚至腐敗、頹廢),或許更為貼心”,國光劇團的改編抓住了原生家庭之痛這一情感共鳴,便抓住了聽眾的心,既免于俗套,又讓戲曲舞臺變得活靈活現。
三、繼承原著結構:關于男人和金錢的故事
(一)下一個七巧
在小說中,關于長安,張愛玲有過一段精彩的描寫“她不時地跟母親慪氣,可是她的言談舉止越來越像她母親了。每逢她單叉著褲子,揸開了兩腿坐著,兩只手按在胯間露出的凳子上,歪著頭,下巴擱在心口上凄凄慘慘瞅住了對面的人說道:‘一家有一家的苦處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處!’——誰都說她是活脫的一個七巧。”長安學會了挑是非,使小壞,干涉家里的行政。這樣一個活脫脫的七巧誕生了,可以極端一點講,中國的每一位母親都是曹七巧,中國的每一位女兒都是長安。長安的人性中所有對于愛和希望的部分都被母親七巧給掠奪,這種掠奪是深入骨髓的精神控制。七巧的精神控制滲透到身體,包括對同樣是女性的閨房生活的打探、對于女兒情愛的控制。這樣的七巧的命運在演變中會孵化出下一個七巧,長安之后代,會有無數的長安誕生。
(二)金錢、身世、身份、男人
在原生家庭之延續、鎖鏈與對立結構、三角穩定結構對立結構中,七巧對于這個世界采取簡單的二分法。是否結婚(是否婚姻幸福):已婚、未婚、新婚;身體是否正常:正常的長白和季澤,殘缺的二爺;是否與之有金錢關系;還關乎身世,比如在原著中,張愛玲就寫“七巧聽了,心頭火起,跺了跺腳,喃喃吶吶罵道:‘敢情你裝不知道就算了!皇帝還有草鞋親呢!這會子有這么勢利的,當初何必三媒六聘的把我抬過來?快刀斬不斷的親戚,別說你今兒是裝死,就是你真死了,他也不能不到你靈前磕三個頭,你也不能不受著他的!’”七巧活在男權、金錢、身世、情欲的多重擠壓之下,變成一個活脫脫的變異的人,金錢成為她最后一道防線,成為她生命里判斷一個人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去與留的衡量標準,長白和長安可以留,因為他們是金錢的繼承者,季澤停留在可留與不可留之間,因為七巧深知自己只有通過金錢才能留住這個男人。國光劇團的舞臺上,開篇便上演了七巧的娘家人過來“收油水”的場景,七巧在這個時候不斷強調自己的身份“是賣過來的”。劇團演出的開場就是七巧的一個夢囈,她和中藥鋪的小劉組建了健康的家庭,緊接著舞臺便由夢幻轉為現實,丫鬟們通報自己的娘家人又要來搜刮一番了。“創造人物不是熟練唱念、安設身段而已,這是一段掏心挖肺、潛入內在、自我剖析的歷程。每一部戲的完成,就像是由內到外徹底的洗滌與凈化。”曹七巧的扮演者魏海敏用自己的生命感悟體味七巧的心靈變換,將舞臺上七巧的愛欲情仇和對金錢的執念表現得淋漓盡致,兩場戲緊密銜接,我們跟隨七巧一起,在虛實之間穿梭。
四、結論
通過對比總結舞臺劇版本和小說文本《金鎖記》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將舞臺版本的《金鎖記》形容為“本我”七巧,將小說版本的《金鎖記》形容為“超我”的七巧,是出于兩種不同的藝術載體在處理同一個故事時所具有的不同的情感基調和情感導向。國光劇團以體察的心態默許了一個小女子在時代和家庭的夾縫中變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張愛玲以自己一貫的冷眼旁觀的姿態表達了一個女人的不堪和局促。本我受控于超我,舞臺受控于小說文本,但兩者絕對不是孤立的存在,多聲部的對話讓兩者融合,奏出更完滿的關于《金鎖記》的多種理解,本我是欲望、理解和包容;超我是管制、偵查和諷刺。兩種藝術體裁的對話,讓我們看到了多面的七巧以及在七巧的統攝之下千萬的中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