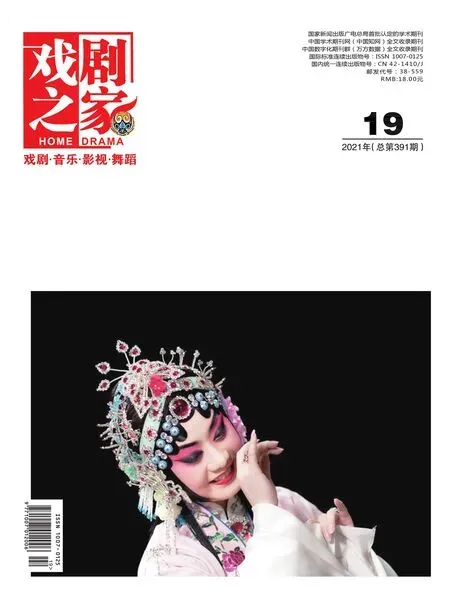從音樂學視角分析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藝術差異
劉孔燁
(華東交通大學 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美聲唱法與民族唱法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唱法風格,本文從音樂學的角度入手,對兩種不同的演唱方法以及音色的差異進行理論分析,為后期創新和發展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奠定基礎,以期將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有效地結合起來。
一、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呼吸技術差異
(一)民族唱法的呼吸技術
演唱者在利用民族唱法唱歌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科學合理地使用呼吸技巧。在遠古時代,民間歌唱者的基本理論是,要想完美地歌唱,必須首先調節好自己的呼吸。使用丹田進行歌唱時,還需要確保單詞和字符足夠清晰、準確。這也闡明了民族唱法對呼吸的基本要求:注意使用丹田氣。歌唱者在吸氣時,不僅要確保呼吸力度適當而完整,而且合理使用下腹部力量也是重點,以便確保發聲的進度和準確度。簡而言之,演唱者在唱歌時要注意合理使用呼吸技巧,并在歌唱之前注意休息。
(二)美聲唱法的呼吸技術
研究可知,Bel Canto(美聲唱法)專注于唱歌時自然呼吸的調節。在Bel Canto 中,主要重點是:演唱者要伸展腰部和腹部,然后在吸氣時按照從上到下的順序進行。在發聲中,有必要在吸氣時支持聲音的發聲。歌手呼吸的整個過程是胸部和腹部肌肉收縮和膨脹的過程,這也為演唱者呼吸提供了一定的動力。
簡而言之,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在呼吸技巧上的最大區別是:前者是氣與詞的結合,主要采用提高氣的基本技巧;而后者是氣在共鳴中的運動,主要是以下沉氣為基本技術。但是不難發現,為了促進歌唱的完美進行,無論是民族唱法還是美聲唱法,都要合理調節呼吸,并且都基于自然呼吸而進行歌唱,這樣才能促使民族唱法及美聲唱法得到合理運用。
二、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共鳴技術差異
研究發現,演唱的共鳴點是演唱者聲音、話語和情感的對話框。良好的共鳴點將增強演唱者的聲音,是咬合和情感的主要表現,可使得演唱效果事半功倍。一個好的歌手能毫不費力地唱歌,其中共鳴點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諧振點必須跨整條線連接,以便將每個位置的諧振點和諧地組合在一起,以產生和諧的諧振點。民族歌唱共鳴點的音質是一種清晰、松散、明亮、柔和的音質,這也是民族歌唱的“清晰發音”,具體特點如下:
第一,民族唱法注重高音,聲音的應用相對先進、柔和、有力,頗具金屬感和穿透力。例如“Luhua”的結束語,調高了一個八度,完成了輝煌而令人驚嘆的高音。只有合理運用出色的演唱技術,實現頭腔共鳴的應用,才能產生出色而令人驚嘆的演唱效果。
第二,民族唱法非常重視口頭共鳴。由于口聲共鳴在民族唱法中被廣泛使用,因此無論是北方地區的清脆,還是南部地區的柔和,都充分發揮了口聲共鳴在唱歌中的優勢,但要注意合理運用極具特征性的歌唱共鳴點技術。
第三,民族歌唱法消除了胸腔內的共振,相對改善了口腔和喉腔內的共振點成分,使得演唱者的聲音開闊明亮。Bel Canto 的共鳴點與民族唱法有明顯不同。具體來說,Bel Canto 是整個共振點的應用,著重于左右連接和聲音的統一性,且Bel Canto 非常重視諧振腔的優化和調整。
總而言之,美聲唱法共鳴腔體的運用其實就是總體共鳴的運用,在具體的演唱當中,演唱者不可以把每一個局部分離,更不能只應用某一個局部的共鳴。民族唱法從技術上注重局部共鳴,而美聲唱法注重的是總體共鳴。民族唱法留意字與共鳴的融合,美聲唱法則更加重視氣場與共鳴的有效融合。二者在共鳴的部位、共鳴的聚焦點等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且在基礎理論見解上也有一定的區別。
三、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語言技術差異
演唱是用歌曲化的語言來觸動觀眾的,民族唱法在歌唱中注重多音字精確,咬字吐詞清楚,讓人聞其音解其義。在咬字的過程中,民族唱法對聲、韻音標發音都具備嚴苛精確的姿勢要求。民族唱法歷來注重咬字、吐詞,明代的魏良輔在《曲律》中強調“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一絕,板正為一絕。”他在明確提出的三絕法中,將“字清”擺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見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民族唱法的行腔吐字上,更重視語言的風韻與語感、語調的應用,注重字、詞、感情、演出的合理結合,行腔吐字靠前,咬字邊角較大,有時候在提升語言重音、拖腔、噴管等實際效果時,一些字頭字尾不但不減少正值,反而有意識地增加,發音的邁向橫中有豎,并非固定不動,吐字真實,以字行腔,最終做到字聲相諧,是“口齒清晰”的基礎規定。根據“口齒清晰”的語言形象化,用美麗的響聲來表述語言的細微轉變,從而組成民族唱法的體系。口齒清晰在民族唱法中貫穿始終,僅有語言的正,才可以在寄情傳意的基礎上產生行腔的美。而行腔的圓滑順暢是字正的審美提升,如此才不容易喪失字的原意,只有二者極致地融合起來,才可以真正做到“口齒清晰”。
美聲唱法始于國外,語音結構特點不同于我國,再加上元音和輔音的組成簡易、便捷,聲調都以元音末尾,沒有眾多英語語法中的鼻化音。因此,美聲唱法的語言技術,不如民族唱法語言那么繁雜。
美聲唱法高度重視元音的發音技術,從聲線訓練管理體系及技術便能窺得一二。演唱者在使用發聲技巧時,全是用單元音進行訓練,如:1、2、3、4、5,十分重視元音部位的統一,強調響聲的連貫性,以達到元音圓滑、溫和、光亮、穿透性強的效果。假如說民族唱法的語言技術與“行腔”的融合密不可分,那么美聲唱法的語言技術則與共鳴點和氣場融合得更加極致,更重視元音與泛音的關聯,以強化高泛音的訓練,尋找到理想化的元音振峰。
四、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審美價值差異
(一)民族唱法的審美價值
民族唱法的審美觀價值主要是以風韻、言辭及設計風格為主導的,這也表明了民族唱法的審美觀念是以民間音樂文化藝術為發展前景的,擁有豐富多彩的色彩。從而在歌唱中會出現多種多樣的規定,以促使民族唱法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優秀的民族唱法,更為重視造型藝術及科學研究的組成,而且往往以豐富多樣的語言為依據,進而融入現代化的民族演唱風格,使得民族唱法的審美價值凸顯,提高演唱者的演唱水平。
(二)美聲唱法的審美價值
基于美聲唱法的審美觀,演唱者更為重視發聲的科學研究,對聲與氣的鏈接也給予關注。因為只有這樣,他們在演唱時才能確保聲線清楚。一個恰當的音色與客觀因素有關聯,進而產生精確的美聲唱法,而這里所說的客觀因素主要包括:聲帶閉合的水平、氣場沖擊性的水平、低喉的部位、軟腭的提高、口腔內部全身肌肉的相互配合、嘴巴發聲的技巧、下頜及嘴型的釋放壓力以及在開始歌唱時的心態。這種客觀因素能夠決定美聲演唱的最終結果。
五、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融合策略
第一,從音樂學視角出發,要想實現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有效融合,我們應該將美聲唱法滲透到民族唱法發聲中,將美聲唱法的混合共鳴點方法應用到民族歌曲演唱中,注意糾正傳統民族唱法中出現的卡、擠、壓、咬的發聲問題。
第二,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在歌曲中抒發中華民族感情。每訓練一首民族歌曲時,歌唱者都應當清楚掌握歌曲所要展現的觀念和思想,帶著主題思想,應用情感和傳統式民族唱法獨有的特點,圍繞全首歌曲來完美地演唱。
第三,要想實現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的有效融合,我們必須在演唱中揚長補短,有效發揮美聲唱法的優勢,合理運用咽喉開啟方式、科學發聲方式等。
總而言之,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存有著一定的差別,我們要學會在民族唱法的基礎上,效仿美聲唱法科學規范的發聲方法,這對于民族唱法的創新發展能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六、結語
綜上所述,民族唱法與美聲唱法這兩種演唱技巧各有千秋,盡管在審美觀價值和觀念上面有諸多差異,但二者也存在相同點。不論是民族唱法還是美聲唱法,追求完美的音樂表達是最終目的。此外,兩者都必須在演唱的基礎上抒發濃郁的情感。民族唱法可以借鑒美聲唱法科學的發聲方法,進一步增強發音的科學性和技術性,讓民族音樂演唱體系能更為系統和完善,實現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