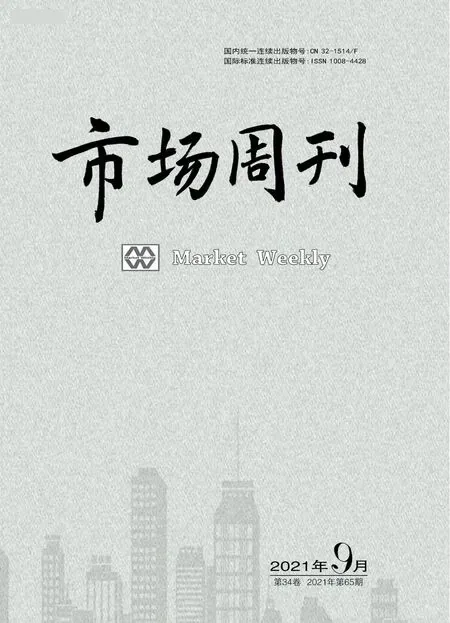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研究述評與展望
郭志文,張嚴嚴
(湖北大學商學院,湖北 武漢430062)
一、 引言
從2001 年安然事件到2019 年的西安“哭訴維權”事件,再到2020 年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全球頻發的非倫理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2020 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提出“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 由此可見,企業倫理責任對企業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近十年來,有關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UPB)的研究逐漸增多,研究主題多為倫理型領導、組織倫理氛圍和道德認同等。 從研究主題可以看出,學者們將研究重點放在對員工UPB 原因機制的探討,提出員工UPB 的前因變量主要可以分為個體、管理者和組織三個因素。 直到近幾年,關于員工UPB 結果的研究才開始增多,人們認為員工UPB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必然的,然而有實證研究證明員工UPB 對員工職業發展也是有一定正向影響的,這為未來該領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
當前國內從員工視角探討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綜合性論述較少,本文基于以往的文獻,采用跨層次分析法,結合個體層面和組織層面,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進行梳理: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概念;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前因變量;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作用機制;述評與展望。
二、 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概念
在提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概念前,眾多學者對非倫理行為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重點多放在非倫理行為的形成機制上,認為人們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偷竊、欺詐等非倫理行為。 Jones 于1991 年首次提出非倫理行為,指出非倫理行為是損害他人利益且在道德上不被廣泛接受的行為。 Ivancevich 等認為縱火、勒索、賄賂、恐嚇、欺騙等都屬于非倫理行為。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員工并不只是為了自身利益做出非倫理行為,出發點也有可能是為了使組織獲益,例如西安“哭訴維權”事件,奔馳4S 店員工為了門店利益而不愿給顧客退換有問題的車。 員工為了維護企業形象和利益,而做出違背法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規范的行為,我們稱之為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UPB)。 親組織非倫理行為這一概念最早由Umphress 等在2010 年提出,其含義為個體為維護組織利益,有意行使的違背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 員工UPB 包含三種邊界情況:第一,該行為是不道德行為,例如為組織利益篡改重要數據、隱瞞企業負面消息等,違背了法律和道德規范;第二,該行為是自愿的,是員工有意做出的行為;第三,該行為的目的是維護組織利益,雖然最終結果不一定對組織有利,但從長期來看,該行為是對組織有害的。
三、 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前因變量
為減少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發生,其形成和作用機制成為學者研究的一大重點。 以往的研究主要以員工為主體,從個體層面、管理者層面以及組織層面三個層面來討論。近年來有關于員工個體層面的研究主要從道德發展程度、員工工作態度以及同事非倫理行為影響三個方面展開;管理者層面的研究主要從不同類型的管理者角度出發,研究各個類型的管理者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影響;組織層面主要從企業偽善、非倫理型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文化與氛圍三個方向展開。
(一)個體因素
1. 道德發展程度
科爾伯格(Kohlberg,1969;1981)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認為個體道德判斷是決定道德行為的基礎。 具體地說,科爾伯格認為道德發展具有六個階段,這六個階段又可以歸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前習俗水平、習俗水平和后習俗水平。 不同層次的發展程度代表個體道德判斷的依據不同。 Greenberg 指出當員工處于習俗水平,并在一個有道德氛圍的環境中工作時,不會做出偷竊等非倫理行為。 當員工處于道德發展低水平時會比處于道德發展水平高時更容易做出盜竊行為,并且組織道德文化對處于習俗水平的員工比處于前習俗水平的影響更大。 Umphress 和Bingham(2011)提出處于習俗水平的個人極易受到情景因素的影響,例如員工與組織和領導的關系,因此員工有較大潛力為了組織利益做出非倫理行為。 通過滿足他人的期望,處于習俗水平的員工可能會認為有利于組織的不道德行為是合理的。
Bersoff 研究發現人們在做出非倫理行為時多處于認知失調狀態,即員工為了自身利益做出非倫理行為后,會利用行為動機中和心理,使非倫理行為變得更容易接受。Harrison 研究也提出個體道德價值觀會通過動機對行為產生影響。 這些結論與科爾伯格道德發展階段理論中的第一層次相符合,當員工道德價值觀處在前習俗水平時,他們為維護自身利益產生利己動機,從而做出非倫理行為。
2. 員工工作態度
員工在工作中會產生各種心理變化,例如組織責任感、組織認同感和工作不安全感等,這些都會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 張宇提出員工的心理所有權作用會讓員工產生一種強烈的組織責任感,促使員工投入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維護和促進組織的發展。 研究最終發現組織支持感會促進員工UPB 發生,其中心理所有權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Umphress 等研究認為積極互惠的社會交換關系或強烈的組織認同感會促使員工積極地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高水平的組織認同可能導致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發生,并且通過中和,員工可能無意甚至有意地使非倫理行為合理化,允許非倫理情況發生。
張永軍等通過實證研究證明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具有負面影響,其中個人-集體主義正向調節了工作不安全感對親組織非倫理行為關系。 當員工集體主義感較強時,個體對工作不安全感會更敏感,從而更加愿意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
3. 同事非倫理行為影響
研究證明,員工最易學習的社會模式即同事的行為模式,員工一般向同事學習其工作行為與處事態度,所以同事的非倫理行為會對員工的倫理決策帶來極大影響。 Ruiz-Palomino 等以馬基雅維利主義為中介,研究同伴非倫理行為對員工倫理判斷的影響,最終證實同伴非倫理行為對員工倫理決策具有負面影響,并且同伴非倫理行為水平較高時,馬基雅維利主義對員工個體倫理判斷的負面影響會有所減弱;當同伴不倫理行為不存在時,馬基雅維利主義對員工個體倫理判斷的負面影響會消失。
(二)管理者因素
企業中管理者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或組織利益,鼓勵甚至壓迫下屬為提高組織績效做出非倫理行為。 Hassan 將這種管理者稱為非倫理型領導,即領導做出犯法或者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員工通過觀察他人行為來了解企業倫理行為標準,從而規范個體行為,所以管理者的非倫理行為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柏萌和胡凡基于社會學習理論,研究證明倫理型領導與親組織非倫理行為顯著負相關,倫理型領導會降低員工從事非倫理行為的可能性。 研究同時發現組織倫理氛圍正向調節倫理型領導與親組織非倫理行為之間的關系,即組織倫理氛圍越高,倫理型領導者越有利于提升員工道德水平,引導員工明確倫理道德的重要性。 Miao 等研究證明了倫理型領導與員工UPB 呈倒U 型曲線關系。 隨著倫理領導水平由低水平上升到高水平,UPB 也隨之上升;隨著倫理領導水平由中等上升到較高,UPB 水平下降。
張永軍等旨在探討家長式領導下三個不同維度分別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影響,研究表明威權式領導有利于員工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德行領導與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呈倒U 型曲線,即相對于無道德標準的領導者和高倫理準則的領導者,中等水平的道德領導者更有利于員工做出非倫理行為;威權領導、德行領導和仁慈領導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具有交互作用。
齊蕾等從時間視角出發,研究證明在建筑行業,時間型領導與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呈負相關關系。 在建筑項目團隊中,高效的時間型領導能夠幫助員工合理地配置時間,分清任務主次,有助于員工按時完成任務,從而避免員工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 Effelsberg 等提出變革型領導與員工UPB呈正向相關關系,即在變革型領導下,員工更易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為。
(三)組織因素
1. 企業偽善
企業偽善是指企業在遵循社會道德規范時所做的一些偽裝現象,究其原因還是企業為了謀求利益而假裝履行社會責任。 以往的研究認為企業實施非倫理行為多數是為了追求短期利益,但是Overall 通過對29 家公司進行調查分析發現如果組織專注于長期成功,這也是不道德的。
趙紅丹和周君研究證明企業偽善現象促進員工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一是由于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可能在發現員工正在做親組織非倫理行為時選擇忽視,甚至鼓勵員工去做該行為;二是由于社會學習理論,企業發生非倫理行為時,員工會傾向于追隨企業。
2. 非倫理型人力資源管理
非倫理型人力資源管理主要體現在不合理的績效薪酬制度和高強度的工作設計。 績效薪酬通常被認為是剝削性的,是為了驅動組織績效而設計的提高工作強化的一種管理工具。 趙慧軍等指出績效薪酬對員工非倫理行為具有正向影響,企業利用績效薪酬激勵及約束員工,使其做出親組織非倫理行為。 張桂平和蘭珊提出高強度績效考核的壓力會影響員工的身心健康,而且當員工績效考核不過關時,將實施嚴厲的問責制度,會使得員工為了自身利益做出非倫理行為。 工作時間安排的不合理、工作內容的單一化以及工作溝通僵化等不合理的工作設計會促使員工產生麻木、抱怨等心理,更容易誘惑員工違背道德準則做出非倫理行為。
3. 組織文化與氛圍
文化在決定道德行為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制定組織道德規范的基礎,組織文化影響員工對事件的態度與處理方式。 良好的組織文化會使企業產生很強的責任感,而不道德組織文化可能會模糊組織道德標準,從而促使有組織認同感的員工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為。 企業文化在約束和引導員工行為上起巨大的作用,當企業重視倫理文化建設時,員工會較少從事非倫理行為,無論其目的是否為維護企業利益。
蔡雙立和高陽根據利益主體導向不同將組織倫理氛圍歸為“自利”和“利他”型。 實證研究發現,自利型倫理氛圍相對于利他型倫理氛圍來說,企業員工更容易在企業做出非倫理行為時選擇沉默。
四、 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作用機制
縱觀各類學者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研究,對員工UPB 的前因變量研究居多,對其作用機制研究較少。 其中員工UPB 作用機制研究多為負面影響,直到近兩年來,對其積極影響的探討逐漸增多,有助于學者跳出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影響思維的限制,為未來研究提供創新視角。 雖然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作用淺層次表現為損害組織長期利益、擾亂經濟秩序等,但對個體職業發展和對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好處。 本小節梳理有關員工UPB 作用機制研究,主要分為個體層面和組織層面。
(一)對個體層面的影響
員工UPB 對個體層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對員工自身的影響和對同事的影響,其中,對員工自身的影響具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 首先,基于社會交換理論,員工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本質是為了組織獲益,在員工向組織表達忠誠后,組織也會給予員工一定的績效福利和升職機會。 王曉辰等研究發現UPB 對員工職業發展起正向影響,即當組織感受到員工對組織的積極付出后,也會促進員工職業的職業發展。 高欣潔也指出UPB 正向影響個體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會促進員工更加積極地工作。
其次,個體通過實施UPB 向管理者傳達了一種良好形象,讓上級覺得能夠與之進行利益交換,領導由于利己主義,會與之建立良好的上下級關系。 員工逐漸發展為“圈內人”,獲得領導賞識和一定的資源。
最后,員工UPB 對員工自身也有消極作用。 Umphress和Bingham 指出員工在做出非倫理行為后會產生后悔和內疚心理。 員工在實施行為后會產生一種羞愧心理,一種來源于組織責任感的消極反應,這種心理可能會促使員工對非倫理行為的受害者進行補償或者不再實施該行為。 并且UPB也會導致員工認知失調,當員工做出非倫理行為后,會感到不和諧和后悔,他們會通過各種方式去緩解這種心態。 Tang等提出UPB 的本質具有兩面性,既是有利于組織的又是不道德的。 基于其矛盾的特征來看,員工實施UPB 后也會產生不同的情感,專注于“行為有利于組織的”會更多地產生驕傲的情緒,認為自己是組織的“英雄”;專注于“行為是不道德的”會更多產生內疚的情緒,而兩種情緒對員工UPB 具有正向影響。
O'Fallon 研究發現從社會學習理論、社會認同理論和社會比較理論三個角度出發,員工UPB 會對同事的非倫理行為造成一定的影響。 當員工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后受到領導賞識并獲得職位晉升后,同事可能會選擇去模仿和學習該行為。 所以同事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即是員工UPB 的前因變量,也可能是員工UPB 的作用結果。 鄭顯偉研究發現員工UPB 顯著負向影響員工被攻擊,即員工實施UPB 不僅不會引發同事乃至其他旁觀者的詆毀和攻擊,反而會使同事學習和模仿。
(二)對組織層面的影響
雖然UPB 的本質是為了組織獲益,但該行為只能給組織帶來短期利益,甚至不能使組織獲益,員工UPB 不利于組織長期發展。 這種行為首先會破壞企業在消費者心中和社會上的信譽和形象,例如“三鹿奶粉”“大眾排放門”,不僅會對該產品系列帶來影響,也會損害公司其他產品銷售。 其次會損害政府、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甚至導致他們取消與企業的合作,破壞企業發展。 最后可能導致企業面臨巨額的罰款,甚至惹上官司。
王洪濤提出員工UPB 易破壞企業形象,為解決這些問題,企業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影響企業生產,阻礙經濟運行,擾亂市場秩序。 特別是一些領導和職能部門的腐敗問題,往往給企業員工帶來惡劣影響,甚至會因此而對企業的發展前景喪失信心,進而影響其生產積極性。
員工UPB 也會危害組織文化和倫理氛圍,一些員工因實施親組織非倫理行為而獲得職業發展,會使其他員工感受到組織不公平和不公正對待,打破了員工間以及員工和領導間真誠、互信的交往模式,使得和諧的組織氛圍受到污染。
五、 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來,有關員工UPB 的研究逐漸增多,可以看出學者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重視。 當前的研究主題多為道德認同、倫理型領導、組織倫理氛圍以及組織認同,可以看出,員工UPB 前因變量是研究的一大熱點。 近兩年,關于員工UPB 問題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視角,有關員工UPB 的作用影響的研究開始增多,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今后員工UPB 研究應多注意以下問題:
(一)完善員工UPB 結果研究
現有研究主要是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形成因素的探討,而關于員工UPB 作用結果的研究直到近兩年才開始逐漸引起重視。 盡管學者對員工UPB 的前因很了解,但是關于其后果的研究還較少。 Umphress 和Bingham 指出員工實施UPB 行為后會產生愧疚和認知失調,但這僅僅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上,缺乏實證研究。 由于以往的研究認為員工UPB 對組織發展是不利的,但是關于員工UPB 的有利影響研究較少。我們可以基于個人-集體主義探討員工UPB 對領導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完善員工UPB 后果研究,可以為研究員工UPB 前因提出新的視角,也能為減少員工UPB 提出針對性建議。
(二)優化員工UPB 測量機制
當前國內對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研究多采用Umphress等開發的行為量表,對其他相關主題測量也采用了國外成熟量表。 道德認同測量采用的是Aquino 開發的道德認同內在化準度測量表、倫理型領導測量采用的是Brown 等的10 題單位量表。 如張永軍等在探討家長式領導對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影響時,對家長式領導、傳統性和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測量均采用國外量表。 王曉辰等在研究UPB 對員工職業發展的影響時,對上下級關系、倫理型領導、職業發展機會和親組織非倫理行為的衡量也采用了國外量表。
國外量表雖然成熟,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許多行為在國內很少出現,或者很多行為只有國內出現,國外量表并不完全適合國內行為測量。 所以,未來研究學者應該基于國外成熟量表,結合國內外企業管理模式差異,制定本土化的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測量量表。
(三)豐富員工UPB 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多采用自評的方式來測量員工親組織非倫理行為,即問卷調查。 雖然采用問卷自評方式是合理的,且強調了問卷的保密性和匿名性,但是由于話題的敏感性,員工在進行問卷填寫時,會受到一定的社會理想性偏見的影響,導致數據的部分失真。 未來的研究可以采取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對具有代表性的員工進行深度訪談,利用定性調查方法去對員工UPB 的原因進行深入探討。 其次,現有研究調查對象主要為員工,數據較為豐富,但樣本涉及范圍并不全面,未來研究可以將調查樣本擴展到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關群體,擴大調查規模,了解員工UPB 對管理者帶來的職業影響,從而更深層次地探討員工UPB 的作用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