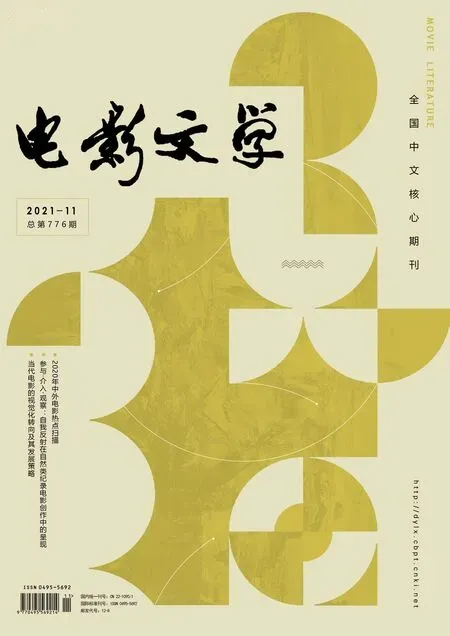2020年中外電影熱點掃描
沈 魯 徐國慶
(南昌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一、國際:底層關(guān)懷、戰(zhàn)爭反思、女性困境
(一)奧斯卡的“人文關(guān)懷”
2020年奧斯卡獎的最大意外當(dāng)屬韓國導(dǎo)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拿下最佳電影、最佳導(dǎo)演、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和最佳國際電影四項大獎,成為本屆最大贏家。這是奧斯卡有史以來第一部非英語獲獎影片,也是韓國電影百年來結(jié)下的一枚碩果。1919年《義理的仇討》的上映,被韓國政府公認(rèn)為“韓國電影的誕生”。百年來韓國電影歷經(jīng)誕生期(1919—1945)、恢復(fù)期(1945—1960)、崛起期(1960—1998)和全面走向世界市場(1998— )四個階段。以1999年姜帝圭導(dǎo)演的《生死諜變》為標(biāo)志,多年來在韓國政府持續(xù)性的電影政策扶持下,韓國電影一舉逆轉(zhuǎn)了本國電影市場長期由好萊塢電影一家獨大的格局,韓國電影在本國及亞洲市場的崛起,為其向國際化邁進(jìn)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得益于韓國電影成熟的工業(yè)體制,《寄生蟲》表現(xiàn)“貧富差距”的常見主題,卻在敘事節(jié)奏上顯示出了導(dǎo)演相當(dāng)成熟的類型范式駕馭能力。電影在兩個家庭的選取上有很強的象征意義,使其跨越國界而幾乎令每個觀眾都能從中感受到自身的困局和尷尬。電影能得到奧斯卡的青睞,除了成熟的敘事,還與美國的政治生態(tài)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好萊塢一直被認(rèn)為是左翼電影的大本營,大批電影藝術(shù)家對底層人士和弱勢群體投以深切的矚目,如近年來的《丹麥女孩》《聚焦》《綠皮書》等入圍或獲獎作品,都曾以不同方式對同性戀、兒童和黑人等弱勢群體進(jìn)行寫實關(guān)照。而《寄生蟲》在貧富差距的兩極對立中對社會生態(tài)的巧妙嘲諷,恰好映照了美國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因此也可以將《寄生蟲》看作是一部符合奧斯卡“政治正確”的作品。“貧困”主題早已屢見于中外電影作品中,但通常電影對“貧困”的書寫更多是一種基于現(xiàn)實困境的展露和反思,而無法給出簡單明確的答案,對“貧困”本身的理解也是這部電影在藝術(shù)文本內(nèi)涵上最耐人尋味之處。
如果對《寄生蟲》的審視更多基于魏伯·司各特總結(jié)的西方文藝批評五種模式中的“社會批評”,那么另一部由薩姆·門德斯執(zhí)導(dǎo)并獲得奧斯卡十項提名的《1917》則應(yīng)當(dāng)從“形式美學(xué)”角度來審視并解讀。電影的最大特色莫過于伴隨兩位男主人公穿過壕溝、越過戰(zhàn)區(qū)的“一鏡到底”。門德斯對戰(zhàn)爭片有兩處設(shè)計使其有別于傳統(tǒng)好萊塢范式的“戰(zhàn)爭片”。首先是極簡的聲畫處理,退去震耳欲聾的官能刺激,拍攝出一部不算喧囂的戰(zhàn)爭電影并非易事。門德斯選擇以長鏡頭創(chuàng)造沉浸感,配合著壕溝——這條非生即死的單行道,用兩個小兵的故事塑造了極為殘酷逼真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在這種沉浸式的影像中,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過形式帶給觀眾的心理體驗,這種形式美學(xué)也給國產(chǎn)電影的形式設(shè)計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如何讓觀眾透過視覺呈現(xiàn)進(jìn)入具體的時間,而非使電影成為停留在暴力美學(xué)、官能刺激層面的消費娛樂品。其次是題材的選擇。比起《血戰(zhàn)沖繩島》《虎口脫險》《珍珠港》等二戰(zhàn)題材電影的繁榮創(chuàng)作,一戰(zhàn)題材由于不太涉及正義與否,沒有鮮明的對立雙方,因此更加考驗導(dǎo)演對戰(zhàn)爭本身的思考。只是不同于《拯救大兵瑞恩》,《1917》里的兩位年輕士兵執(zhí)行的是“以兩人救千人”的艱巨任務(wù)。在執(zhí)行任務(wù)的過程中,門德斯借助人物內(nèi)心不斷傳達(dá)“榮譽與生命孰輕孰重”“戰(zhàn)爭是否本無意義”的批判反思。人物弧光也不在于“傳奇”式的個人英雄,而是小人物的生命在戰(zhàn)爭中的脆弱和掙扎,這也對國產(chǎn)戰(zhàn)爭片予以新的啟示。
(二)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人性困局
新世紀(jì)以來的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一方面延續(xù)了一貫對意識形態(tài)和嚴(yán)肅人性道德主題的青睞,同時也加大了對在政治底色下小人物生存境遇的關(guān)注與轉(zhuǎn)向。
伊朗導(dǎo)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的《無邪》似乎正是一部具有著濃厚“柏林風(fēng)格”的影片。拋開文本本身,單就導(dǎo)演拉索洛夫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及其自身的曲折經(jīng)歷,電影的存在或許已經(jīng)超過了其價值本身。這是伊朗電影在《一次別離》和《出租車》之后第三次摘得金熊獎。不了解伊朗電影的觀眾或許會認(rèn)為電影中所表達(dá)的極端個人生存狀態(tài)不過是又一部迎合西方電影節(jié)對第三世界國家“他者”想象的逢迎之作,但當(dāng)觀眾了解到以阿巴斯為首的伊朗藝術(shù)電影導(dǎo)演多年來大膽挑戰(zhàn)禁忌,試圖以電影沖破體制環(huán)境所做出的努力時,才會體會到《無邪》真正的價值,也會敬佩柏林電影節(jié)一貫秉持的開放的立場和國際視野。電影名為“無邪”,可恰恰講的卻是罪惡。無邪與罪惡的關(guān)鍵在于,面對他人的苦難,我們是選擇起身反抗,還是背過身去。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用“平庸之惡”一詞給出了答案,她認(rèn)為比“集權(quán)之惡”更加嚴(yán)重的是“這種不思考所導(dǎo)致的災(zāi)難,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還要可怕”,它體現(xiàn)為一種對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絕對服從,并在此之下思想能力和個人自由的完全喪失。《無邪》中四個死刑執(zhí)行犯的焦慮與痛苦,恰好在于如何使自身臣服于“平庸之惡”,并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圓其說。電影中的四個人面對絕對權(quán)力,有人麻木,有人逃離,有人掙扎,四組任務(wù)群像巧妙地串聯(lián)了每一個人,這是伊朗人的困苦迷茫和焦慮,或許也映照著世界上的許多人。
回顧世界電影史,每一次新運動、新思潮的興起總離不開對女性境遇的關(guān)照、想象與關(guān)懷。尤其是在當(dāng)下這個特殊時期,電影藝術(shù)的轉(zhuǎn)向更加離不開對女性的摹寫。導(dǎo)演伊莉莎·希特曼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以未成年女性“殘酷的青春記憶”為母題,以一種人文關(guān)懷和救贖意味窺視著美國未成年少女的世界。這部在柏林電影節(jié)斬獲評審團大獎的作品有著傳統(tǒng)女性主義電影對男權(quán)世界的厭惡,也涉及對“墮胎”等青春禁忌的沖破。影片并未展現(xiàn)出一種超乎常規(guī)體驗的殘酷和用力過猛的呈現(xiàn),更多是在一種凝視下的溫和鞭笞。如今的女性電影似乎已經(jīng)告別了《末路狂花》時期對于男權(quán)社會強烈的反抗與沖破意識,這部作品中多數(shù)女性對已然成風(fēng)的性別歧視早已見怪不怪,甚至在男權(quán)侵犯之下表現(xiàn)出默認(rèn)乃至主動迎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是女孩在做心理咨詢時,她的回答只有“從不,很少,有時,總是”,這暗示著女性在當(dāng)代社會的失語,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她所面對的咨詢師,也恰好是一名女性。
對“性別與種族”等公共政治話題的青睞,在二元思維之外的對人性復(fù)雜性探討,讓2020年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繼續(xù)保持了它基本的價值立場和文化尊嚴(yán)。
(三)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華人女性藝術(shù)家的生存探索
2020年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是華人女性導(dǎo)演嶄露頭角的一屆。首先是由華人導(dǎo)演趙婷執(zhí)導(dǎo)的《無依之地》獲得金獅獎最佳電影(該片同時斬獲2020多倫多電影節(jié)人民選擇獎和2021金球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dǎo)演獎),這也是首位華人女導(dǎo)演的作品獲此殊榮。拋開外界對導(dǎo)演身份的爭議,從她的《騎士》開始,這位華人女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清晰的反類型傾向。《騎士》場景依然是傳統(tǒng)西部片一樣蔓延的高原、蒼涼的黃土,但騎士已經(jīng)不是曾經(jīng)的正義使者和西部英雄,男主人公——一位腦部受傷的馴馬師,因身體傷害呈現(xiàn)出英雄遲暮的失落感,他用摔跤、騎馬、文身顯示自身男性身份,同時也在揮之不去的孤獨中尋找著自我身份認(rèn)同。而《無依之地》延續(xù)了這種孤獨感,鏡頭伴隨著內(nèi)華達(dá)州下崗女工弗恩一路開著房車橫穿西部,通過弗恩的一系列所見所聞,跟隨不同人物內(nèi)心求索關(guān)于生命和人生際遇的答案。馴馬師和下崗中年女性這兩類截然不同的群體,他們自我迷失的困局和對身份認(rèn)同的渴求很容易與觀眾發(fā)生共鳴。無論是《騎士》中馳行草原的馬還是《無依之地》中不斷變換目的地的房車,兩部作品的人物都在遷徙中尋找著生命的歸宿和意義,顯示出這位年輕的華人女導(dǎo)演對個體生命體驗的持續(xù)關(guān)注。對個體命運的存在價值和永恒意義的追問看似是電影藝術(shù)的及格線,但真正縱觀中外電影發(fā)展史,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電影還徘徊在這條及格線之外。在此高度上,趙婷作為年輕導(dǎo)演無疑做出了積極嘗試。
(四)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商業(yè)大片的突圍
在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jié)中,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對電影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的推動、新人力量的挖掘和各國本土藝術(shù)特色并重而使其具有相當(dāng)?shù)姆至俊6騺硪跃哂猩疃日芾硭伎己退囆g(shù)氣質(zhì)為取向的戛納電影節(jié)中,商業(yè)類型片的突圍則值得關(guān)注。
延尚昊憑借《釜山行2》再次入圍戛納,電影雖名為《釜山行》續(xù)集,但整體呈現(xiàn)出的更像是前作的拓展影片,由于前作在人物塑造和劇情上都有了較強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續(xù)集的拍攝難以復(fù)刻舊有套路。因此《釜山行2》選擇好萊塢大片“任務(wù)主導(dǎo)”的劇情推進(jìn)模式,顯示出了韓國電影成熟的工業(yè)模式帶來的優(yōu)勢。劇情上以在喪尸災(zāi)難中存活并流亡海外的男主角回國“尋金”為線索,劇情跟隨著男主角在遍布喪尸的人間煉獄半島中糾纏廝殺。無論是形式層面還是故事脊椎,《釜山行2》都是一部為普羅大眾制作的商業(yè)大片。當(dāng)觀眾從形式藝術(shù)的角度審視此片,必然會發(fā)現(xiàn)電影對敘事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長鏡頭、荷槍實彈的打斗和追車戲碼。而對于角色塑造呈現(xiàn)出扁平化特征,整體觀感與好萊塢災(zāi)難片幾無差別,盡管有延尚昊作為前作導(dǎo)演保駕護(hù)航,整體仍然不盡如人意。但前作當(dāng)中還有開放式情節(jié)和人物走向值得發(fā)掘,這也讓人對《釜山行》系列仍然有后續(xù)開發(fā)的可能有所期許。
此外,《薄暮之間》《心靈奇旅》《阿雅與魔女》等為數(shù)不多的商業(yè)電影入圍“戛納2020”,也顯示出該年度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雖然在特殊疫情時期缺席線下活動,但依舊以“戛納2020”的關(guān)注進(jìn)一步標(biāo)簽化了自身對世界電影藝術(shù)旨趣的新轉(zhuǎn)向。
二、中國: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的蓄勢待發(fā)
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曾推斷:“對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適應(yīng),極有可能與中國社會和技術(shù)上的更顯著的社會轉(zhuǎn)型同步。”這對2020年的中國電影行業(yè)而言或許是一種啟示。從2020年年初《囧媽》與西瓜視頻合作創(chuàng)造疫情之下新的觀影模式,院線放映與線上播放的復(fù)合觀影形式構(gòu)成了特殊時期中國電影放映的特殊景觀。截至2020年底,中國電影創(chuàng)下204億元年度總票房,位居世界第一,這樣的成績不僅是市場和票房意義上的,更顯出2020年的中國電影在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推動著國產(chǎn)電影在內(nèi)容創(chuàng)作上新的表達(dá)。
(一)“國慶檔”的家國情懷
2020年院線電影從暑期開始恢復(fù),“十一檔”開始全面復(fù)蘇。在電影院上座率不得超過75%的防疫規(guī)范前提下,國慶檔票房突破39.53億元。與2019年相同,2020年的國慶檔依舊稱得上“新主流大片”的高光時刻。
在年初一預(yù)售后又撤檔延期的《奪冠》卷土重來,成為“國慶檔”開門之作。已經(jīng)在《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篇》中對中國女排奪冠的激情瞬間有所體驗的觀眾依然顯示出對這類題材的熱情,這其中有陳可辛作為“后CEPA時代”中國香港導(dǎo)演的號召力以及女演員鞏俐的個人魅力,也有故事題材本身作為家國圓夢的歷史記憶在觀眾心中激起的持續(xù)的個人情感共鳴。電影前半段可以看作“郎平傳”,隨著影片推進(jìn),一個個女運動員的名字開始出現(xiàn),這其實印證了不同時代體育精神的變化。從20世紀(jì)80年代的“大國精神”到如今的“個體綻放”,個人在歷史體驗中的真實情感得以被重視和書寫。影片借助個體表現(xiàn)體育精神,又借體育滲入個體精神世界,與西方體育類型片有本質(zhì)區(qū)別,其中傳達(dá)的女排精神是一個結(jié),以自我的綻放串起民族之魂。陳可辛在敘事上的把控功不可沒,他在多個場合表示過電影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能夠講好故事的工業(yè)產(chǎn)品,從《中國合伙人》到《親愛的》,他在與內(nèi)地電影人的合作中日漸熟稔于能使兩地觀眾產(chǎn)生情感共鳴的制作范式。《奪冠》以兩個人物、三次比賽架構(gòu)起整部電影,戲劇節(jié)奏和情感高潮安排得當(dāng)之余,又將人物與時代緊緊咬合,將個體生命與國家精神聯(lián)結(jié),使《奪冠》既非概念化觀念輸出,也未淪為一般的工業(yè)體制產(chǎn)品,是“新主流大片”的又一次有益嘗試。
《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和《一點就到家》可以稱作國慶檔中的“返鄉(xiāng)題材”。相比《我和我的祖國》的歷史記憶回溯,《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回歸現(xiàn)代,以五個板塊涵蓋農(nóng)村醫(yī)保、文旅、鄉(xiāng)村教育、脫貧致富和環(huán)境治理,拼接出一幅完整的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正在發(fā)生和即將實現(xiàn)的未來圖景。電影人物涉及網(wǎng)紅電商、旅美教師、普通市民等各色小人物,仍舊以《我和我的祖國》集群創(chuàng)作模式讓觀眾在同一作品中感受到多種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形象。《一點就到家》無論是劇情還是陳可辛監(jiān)制都使電影帶有鄉(xiāng)村版“中國合伙人”的色彩,由三個年輕人下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構(gòu)建起的故事使電影在“返鄉(xiāng)”基礎(chǔ)上又具備了“青春”“勵志”等多重元素,用年輕人的熱血沖撞從鄉(xiāng)村扶貧、電商、互聯(lián)網(wǎng)等熱點揭開鄉(xiāng)村變遷、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新面貌,也以新一代青年人的視角引領(lǐng)社會對鄉(xiāng)野認(rèn)知的重構(gòu)。改革開放40年來的人口流動更多是鄉(xiāng)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新型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建立成為一種迫切需要。西方社會對“鄉(xiāng)村”的概念僅是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業(yè)承載地,但中國作為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大國,“鄉(xiāng)村”則被賦予了生態(tài)、生活與文化等多重含義。2020年是中國鄉(xiāng)村的承上啟下之年,國家第一次提出以國內(nèi)大循環(huán)為主體,進(jìn)一步提升城鎮(zhèn)化比例,這個節(jié)點上重新審視中國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則顯得尤為重要。正如費孝通認(rèn)為中國社會終究是鄉(xiāng)土性社會,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踽踽獨行了數(shù)千年的鄉(xiāng)土文明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鄉(xiāng)村文明有條件在特殊的時間拐點上積極參與市場體系,并反過來實現(xiàn)對城市經(jīng)濟的牽引。《我和我的家鄉(xiāng)》《一點就到家》等作品站在新型城鄉(xiāng)關(guān)系建構(gòu)的角度,通過一個個飽滿的人物、鮮活的故事引導(dǎo)觀眾思考:當(dāng)西方先進(jìn)文明的光環(huán)逐漸退去,未來的中國故事的書寫是否還會是“金融創(chuàng)新”“資本壟斷”?或許歷經(jīng)歲月淘洗后的中國鄉(xiāng)村,能夠為這個故事寫下新的一筆。在此意義上,以《我和我的家鄉(xiāng)》《一點就到家》為代表的“國慶片”,是“政府、制作方和觀眾的集體合創(chuàng)成果,也是我們不斷堅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產(chǎn)物”。
(二)“新主流大片”的范式與創(chuàng)新
《急先鋒》《八佰》和《金剛川》無論類型范式還是家國同構(gòu)的主題都是觀眾熟悉的“新主流大片”形式。受《我和我的家鄉(xiāng)》《姜子牙》《奪冠》國慶檔三巨頭的影響,經(jīng)典“香港警匪+內(nèi)地家國情懷”模式的《急先鋒》,哪怕有老將成龍和人氣明星楊洋、喜劇演員艾倫的多重加持依舊未能成功突圍。曾幾何時,成龍銀幕形象已經(jīng)悄然實現(xiàn)從“功夫小子”“孤膽英雄”的個人英雄到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的轉(zhuǎn)變。成龍在電影中的國際警察角色更多是“任務(wù)推動敘事”的執(zhí)行者,人物光環(huán)不在于個體拯救世界的天賜神力,而是一種家國使命感的承接。即便槍戰(zhàn)元素、跨國敘事、追車大戰(zhàn)等常見的港式警匪片戲碼依舊在電影中處處可見,但如今的受眾群體已經(jīng)悄然更迭,舊有的類型模式已經(jīng)不再為新一代的受眾群體追捧。“功夫巨星”光芒的漸趨暗淡,令人悵惘的同時,想必也會令與內(nèi)地合拍的香港電影人從困境中思索出一條更符合年青一代欣賞品位的警匪片新范式。相比之下,2020年末上映的《拆彈專家2》同樣是經(jīng)典港片故事范式,以7億票房進(jìn)入年度票房前十。《拆彈專家2》的成功除了因為享有前作的紅利,更重要的是電影在保持經(jīng)典“港味”的基礎(chǔ)上講述的不是英雄主義執(zhí)行國家任務(wù)的宏大主題,而是在驚險的警匪較量中關(guān)注個體內(nèi)心與社會公序的矛盾。這種個體的矛盾性消解了英雄主義光環(huán),從而與觀眾更加貼近。而電影中潘乘風(fēng)“失憶”“恢復(fù)記憶”的一系列過程以強戲劇性吸引著觀眾,最終潘乘風(fēng)犧牲自我拯救香港城市也使小人物在最后一刻完成了英雄主義的升華,這樣的自我救贖過程目前看來更具有觀眾基礎(chǔ)。
單從作品本身的歷史存像意義來看,《八佰》與《金剛川》的確存在值得商榷之處,而從電影藝術(shù)文本的角度上講,兩部作品在精神意象的構(gòu)建、家國主題傳達(dá)和宏大歷史的架構(gòu)上都往優(yōu)秀戰(zhàn)爭片邁進(jìn)了一步。無論是《八佰》中的白馬、國旗和《金剛川》中的木橋,都能看見管虎在營造戰(zhàn)爭場面真實感和制造官能刺激的同時,從精神意象層面對主題升華做出的努力。盡管《八佰》和《金剛川》以及《緊急救援》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但無論是歷史記憶還是現(xiàn)代敘述的“新主流大片”在口碑與熱度上都較前些年呈現(xiàn)式微征兆。《緊急救援》盡管仍舊是以真實社會事件為基礎(chǔ)、國家任務(wù)為主導(dǎo)的家國題材,卻沒能延續(xù)林超賢《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的熱烈反響。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電影故事“三段式”的重復(fù)續(xù)寫,板塊斷裂感強的敘事缺陷;另一方面從《烈火英雄》開始,此類題材就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同質(zhì)化的傾向。同時當(dāng)下“新主流大片”題材更多局限于國內(nèi)新聞事件和重大任務(wù),“在地化”風(fēng)格明顯,也使得這一類型在海外傳播中難以取得預(yù)期效果。未來“新主流大片”在進(jìn)行題材類型多元化選取的同時,還應(yīng)當(dāng)具有國際視野,關(guān)注海外觀眾喜好。而2020年9月上映的由迪士尼改編的真人版《花木蘭》,可以看出海外制作公司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題材的興趣,這也可以作為未來“新主流大片”的創(chuàng)新方向。
未來的“新主流大片”,應(yīng)當(dāng)在真實歷史的碎片中以現(xiàn)實主義為原則、以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為內(nèi)核,用更加多元化的類型范式實現(xiàn)對歷史的藝術(shù)化重構(gòu),在商業(yè)元素與家國形象傳達(dá)之余,引導(dǎo)觀眾對歷史及現(xiàn)實困境的反思。
(三)張藝謀和《一秒鐘》
2020年,無論是警匪片《堅如磐石》還是充滿懸疑色彩的諜戰(zhàn)大戲《懸崖之上》都是年過古稀的張藝謀積極求變的成果。而年末《一秒鐘》的上映,則讓許多觀眾看到了一個返璞歸真的張藝謀,一個闊別已久、令人備感親切的張藝謀。
無論是視覺造型或敘事,《一秒鐘》都給人洗盡鉛華的凝練感。早期的張藝謀擅長為電影做減法,對莫言、蘇童等小說家的作品改編都在極力去雜留純,得益于那時的積淀,才使我們看到了《一秒鐘》的極簡之美。影片以西北農(nóng)場的一場電影放映為開端,以一盒膠片串聯(lián)起勞改犯和小女孩這兩位時代的“邊緣人”。簡單的色彩、場景和人物,將特殊時代里小人物的卑微與掙扎娓娓道來。電影于張藝謀而言是緬懷了一個逝去的時代,于年輕觀眾而言,電影中的時代則是一個陌生又令人充滿好奇的時代。那個年代里的人為能看一場電影狂熱不已,甚至愿意貢獻(xiàn)物資、吹捧放映員、配合放映員撒謊,嚴(yán)肅中帶著荒誕。而電影中最吸引觀眾的場景不是比肩接踵的放映場,反而是躲在銀幕背后或坐在影院外的勞改犯、張閨女這些“無名之輩”。一個時代值得被銘記和歌頌的只有“英雄兒女”,而小人物在歷史的放映機里只有“一秒鐘”,隨即被掩埋在黃沙塵埃里。張藝謀重新走入黃土地,帶領(lǐng)觀眾回到了充滿集群儀式感的“膠片時代”。電影之于那個年代的人猶如身處黑暗的人仰望星空,他們渴望著電影豐富匱乏的精神生活,“苦難中帶著希望”是張藝謀為那個年代寫下的最深刻的注腳。“一秒鐘”的時間概念如同一部電影之于一個人、一個人之于一段歷史一般短暫。當(dāng)人們因疫情不得已停下腳步,《一秒鐘》在2020年末帶領(lǐng)觀眾撫今追昔進(jìn)行集體記憶的歷史回溯,顯得恰如其時。
2020年已經(jīng)過去。在以“全球疫情”為最大主題的2020年,包括中外電影行業(yè)在內(nèi)的很多領(lǐng)域都受到深遠(yuǎn)影響,但在這深遠(yuǎn)影響的背后,不變的是觀眾和電影藝術(shù)工作者對電影不懈的熱愛。2020年的電影行業(yè):從不停止思考,很少耽溺不前,有時駐足凝視,但總是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