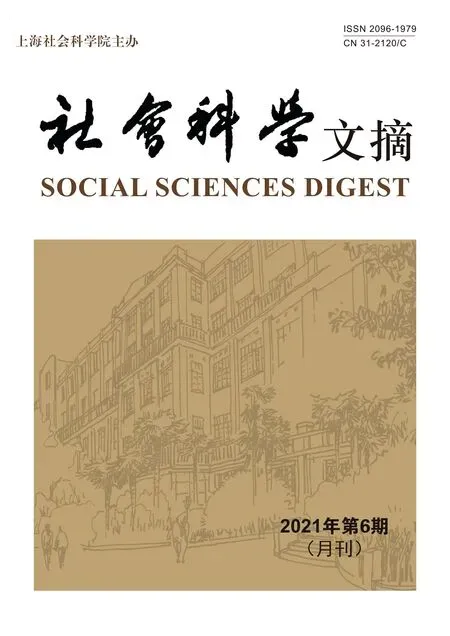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考察
文/沈長云
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逐步實現,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探尋中華民族及其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成為關乎時代發(fā)展的重要問題。中華文明有多久遠?如何起源?怎樣形成?這些問題不僅是學界、公眾的關注焦點,也是黨和國家關心的重大歷史問題。歷史與考古工作者有責任“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fā)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
本文將就中華文明起源這一課題,從歷史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的角度,談幾點個人的認識和體會。
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脈絡
中華文明起源是一個過程。中國古代社會是農業(yè)社會,強調以農為本。農業(yè)產生后,人們開始定居生活,才會有社會分工,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和貧富分化,由此產生階級、階層和各種社會組織,最終發(fā)展為國家。因此,中華文明的起源可以農業(yè)產生為上限,以國家的出現為下限。
中國古代文獻將農業(yè)產生的原因歸功于神農氏。《易·系辭下》稱“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即以神農氏為教民使用農具、進行農業(yè)耕作活動的第一人。這篇文獻還提到神農氏以前的伏(庖)犧氏,稱伏犧氏創(chuàng)造了八卦和結繩記事,并發(fā)明了網罟,教民“以佃以漁”,即進行田獵和捕魚活動。后來的一些文獻又提到伏犧氏之前還有燧人氏,他發(fā)明了鉆木取火之法并教民熟食。以上三人被人們尊為“三皇”。“皇”的意思是光明、偉大,后引申為對圣王的尊稱。其實,無論是用火、漁獵,還是農業(yè),都不應是個人發(fā)明,農業(yè)剛剛誕生時,也沒有真正的“皇”或“王”。“三皇”時代應當理解為自遠古直至農業(yè)產生過程中社會發(fā)展的三個階段。
在古代文獻中,常將神農氏與“炎帝”并提,這種情況或許反映了我國早期農業(yè)生產的基本特點。神農氏又被稱作烈山氏,“烈山”的本義是“燒山”,亦即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yè)生產方式。據研究,炎帝生活在陜西渭水上游一帶,表明渭水流域是我國農業(yè)的發(fā)祥地之一。
“三皇”之后的“五帝”時代,是向國家社會過渡的階段,也是諸多文明因素蓬勃發(fā)展的時代。所謂“五帝”,出自孔子所傳《五帝德》和《帝系》,具體指夏代以前的五位古帝王,即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和虞舜。但所謂“古帝王”,也只是前人的一種解釋。實際上,“五帝”是夏以前一些氏族部落集團的首領。早期文獻稱黃帝、顓頊為“黃帝氏”“顓頊氏”,又稱顓頊為“高陽氏”,稱帝嚳為“高辛氏”,稱他們的16位后人(所謂“才子”)為“十六族”。這些稱謂也反映出所謂“五帝”應是我國上古時期一些氏族部落首領。這些氏族部落勢力有限。《國語·晉語四》記載了黃帝、炎帝兩個氏族部落的情況:“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他們都生活在陜西西、北部一帶。另外,那時所謂的“帝”也不止五位,僅《山海經》就談到“五帝”之外還有帝鴻、帝俊、帝江,其他未有“帝”稱號卻與“五帝”地位接近的尚有蚩尤、共工、祝融、太昊、少昊等,他們也是部族首領。
“五帝”以黃帝為首。黃帝生活在距今4500年或4300年前后,這意味著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所謂龍山時代大體相當。此時社會分化已相當明顯,各氏族部落及部落內部的不平等已是普遍現象。氏族上層役使下層民眾,驅使他們掠奪其他部族的財富,引發(fā)部族間的沖突和戰(zhàn)爭。黃帝和炎帝之間就發(fā)生過沖突。文獻記載他們因為“異德”而“用師以相濟(擠)”,即兩個部族為利益而相互逼迫,以致發(fā)生阪泉之戰(zhàn)。黃帝與東夷部族首領蚩尤也發(fā)生過一場戰(zhàn)爭,史稱涿鹿之戰(zhàn)。據研究,涿鹿與阪泉都在今河北張家口地區(qū),由此可以推想其時黃帝的勢力主要在北方,并沒有擴展到中原一帶。但是,戰(zhàn)爭和掠奪對國家的產生起到推動作用。各部落為了自衛(wèi),紛紛建起城墻,有的還附帶壕溝。正如恩格斯所言,“它們的塹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高聳入文明時代了”。這正是我國文明社會產生前夕社會面貌的生動寫照。
經過“五帝”時代的發(fā)展和戰(zhàn)爭催化,夏朝誕生了。夏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其誕生可以作為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有學者稱之為“廣域王權國家”,可以說抓住了夏代國家的最主要特征。從制度上說,堯、舜擔任氏族部落聯(lián)盟首長時,實行禪讓制,即由部落聯(lián)合體內各部落首領推舉聯(lián)盟首長的制度。啟繼禹位,開啟了“家天下”的世襲制,才形成真正的王權國家制度。更為重要的是,夏朝將不同血緣關系的氏族部落,如《左傳》《國語》所載之有虞氏、有扈氏、有莘氏、斟灌氏、斟尋氏、有仍氏、有戎氏、昆吾氏、豕韋氏、有窮氏等,納入其統(tǒng)治,其中有的部落與夏后氏不同姓,可見夏顯然已經具備了恩格斯所說的“按地區(qū)來劃分它的國民”這一國家形成的標志,成為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
夏建立在豫東魯西一帶。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古河濟之間即今豫東魯西地區(qū)。這里正處在黃河中下游的華北平原,與世界上其他發(fā)源于大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區(qū)的古代文明一樣,我國最早的文明古國的產生也與河流滋養(yǎng)密不可分。
在文獻傳說中,夏的建立與大禹治水緊密相連。禹由于治水成功,取得了對參與治水部落人力、物力的控制,并逐漸成為凌駕于這些氏族部落之上的統(tǒng)治者。禹治水的地域問題涉及治水之事的真實性問題。徐旭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專作《洪水解》一章,根據我國地形特征和歷史發(fā)展階段,指出大禹治理的洪水并非《創(chuàng)世紀》記錄的世界性大洪水,其發(fā)生地域主要是在兗州,即古代的河濟之間。這個說法與上述我們推測的夏代地域相呼應,證明前人有關夏朝史事并非憑空捏造。
夏直到滅亡前,其中心區(qū)域仍在古河濟一帶。《詩經·商頌》記載了商人對夏的征伐,稱“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豕韋、有扈、昆吾皆屬河濟地區(qū)的部族,可見夏桀居處仍在東方。夏朝滅亡后,其后裔在更遠的東方建立起杞、鄫兩個小國,這些都證明夏是建立在東方的國家。
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闡釋
考古學成果表明,我國農業(yè)產生的時間大致在距今1萬年前后,即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開端。較早從事農業(yè)生產的地域,主要是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流域。黃河流域主要種植粟、黍兩種糧食作物,長江流域基本種植水稻。到距今8000—7000年,隨著農業(yè)發(fā)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穩(wěn)定,村落也出現了。其時黃河流域幾支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如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及大地灣文化等,都發(fā)現有村落遺址。南方的彭頭山文化八十垱遺址四周還有壕溝和土筑圍墻,儼然是一個設施完備的村落。在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北方的村落數量已發(fā)展到5000余處,南方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包括河姆渡、馬家浜、大溪等)的村落數量也已超過2000處。仰韶文化是我國農業(yè)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當時的農業(yè)、手工業(yè)技術已達到整個東亞的最高水平。與“五帝”時代相當的龍山文化時期,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末期。如前所述,這個時期是我國文明社會的前夜,許多大型遺址或城址——良渚、陶寺、石峁、蘆山峁等——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仰韶文化前期,由于整個社會尚處在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階段,聚落數量雖多,但規(guī)模有限,面積一般僅有數萬平方米或十余萬平方米。聚落之間未發(fā)現明確的從屬關系,聚落內部成員基本平等。迨至仰韶文化中后期,情況發(fā)生變化。不僅聚落內部開始出現分化現象,而且隨著聚落間人口和經濟實力差距的出現,各聚落也產生了等級分化,并出現了一些強勢聚落對弱小聚落的控制現象。在聚落形態(tài)上,呈現出以一個較大型聚落為中心、四周伴以若干中小聚落的所謂“聚落群”結構。至龍山文化時期,各相鄰聚落群或因血緣相近的關系,又往往集結成更大的聚落群團,這應當就是人們習稱的“族邦”。那時各地出現了很多類似的族邦,文獻所稱“五帝”時期“天下萬邦”的政治格局,便是這樣產生的。
“五帝”時期,物質文明的進步十分顯著。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具有文明進步標志意義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不斷涌現。歷史文獻將眾多發(fā)明創(chuàng)造歸功于黃帝,反映出“五帝”時期是一個文明較快發(fā)展的時代。戰(zhàn)國時期成書的《世本·作篇》專言歷史上各時期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所言黃帝時期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多數與該時期(不限于黃帝時)的考古發(fā)現相印證。如打井技術的出現,旗幟、冠冕、服飾、器用、埋葬等禮儀制度或用品的使用(例如玉禮器的使用),禮樂、樂器與樂律的出現,等等。
還有一些“五帝”時期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記載,如羲和占日、伶?zhèn)愒炻傻取F渲凶钪档米⒁獾氖蔷谡b、倉頡“作書”,即創(chuàng)造文字。目前學術界對我國文字產生的年代仍有爭論,但龍山文化時期已有文字雛形的觀點,獲得大部分學者認可。考古發(fā)現山東、江蘇一帶龍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晚期的陶文,有多個符號連用的現象,說明它們已經具備了記錄語言的功能。另外,傳說黃帝妃嫘祖首創(chuàng)種桑養(yǎng)蠶之法,與這一時期遺址出土的絲織殘片亦可相互印證。如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距今4400—4200年)出土絲線、絲帶、絹片等使用的蠶絲,經鑒定為家蠶絲。
“五帝”時代以后,便是有關夏代的考古。談到這個問題,很多學者一般會想起分布在今河南省西部伊洛汝潁一帶的二里頭文化,認為該考古學文化就是夏文化。筆者贊同二里頭文化包含夏文化的遺存,但不認為二里頭類型可以反映夏文化的全貌。因為據張雪蓮等學者的測年結果,二里頭遺址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這表明二里頭文化的年代主要是夏代后期。偃師二里頭遺址也確實是夏晚期的一處都邑,因為文獻明確記載這里是夏桀的居處,但是二里頭類型以前的夏文化面貌卻并不明朗。有學者將搜索的目光落在二里頭遺址東南方向的新砦遺址上,但新砦文化存續(xù)時間較短,也難說是早期夏文化。一些考古工作者認為,新砦遺址中的許多文化因素,來自更靠東方的造律臺文化和后崗二期文化,這表明早期夏文化,或者說其中的部分文化因素,也應來自東方。由此,筆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當是夏朝末年向西擴張后修建的一處別都性質的邑落。文獻有夏末幾個君主在此活動的記錄,這與二里頭文化中存在來自東方文化因素的現象可以相互印證。
筆者認為,有關早期夏文化的考古學證據應當到東方去尋找。如上所述,文獻記載夏的地域主要在今豫東魯西一帶。這一觀點,在考古學材料上并非沒有線索。其一,部分夏的都邑及諸侯居邑已可與河濟地區(qū)的考古遺址對應,如濮陽高城之于夏后相所都之帝丘,曹縣莘冢集之于有莘氏,滕州薛國故城疊壓著的龍山夯土層之于任姓薛國等。其二,《禹貢》所述禹時民眾“降丘宅土”,亦可以落實。豫東魯西一帶至今仍留有許多土丘,不少可上溯到龍山文化時期,當時人們很可能是依靠這些土丘躲避洪水。與中國同樣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也大多興起于河谷或平原地區(qū),在河水泛濫時會利用人工壘筑的土丘避難。其三,考古發(fā)現古河濟地區(qū)存有不少龍山時代的夯土城址,城墻有抵御洪水的功能,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鯀禹在此抗御洪水的真實性。其四,這一帶曾發(fā)現早商時期的溝洫遺跡,雖時代稍晚,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禹治水“盡力乎溝洫”的歷史線索。
中華文明起源的人類學考察
文化人類學是探尋人類各種文化形態(tài)的科學,與歷史學對各個具體民族歷史的考察不同,主要是通過一系列民族調查,對整個人類所具有的各種文化形態(tài)及文化演進展開研究。其中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階段、早期國家等理論問題的討論,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參照價值。
首先是我國文明起源跨越了人類學中哪幾個社會發(fā)展階段的問題。過去,馬克思、恩格斯根據摩爾根(L.H.Morgan)的進化理論,提出人類早期社會經歷了原始群、氏族組織、國家三個發(fā)展階段。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卻有些籠統(tǒng)。特別是從氏族組織到國家這一發(fā)展階段,到底這種“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如何過渡至以不平等、階級壓迫為基礎的國家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未能作很好的解釋,以至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從原始社會(societas)到政治社會(civitas)的政治變遷,相對而言是突然發(fā)生的。”有鑒于此,以塞維斯(E.R.Service)等人為代表的新進化論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會與國家社會之間存在一個“不平等氏族”社會的發(fā)展階段,即“酋邦”。應當說,酋邦理論確實能夠更好地闡釋有關氏族社會向國家過渡的問題,其構建的國家形成理論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實際。從理論上說,“酋邦時代”的提出,對馬克思有關國家起源的理論有所補充和完善,對中華文明起源及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有借鑒意義,對相應的考古學文化研究也有推動作用。
就我國歷史而言,酋邦的出現或可上溯至仰韶文化中晚期,也是出現社會分化的時期。此前,我國基本還處在平等社會階段。直到此時,社會才開始進化到不平等社會,亦即酋邦社會階段。上文已述,龍山時代是“天下萬邦”的局面,這里的“邦”就是酋邦,也即部分考古學者所說的“古國”。“古國”的性質并不是真正的國家,而只是酋邦。從事聚落考古研究的學者發(fā)現,龍山時期的社會實由許多聚落群構成,每個聚落群由一個較大的聚落統(tǒng)率若干小聚落,若干聚落群又往往構成更大的聚落群團,這些聚落群或聚落群團實際便是一個個酋邦。聚落群或聚落群團的這種分層結構,正是酋邦社會的典型特征。酋邦有大有小,一些較大型的酋邦可稱為復雜酋邦,但其性質仍然是單純的氏族組織,并不是由不同血緣關系的人群組成的社會組織。
酋邦在適當的地理環(huán)境中,隨著人口增加、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一般會發(fā)展成國家。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結合世界歷史發(fā)展,我們認為,由酋邦過渡到國家的道路一般有兩條:一條是在私有財產和奴隸制發(fā)展的背景下,通過對酋邦內部結構的改變,在氏族制度廢墟上建立起對下層民眾和奴隸的統(tǒng)治,即古希臘羅馬奴隸制國家形成的道路;另一條是通過眾邦(眾酋邦)的不平等聯(lián)合,即在一個大邦的控制下,通過這個邦首領的身份性質的轉換,從而建立起對各個族邦的統(tǒng)治性政體。后者涉及的地區(qū)更為廣泛,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軌跡與此類似。
對于經由后一條道路建立起國家制度的民族來說,由于未對原有酋邦組織進行徹底破壞,在國家建立以后,這些酋邦組織及相關氏族制度仍然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得以保留,并且新的國家還要依靠各酋邦及氏族組織對廣大民眾進行統(tǒng)治。據此,我們可以稱這些國家為“早期國家”。夏、商、周三代,就是早期國家。在整個三代時期,酋邦或由酋邦演化成的各種血緣組織一直存在,直到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