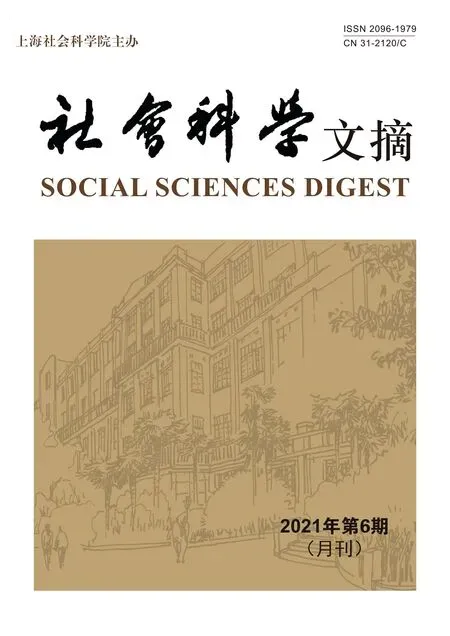探索華夏民族與中華文明的遠古根系
文/高星
中國境內的遠古人類怎樣演變成今天的華夏民族?洪荒時代的古文化如何發展為現今的中華文明?深埋于地下的歷史與當今社會又有怎樣的關聯?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清晰的答案,拉長了的華夏歷史尚有很多空白,族群與文化演變的過程和原因仍有待深入解讀。本文嘗試將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的根基溯源至舊石器時代,用考古材料串連起先民生存繁衍的些許篇章,將對華夏根系的研討引向深入。
中華大地人類肇始
自1871年達爾文出版《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以來,人類起源于非洲、演化自一支古猿,逐漸成為學術共識。目前學術界對人類的定義是靈長類中能常規兩足直立行走的類群。因而追溯人類起源就是尋找最早的直立行走證據,亦即人類與血緣關系最近的黑猩猩相揖別的節點。最近20年來在非洲已發現700萬年前開始直立行走的撒海爾人,600萬年前的原初人,以及其后的地猿、南方古猿等。最早的文化證據也出自非洲,包括肯尼亞Lomekwi3遺址出土的約330萬年前的石制品,埃塞俄比亞Gon遺址出土的約250萬年前的石制品等。地質學研究表明,非洲大陸發生過劇烈的氣候變化,熱帶叢林退縮,很多區域變成疏林草原、干草原乃至荒漠,使部分樹棲古猿被迫改變棲居方式到地面生活,這被認為是從猿向人過渡、直立行走出現、人類在非洲起源的環境動因。
相關證據的缺失使中國乃至亞洲不再被看作人類的起源地,那么中國乃至亞洲是否就對人類的演化不再重要?恰恰相反,中國一直是學界關注的早期人類演化中心之一,是非洲之外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最古老、最豐富的地區。目前早期人類的文化證據已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重慶巫山龍骨坡、湖北建始龍骨洞、陜西藍田上陳等遺址或地區被發現,年代在距今240萬—200萬年。這些材料多為原始、粗糙的石制品,人類化石稀少并存在爭議,個別遺址的年代數據也存在不確定性,但約200萬年前中國乃至亞洲有古老人類生存的事實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這些人類遺存被認為是非洲人類最早向外擴散的結果,即他們都來自非洲。一般認為他們是直立人,少數學者認為在能人階段可能就開始了走出非洲的征程。這些早期人類到達東方后,開始了漫長的適應生存。直立人這個種群是在中國、東南亞地區發展壯大的,構成具有區域體質特征、文化特點和行為方式的重要演化階段。
東方古人類生生不息
對中國乃至東亞人類百萬年連續演化的認識,經歷了長期、曲折的尋找證據和論證的過程。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存的發現是東亞人類百萬年連續演化研究的發端。1929年底,裴文中在周口店第1地點發掘出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其后在其他地點也發現了不同階段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德裔解剖學家魏敦瑞對周口店出土的人類化石進行觀測研究,出版多部專著,詳細描述了北京猿人的體質特征,并嘗試探討北京猿人與現代蒙古人種之間的關系。他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現代中國人乃至蒙古人種祖先的觀點,其后又提出,在東亞、歐洲、非洲和東南亞—澳洲存在四個人類演化世系,并在東亞世系上標出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蒙古人種的承繼關系。
20世紀50年代,在四川資陽、山西丁村、湖北長陽、廣西柳江、廣東馬壩等遺址或地區相繼發現時代介于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的人類化石,填補了直立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的證據缺環。吳汝康等據此進一步論證了中國地區古人類演化的連續性。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元謀、貴州桐梓、湖北建始、陜西藍田等地發現更多早期人類化石。吳新智等通過對中國人類化石的綜合分析,指出大多數中國古人類頭骨存在明顯的相似性,據此認為,中國不同時期的古人類連續演化,具有明確的傳承關系,并首次提出不同地區古人群之間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遺傳學家提出所有現代人類的祖先皆可追溯至非洲一位老祖母的假說。這種假說很快在西方人類學、考古學界流行起來,并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影響。按照這一假說,非洲之外人類演化的鏈條都中斷過,中國—東亞在距今10萬—5萬年間出現人類生存的空窗期,歐亞大陸的現代人與土著古人類群之間沒有遺傳關系。1998年,吳新智在現代人起源“多地區進化說”的基礎上,提出“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假說,認為東亞自直立人以來人類連續演化,不存在整體上的中斷,未發生過外來人群對本土人群的整體替代。他同時指出,東亞本土與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時而發生,與時俱增,使得該地區的人類雖與外界有一定的隔離并形成一些區域特點,但仍與西方人群維持同一物種;與本土人群的代代相傳相比,不同人群的混血是次要的,本地主體人群與少量外來移民之間是融合而非替代關系。
近20年來,中國在相關學術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在湖北鄖西黃龍洞、廣西崇左智人洞、貴州盤縣大洞、河南許昌靈井、安徽東至華龍洞等多處遺址發現人類化石。在新科技條件下,對以前發現的遺址和人類化石開展了新研究,揭示出距今30萬—10萬年中國地區人類演化的連續性和復雜過程。在安徽東至華龍洞發現的30余件人類化石和100余件石制品,年代為距今33萬—27萬年。這批人類化石具有第三臼齒先天缺失等東亞古人類的典型特征,并在頭骨、下頜骨、牙齒上提取到一系列與現代人相似的性狀,顯示出直立人向智人過渡階段的形態鑲嵌特點,為東亞古人類連續演化增添新實證。對距今30萬—25萬年的陜西大荔人顱骨的最新研究表明,該個體表現為中更新世晚期人類共有特征和早期現代人部分特征的鑲嵌體,并兼具東亞直立人和舊大陸西部中更新世人群特點,有諸多進步性狀,所代表的世系可能比其他人群對中國現代人的形成作出過更大的遺傳貢獻。
距今12萬—10萬年的河南許昌靈井人化石,亦顯示出古老形態與現代特征鑲嵌的特點,兼具早期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以下簡稱“尼人”)的諸多性狀,頭骨的總體特征,尤其是寬闊的顱底和低矮的腦顱等,明顯承襲自東亞中更新世人群,表現出區域連續演化為主,同時存在一定程度東西方人群交流的特點。發現于貴州盤縣大洞遺址年代為距今30萬—13萬年的人類牙齒,已經呈現出早期現代人的特征;廣西崇左智人洞出土的距今約10萬年的下頜骨亦出現現代人類的衍生性狀。這些人類化石的鑲嵌特征說明,當時中國存在從古老型智人向現代人演化的過渡階段人群,屬于形成中的早期現代人。而在湖南道縣福巖洞和湖北鄖西黃龍洞等遺址發現的一些距今12萬—5萬年的人類牙齒,則具有完全現代人的形態特征。約4萬—3萬年前的周口店田園洞人與山頂洞人更是盡顯現代人特征。這些都表明中國境內古老型人類向現代人演化是一個連續、無縫銜接的過程,從非洲遷徙至此的早期現代人整體替代本土古人群的假說得不到任何化石證據支持。
華夏舊石器時代文化薪火相傳
從文化角度劃定的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是舊石器時代,從文化遺存(主要是石器)的出現起,至大約1萬年前結束,占據人類歷史的99%。古人群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留下的文化遺存具有區域性、時代性特點,可以據此分析人類在特定區域的生存時間、遷徙路線、技術文化特點與生存方式以及人群間的互動。
非洲舊石器時代文化,可以追溯到330萬年前的簡單、人工特征初顯的石制品(肯尼亞Lomekwi3遺址出土)。在約250萬年前進入奧杜威技術模式,即用礫石加工簡單、古樸的砍砸、切割、挖掘工具。約170萬年前出現阿舍利技術模式,在大石片或礫石上修制兩面加工、器身對稱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鎬等大型切割、挖掘工具。隨著直立人的擴散,這套技術體系被傳播到西亞、歐洲和東亞。在距今30萬—20萬年間,舊大陸西部出現莫斯特技術模式,用勒瓦婁哇技術生產規范的石片并以此加工小型、規整的刮削器、尖狀器等。此技術傳統續存很長時間。在距今4.5萬—4萬年,舊大陸西部出現精美的石葉技術,其后又出現小巧精細的細石葉工具組合。當然,這僅是以典型石器技術為代表的西方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大致輪廓,其間還有石器技術與組合的時空變異、藝術創作與墓葬所體現的審美追求、社會標識和宗教萌芽等。
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可追溯到距今200萬年前后。雖然有遺址或遺存經測年獲得了更早的年代數據,但存在爭議和不確定性。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有很多異于西方的特征,表明東方的古人群與西方有異,同時東西方之間又有一定的文化相似性,從中可以提取出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證據。現有資料表明,中國、東亞舊石器時代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一脈相承并有別于西方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1)就地取材,機動靈活;(2)制作簡樸,加工隨意;(3)器類有限,變異性大;(4)南北分異,多樣性強;(5)發展緩慢,格局穩定;(6)“西方元素”寥若晨星;(7)不存在演化空白期。
由此可見,中國乃至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有很多異于西方的特征,主體文化綿延不斷、緩慢發展,表明這里的古人群連續演化、薪火相傳,形成了穩定的文化傳統。間或有外來人群及文化帶來新元素,但很快被主體人群與文化吸收、同化,未發生過人群與文化的置換或替代。
交流與融合鑄成現代族群
主張中國本土人類連續演化,并非排斥外來人群遷徙、混血和融合的可能性。相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沒有一個地區是某一特定族群長期繁衍的專屬領地,沒有一個族群是不含其他人群基因的“純種”。交流與融合鑄就了當代族群,中華民族亦如此。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南北方人群格局已經形成,南北方人群不斷交融,構筑了華夏族群的遺傳基礎。這一過程早在舊石器時代即已開始。
對北京田園洞4萬年前人骨的DNA分析表明,該個體是古老型東亞人,其基因在東亞蒙古人種和美洲印第安人中仍被攜帶和流傳,但該個體并非現代東亞人的直接祖先,其后還經歷了復雜的混血和演化過程。DNA分析還揭示,現代東亞人群攜帶少量尼人和丹尼索瓦人(以下簡稱“丹人”)的基因。尼人曾被認為是徹底滅絕的群體,但遺傳學研究在我們身上找到了他們的遺傳信息。通過CT掃描技術,在許家窯人、靈井人、馬壩人等中國古人類化石上發現了“尼人內耳迷路模式”,說明尼人曾經擴散到中國、東亞,與本土人群發生過基因交流。丹人以前只發現于西伯利亞,通過對古蛋白和古DNA的分析,證明他們在更早的時候就長時間生存于青藏高原邊緣的甘南白石崖洞穴,這說明丹人原本就是中國古人類的一個支系。
文化證據也顯示,至少在局部地區發生過不同人群與文化的交流、互動。新疆通天洞遺址和內蒙古金斯太遺址下部層位出土的勒瓦婁哇產品,和舊石器時代中期典型的刮削器、尖狀器,其組合及技術風格與中國、東亞本土文化明顯不同,更接近歐洲、西亞、中亞、西伯利亞舊石器時代中期的莫斯特技術體系,這一體系常與尼人化石共生。寧夏水洞溝遺址群也發現了相似案例。這些現象表明,外來人群沒有替代本土人群,很可能發生了融合與文化交流;本土人群在簡單石核—石片體系內產生了一系列技術和認知革新,進入現代人群的序列。
具有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特點的遺存,在中國分布的時空范圍有限,發現于靠近中亞與東北亞邊陲地帶的少數遺址,未能成為文化的主流,遑論對本土文化的更新替代。為何這樣的文化體系未能繼續向東、南方向擴張進入華夏腹地,而是很快消失于無形?通過對莫斯特—石葉技術遺存與中國北方本土小石片石器遺存分布區域與數量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新來人群在華北遭遇本土人群阻擋,后者人數更多、更強勢、更適應本土的生態環境,占據了資源優裕的生態位,使前者只能止步、退卻或者被同化吸收。不同人群遷徙互動、競爭互鑒,這應該是舊石器時代中華大地人群繁衍、生存、融合、發展的主旋律,中華民族及其文明多元一體的遠古根基就這樣孕育、伸展,并在后世變得根深葉茂。
中華民族及其文明形成的機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地處東亞中心,幅員遼闊,生態多樣。生活在這樣廣袤地理空間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環境便利,獲取各類動植物食材和生活資源,并在氣候波動時做南北間和高程上的遷徙移動,趨利避害,維持生存。地質學和古環境學研究表明,東亞在更新世的氣候波動遠遜于歐洲和美洲,即使在冰期,其寒冷程度也遠不及歐美,甚至中國有無真正的冰期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這說明中國大部分地區在舊石器時代適宜人類生存繁衍,這是東方古人類能長期固守家園的環境條件。
中國地理位置相對獨立,地貌、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特點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西有阿爾泰山、天山、昆侖山等高山聳立,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西部、北部還有青藏高原、中亞沙漠和蒙古戈壁荒漠。它們雖不能完全構成人類遷徙的屏障,但在環境惡化時會對大規模人群遷徙構成挑戰,主要困難是食物和飲水匱乏。大陸東方面海,人類無法繼續東遷,形成阻擋效應。在這樣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適宜期遷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演化,形成具有區域特點的人群和文化。其間雖然會有少量人群移入、遷出,但大規模移民很少發生,新來的人群只能融入本土主體人群中,其體質特征和文化特點偶有存留,但無法成為主流。由于地理空間廣大且資源充足,人群能保持生存繁盛和多樣性,不至于特化和自生自滅。這樣的演化過程在歷史時期仍然存續。
中國、東亞古人群能連續演化,文化不斷發展,還有內在原因,即特定的生存之道。筆者曾用“綜合行為模式”表述中國、東亞古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適應生存方式,可表述為“舊石器時代東方行為模式”。其涵蓋的主要內容有:(1)因地制宜,因陋就簡;(2)低限開發資源,與環境和諧發展;(3)不斷遷徙,趨利避害;(4)機動靈活,簡便務實;(5)開放包容,兼收并蓄;(6)進取創新,發展增益。透過石器文化緩慢發展的表層,我們仍可在中國、東亞古人類身上看到進取、創新、不斷演進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克服劣質石器原料的粗糙、剝片技術不斷成熟、石器加工不斷精良和開發利用不同材質原料等方面。
考古研究的要義是透物見人。“舊時器時代東方行為模式”不一定適合所有時期和所有東方人群,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東方古人有別于西方人群的認知模式、技術特點、行為方式和生存方略。這些文化特點和行為模式的鑄就,是環境背景、資源條件、社會結構、人際關系、思維習慣、文化傳統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旦形成,就有了強大生命力、裹挾力和延續性,對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