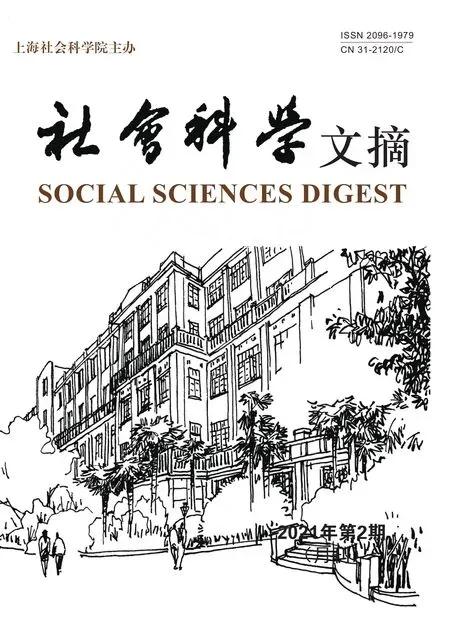經(jīng)典詮釋學對哲學詮釋學之揚棄
文/李清良 張洪志
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雖然源遠流長,但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詮釋學”迄今尚未形成,有待我們繼續(xù)探索和建構(gòu)。在有關“中國詮釋學”的諸種構(gòu)想中,“經(jīng)典詮釋學”方案越來越為學界所接受。
“經(jīng)典詮釋學”的提出及其依據(jù)
關于“經(jīng)典詮釋學”的基本內(nèi)涵,學者們的說法雖不盡相同,但在以下三個方面基本達成了共識。
其一,作為現(xiàn)代“中國詮釋學”構(gòu)想之一的“經(jīng)典詮釋學”,是指一門有待建構(gòu)的現(xiàn)代學問,而不是指歷史上任何一種有關經(jīng)典詮釋的學問,訓詁學或傳統(tǒng)經(jīng)學僅是建構(gòu)這門現(xiàn)代學問的傳統(tǒng)資源。黃俊杰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指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詮釋學””可以說是一種“經(jīng)典詮釋學”,即“以經(jīng)典注疏為中心所形成的詮釋學傳統(tǒng)”,但他所希望建立的“中國詮釋學”是基于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詮釋學”。余敦康也明確說,“中國的經(jīng)典詮釋學從先秦就有了”,但21世紀的中國迫切需要一種現(xiàn)代意義的“經(jīng)典詮釋學”,要兼重理論與實踐、打通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通過經(jīng)典詮釋形成一套可以解決時代問題的理論與思想。潘德榮認為,建構(gòu)“經(jīng)典詮釋學”并不是要倒退至古典的特殊詮釋學,而是一種加入了新元素并指向未來的理論“返回”。
其二,“經(jīng)典詮釋學”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詮釋學。也就是說,它雖以經(jīng)典詮釋為核心關注對象,但目的卻指向一切文本的詮釋問題。一種普遍困惑是,“經(jīng)典詮釋學”應該只是一種與圣經(jīng)詮釋學類似的特殊詮釋學,并不能成為一種普遍詮釋學。其實,“經(jīng)典詮釋學”究竟成為特殊的還是普遍的詮釋學,主要取決于研究的視野和目的。在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中,宋代理學家已經(jīng)建立了一種古典形態(tài)的普遍的經(jīng)典詮釋學。美國學者范佐仁在《詩歌與人格: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解與詮釋學》一書中指出,“比起歷史上任何其他文明來,中華文明也許更注重解釋問題”,因此很早就有了各種特殊的經(jīng)典詮釋學,并且從11世紀起,宋代理學家程頤及其同道便發(fā)展出一種“普遍的經(jīng)典詮釋學”,經(jīng)由朱熹及其后學的努力,這種普遍的經(jīng)典詮釋學被進一步完善和制度化,逐漸成為傳統(tǒng)中國近千年來占主流的詮釋學,以致文學、繪畫和音樂作品的理解與創(chuàng)作都深受其影響。可見,只要具有自覺的普遍詮釋學意識,建構(gòu)一種普遍的經(jīng)典詮釋學就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經(jīng)典詮釋學”是一種具有普適性、世界性的現(xiàn)代詮釋學新形態(tài),而不是只適用于中國的地方性知識。它不僅普遍適用于一切文本或詮釋對象,也普遍適用于現(xiàn)代世界各大文明的詮釋活動。正如潘德榮所說,中國學者的“經(jīng)典詮釋學”主張實際上“包含了對當前西方詮釋學領域處于對峙狀態(tài)的本體論與方法論詮釋學的整體思考”,“也包含著對中、西不同的詮釋理念之綜合反思,以期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中促成這二者的整合與統(tǒng)一”。當然,“經(jīng)典詮釋學”的普適性在事實上究竟能否實現(xiàn),從根本上還取決于中華文明在當代世界的影響力的最終走勢。
總之,我們所要建構(gòu)的“經(jīng)典詮釋學”,雖然主要是以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作為思想資源和研究對象,但面向現(xiàn)代、指向未來,既普遍適用于一切文本的詮釋,也普遍適用于其他文化與文明的詮釋。
中國學者提出這種主張,顯然是試圖在廣泛流行的當代西方詮釋學尤其是哲學詮釋學之外另辟蹊徑,建構(gòu)一種新的現(xiàn)代詮釋學形態(tài)。總體來看,其原因有三:
首先,中國學者在充分吸收借鑒當代西方詮釋學時,逐漸意識到它存在明顯的缺陷,只有另辟蹊徑,才能擺脫理論困境。中國學者主要是從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入手來認識西方詮釋學的,然而,正如保羅·利科所說,無論是海德格爾的事實性詮釋學還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雖然達到了“理解的存在論”高度,卻取消了“理解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而未能在二者之間實現(xiàn)貫通,人們在詮釋實踐中所碰到的各種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此利科主張“用由語言分析出發(fā)的長程途徑來替代此在分析的短程途徑”,“并將拒絕把理解特有的真理與由源自解經(jīng)學的學科所操作的方法分隔開來這樣的誘惑”。成中英也有見于此,提出“本體詮釋學”主張,試圖利用中國哲學智慧來解決西方詮釋學本體論與方法論的貫通問題,這對國內(nèi)學者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進一步發(fā)現(xiàn),當代西方詮釋學雖然認識到詮釋學本質(zhì)上是亞里士多德說的實踐智慧,但在進行理論思考時又背離了這一基本原則,而中國的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頗能體現(xiàn)實踐智慧原則。潘德榮提出“經(jīng)典詮釋學”或“德行詮釋學”主張,就是試圖通過整合中西思想資源來突破當代西方詮釋學的理論困境和發(fā)展瓶頸。
其次,現(xiàn)代詮釋學有多種形態(tài)而并非只有西方形態(tài)。余敦康指出,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詮釋學,“中國有中國的詮釋學,西方有西方的詮釋學,印度有印度的詮釋學”。筆者也認為,各大文明其實各有自成一體的“詮釋之道”,即用以反思、解釋、規(guī)范和引導各種詮釋實踐的基本理念、規(guī)則、方法等,其具體表現(xiàn)便是不斷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各種形態(tài)的“詮釋學”;進入現(xiàn)代社會,由于核心價值、基本觀念和生存方式等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各大文明的“詮釋之道”也必須從古典形態(tài)轉(zhuǎn)換成現(xiàn)代形態(tài),而且隨著“后西方時代”的到來,這一趨勢日益明顯。由于各大文明的自主參與,現(xiàn)代詮釋學理論必將從一枝獨秀(西方)走向百花齊放(各大文明),呈現(xiàn)出多種形態(tài) 。
最后,中國古典形態(tài)的經(jīng)典詮釋學所具有的廣泛深遠的影響,有力地說明了建立一種普遍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詮釋學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將為現(xiàn)代詮釋學的理論突破和多樣化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是最具連續(xù)性、也最具典型性的詮釋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在經(jīng)過深入分析、總結(jié)和反思之后,尤其是在充分吸收、借鑒包括西方在內(nèi)的詮釋傳統(tǒng)之后,必可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換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
綜上所述,建構(gòu)中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詮釋學”,主要是基于對西方詮釋學的內(nèi)在局限性的認識,以及對詮釋學的本質(zhì)屬性和發(fā)展趨勢的認識,同時也是基于“后西方”語境下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認同的自覺。中國學者的這種突破和努力,主要不是為了解決西方詮釋學的問題,而是力圖為現(xiàn)代中華文明建立屬于自己的“詮釋之道”。
“經(jīng)典詮釋學”是對哲學詮釋學的揚棄
有學者認為,這種“經(jīng)典詮釋學”不過是為當代西方詮釋學提供中國經(jīng)驗,最終還是要走向哲學詮釋學,因為后者代表了現(xiàn)代詮釋學的最高水平。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經(jīng)典詮釋學”與哲學詮釋學分別屬于中西兩大文明的現(xiàn)代“詮釋之道”,是兩種不同的現(xiàn)代詮釋學形態(tài),不存在高低之論。如果單從理論發(fā)展來看,“經(jīng)典詮釋學”反倒是對哲學詮釋學的揚棄,是中西兩大文明詮釋傳統(tǒng)“視域交融”的結(jié)果,而視域交融的結(jié)果“總是意味著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普遍性,不僅克服了自己的個別性,也克服了那個他者的個別性”。
“經(jīng)典詮釋學”對哲學詮釋學的揚棄集中表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經(jīng)典詮釋學將更強調(diào)詮釋學經(jīng)驗的典型性和綜合性。
哲學詮釋學在方法論上嚴格遵循“回到事情本身”這一現(xiàn)象學原則,明確主張詮釋學理論必須從實際的詮釋學經(jīng)驗出發(fā),而不能從主觀反思或抽象思辨出發(fā)。這是哲學詮釋學的一大特色和貢獻。但它最注重的還是藝術(shù)經(jīng)驗,也主要以對藝術(shù)經(jīng)驗的分析為基礎,“試圖從這個出發(fā)點開始去發(fā)展一種與我們整個詮釋學經(jīng)驗相適應的認識和真理的概念”。究其緣由,乃是因為哲學詮釋學的目的并非直接指導詮釋學實踐,而是“試圖理解什么是超出了方法論自我意識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學,以及什么使精神科學與我們的整個世界經(jīng)驗相聯(lián)系”,即抵制科學方法論的普遍要求,以捍衛(wèi)精神科學的獨特性質(zhì),而對科學方法論意識構(gòu)成“最嚴重的挑戰(zhàn)”的就是藝術(shù)經(jīng)驗。
然而,如果我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抵制科學方法論的普遍要求”(盡管這也是現(xiàn)代詮釋學應當承擔的一個重要任務),同時也是為了建構(gòu)更具實踐性和普適性的現(xiàn)代詮釋學,那么,我們深入分析和探究的對象就應該是最具典范性的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這種典范性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首先,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更具有綜合性,也就是說,這種經(jīng)驗不是單一維度的,而是同時包含了哲學、藝術(shù)、歷史、政治、倫理等多個維度,譬如自古以來人們對于《荷馬史詩》《詩經(jīng)》等經(jīng)典,很少只從某一個維度來理解和解釋,也很少會把人們從經(jīng)典中獲得的真理明確區(qū)分為文學真理、歷史真理或哲學真理。其次,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具有普遍的價值性。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實際上是人們獲取價值共識的主要經(jīng)驗形式,經(jīng)典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就在于它與其他各種文本相比,被人們更廣泛、更持久也更靈活地接受。最后,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具有豐富的歷史性。它比任何單純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哲學經(jīng)驗和歷史經(jīng)驗,都有更悠久的歷史、更豐富的內(nèi)容、更多樣的形態(tài)和更深厚的傳統(tǒng)。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探索已經(jīng)包含了提出“經(jīng)典詮釋學”的可能性,只是這一可能的探索路徑充滿著荊棘而一直未能彰顯出來。“經(jīng)典詮釋學”正是要以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作為最重要的關注核心,以克服哲學詮釋學在詮釋學經(jīng)驗分析方面的明顯不足。
其二,經(jīng)典詮釋學將更加注重實踐智慧的實際運用。
哲學詮釋學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闡明了詮釋學活動乃是亞里士德多所說的實踐智慧活動,并從多方面指出了實踐智慧不同于一般的制作技藝和以數(shù)學為范例的純理論知識的一般特點。第一,實踐智慧不是像數(shù)學那樣的純粹靜觀的知識,而是必須親身參與和行動的實踐性知識,是“某種他必須去行動的東西”,是“用詞做事”,甚至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現(xiàn)實”。第二,實踐智慧不是抽象的普遍知識,而是具體的普遍知識,“總是首先具體化自身于行動者的具體境況中”,并根據(jù)具體情況而不斷作出相應調(diào)整,所以是一種具體而普遍的“隨時之義”。第三,實踐智慧不是純粹的理論知識,而是成熟的經(jīng)驗型知識,是達到某種普遍性的實踐經(jīng)驗,并不是作為純理論知識的“科學”的初級階段。第四,實踐智慧不是無關價值、客觀中立的知識,而是以善為目的的“實踐合理性的德性”,“關系到整個正當生活的大事”。詮釋學理論應該是對這種實踐智慧活動加以理論反思的實踐哲學。
然而,哲學詮釋學還只能說是未完成的實踐哲學。因為它不僅未能進一步闡明詮釋活動是如何運用和體現(xiàn)實踐智慧的,還片面地認為這是不可描述也沒有必要描述的。伽達默爾坦承:“我所說的詮釋學指的是一種理論。……詮釋學所關涉的只是一種理論態(tài)度……這種理論態(tài)度只是讓我們深刻地意識到,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實際的理解經(jīng)驗中起作用。”“我本人的真正主張過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一種哲學的主張:問題不是我們做什么,也不是我們應當做什么,而是什么東西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與我們一起發(fā)生。”哲學詮釋學并不想引導和規(guī)范詮釋實踐,而只是滿足于從理論上闡明理解活動是一種實踐智慧活動。此前的“詮釋學”總是具有某種實踐功能,哲學詮釋學卻窄化甚至背離了這一傳統(tǒng),只會加深我們對于現(xiàn)象的理解,卻無助于我們的理解實踐甚至還會令人無所適從。哲學詮釋學在這個方面的欠缺導致它在理論上具有明顯的不足甚至是矛盾,人為地將詮釋學的存在論與方法論對立起來,從而既不能引導詮釋學實踐,也無法彰顯詮釋學活動如何追求“善”,因而不能成為真正的實踐哲學。哲學詮釋學的這些理論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由其哲學化進路所導致的。詮釋學理論要成為兼具理論性與實踐性的實踐哲學,就必須對實踐智慧的運用規(guī)則及其變化加以理論分析和闡明。經(jīng)典詮釋學的興起,正可以克服哲學詮釋學的這一局限。
“經(jīng)典詮釋學”的研究進路
經(jīng)典詮釋學的進路不是哲學詮釋學那種哲學化進路,而是一種源于經(jīng)典詮釋經(jīng)驗的最具綜合性、價值性和歷史性的進路。
所謂最具綜合性,是指經(jīng)典詮釋學的探究包括多個維度和層面——既有哲學維度,也有語文學、文學、歷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維度;既包含形上抽象的理論觀念層面,也包含較為具體的規(guī)則、技巧和方法層面,甚至還有更具體的范例層面。經(jīng)典詮釋學的這種綜合性意味著,無論是作為實踐智慧的詮釋學經(jīng)驗,還是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理論,總是自然而然地同時包括了多個層面和多個維度。因而,不僅有存在論的自覺,也有方法論的自覺,還有無數(shù)可資借鑒的具體范例;其理論思考的維度不僅有哲學維度的,還有歷史的、倫理的、政治的維度,等等。
所謂最具價值性,是指經(jīng)典詮釋學的探究總是以從不同層面凸顯經(jīng)典蘊含的永恒價值為其重要任務,從而有效地解決在詮釋活動中如何彰顯“善”的問題。首先,經(jīng)典及其詮釋傳統(tǒng)形塑了各大文明最基本的價值觀念,因此對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的分析與反思可以最直接的方式認識各種善的觀念和方式,包括善的詮釋觀念、詮釋方法、詮釋規(guī)則、詮釋技藝等。其次,通過梳理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善”的價值是如何在不同時代得到調(diào)整、擴展甚至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這就為我們在現(xiàn)代社會如何守護這些價值、彰顯和踐行善的價值、追求正當?shù)纳钐峁┝藛⑹旧踔练独T俅危瑥牡覡柼┯绕涫琴み_默爾以來,現(xiàn)代詮釋學還承擔著反思和校正片面的現(xiàn)代性觀念的重任,這就必須充分利用各大文明的經(jīng)典及其詮釋傳統(tǒng)所彰顯和體現(xiàn)的基本價值觀念、思想資源以及自然具有的歷史合理性和權(quán)威性。
經(jīng)典詮釋學探究也最具歷史性。第一,“經(jīng)典詮釋學”探究,不是從某種抽象的形而上預設出發(fā),而是以對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的歷史回顧和窮原竟委的細致梳理為前提,既是從歷史經(jīng)驗引出理論反思,也是以歷史理性成就實踐理性。第二,“經(jīng)典詮釋學”探究,既從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中總結(jié)出“通古今之變”的基本方法、規(guī)則和技巧,又不斷揭示它們“唯變所適”而“不可為典要”,亦即總是隨著時代、流派、個體甚至文體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最能呈現(xiàn)詮釋活動作為實踐智慧活動的歷史性。第三,“經(jīng)典詮釋學”探究,通過對歷史上的典型范例的發(fā)掘,來展示運用實踐智慧進行詮釋活動,以及辯證處理涉及方法論問題的傳統(tǒng)思想資源。比如,宋代學者呂本中《夏均父集序》云:“所謂活法者,規(guī)矩備具,而能出于規(guī)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guī)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這種“活法”論對我們思考存在論與方法論的辯證關系就極具啟發(fā)意義。
可見,“經(jīng)典詮釋學”可以更好地揭示詮釋學活動乃是一種運用實踐智慧的活動,它的這種進路更符合實踐智慧的本質(zhì)特性。
總之,現(xiàn)代“經(jīng)典詮釋學”因為更為注重詮釋學經(jīng)驗的典型性和實踐智慧的實際運用而可以揚棄哲學詮釋學,成為一種更具綜合性、普遍性的現(xiàn)代詮釋學新形態(tài)。當然,哲學詮釋學并不因此就完全過時,現(xiàn)代詮釋學亦永遠不會只局限于一種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