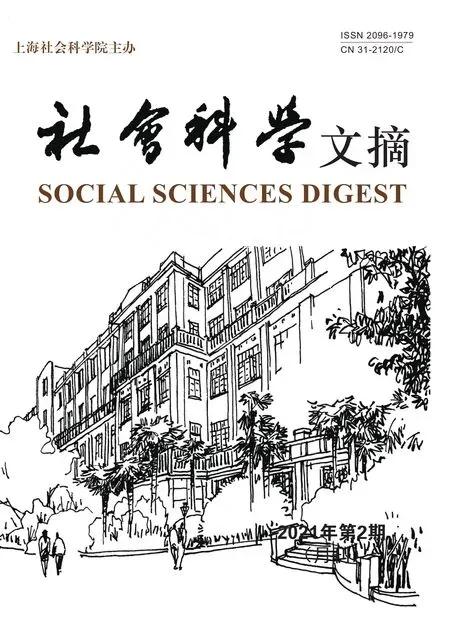禪讓的變異:從傳說、理想到制度設計
文/王士俊
遠古傳說的堯舜禪讓,是先秦儒墨兩家謳歌的理想。但這并不能消弭傳說引發的爭議。兩千多年來,認傳說為史實的除儒墨外,代有其人。及至近代郭沫若、范文瀾等史家不僅肯定傳說,而且將其釋讀為部落聯盟時代的民主選舉制度。與儒墨及后人對傳說的肯定相反,先秦的荀子、韓非持質疑堯舜禪讓說的立場。荀子認為,堯舜禪讓“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唐劉知幾在《史通》中持與荀韓相同的看法。清代崔述、康有為也不信堯舜禪讓之說。及至20世紀上葉,疑古思潮濫觴,顧頡剛等人更是直斥傳說是戰國秦漢間的“造偽”。堯舜禪讓的傳說之爭,至今尚未平息。本文不置喙傳說的真偽之爭,僅著重討論堯舜禪讓說提出的意義,以及由此展開的實際操作及制度設計,探討一個美好的傳說變為理想進入實踐操作過程的變化。由此,觀察變化的結果與原初傳說、理想訴求的差距。
以傳說表達的理想:禪讓說的最初主旨及權力轉換構想
堯舜禪讓的真偽之爭,對說明古史傳說的堯舜時代的“歷史”有重大意義。但是,即使傳說有偽也不能表明這類材料無價值。本文就本著這種理念,檢閱有關堯舜禪讓傳說的史籍、材料。
就歷史上的禪讓傳說而言,爭議很大的材料之一,要算《尚書》中被稱為“虞夏書”的《堯典》。《堯典》記述了堯舜禪讓之事。近人顧頡剛先生從《堯典》涉及的地名上分析指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此論一出,引發眾多學者反駁。竺可楨、唐蘭、董作賓、胡厚宣等人分別從分析《堯典》涉及的天象、殷卜辭、祭名的角度發表了反對意見。
細觀《堯典》論爭中,各家對顧頡剛的駁難,雖能質疑顧先生的立論,但也不能證明《堯典》的純真。如果撇開以《堯典》證夏商之前的歷史,將它視為提出禪讓問題、敘述禪讓方式的材料,應該說是完全可以的。若如此,則需要弄明白,這份材料“作偽”或說形成的年代,這樣才能明白它提出禪讓問題的時代背景及目的,等等。顧頡剛先生認為,《堯典》“作偽”于西漢,至于《堯典》的禪讓思想,他說最早是由墨家提出的:“……要知道禪讓說是直接從尚賢主義里產生出來的;倘沒有墨家的尚賢思想,就決不會有禪讓的傳說!”針對顧先生此說,劉起釪先生通過詳細考辨,給予反駁。劉先生認為,《堯典》為孔子所編,成于春秋晚期。《堯典》是禪讓思想的重要材料。若按此說,則禪讓說源起春秋晚期。此問題,現今學界仍有爭議。許景超研究《左傳》《國語》有關古史記述,得出這樣的看法:探討春秋時期的一些有關古史傳說,“可知堯舜禹時期之事跡已流傳得比較廣泛。堯以后的事跡,使我們清楚知道戰國諸子所傳的古史,是從春秋時期(或更早)便流傳下來的”。
學界所做的這些推測并非空穴來風。要言之,流行于公元前五世紀的禪讓說,有一個源起與形成的過程。《尚書·堯典》《論語·堯曰》應是出現較早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購得的竹書,以及清華藏竹簡中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保訓》所論及的禪讓傳說,涉及年代久遠、敘事之詳、討論之廣都遠超傳世經典。出土文獻記錄的禪讓文字,也從另一側面顯示出傳說的更早源起。
關于禪讓說興起的原由,學界的主流看法是當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的社會情勢下,“士”階層崛起,尚賢、尚德思潮的流行,進而衍生出德治、賢人政治的理想訴求。于是有“善善相授”、禪讓賢人的王朝更迭、君權傳承制度的構想。古代士人在春秋戰國之際以傳說倡禪讓,在世襲、湯武革命這兩種君權傳承、轉換方式之外,提出了第三種君權轉換途徑。
春秋晚期至戰國,士人以禪讓傳說倡理想,勾畫君權傳承、轉換的第三種方式,其用心良苦。他們勾畫的禪讓方式之要者有:(一)上德(君主)起意,主動禪賢;(二)與“四岳”(邦主、諸侯)商討、選擇賢人(禪位對象);(三)上德(君主)親自面試被選擇的賢人(與之交談等);(四)將被選的對象舉之高位,授職考驗;(五)考核滿意,確定禪位;(六)受禪賢者五讓他者,“天下賢者莫之能受”;(七)上德禪位,賢者受禪,舉行即位儀式。
需要指出的是,這是先秦士人依據傳說敘述的理想。在此之后的數百年中,它以一種思想、學說、思潮而存在,直至西漢中后期被政治家接受之前,其未登廟堂、難入密室。然而,世上所有的理想都有被實踐的渴望,政治理想更是如此。
走向實踐的理想:初行禪代的權力轉換設計及其亂局
禪讓由傳說變成理想,是春秋戰國士人思想的成果。但是,這種屬性的理想,在思考、交流、爭辯的過程中,很少考慮付諸實踐的細節及諸多條件的要求。比如,禪讓由上德(君主)禪讓和受禪者(賢人)兩方面構成。歷史上,就曾有君主想禪讓而被選為禪讓的對象不愿受禪的傳說。《莊子》載,“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逃堯”,不受禪。“舜以天下讓”于善卷,竟遭到善卷的拒絕。理想的受禪者不接受禪讓,這肯定不只令禪讓者尷尬,也是事關權力轉換成功度的大問題。此外,即使禪者與受者達成一致,禪讓也可能出問題。《史記》說,禹受禪后,已“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更糟糕的情況是,禹另選了禪讓對象益,而當禹駕崩時,禹的兒子和諸侯違背禹的意志,讓禹子啟取代了益登基即位。禹的禪讓傳說,其實早就嚴峻、現實地提出了禪讓的實踐問題。只是這方面的問題,未受到提倡禪讓說的思想家們的重視。嚴格說,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不是思想家的任務。禪讓說興起后,可作為較早的禪讓事件來研究的,要算《戰國策》記載的燕王噲禪位:
公元前320年,燕國的噲被立為王。噲用子之為相。鹿毛壽窺得燕王噲有圖圣君之名,干大事的雄心,便設計勸燕王“以國讓子之”。他說,子之肯定會像歷史上的許由一樣不接受讓國,這樣,燕王既得了堯舜的賢名,又不會失去王位。公元前218年,燕王讓位予子之。不料,子之沒拒絕。燕王丟了王位,結果引發燕國大亂。齊、魏、秦、韓、趙等國出兵伐燕平亂。噲、子之均被殺,太子平被立為燕國新君。自禪讓說興起,歷史有記載且為史實的禪讓之事,這可謂第一件。
燕國“禪讓”之亂尖銳地提出了,禪讓由理想到實踐必須解決權力轉換的正當性問題。自人類群居始就存在權力轉換現象。無論以何種方式轉換權力,都必須要讓轉換的權力獲得正當性。世襲制權力轉換的正當性是通過故君與新君的血緣一體來實現的;湯武革命為異姓之間的權力轉換,周人以天命、德治及瑞應等理論闡釋商周權力轉換的正當性,也即以天命證明權力獲得的正當性。當禪讓說興起,其提出賢人政治并欲實行賢賢相授的權力轉換時,那么,權力的賢賢相授憑什么是正當的、為什么應該被認可等問題立即凸顯出來。由此連帶出許多問題,需要人們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論和可操作的方法、程序來解決。顯然,當禪讓說流行之初,這方面的理論說明、制度設計并沒有被認真考慮。真正將禪讓作為異姓權力轉換的方式,并在制度上有所行動的,要到燕噲禪讓失敗三百年后的西漢末年——由西漢儒士圍繞新莽代漢開創的權力轉換機制。
西漢末的儒士們能做這件事,得益于西漢中期朝廷的政策轉變。漢武帝“獨尊儒術”,使先秦至漢初的儒學逐漸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儒學地位的這種轉變,除了皇帝出于統治的需要外,也與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改造儒學有關。漢儒強化儒學經世致用的因素,吸納陰陽、五行、道術等思想資源,雜糅出一套思想、原則及可操作的規制、儀式。比如,董仲舒所說的“天人感應”“災異”“天譴”等思想。“天人感應”將“災異”與“天譴”、“祥瑞”與“盛德”“大治”相聯系,使“天命”“天意”能夠獲得更為具體的解讀。由此,可將國家的政治乃至社會的種種行為納入可觀察、驗證、預測的體系,進而獲得權威的支持。
漢儒的這套理論原本用于論證以漢代秦的正當性的。然而,西漢盛行的五行五德之說,在說明以漢代秦正當性的同時,也產生了負面影響。五行五德說將周人的“天命”觀從勝利者的言說變為世人之識;“天命靡常”變為有規律的五行運轉。五德像自然規律一樣周而復始,那么,由此很自然地會生出“天命”非一姓所獨有的觀念。在西漢五行五德思潮正熾之時,自宣帝至哀帝的六七十年間,連年災異頻發,社會不安,人心惶惶。時人從五行觀念看,漢家氣數已盡。漢末王莽的禪代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醞釀、謀劃、操作的。
客觀地說,在中國歷史上以“禪代”之名搞王朝更迭權力轉換的,王莽是第一人。若論中國“禪代”歷史上,最具儒術、儒味的“禪代”,恐怕也唯有王莽這一次。
王莽靠著家族背景,自身的“折節力行”“勤勞國家”,以及憑借權力翦除異己,達到權傾天下的地位。不過,他有代漢的野心,選擇禪代之途,還有其內在的社會原因。一是,其時社會主流意識極度崇尚經義。趙翼《廿二史劄記》說,“漢時以經義斷事”,可見一斑;又說“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則證明世有所好,行必盛矣。由經義舉禪讓,行禪代,順理成章,難察其奸,取代成本最低。二是,在王莽取禪代之途奪漢位之前,西漢社會早已流行“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的說法,受禪者只需由此往下說,受者為舜之后,即可。王莽代漢,就選擇了這個路子。三是,王莽雖與歷朝取代君位的權臣一樣,是在權傾天下時攫取權力的,但是他以受禮服儒的文臣身份問鼎帝座,既與此前湯武、漢高獲得權力時的身份不同,也與此后漢魏以降操弄禪代的權臣有異。即使他效仿的周公,雖以文臣身份輔佐成王,但其出身卻是武官。要言之,自三代以降,歷代操弄王權更迭、禪代者,多為能統兵作戰的將帥,鮮有受禮服儒的文臣。王莽禪代,是一個不多見的史例。
從《漢書·王莽傳》的記述看,王莽雖以唐虞禪代為輿論,但其禪代行為多以周公、周禮為模本。這既是王莽代漢的路徑特點,也是其禪代命運的規定。王莽如何陰謀策劃取漢而代的過程,已有史書記載,本文不作贅言,只就其采行、建構的禪讓儀規、制度作一些探討,以窺其與禪讓理想吻合的程度。依《漢書》看,王莽行禪代,未采用傳說中的堯舜、舜禹禪讓的方式,而是采周禮加以改造,效周公加以重塑。其設計了立公國、賜九錫、行居攝、偽揖讓、進禪代的禪讓程序:
(一)立公國。傳說中的堯舜禪讓,無立公國之說。王莽于元始元年被賜號“安漢公”,享公爵封邑。王莽以周公的封國為模本建公國,但又受限于漢制。首先,兩者冊立的主旨不同。西周分封諸侯出于“以藩屏周”;漢賜王莽立國,是為褒獎行殊禮,是一種禮遇。其次,由此設立的公國建置不同。西周的周公封國是一方的政治實體,有行政職能、官吏等;而王莽的公國封邑很大,但這只是食邑,非行政區域。再次,西周封國在官員任命等行政事務方面,自主權比較大;而西漢封國的重要官職均由中央委派。由此諸項觀之,王莽的公國實在是以仿周制之名行漢制之實。總之,周制封國的意圖是“以藩屏周”,王莽封國的意圖是欲行禪代。王莽封國建制與立國意圖的錯位,一目了然。
(二)九錫禮。漢魏以降,行禪代前,例行九錫禮。此禮也不是堯舜禹禪讓傳說中的制度。《十三經注疏》說,何休注《公羊》對“九錫”有具體解釋:“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漢之前,帝王為褒獎有功的諸侯,或賦予大臣某種權勢而行九錫禮。《左傳》就有周天子為春秋先后出現的五霸行九錫禮的記載。西漢以降,九錫禮成為歷代受禪者先邀之殊禮。此制始于王莽。王莽所受九錫禮,是漢人按西周“九命上公”“九錫登等”的原則,擇取古制擬作的。西周以禮賜周公封國,是“以藩屏周”;而漢末為王莽設計的九錫禮,除褒獎功能外,更具有對其權力僭越君臣之禮的承認。這是九錫禮成為后世禪代符號、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行居攝。中國歷史上的居攝,指嗣君年幼不能親政,由大臣代居其位理政。這種制度原本與堯舜禪讓傳說及先秦禪讓說無關。王莽禪代前行居攝,實是不能一蹴代漢的無奈之舉。元始五年,漢平帝14歲駕崩,此時的王莽已權傾天下。在立新君的過程中,他選了皇室后裔中最小的廣戚侯子嬰為嗣君,年僅2歲。太后同意王莽居攝,頒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王莽居攝才4個月,安眾侯劉崇率眾反莽,兵敗。朝中大臣以此為借口,說謀逆是因為王莽握權太輕,不足以鎮叛。由是,讓太后允準稱王莽為“假皇帝”。王莽以“假皇帝”之名居攝3年,終行禪代。
(四)即真代漢。王莽居攝是效周公之制,居攝三年,即真代漢,計劃以堯舜禪讓的方式來操作。此時出了一樁“金匱神嬗”的符命之事。《漢書·王莽傳》說:“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對此,王莽沒有效仿先秦禪讓說中許由、善卷等人的諸多揖讓之舉,而是當即下書說:“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
按王莽的說法,他是按照金匱中的漢高祖傳國金策來受禪即真的。也就是說,王莽即真用的是禪讓方式,但不是在位君主(孺子嬰)的禪位,而是以在位君主的先祖劉邦之名禪讓受禪的。雖然,漢末早有高祖為堯后之說、王莽為舜裔之論,但這種堯舜后人的禪讓方式,還是與先秦禪讓的傳說和理想大相徑庭。公元九年,王莽得金匱當日,便即位稱帝(即真皇帝),宣布改正朔,易服色,定國號為“新”。公元20年(地黃四年),更始帝的漢兵攻入長安,殺王莽,西漢末的禪代,就此落幕。
對王莽禪代之敗,論者多矣。筆者從禪讓說進入實踐的視角來觀察:王莽在中國大一統王朝史上,第一個以禪讓名義操弄君權轉換。他從古制中攝取各種規章、禮儀,構建君權禪代制度,為新舊王朝更迭提供了湯武革命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但是,他以周公攝政作為權力轉換方式的模本,這一路徑選擇自始就已陷自身于困局。須知,周公攝政的模式指向是歸政,不是取代。以周公形象自居的王莽,從居攝走向代漢,等于讓周公代周,何其荒謬!此荒謬加上他代漢后實行的種種改制錯誤,使其難以培育新朝代漢的正當性。正當性缺失,新權威難立,是劉氏復漢、王莽失敗的重要原因。
先秦士人的禪讓理想,在走入實踐領域出現的亂象,是不是理想面對實踐命中注定的遭際?但是,有一點清晰可見,禪讓說是由御用漢儒幫扶權臣、政客納入政治領域的。自此,禪讓成為權臣操弄權力轉換的工具。
成為鼎革主流選擇的禪讓制:由受禪者驅動蛻變的權力轉換方式
王莽以禪代方式易漢為新,為后世權臣、野心家以禪讓規避惡名、謀奪君位提供了先例。繼王莽禪代即真后,曹魏代漢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個案。
曹氏以魏代漢,行于文帝丕,萌于武帝操。具體過程,史書記載頗詳。此處僅就曹魏以禪代之名操弄君權轉換,對禪讓禮儀制度的增刪、改變等作一討論。
(一)改換禪代路徑。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去世,曹丕襲位。曹氏代漢提上議事日程。據史載,漢魏禪代,漢群臣、魏公國臣僚勸禪代多達十余次。每次勸禪所引史上先例,多以堯舜禹的禪讓事跡為說辭。可見東漢末的操弄禪代者,刻意避諱王莽的居攝—禪代模式。
(二)改仿西周公國制,建置預備禪代的政體。王莽代漢以周公為范本,建公國取西周上等公國之名,實際操作則按西漢的封國規制。史載,曹氏的封國不效仿王莽的公國做法,而是實質上采行西周裂土分封的方式。這可能與曹氏以武功崛起登頂權臣有關。曹操以武功“相天子”,不似王莽。其受漢封國,由公而王,是在漢獻帝茍延殘喘的局面下操作的。曹操的公國以魏郡為中心,重新劃定九州,分置行政區劃,還按公國禮制,建社稷宗廟。最重要的是曹操的魏國與漢朝一樣,設有尚書、侍中與六卿,也設相國、郎中令等官職。因此,曹魏代漢前,在漢朝事實上存在兩套行政機構,一個是朝廷的,一個是曹魏的。曹魏公國在東漢體內日益壯大,不斷蠶食東漢母體,最終以禪代方式轉換君權。
(三)揖讓禮。古史中的禪讓說,是以賢德為核心,禮讓為準則的。禪讓的要義,就是賢賢相授,不爭。《漢書》載,王莽行揖讓是在受封安漢公爵位和宰衡職位之際。前者封爵固讓了兩次,后者授職也固辭了兩次。至于曹魏代漢時的勸禪、揖讓,裴松之《三國志注》記錄甚詳。按此書的記錄統計,曹丕辭禪、揖讓達19次之多。
自曹魏代漢行如此揖讓始,揖讓成為后世禪代的一種禮儀制度。其后,司馬昭受魏封爵、加九錫,也仿曹丕行揖讓。據《晉書》所載統計,揖讓達十三四次之多。魏晉以降直至隋唐,凡以禪讓改朝換代的,均行揖讓禮。只是,每代史書記載的揖讓內容愈益簡略,次數每況愈下。此種現象表明,原本作為禪讓理想體現賢德禮讓的原則,被轉換設計成了一種君權易姓的禮儀。儀式化的揖讓不再是賢德禮讓。行之越久,儀式越固化,離其原則也越遠。失去內涵的禮儀,同時也失去了令人敬畏的約束力。由此,漢魏以降,用禪讓操作君權轉換,所行的揖讓禮多為血腥易代的偽飾,行之越久,雙方心知肚明,強者奪權在手,揖讓便成為走形式的虛禮。
(四)處置禪君。以禪讓操作君權轉換,實現的是君臣易位。由此便出現一個禪代后禪君(原君王)的處置問題。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禪讓,均為前君衰老、亡故,受禪者即位,不存在舊君安置問題。當先秦盛行禪讓說時,以禪讓理想處理君臣易位的燕國,采取的是受禪者為君、禪君為臣的做法。及至王莽禪代即真,處置漢帝孺子嬰時,明面上雖給予禮遇特權,但行為上要求孺子嬰“北面稱臣”。魏晉以降,曹魏、司馬晉、北齊、劉宋、蕭齊、楊隋的新君對舊主都規定“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也就是說,新君不將舊主降格為臣,突顯禪代中的不臣之禮。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曹魏代漢、司馬晉代魏,雖將禪君封為王公,享不臣之禮,但其封地受監鎮,行動受限制。及至劉裕代晉,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隋代北周,唐代隋,禪君均在禪位不久薨、崩。
以上古傳說構建的禪讓理想,自春秋戰國倡行,至中國史上最后一次以禪代之名操弄趙宋代后周,蹇蹇而行千年。細察這一“理想”走向實踐的歷程,其在西漢末被踐行之初,首先接納它的不是在位的君王,而是欲取代君主的權臣、政客。由此,促成禪讓的第一個變異:自此行禪代不再是上位禪君主動的推動,而是下位權臣謀奪的操弄。禪讓主導角色的這個變化,導致第二個變異:禪讓理想規定的賢賢相授、禮讓易位的核心原則,被位極人臣的權臣所擁有的強力所閹代。禪君平庸不賢,受禪者被考量的不是賢否,而是實力如何。賢賢相授變為權力較量。第三個變異:謀奪者偷換了禪讓理想的核心內容及禮讓程序后,將禪讓最初規定的賢賢相授的內在正當性證明,轉移至以五行、讖緯、瑞徵等方術的外在正當性證明。原本禪讓理想所說的堯舜禪讓,是由禪君的讓與行為使受禪獲得正當性,其禪受雙方內在關聯的權威基礎是天下公認的賢德。觀察賢德的重要表現,是禪受雙方對最高權力真正的敬畏和揖讓。及至權臣用禪讓操作權力轉換,被迫讓位的禪君,雖下一紙禪位詔書,但無內在的權威基礎,由此不得不求助于神怪瑞應的外在證明。最后,在禪代走完封國、錫命、易位的程序后,手握君權的“受禪者”對不久前相揖、禮讓的禪君加之幽閉、鴆殺,可憐的一點禮儀偽飾都被浸入宮廷喋血之中。
先秦士人以禪讓傳說構建禪讓理想,以圖實現賢賢相授的賢人政治,消弭人類在最高層面的權力惡爭,可謂用心良苦。政治理想有擁抱政治的渴望,然而所有進入政治場域之人、事(思想、行為)必定要遵循政治的邏輯。政治邏輯本質上是權力邏輯。通行的不是士人所尊崇的賢德原則。中國自秦漢大一統之后,整個國家的吊詭之處在于,無處不稱“禮”,卻處處皆有爭。在此背景下,禪讓的旗幟高祭了千年。理想實現了?理想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