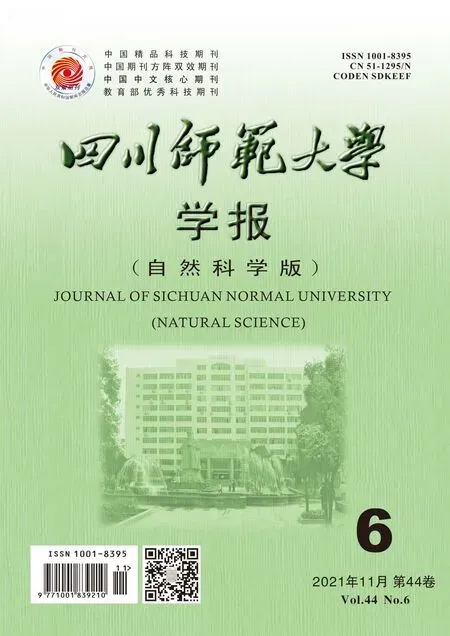CdSe/ZnS量子點對四膜蟲的毒性研究
王志正, 林志康, 沈 陽, 趙宇俠
(1.上海理工大學 醫療器械與食品學院,上海200093; 2.上海健康醫學院 醫學技術學院,上海201318;3.上海中醫藥大學 中藥學院,上海201203)
量子點(quantum dots,QDs)是一種新型熒光納米材料,粒徑范圍一般在1~10 nm之間,由Ⅲ~Ⅴ族或Ⅱ~Ⅵ族元素合成,通常以某種半導體材料為內核,外面包裹其他半導體材料,量子點也因此具有良好的光電性質.目前應用比較多的是CdX(X=S、Se、Te)量子點,其中以CdSe/ZnS量子點熒光強烈、發光穩定、易于合成等特點備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材料的制備及表面生物修飾技術的進步,鎘系量子點被廣泛應用于藥物檢測和生物成像等領域.Cui等[1]用寡核苷酸雜化的CdSe量子點檢測了最低限度0.2 pmol/L的DNA;龐代文等[2]用BSA修飾的CdSe/ZnS量子點測定了中藥片中微量的銅,檢測限達到了1.0×10-4μg/mL.另一方面,量子點對環境以及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和風險也同時引起廣泛關注[3-7].國內外學者對量子點毒性機制、體內遷移路徑和環境暴露風險等方面安全隱患進行了大量的報道[3-7],其中對哺乳動物細胞和動物模型的毒性是目前報道最多、研究最透徹的,其細胞毒性機理可以歸納為以下3點:1)量子點內核與介質相互作用,降解釋放Cd2+等重金屬離子[8-9];2)通過產生活性氧物質(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增加胞內氧化壓力,誘導細胞凋亡[10];3)非特異性吸附到細胞表面,與蛋白結合,破壞結構,影響細胞的正常功能[11-12].
以水生生物包括藻類、菌類、魚類以及無脊椎動物為模型的納米材料生態毒性也有報道.文獻[13-14]報道了不同濃度的C60暴露于自然水環境后黑鱸大腦及中樞神經中起保護作用的細胞遭到了破壞;朱小山等[15]報道了3種碳納米材料對斜生柵藻和大型蚤的生長抑制具有個體差異性;羅勛等[16]報道了納米銀對線蟲的生殖抑制和氧化應激損傷.這些報道說明了量子點對水生生物的毒性效應可能類似于哺乳動物細胞,而目前關于量子點對水生生物的毒性效應,尤其是毒性機制的報道還不是很多,水生生物作為水生生態系統的重要組分,遭遇的毒性效應過程以及產生的生物學變化關聯著生態系統的安全,明確量子點納米對水生生物的毒性機制,豐富毒性效應及機制的相關數據資料將有助于掌握量子點并推斷其他納米材料的水生生態系統安全的風險.
四膜蟲是一種分布于全球各地淡水環境中的纖毛蟲原生動物,在水生生態系統食物鏈中處于重要的位置.四膜蟲對許多毒物的響應比其他高等生物更為敏感、直接,是較理想的生物毒性試驗對象,四膜蟲具有高等真核生物所共有的保守基因和基礎代謝通路[17-18],在毒理學研究中作為水生生態系統模式生物使用.關于納米材料誘導的四膜蟲毒性的報道目前也僅限幾篇,姚瑩等[19]發現納米ZnO對四膜蟲的生長及抗氧化系統的抑制作用.羅慧[20]發現硒化鎘和硒化銀量子點能夠通過內吞作用進入四膜蟲細胞內分布在細胞器,抑制細胞生長,破壞細胞膜,對DNA和線粒體造成損傷,誘導線粒體介導的細胞凋亡.
這些毒性效應都可能與氧化損傷相關聯,氧化損傷作為量子點的毒性機制之一,在細胞和動物范圍被廣泛研究報道,但是未見對四膜蟲的報道,四模蟲作為水生模式生物,一方面可以代表單細胞真核生物的毒性反應,同時也可以闡釋量子點對水生生物的生態毒性風險,本研究擬就量子點對四膜蟲的氧化損傷進行初步調查,分別研究四膜蟲ROS的產生情況,四膜蟲細胞膜損傷情況以及抗氧化系統的調控等方面來考察該機制的影響,同時結合量子點對四膜蟲種群密度的抑制確定其毒性效果,通過研究量子點對四膜蟲的影響,一方面可以闡釋量子點納米作用于生物體后可能產生的毒性及其作用機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其對于整個水生生態系統潛在的風險.
1 材料與方法
1.1 四膜蟲的培養嗜熱四膜蟲SB210株系,由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繆偉實驗組饋贈.四膜蟲是一種單細胞真核原生生物,呈橢圓長梨形,全身布滿纖毛,體長約40~60μm,廣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淡水環境中,其生長周期短,易于培養.四膜蟲的培養基組分為:2%蛋白胨,0.1%酵母提取物,0.2%葡萄糖溶于超純水,121℃滅菌20 min,冷卻后接種四膜蟲,在28℃、150 r/min條件下于恒溫搖床無菌培養至對數期進行后續實驗.
1.2 試劑與儀器實驗所用的試劑:CdSe/ZnS量子點購自上海星紫科技有限公司,粒徑為4.5 nm左右,所用PCR引物由生工公司合成,RNA提取試劑Trizol購自Takara公司,熒光定量PCR試劑購自羅氏公司,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 PI)熒光染色劑、Bradford蛋白定量試劑盒均購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預染蛋白Marker購自Thermo公司;SOD蛋白抗體購自安諾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CL超敏發光液購自美國Bio-Rad公司;無水乙醇購于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其他試劑均為分析純.
實驗所用的儀器:激光共聚焦顯微鏡(Leica TCS-SP8,德國);RT-PCR儀(羅氏Light Cycler 96,瑞士);水合粒徑儀(馬爾文Zetasizer Nano ZS,英國);冷凍離心機(Eppendorf H1650-W,德國);混勻儀(Vorter Mixer QL-866);流式細胞儀(BD LSRFortessa,美國);熒光光譜儀(Horiba QM-8075);透射電鏡(Hitachi HT7700,日本);蛋白凝膠成像系統(Molecular Imager ChemiDocTM XRS+Imaging System,BIO-RAD公司).
1.3 CdSe/ZnS量子點的表征量子點樣品的TEM圖在透射電鏡工作電位為200 kV測定;量子點的熒光光譜在熒光光譜儀上測定,激發光源為75 W氙燈,檢測器為PMT F900.QDs的水合粒徑通過馬爾文的粒徑分析儀測定.
1.4 激光共聚焦觀察量子點與四膜蟲的結合在培養基中加入適量量子點母液,使得終質量濃度為2.4μg/mL,接種0.5 mL對數生長期的嗜熱四膜蟲,于恒溫搖床150 r/min培養1 h,收集培養基于EP管中,4 000 r/min離心5 min,PBS洗滌兩次,去除培養基及四膜蟲細胞上附著的量子點,用4%多聚甲醛固定四膜蟲后,在激發波長為630 nm的激光共聚焦顯微鏡下觀察四膜蟲與量子點的結合.
1.5 流式細胞儀檢測ROS及細胞膜損傷取對數期的四膜蟲9 mL分裝到25 mL錐形瓶中,共設四組實驗組,每組3個平行樣,加入1 mL不同濃度量子點母液,使量子點的終質量濃度分別為0、0.1、2、8μg/mL,在28℃恒溫培養箱中培養48 h后離心(2 000 r/min 10 min)并去除上清,加入預先配置好的PI、DCFH-DA熒光探針分別用于檢測細胞膜損傷、ROS的量,室溫避光孵育20 min后,用磷酸緩沖液(PBS)洗滌兩次去除未裝載的熒光探針,流式細胞儀檢測,PI的激發波長和發射波長分別為530和620 nm,ROS的激發波長和發射波長分別為488和525 nm.
1.6 量子點對四膜蟲存活率影響首先配置質量濃度為250 mg/L的CdSe/ZnS量子點母液,在裝有無菌培養液的錐形瓶中加入不同量的母液使量子點終質量濃度為0、0.1、0.4、2.4、9.6μg/mL,接種0.5 mL對數生長期的嗜熱四膜蟲,于28℃恒溫搖床培養,在150 r/min下培養48 h后,在體式顯微鏡下觀察記數細胞密度,每組3個平行,計算平均值,另設空白對照,與對照相比計算四膜蟲存活率,

并利用t檢驗確定是否具有顯著性.
1.7 熒光定量PCR實驗依據嗜熱四膜蟲GAPDH(序 列 號:AF319450.1)、GST(序 列 號:FJ175686.1)、SOD(序列號:XM_001007667.2)基因在GenBank和NCBI Reference Sequence中的序列,用軟件Primer 6設計基因的引物(見表1),由生工公司合成引物;按照試劑盒操作用Trizol提取總RNA,逆轉錄試劑盒反轉錄cDNA,根據RT-PCR試劑盒說明書取cDNA1.6μL、2×SYBR 5μL、引物0.4μL、ddH2O 3μL配制10μL的RT-PCR反應體系,設置三組重復,95℃預變性30 s后,經過95℃10 s,60℃30 s,共40個循環,最后95℃15 s,60℃1 min,測定溶峰曲線.

表1 實時熒光定量PCR引物Tab.1 Primers for real 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RT-qPCR)
1.8 蛋白免疫印跡法檢測蛋白的表達用100μL含有蛋白酶抑制劑的RIPA緩沖液從量子點處理后的四膜蟲中提取總蛋白,細胞裂解液以12 000 r/min離心20 min,收集上清液即為提取的總蛋白,采用Bradford法測定總蛋白濃度.將等量的總蛋白經十二烷基硫酸鈉-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SDSPAGE)后轉移到硝基纖維素膜上,用5%脫脂牛奶于室溫封閉膜1 h,分別與anti-GAPDH和anti-SOD抗體(1∶1 000)4℃孵育過夜,用TBST洗滌膜3次后用HRP標記的二抗(1∶5 000)室溫孵育2 h,再漂洗3次,每次10 min,辣根過氧化物酶顯色.
1.9 統計學處理方法采用SPSS 21.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數據均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較組間差異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與討論
2.1 量子點表征通過TEM、DLS及熒光光譜對CdSe/ZnS量子點進行了表征,透射電鏡(圖1(a))顯示CdSe/ZnS量子點平均直徑在4.5 nm左右,熒光光譜儀(圖1(b))檢測結果顯示量子點的最大激發波長在573 nm,最大發射波長在603 nm.水合粒徑(圖1(c))結果顯示量子點平均直徑在116.5 nm,Pdi系數0.245,說明量子點在液體中存在聚團現象,但分散情況良好.

圖1 量子點表征Fig.1 Characterization of quantum dots
2.2 量子點與四膜蟲的結合及對四膜蟲存活率的影響如圖2所示,(a)為熒光圖,(b)為明場圖,(c)為merge圖,激光共聚焦顯微鏡可以觀察到,量子點可以聚集在四膜蟲表面并發射熒光,說明量子點可以與四膜蟲細胞結合,具備誘導毒性效應、抑制細胞生長的基礎,圖2(d)存活率的結果顯示,在實驗的濃度范圍內(0、0.1、0.4、2.4、9.6μg/mL),量子點對四膜蟲的生長抑制呈劑量依賴效應,9.6μg/mL的CdSe/ZnS量子點對四膜蟲的生長抑制有39.6%左右,說明量子點對四膜蟲細胞具有毒性,但是在實驗的過程中增加量子點劑量后四膜蟲的種群密度并沒有明顯下降(數據未附加),這可能是由于量子點在液體中存在聚團現象,水合粒徑結果表明聚團的量子點顆粒粒徑遠大于正常量子點,文獻[21]研究表明量子點粒徑越大,對細胞的毒性越小,在本實驗中更高的濃度沒有觀察到明顯的存活率抑制的增加,可能是由于高濃度條件下量子點的聚合現象帶來的影響,聚合后大粒徑的量子點具有小的比表面積,暴露在表面的鎘相對于小粒徑的少,與介質作用產生的游離Cd2+下降,毒性效應受到影響.圖2(d)也說明增加濃度并不會造成更大的毒性效果.圖2中,與CK組相比有顯著差異,*表示P<0.05,**表示P<0.01.

圖2 量子點與四膜蟲結合及對存活率影響Fig.2 Quantum dots bind to Tetrahymena cell and inhibitory effects of QDs on Tetrahymena cellular viability
生長抑制作用是毒理學最基本的指標之一,在本研究中對量子點納米材料對四膜蟲的生長抑制作用也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在研究的濃度范圍內呈現了劑量毒性效應,羅慧[20]也發現CdSe量子點對四膜蟲生長存在抑制作用,且毒性強度與濃度成正比,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
2.3 量子點對四膜蟲的氧化損傷被廣泛接受的鎘系量子點的毒性機制的探討主要集中在重金屬元素Cd2+的釋放、氧化過程中活性氧的產生以及活性氧自由基ROS介導的氧化應激等方面[22],而氧化損傷也是重金屬離子Cd2+的毒性機制之一.活性氧可啟動一個鏈式反應,易與細胞膜上的各種不飽和脂肪酸及膽固醇反應,這種直接作用于細胞的氧化損傷能導致細胞脂質過氧化水平升高,引起DNA氧化損傷,細胞凋亡[23].
圖3(b)的結果顯示,隨著量子點的質量濃度增加(0.1、2、8μg/mL),ROS的產生量基本上呈現了平行增加的趨勢,相對于對照組,2μg/mL處理組四膜蟲的ROS增加了109.4%,增加最多;8μg/mL處理組比對照組增加了73.2%,比2μg/mL處理組略有下降,這可能是在高濃度的溶液中,受到量子點的聚合影響.ROS的作用之一就是攻擊細胞膜,PI用于檢測細胞膜的通透性變化,檢測結果代表細胞膜損傷程度,圖3(a)結果顯示隨著量子點濃度增加,細胞膜的損傷也對應嚴重,除了8μg/mL量子點處理組沒有與ROS的產生呈現一致的趨勢外,其他處理組也大體與ROS的產生相呼應.說明了ROS的產生是膜損傷的主要原因.

圖3 量子點對四膜蟲的氧化損傷.Fig.3 Oxidative damage on Tetrahymena caused by QDs
Wang等[24]研究也發現,TiO2NPs的細胞毒性主要與活性氧自由基的產生有關,與本研究結果類似,印證了ROS介導的氧化損傷;Mortimer等[25]觀察到羧酸化CdSe/ZnS量子點在亞致死濃度下作用24 h內沒有出現細胞壞死、嚴重氧化損傷、脂質氧化和DNA損傷等明顯的細胞毒性,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不一致,本研究的最高濃度在亞致死濃度下,但是細胞膜破壞和ROS的量都顯著增加,可能因為本研究作用的時間48 h比文獻[25]研究的24 h作用時間長.
量子點具有高的比表面活性,能夠轉移電子給溶液中的氧,產生單線氧等活性氧自由基,考慮到活性氧自由基的生命周期只有10-5~10-6s,所以產生的ROS要對四膜蟲實施毒性的必要條件是ROS產生位置要與細胞膜足夠近[26],在本研究中共聚焦的觀察結果能夠看到量子點結合在細胞表面,有足夠近的距離給產生的ROS在生命周期內完成與細胞膜的反應過程,破壞細胞膜.
2.4 量子點對四膜蟲抗氧化系統的影響一般生物體都處在正常的氧化平衡狀態,自由基產生系統及抗氧化系統可以有一定的調節能力,細胞在遭到ROS攻擊,體內的抗氧化系統會通過啟動抗氧化基因編碼抗氧化蛋白的表達來調節機體的氧化還原平衡,圖4(a)和(b)結果表明,隨著量子點濃度的增加,四膜蟲細胞內的抗氧化基因SOD和GST的表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相對對照組來說都處在低表達狀態,Western blot結果顯示如圖4(c)和(d),SOD蛋白的表達與SOD基因也大體一致:隨量子點劑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對對照組呈現低表達.

圖4 量子點對四膜蟲抗氧化系統的影響Fig.4 Effects of quantum dots on antioxidant system of Tetrahymnias
在機體受到ROS攻擊時,對應的抗氧化酶GST和SOD等表達一般會上升,以平衡ROS帶來的氧化應激損傷,在本研究中隨著量子點濃度的增加,四膜蟲細胞內的抗氧化基因GST和SOD及SOD蛋白的表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呼應了ROS產生的效果,Zou等[27]研究了光照條件下TiO2NPs對梨形四膜蟲代謝水平的影響,數據顯示四膜蟲體內的活性氧自由基水平在光照下比在同濃度黑暗條件下增加了1.9倍,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增加了3.9倍,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
但是對本研究來說,各處理組無論蛋白還是基因的表達,相對對照組來說都處在低表達狀態,可能源于量子點與蛋白結合、干擾蛋白表達的能力,本研究量子點具有納米級的小粒徑,能與大分子蛋白接近,并且量子點具有高反應活性,其毒性機制中有一個重要的機制是量子點可能與大分子蛋白結合阻礙其實施對應的生物學功能[8,12].在本研究中出現的現象可能是由于低濃度時,納米聚合情況比較少(聚合的水合粒徑約為116 nm),非聚合狀態的游離納米粒子(4.5 nm)較多,所以和大分子蛋白結合率可能比較高,抑制了對應的抗氧化系統的蛋白和基因的表達,而在高濃度組時游離的小納米相對較少,對抗氧化蛋白的抑制作用減弱,所以能夠觀察到蛋白和基因的表達均高于低濃度組.
3 結論
1)氧化損傷是量子點的毒性機制,本實驗ROS的量與細胞膜損傷程度基本呈一致變化,說明ROS所誘導的氧化損傷是四膜蟲細胞膜損傷的主要原因.
2)細胞膜作為機體的第一屏障,與細胞的生長存活直接相關,所以本研究觀察到的量子點對細胞存活的抑制可能來源與量子點的氧化損傷所導致的細胞膜的破壞.詳細的機制還有待于后續研究.
3)本研究結果中,無論對四膜蟲生長的抑制、細胞膜的破壞、氧化應激等效應都可能帶來食物鏈和生態系統的擾動,水生生態系統的安全需要更多的研究關注.
致謝上海健康醫學院種子基金(E1-0200-19-201132)和上海健康醫學院百人庫項目(B1-0200-19-311133)對本文給予了資助,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