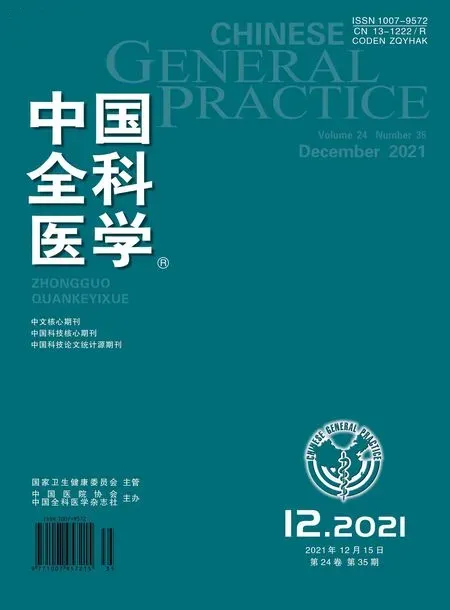電子化認知行為療法治療失眠效果的系統評價
王月瑩,牟云平,尹又,朱冰倩*
失眠是一種常見的睡眠疾病且會帶來較大的危害[1]。研究顯示20%~40%的成人經受失眠困擾[2],約10%的中國人被診斷為失眠[3]。失眠除了會增加心理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癥、焦慮癥)、酗酒、藥物濫用和自殺的危險外,還與免疫功能下降有關[4]。目前失眠主要的治療方式有藥物治療、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CBT-I)或二者聯合應用。藥物短期內作用效果好,但長期應用難免有依賴性及不良反應[5]。CBT-I治療失眠的療效已得到驗證,其可改善失眠癥狀且不會產生藥物帶來的不良反應,該療法已被推薦為失眠的一線治療方案[6]。傳統的CBT-I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形式較復雜、經濟成本高且無法滿足失眠患者日益增長的需求。故電子化CBT-I(digital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dCBT-I)不斷被開發和使用,其是通過各種現代電子科技所呈現/實施的CBT-I,媒介可以是計算機、智能手機等電子設備[7]。有學者對目前12款針對CBT-I的APP 進行了回顧分析,發現其質量參差不齊[8]。全球來看,目前僅有英國的Sleepio和美國的SHUTi這兩種dCBT-I相對較成熟。
相較于西方國家,我國的dCBT-I發展較緩慢[9],特有的文化背景、醫療背景和科技發展水平讓我國的dCBT-I獨具特色。近年來,我國dCBT-I相關研究日漸增多,形式各異(如:微信平臺、自主研發小程序和APP),但干預方案未有統一標準、干預效果也有待明確。基于此,本文對目前針對我國人群設計的dCBT-I及其應用效果進行系統評價,進而為優化失眠的疾病管理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設計 根據PRISMA系統評價方法進行研究[10]。
本研究價值及局限性:
(1)本研究首次聚焦于中國失眠患者,對電子化認知行為療法的應用情況及效果進行了回顧分析,內容上具有創新性。(2)本研究的開展遵守了嚴謹的方法學,且僅納入了隨機對照試驗,有效地減少了偏倚,進而保證因果推斷,方法上具有創新性。(3)本研究首次量化了電子化認知行為療法與藥物治療對于改善失眠的效果,為今后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據。(4)本研究所納入的研究數量仍比較有限,有必要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驗證電子化認知行為療法的有效性。
1.2 檢索策略
1.2.1 檢索數據庫 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維普網、SinoMed、PubMed、EMBase、CINAHL、Web of Science、Cochrane、PsyINFO。檢索年限為建庫至2020年12月,檢索語言限定為中文、英文。
1.2.2 檢索詞 中文為(失眠or睡眠障礙or入睡困難or早醒)and(認知行為療法or CBT or CBT-I or認知行為or行為療法)and(網絡or計算機or遠程or互聯網or在線or平臺or系統);英文為(“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or“behavioral therapy”or“cognitive therapy” or “CBT” or“CBT-I”)and (“insomnia” or “sleep disorder”or“sleep problem”or“sleep disturbance”or “dyssomnia”) and (Internet or online or mobile or digital or computer*or electronic*or telehealth or web*or “web-based” or “ehealth or mhealth”) and (China or Chinese)。以上述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系統檢索。
以PubMed為例:(insomnia[Title/Abstract]OR (((“Sleep Initiation and Maintenance Disorders”[Mesh]) OR “Sleep Wake Disorders”[Mesh]) OR “Dyssomnias”[Mesh]))and (((CBT[Title/Abstract]) OR (CBTI[Title/Abstract]))OR (CBT-I[Title/Abstract]) OR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Mesh])) and (((((online[Title/Abstract])OR (digital[Title/Abstract])) OR (electronic*[Title/Abstract]))OR (web*[Title/Abstract])) OR (internet[Title/Abstract])OR (((((“Internet”[Mesh]) OR “Mobile Applications”[Mesh]) OR “Computers”[Mesh])OR “Internet-Based Intervention”[Mesh]) OR“Telemedicine”[Mesh])) and ((Chinese[Title/Abstract])AND (China[Title/Abstract]) OR (“China”[Mesh]))
以中國知網為例:(主題=失眠+睡眠障礙+入睡困難+早醒)AND(主題=認知行為療法+CBT+CBT-I+認知行為+行為療法)AND(主題=網絡+計算機+遠程+互聯網+在線+平臺+系統)
1.3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1.3.1 納入標準 (1)研究對象:中國成人(≥18歲)。(2)干預方法:試驗組接受dCBT-I,其定義為以現代電子科技所呈現/實施的CBT-I[7],完整的CBT-I包括睡眠教育、刺激控制、睡眠限制、放松、睡眠衛生、認知技術6個板塊。為了更加全面地對dCBT-I的應用情況進行回顧,本課題組納入了干預措施至少包含兩個板塊(認知板塊和行為板塊各一個)的研究,與既往研究一致[9]。對照組接受其他非dCBT-I干預,包括空白對照、傳統面對面CBT-I或藥物治療。(3)結局指標:研究至少匯報了一個睡眠相關指標。主要指標:睡眠質量、失眠嚴重指數、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潛伏期。次要指標:心理社會功能相關指標,包括睡眠信念與態度、焦慮、抑郁。(4)研究設計: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1.3.2 排除標準 (1)研究對象近期接受過CBT-I治療或正在進行其他心理治療。(2)存在精神失調及其他重大疾病者,如嚴重抑郁癥患者。(3)值夜班人群。
1.4 文獻篩選、數據提取與質量評價 文獻篩選、數據提取和質量評價由兩名作者獨立完成;存在意見不一致時,咨詢通信作者的意見,直至達成一致。使用EndNote X9(Clarivate Analytics)進行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管理,根據PRISMA流程圖對文獻進行篩選。首先對標題及摘要進行篩選,進而對潛在的文章進一步閱讀全文并篩選。使用小組團隊自行設計的表格整理所提取信息,主要包含第一作者、年份、樣本量及性別、年齡、干預方法、觀察指標及測量工具、測量時間、脫落人數。
使用Cochrane的Risk of Bias 2 (ROB2)對RCT進行質量評價[11],此工具涵蓋5個領域:隨機過程中產生的偏倚、偏離既定干預的偏倚、結局數據缺失的偏倚、結局測量的偏倚以及結果選擇性報告的偏倚。每一個領域評價結果包括高風險、有一定風險和低風險,各個領域綜合評價后產生一個總評價結果。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Revman 5.4(Cochrane Collaboration)進行統計分析。針對某結局指標,如果至少有兩個研究進行了匯報,則對其進行Meta分析[12]。采用Q檢驗并結合I2判斷各研究的異質性,I2≥50%(P≤0.1)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否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13-14]。采用相同量表進行測量的結局指標,選用加權均數差(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及95%CI為效應統計量進行分析。若研究有多個測量時間點時,則僅將最后一個時間點數據納入分析。若需要的數據研究中沒有報告,則根據文中所提供數據進行相應轉化。對于無法進行Meta分析的數據,采用文字描述進行歸納。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文獻505篇,其中中文433篇,英文72篇。經EndNote及手工去重后剩余354篇;根據標題及摘要去除與文章內容不符的文獻后剩余52篇;7篇文獻被納入最終分析,對其中5篇進行Meta分析,其余展開描述性歸納和總結。文獻納入流程見圖1。

圖1 PRISMA文獻篩選流程圖Figure 1 PRISMA flow chart for study selection
2.2 納入研究基本特征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研究多開展于近5年,6項研究采用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 edition,DSM-5)中的標準診斷失眠,即存在入睡困難、睡眠維持困難和/或早醒、伴隨日間功能損害,每周至少出現3次且持續超過3個月[15];1項研究[16]采用了匹茲堡睡眠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對睡眠質量進行評估。7項研究中,1項研究[17]人群為失眠伴高血壓者,1項研究[16]人群為醫學生。研究樣本量為60~312例,共957例;多以女性為主;年齡19.4~56.4歲。7項研究中,3項[18-20]包含3個組別,其余4項[16-17,21-22]包含2個組別。

表1 研究基本信息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
研究均使用了睡眠日記對各睡眠指標進行測量。5項[16-17,19-20,22]研究使用 PSQI對睡眠質量進行評價,3項[19-21]研究使用失眠嚴重程度指數量表(Insomnia Sleep Index,ISI)對失眠嚴重程度進行評價,另有2項[19-20]研究使用睡眠個人信念與態度簡化量表評價研究對象睡眠相關的信念與態度,其他觀察指標及測量工具見表1。各觀察指標測量時間點多在4~8周;除了1項研究[16]沒有數據脫落,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數據脫落。
2.3 質量評價 7項研究采用隨機化分組方法,其中6項[16-20,22]明確說明了采取隨機化的具體方法;觀察指標測量工具均為主觀量表或睡眠日記,因此結局測量的偏倚中均存在“有一定風險”或“高風險”;約一半的研究中研究對象的脫落率略高,且文中未見對脫落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故存在一定偏倚風險;其他部分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偏倚風險。總體來看,1項研究[19]被評為存在一定風險,6項研究[16-18,20-22]被評為高風險,具體質量評價見圖2。

圖2 各研究質量評價結果Figure 2 Quality appraisal of included studies
2.4 dCBT-I特點 各研究干預平臺差異較大,包括微信平臺、APP、網頁;各研究所包含的干預板塊不同,干預時間4~8周,具體見表2。

表2 電子化認知行為療法干預特點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CBT-I intervention in included studies
2.5 dCBT-I的應用效果
2.5.1 dCBT-I與藥物治療 有2項研究[18,20]比較了dCBT-I與藥物治療的效果,兩組總治療時間在6~8周,均采用睡眠日記測量了睡眠效率、睡眠潛伏期、入睡后覺醒時間和睡眠時間,對二者進行了Meta分析,睡眠效率(P=0.46,I2=0)、睡眠潛伏期(P=0.98,I2=0)、入睡后覺醒時間(P=0.23,I2=30%)、睡眠時間(P=0.58,I2=0)及抑郁情況(P=0.28,I2=1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焦慮情況(P=0.009,I2=85%)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結果顯示,dCBT-I睡眠效率高于藥物治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4.63,95%CI(0.63,8.63),P=0.02〕,見圖3;dCBT-I睡眠潛伏期短于藥物治療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12.18,95%CI(-20.48,-3.88),P=0.004〕,見圖4;dCBT-I入睡后覺醒時間短于藥物治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17.18,95%CI(-30.29,-4.08),P=0.01〕,見圖5;dCBT-I與藥物治療改善睡眠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16,95%CI(-21.25,21.58),P=0.99〕,見圖6;dCBT-I與藥物治療緩解焦慮和抑郁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52,95%CI(-5.06,4.01),P=0.82;WMD=-0.12,95%CI(-1.65,1.40),P=0.87〕,見圖7、8。

圖3 dCBT-I與藥物治療對睡眠效率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3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sleep efficiency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 treatment

圖4 dCBT-I與藥物治療對睡眠潛伏期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4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sleep onset latency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treatment

圖5 dCBT-I與藥物治療對入睡后覺醒時間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5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wake after sleep onset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treatment

圖6 dCBT-I與藥物治療對睡眠時間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6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total sleep time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treatment

圖7 dCBT-I與藥物治療對焦慮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7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anxiety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treatment

圖8 dCBT-I與藥物治療對抑郁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8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depression between dCBT-I and medicationtreatment
2.5.2 dCBT-I與空白對照 有 3項研究[17,19,21]比較了dCBT-I與空白對照的干預效果,3組總治療時間4~8周,均采用睡眠日記測量了睡眠效率、睡眠潛伏期、睡眠時間和失眠嚴重程度(ISI得分),2項研究[17,19]測量了PSQI得分,分別對其進行Meta分析。其中,PSQI得分(P=0.27,I2=16%)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睡眠效率(P=0.003,I2=83%)、睡眠潛伏期(P=0.002,I2=84%)、失眠嚴重程度(P=0.000 1,I2=89%)及睡眠時間(P=0.009,I2=79%)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dCBT-I睡眠效率高于空白對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8.94,95%CI(1.64,16.24),P=0.02〕,見圖9;dCBT-I睡眠潛伏期短于空白對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14.71,95%CI(-27.61,-1.81),P=0.03〕,見圖10;dCBT-I減輕失眠嚴重程度(ISI得分)優于空白對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3.73,95%CI(-6.57,-0.88),P=0.01〕,見圖11。dCBT-I與空白對照睡眠總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14.57,95%CI(-14.35,43.49),P=0.32〕,見圖12。dCBT-I改善睡眠質量(PSQI得分)優于空白對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2.21,95%CI(-3.04,1.38),P<0.000 01〕,見圖13。

圖9 dCBT-I與空白對照對睡眠效率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9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sleep efficiency between dCBT-I and non-active treatment

圖10 dCBT-I與空白對照對睡眠潛伏期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10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sleep onset latency between dCBT-I and non-active treatment

圖11 dCBT-I與空白對照對失眠嚴重程度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11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insomnia severity between dCBT-I and non-active treatment

圖12 dCBT-I與空白對照對睡眠時間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12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total sleep time between dCBT-I and non-active treatment

圖13 dCBT-I與空白對照對睡眠質量影響的Meta分析Figure 13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n sleep quality between dCBT-I and non-active treatment
2.5.3 dCBT-I與傳統 CBT-I 有 2 項研究[18,22]對 dCBT-I與CBT-I進行了對比。因這2項研究的結局指標并不相同,無法進行Meta分析,故對其進行描述性分析。葉圓圓等[18]與毛洪京等[22]研究均顯示,經過8周的治療后,dCBT-I和傳統CBT-I均可有效改善睡眠,且二者在效果上無顯著差異。
2.5.4 其他研究結果 根據一項研究對象為醫學生的研究[16],dCBT-I在改善整體睡眠質量(PSQI得分)方面優于常規睡眠相關健康教育(t=3.231,P=0.002)。此外,一項研究[20]發現,dCBT-I和藥物治療均能顯著改善患者的焦慮、抑郁情況(治療后數據與基線相比:P<0.05),dCBT-I還可改善研究對象的睡眠信念和態度(治療后數據與基線相比:P<0.05)。另一項研究[19]也發現,dCBT-I較空白對照也能改善睡眠信念和態度(P<0.01)。
3 討論
本文對針對我國人群設計的dCBT-I及其應用效果進行了總結和分析發現,目前的dCBT-I應用形式較多樣,其可有效改善睡眠,且效果與傳統面對面dCBT-I具有可比性。
3.1 我國dCBT-I的應用 通過對既往文獻進行回顧發現,各研究所使用的平臺比較零散,沒有統一的標準。本研究納入的文獻中,應用平臺更是從自主研發的APP、第三方小程序到僅通過網絡平臺發送學習音頻、視頻不等,研究對象參與平臺不一致,這可能會對治療效果產生一定的影響。目前,國內比較成熟的網絡化平臺有“30天心理自助平臺”,是由中國CBT專業組織出品的首個CBT網絡平臺,于2016年正式上線。李金陽等[23]在2017年對CBT網絡平臺上線1年的應用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其在老年失眠患者中的應用不足且使用者大多為病程較短、首次發病的患者。相對而言,國外成熟的dCBT-I應用平臺較多,包括SHUTi、Sleepio、CBT-I Coach[24],這些項目可為我國dCBT-I的研發和優化提供參考。
本文中各研究的dCBT-I組脫落率為0~42.1%,這與國外一項Meta分析[25]的結果基本一致,提示在今后的實踐中要進一步優化dCBT-I的使用,降低使用人群的脫落率。目前,我國dCBT-I的應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僅有一項研究涉及大學生人群。我國的近期研究中還出現了骨科焦慮并失眠患者應用dCBT-I(非RCT)[26],同時也有將電子化形式的認知行為療法結合藥物治療共同進行的研究[27]。相比而言,國外dCBT-I應用人群較廣,包括抑郁癥患者[28]、軍人[29]、工人[30]、乳腺癌存活者[31]等,其應用較成熟且取得了較好療效。在今后的實踐中,也可在其他人群中驗證dCBT-I的效果。
針對失眠的完整CBT-I多包括6個內容、5個板塊。本文中6項研究包含了所有5個板塊,1項研究未納入認知干預模塊。目前,關于哪些板塊對于治療失眠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研究尚有限。2019年的一項RCT[32]將一整套CBT-I的模塊與單獨使用其中的睡眠限制模塊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種方法的治療效果基本一致,沒有明顯差異;但是,接受了完整CBT-I的研究對象對治療的滿意度更高。今后可開展相關研究,對其進行驗證。另外,7項研究中的睡眠限制板塊均進行了個體化調整,僅有毛洪京等[22]將研究對象的失眠癥狀進行亞型分類(3類):入睡困難、睡眠效率低、主觀睡眠質量差,睡眠障礙(夜間反復易醒),睡眠時間過短、日間睡眠障礙;其他研究中未進行分類。不同亞型的失眠可能對于dCBT-I治療反應有所不同;正如毛洪京等[22]所提出的,以入睡困難為特點的失眠患者效果好于其他亞型失眠患者。這提示在今后的研究中,應針對不同亞型的失眠患者制訂更加個性化的干預方案,以便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本綜述中,超過一半的研究在干預過程中通過干預平臺與患者進行1次/周的溝通,但鮮有進行長期隨訪的研究。HO等[19]研究中干預組中采取了dCBT-I與電話支持相結合的方法,發現在干預后第12周后的隨訪中,dCBT-I與傳統CBT-I在睡眠質量上有顯著差異,有電話支持隨訪的dCBT-I有更大的改善,且dCBT-I的數據脫落率相比CBT-I 更低一些。目前,我國對dCBT-I的長期隨訪數據尚不足;國外相對較多[33]。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34]發現,dCBT-I對于提高患者幸福感、生活質量均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持續。此外,2019年的一項研究[35]也發現dCBT-I在干預后18個月對改善失眠、日間功能及睡眠信念仍有效。基于以上結果,有必要對我國dCBT-I的應用效果開展長期隨訪研究。
3.2 dCBT-I的應用效果 目前,較少有研究對dCBT-I與藥物治療進行比較。本研究發現與藥物治療相比,dCBT-I在改善睡眠方面效果更優,其可緩解焦慮、抑郁,且效果與藥物治療具有可比性。既往的文獻綜述中,尚缺乏相關系統評價直接將dCBT-I與藥物治療進行比較。根據國外的1項實證研究[36],經過藥物治療仍有失眠癥狀的患者接受6周的dCBT-I治療后,其失眠癥狀得到緩解。既往國內外研究中,有學者將dCBT-I與藥物聯合,發現在治療結束后,聯合組的睡眠改善效果顯著高于單純藥物組[20,37]。基于目前的研究現況,有必要開展更多的研究對dCBT-I與藥物治療失眠的效果進行比較。
通過對3項研究進行Meta分析,發現與空白對照組相比,dCBT-I可明顯改善睡眠質量(例如睡眠效率、睡眠潛伏期、ISI得分、PSQI得分)。這一結果與既往Meta分析結果基本一致[12,25,33,38],然而,在延長睡眠時間方面,本研究未發現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與既往開展于西方人群中的eta分析[9]有所不同:與對照組相比,dCBT-I可以增加睡眠時間約15 min。分析造成此種差異主要原因為本Meta分析綜述所納入的文獻數量比較少,樣本量不足以檢驗睡眠時間方面的統計學差異。
本研究還發現,dCBT-I與傳統面對面CBT-I在改善睡眠方面效果相當。這一結果與既往Meta分析結果基本一致[12]:該Meta分析發現以上兩種干預在ISI評分、睡眠效率、睡眠時間上無顯著性差異。值得一提的是,葉圓圓等[18]研究中,治療第4周時,與CBT-I相比,dCBT-I各項睡眠參數均差一些,而第8周時,二者便沒有顯著差異,提示dCBT-I治療起效較慢。毛洪京等[22]發現dCBT-I與傳統CBT-I的總體療效差異不大,但不同因子對治療的響應有差異。例如,傳統CBT-I的整體睡眠質量有明顯改善,這可能與面對面時醫生給予患者更多的鼓勵和支持有關。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考慮在實施dCBT-I時應注意人文關懷以提高患者的主觀感受。
3.3 局限性 本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僅納入了RCT,有效地減少了偏倚并保證了因果推斷。本研究還首次量化了dCBT-I與藥物治療對于改善失眠的效果。本研究存在以下主要局限性:雖然進行了全面的檢索,但符合納入和排除標準的研究數量仍十分有限。這一方面體現了目前關于此領域的研究現況,另一方面也導致沒有足夠多的數據對dCBT-I與面對面CBT-I的效果進行Meta分析。此外,為了對目前我國dCBT-I的使用情況進行全面、完整的回顧,未對dCBT-I的開展平臺和形式進行限定。因此,各研究所使用平臺較零散、開展形式及內容不夠統一,這也提示今后有必要開展更多的研究驗證dCBT-I的使用效果。與既往研究類似[9,38],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均采用了問卷對睡眠進行測量,易造成主觀偏倚。雖然失眠的評估主要基于主觀自我報告,但客觀方法也具有一定價值。此外,約有一半研究脫落率略高[17-18,20]且脫落原因未知。這兩點主要導致了所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價結果呈現出較高的偏倚風險。另外,本研究所納入的研究多為中老年人群,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于年輕的失眠患者。基于以上,今后有必要開展更多的高質量研究對本研究的結果進行驗證。
目前,我國dCBT-I形式和內容多樣,尚未有統一的實施模式。今后的實踐中,應結合我國的醫療環境、文化環境、人群特點,進一步優化已有的dCBT-I平臺,以便特異性地對我國失眠人群實施遠程干預。此種平臺的構建,不僅可以緩解醫療壓力,還能推動睡眠醫學的發展。基于現階段證據,dCBT-I是改善失眠的一種有效方法。今后的研究中,可采用主、客觀結合的方法(例如,睡眠日記和體動記錄儀)對不同年齡段失眠患者的睡眠進行測量,同時可對比dCBT-I和傳統面對面CBT-I或藥物治療的效果。此外,還應增加隨訪時間,以觀察dCBT-I的長期應用效果。
作者貢獻:王月瑩進行研究設計與實施、資料收集整理、評估、撰寫論文;牟云平進行研究實施、資料收集、評估;尹又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判性評閱、指導;朱冰倩進行研究設計,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判性評閱、指導,獲取研究經費,進行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