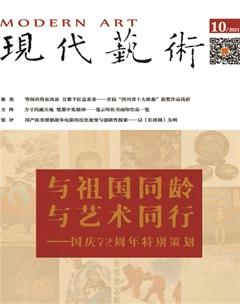《涼山紀》:何萬敏“戀地情結”的書寫
謝天開
紀,同記,作為一種文體,書寫靈動,在繽紛與靜默間,既可致廣大,亦可盡精微。此書命名為《涼山紀》,總41萬字,以記述涼山的歷史地理民族,是著者何萬敏對涼山“戀地情結”的大書特寫。
“天空飄著密雨,云霧也遮掩了北麓高聳的小相嶺。在97歲的王青美老人越來越模糊的印象里,登相營里的上北街和下北街好似一條扁擔,兩頭挑起了她的人生中熾熱的青春與從容的晚年。”
《涼山紀》帶有新聞視角與風格,這是長期作為新聞記者的何萬敏醉心于非虛構寫作的胎記。在《涼山紀》中我們讀到何萬敏對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唐《蠻書》《喜德縣志》《甘洛志》的引用,對1936年6月上海《良友》雜志的查證,對曾昭掄教授《滇康道上》記述的再訪驗證,這些無不顯示出何萬敏作為涼山地方文化學者的嚴謹。如此,知行合一的田野考察讓《涼山紀》作為一部人文歷史地理隨筆,在且行且止,且觀且悟間,兼具新聞工作者的敏銳與地方文化學者嚴謹以及人文作家流暢又貼切的文筆,這是何萬敏的文字之所以耐讀的奧義之一。
何萬敏生于涼山美姑縣一個叫“侯播乃拖”的地方,自從小行走于崎嶇山路間,后來讀大學,再后來在成都工作了一段時間,最終還是返回了心念不舍的涼山。何萬敏雖為漢族,卻因為生于斯長于斯,竟然不自覺養成了常年放牧在大涼山上彝人的身體姿勢——“置身山巒重疊的原野,時常會用雙手抵在眉骨的位置,以手的影子遮擋高原的熾熱的陽光,時常瞇起眼睛,眼角過早堆積的皺紋,安靜守候心愛的牛羊。的確,光亮刺得人睜不開雙眼,眼力還得盡可能放得遠些,更遠一些。”其實這樣的姿勢,就是在涼山這個陽光異常明亮之地下,人地互動的身體塑造與體驗。
不過,何萬敏眼目中的“牛羊”不是牲畜,而是那些似牛如羊的涼山山形嶺勢,他說:“涼山,我的精神高地。”又言“我唯有以山之子,進出于大涼山中。”這正是何萬敏對大涼山的熟悉與依附,不過,生于其中長于其中的他又是如何獲得對于涼山的審美距離的呢?
為了建立對于涼山的審美距離,何萬敏除去了功利性,在田野考察與文獻考證方面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在讀書評書、交友交流方面,更為“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何萬敏所交益友多,也正是因為在二十年前的一個夏天交往了林耀華先生的大弟子莊孔韶的研究生蕭亮中,才得以讀到林耀華的《涼山夷家》,進而走上了描述研究涼山地方文化的文學與學術道路,何萬敏還曾交往過涼山影像作品《百褶裙》的作者林茨,何萬敏在《涼山紀》前言里專門紀念道:“毫無疑問,林耀華先生,還有后來的蕭亮中、林茨等諸多學者對待學術的專注與誠實,對待生命的珍惜與信念,令人充滿敬意,我望其項背,誠懇地追尋。”正是這樣的考察考證,讀書評書,交友交流,讓何萬敏對大涼山保持了自己的審美距離,把對在涼山的行走與閱讀,轉化為對涼山空間的把握與領悟,進而抵達了對涼山的審美精神高地,這是《涼山紀》文字之所以耐讀的又一奧義。
何萬敏對于自己的出生地美姑縣侯播乃拖的關隘之地——“牛牛壩”充滿一種崇高的敬意,有一種依戀母親般的戀地情結。牛牛壩在涼山負有盛名,相傳曾有一位名叫牛牛的彝族婦女最先定居此地,這在涼山彝族傳說及《送魂經》《招魂經》中都有記載。何萬敏自語道:“牛牛壩既是一個短暫的終點,也是另一段旅程的起點。我曾無數接近它,又無數遠離它,每一次心中都充溢莫名的感懷,仿佛那是一扇門,是生命與一方天地達成某種會意或默契的通道。”可以說,牛牛壩就是涼山在何萬敏心中的濃縮象征,他對牛牛壩的戀地情結,就是對整個涼山的身心和環境的同頻共鳴,環境的嚴酷養成了敏銳的感覺,童年的經歷影響了一生。
何萬敏與筆下的涼山人不僅是采訪者與受訪人的關系,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彼此深交信任的朋友,因為大家都是涼山人,大家都有著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都有共同的文化胎記。正是這樣,《涼山紀》中詳細記述了西昌古城的歷史;記述了“彝族的主要支系”對涼山彝族的考證;解析了摩梭人的婚俗;探析了涼山節俗;述評了彝族信仰……如此描述,不僅是在向前輩學者們致敬,并且讓《涼山紀》隱隱存有一條涼山民族志的脈絡,顯示了涼山人獨特的文化心理模式:雄渾、狂野、堅毅、深情。
“在大涼山深處的美姑縣,依洛拉達是侯播乃拖之后,我迄今為止所到次數最多的鄉……村會計阿以格是當地有名的精明人,開過瓦廠賺了一些錢,瓦廠拆了,現在又開小賣部。小賣部的窗口很小,對著小窗口的一面木柜上擺滿了廉價的糖果、餅干、礦泉水、方便面等。賣得最多的是啤酒,從縣城批發價每件31.5元,他拉來單件賣35元,10件以上賣32.5元,50件以上賣32元。‘差不多賣1000元有70元利潤,小賣部每個月能收入2000元左右。阿以日格人到中年,和他人聊起時并不諱言:‘因為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超生兩個總共‘賠了3萬元,最小的兒子才1歲,其余4個都在讀書,平常娃兒媽媽守小賣部。”
在“山上依洛拉達”一節中,何萬敏的描述如法國歷史學年鑒學派一樣細致扎實,將大山深處彝族人家的微觀經濟狀況呈現得一清二楚。如此記錄書中比比皆是,可見是有意為之,這也是《涼山紀》較一般人文游記更耐讀的奧義。
作為涼山的歷史地理民族人文“紀”,《涼山紀》不僅有文字,還有大量圖像記錄。以圖證史,圖文互證是此書最明顯的特色,每一幅圖像都是精心選擇過的,兼具新聞記錄與藝術美學特質,一幀幀光影斑斕,一幅幅美侖美奐,這既是何萬敏作為作家、學者與攝影家的合作結晶,也與他本人畢業于美術專業并長期從事新聞寫作攝影工作有關,這肯定又為《涼山紀》耐讀的一奧義所在。
“從最早走出大涼山的曲比阿烏、蘇都阿洛算起……這是一份長長的名單。我在這份并不完整的歌手名單中,似乎找到了一條音樂的譜系。他們各有特色,卻又有相同的底蘊——天高地遠,群山渾厚。”
在讀至《涼山紀》最后的章節“彝人之歌”時,我驚訝于何萬敏對涼山音樂文化猶如細看掌紋一樣清楚確定——“由于歌唱很自然地與文學結合,唱往往使祈禱和巫術中的語調更有力,所以歌唱很可能就是由說話的語調發展來的。”這是他引述蘇珊·朗格的美學名著《情感與形式》來評論涼山的音樂文化。在這一章節中,何萬敏還深入地探討了涼山音樂文化的“民族化”與“國際化”,比對了“現代性”“都市化”與彝族新民歌的“邊緣化”“異質化”,其間的描述、分析、評論、結論準確、妥貼又充滿新見。
天高地遠,群山渾厚,江流激蕩,民生其間,自有稟性。“戀地情結”是人與地之間的感情紐帶,而《涼山紀》則是何萬敏“戀地情結”的真誠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