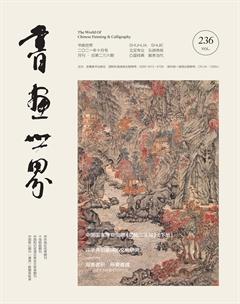陶養(yǎng)筆墨靜守花開
祝振中
陳昭在讀碩士期間,曾囑余為他的畫作寫過一篇短文,至今已近十年。十年樹木,該有成材之相了。事實(shí)上,十年來他的進(jìn)步也是顯而易見的:繪畫語言漸趨成熟,個(gè)人風(fēng)格初現(xiàn)崢嶸,已從一位才情少年成長為實(shí)力不俗的畫家了。而今博士甫一畢業(yè),他就入職天津美術(shù)學(xué)院,從藝生涯更上了一個(gè)平臺,預(yù)示著在學(xué)術(shù)研究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將有更廣闊的眼界、更高級的思維,以及更為便利的條件,其繪畫技藝與境界的提升,當(dāng)是指日可待的。
陳昭近年來的創(chuàng)作,也顯示了這樣一個(gè)良好的勢頭。與其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創(chuàng)作相比,他近期作品在用筆線質(zhì)上更強(qiáng)調(diào)骨法之力;在用色用墨上,更關(guān)注水的運(yùn)化之妙;在篇章布局上,更注重虛實(shí)開合的多種要素融合。其繪畫境界呈現(xiàn)出單純與燦爛之間的豐富意象,在文化品位上展現(xiàn)出體證與踐行的堅(jiān)實(shí)步履。
其一,對筆墨技法的理解與表現(xiàn),由體悟漸入實(shí)踐,已轉(zhuǎn)向筆墨文化的核心環(huán)節(jié)。

陳昭 古意雜花四條屏138cm×34.5cm×42021
凡對傳統(tǒng)中國畫有深切體驗(yàn)的人,都不能不承認(rèn):筆墨呈現(xiàn)的是中國畫的技術(shù)與精神高度。從技術(shù)層面說,筆墨技法的錘煉,離不開書法修養(yǎng)。對書法筆法的運(yùn)用,以及由筆法而衍生的中國畫的描繪與書寫之法,都是技法的核心內(nèi)容。古人一直強(qiáng)調(diào)書畫同源之說,趙孟說:“方知書畫本來同。”石濤也說:“畫法關(guān)通書法津。”此皆過關(guān)者語,絕非玄言欺我。前人有具體解語。如元人說:“寫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董玄宰則說:“士人作畫,當(dāng)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黃賓虹深以為然,曾說“吾嘗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畫”。賓老一生研習(xí)吉金、草書,其繪畫筆法之源,當(dāng)賴此不少。
事實(shí)上,我們讀前代大師畫作,對書法、畫法之辨,自然會有真切而實(shí)在的體驗(yàn)。然而,筆法也只是方便門徑,終須由筆法而上窺精神,直見性情、氣格。此一關(guān),卻非人人易過。修持得法,而又勤勉不輟者,方有望解脫繩束,成為“透網(wǎng)之鱗”。所以這一關(guān)也是難關(guān),唯其為難,于有志者而言,才有攀越的鵠的與高度。
明清以來的花鳥畫大家,功成者皆在書法與繪畫之中兩相補(bǔ)益,映照生輝。如八大山人的奇逸靈變,金冬心的質(zhì)樸古拙,皆在技法與精神層面修煉到書畫一如的境地。近世以來,蒲華、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都代表了這一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展,其生命力歷久彌新。

陳昭 使君子245cm×125cm2019
陳昭的花鳥畫,在筆墨取法上,曾以八大山人為主,筆致求沉著清厚,兼參蒲華、吳昌碩等數(shù)家,通過行筆中平和的提按,強(qiáng)其骨力。他近期的作品,則轉(zhuǎn)向以黃賓虹為主,同時(shí)旁參潘天壽、李苦禪等大家,注重行筆的質(zhì)感與內(nèi)力,加大了提按頓挫對筆線形質(zhì)的修正,使骨法用筆更具有視覺上的造型意義。
他的這一改變,主要源自對黃賓虹的研習(xí),也有工具習(xí)性的影響。在其筆線中棱角與蒼茫互映呈現(xiàn)的背后,可以看出他心性修為中的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將更利于其筆墨個(gè)性的內(nèi)修,以及語言自信的呈現(xiàn)。
其二,在用水用色上,陳昭作品體現(xiàn)出對黃賓虹花鳥畫的深切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強(qiáng)化了他近期作品的風(fēng)格特征。
黃賓虹的花鳥畫,在用水用色上一如其山水畫,有著豐富的樣貌,有時(shí)看似隨意,實(shí)則有深刻的理性考量。這使他的作品技法出神入化,似乎法無定法,更多是隨境而生。所以學(xué)習(xí)賓老的花鳥畫,當(dāng)獨(dú)具只眼,既須見出其技法之門,又須深察其幽微內(nèi)心,于燦爛之中歷歷分明,于分明之處又不著氣力。禪宗所謂如鹽入水,戴本孝所說“最分明處最模糊”,此境可與賓老花鳥互參。所以后人臨習(xí),既須由法而入,又要不拘法相,“爐錘在手,矩鑊從心”,其難度之高,常令人無奈。

陳昭 百葉繁茂281.5cm×192cm2021
陳昭研習(xí)黃賓虹,已有數(shù)年之功,在花鳥畫用色上,可謂深體其微,領(lǐng)其妙旨。他的近期作品,用色濃艷時(shí)不失腴潤;水色清淡處,或以沉著求其厚,或以實(shí)筆見其骨。賓老由漬墨法演為漬色,用色時(shí)常以宿色或雜色著筆,落紙時(shí)飽蘸水分,求得漬色的潤澤與爛漫,兼以宿色中的顆粒助其清厚。賓老用色,得于用水之活,無可而無不可,全在以心使筆。他說:“水墨神化,仍在筆力。”所以其畫面看似融漲一團(tuán),實(shí)則筆致幽微,起訖分明。后學(xué)者當(dāng)參其用心,不落皮相乃為得法。
陳昭花鳥畫用色上的另一過人處,還在于他應(yīng)物象形而直見物象生機(jī)。這得力于他長年的寫生實(shí)踐,以及隨時(shí)隨處觀察物象的養(yǎng)成之功。常見一些畫家,寫生時(shí)匆忙落筆,以瀟灑飛動為筆墨時(shí)尚,物象形神懸隔萬里,使寫生成為宣泄一己情緒的借口,未免失其本旨。取法黃賓虹這樣的筆墨風(fēng)格,更易流于浮煙漲墨,以水墨滋漫、點(diǎn)畫狼藉自標(biāo)不俗,實(shí)不知已入魔道矣。
陳昭的花鳥畫很好地觀照了色墨漬融與神形精微相兼顧的課題。如他畫的繁復(fù)牡丹,無論勾勒還是點(diǎn)染,皆于虛實(shí)濃淡中水色浸潤,融滲有度,常得天然之妙。宿色用得清透凈朗,花的形狀與風(fēng)神毫無漫漶與污濁之相,始終有清潤之氣,著實(shí)不易。
其三,陳昭花鳥畫的境界取向,已向燦爛沉靜、自然曠達(dá)更進(jìn)一層,顯示出藝道兼修的天分。

陳昭 秋意圖70cm×35cm2019
毋庸諱言,其前期的花鳥畫雖然在對八大山人的理解上有獨(dú)到之行,但畫面形式過于強(qiáng)調(diào)對比關(guān)系,稍有生硬之嫌,且氣息未能盡脫濁厲。這當(dāng)是少年時(shí)期所不可避免的。而近年之作,則在燦爛之中不失沉靜,畫面疏密虛實(shí)趨向自然而然,可見其修心與為藝,積淀已厚矣。
中國畫雖重氣勢,然境界以靜氣為高。即便筆致霸悍、墨彩飛動,然落筆終須氣定神閑、游刃有余。高韻深情、堅(jiān)質(zhì)浩氣,于書于畫既為必需,養(yǎng)成之功,又豈是言語所能道盡。東坡學(xué)士學(xué)問贍富、修養(yǎng)達(dá)觀,于書于畫乃能著筆成境,“無意于佳乃佳”。他說:“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一靜一空,道出修心真諦。清風(fēng)明月,水流花開,吾輩為藝,內(nèi)心有多少歷練,前路就有多少資糧。惲南田妙于寫生,自陳心曲曰:“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苔草,抽毫研色,以吟春風(fēng),信造化之在我矣。”其心境若此,畫境燦爛之外,方不乏靜氣。惜我輩再無那樣福分,像梭羅一樣,在瓦爾登湖畔自筑木屋,耕讀自給,以深入大自然內(nèi)心,聆聽萬物之靈的隱語。—現(xiàn)實(shí)已讓我們變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然而今人也有今人的條件。可依交通之便利,廣見奇花異草,在寫生中反觀自性,得窺萬類之靈,庶幾可近天地之心。

陳昭 家鄉(xiāng)風(fēng)情144cm×77cm2016
近年來,陳昭每年都拿出大量時(shí)間用于寫生,在其住處的小園中也不忘養(yǎng)花蒔草,既為陶養(yǎng)性情,也為更近距離地觀察花卉的生長。“萬物靜觀皆自得”,心與物會,融情于境,下筆時(shí)自然能夠體會那層心隨筆運(yùn)、忘我而忘物的畫禪境界。八指頭陀有句:“心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于畫家而言,眼中之花也就是心中之花。由此我想,陳昭筆下那些燦爛的春花秋卉,有多少不是親手所植、真心所守呢。所以陶養(yǎng)性情,也就是陶養(yǎng)筆墨,當(dāng)兩者相合無間時(shí),筆下也就無所不適了。
另外,我注意到陳昭近年來的花鳥題材畫,家鄉(xiāng)風(fēng)物越來越多了。如他畫沱湖風(fēng)物中的水鳥、魚類等,雖從李苦禪、潘天壽處取法較多,但看得出他的描繪帶著一種記憶的溫情,留有兒時(shí)生活的回饋,使這些畫作染上一層真醇樸厚的基調(diào),別具一番感人的力量。
海德格爾曾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xiāng)。其實(shí)一切藝術(shù)終究會走向這一歸宿。劉亮程先生的《一個(gè)人的村莊》,是文學(xué)最精彩的抵達(dá)。由此,我又想起《瓦爾登湖》里的一句話:“一個(gè)活得真摯坦誠的人,一定生活在遙遠(yuǎn)的地方。”作為一個(gè)畫者,如果他能隨時(shí)深入身邊的生活,聆聽草木拔節(jié)、蟲鳥翻身的聲音,其實(shí)他就同時(shí)遠(yuǎn)離了那些俗塵的遮蔽,而獲得了遠(yuǎn)看的視野。只是我們尚須時(shí)時(shí)拂拭,以保護(hù)我們脆弱的真誠。因?yàn)椋安徽\無物”。
我很樂意看到陳昭這些流露真摯情感的繪畫,也希望他一直真誠地走下去,找到筆墨安頓的心靈故鄉(xiāng)。
其四,對畫面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注,使他的繪畫逐步從理性的自覺,進(jìn)入自如駕馭的層面,向文化的綜合表現(xiàn)更進(jìn)一階。
陳昭在研習(xí)八大山人繪畫時(shí),已建立了畫面結(jié)構(gòu)的理性框架,于疏密虛實(shí)、分間布白尤有體悟。讀博士階段,他又在張立辰先生的指導(dǎo)下向課題高處深研,以潘天壽繪畫的款識作為研究方向,提綱挈領(lǐng),由畫面結(jié)構(gòu)深入境界營造,切入了寫意花鳥畫綜合表現(xiàn)的文化內(nèi)核。
誠然,潘天壽繪畫構(gòu)圖上的理性思考,當(dāng)承八大山人而來。而潘天壽畫面形式中的各種要素則更為全面,更為完整統(tǒng)一。例如題款的位置、形狀,字體與內(nèi)容的匹配,多款的呼應(yīng),款與印的搭配,款識與意境的關(guān)系等,已將款識強(qiáng)化為畫面不可或缺的造境要素。他所提出的中國畫家“不必三絕,但須四全”的主張,既是對修養(yǎng)的強(qiáng)調(diào),也是著眼畫面結(jié)構(gòu)的綜合性要求所提出的對策。
當(dāng)然,能“四全”,是否就可直上中國畫文化品格的高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愚倒以為,從目下實(shí)際出發(fā),暫且放下“四全”之忙,以讀書作引領(lǐng),以試內(nèi)心之慧根:倘能直會一項(xiàng)之妙旨,便可深入下去,撥亮心燈;如有余力,自可觸類旁通,甚至一通百通,則善莫大焉。陸儼少先生提出的“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的主張,是否也是從這一角度做出的考量,余不敢斷言,但深以為然。
近十年來,陳昭一直行走在讀書、畫畫的修習(xí)之路上,從碩士到博士,讀書之量自不待言。而在今后的專業(yè)教學(xué)中,讀書思考也肯定仍是常態(tài)。所以在讀書中陶冶性靈、涵養(yǎng)筆墨,其畫面的文化品格會在不知不覺中更上高階,畫境的不斷提升也就順理成章了。
陳昭正當(dāng)盛年,有著良好的自身?xiàng)l件與外部環(huán)境。相信不久的將來,他筆下定會綻放出更多彩、更自如的寫意之花。
2021年元月于見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