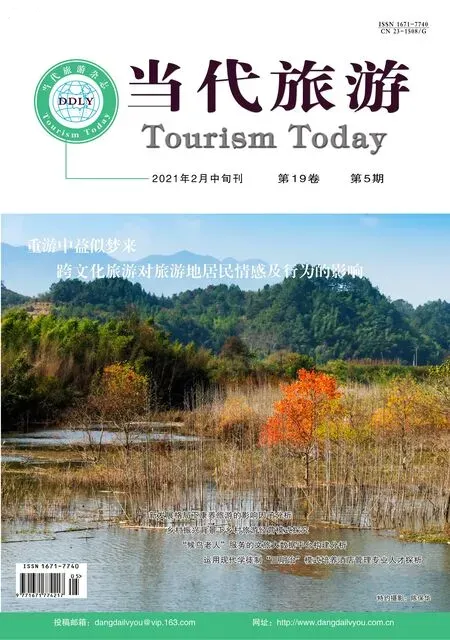上海會展業發展因素分析
鄭鈺杰
上海大學,上海 200072
引言
會展活動為旅游注入內容,旅游為展會提供服務;會展為地區帶來游客,旅游為展會增加內涵。目前,在傳統旅游業邊際效用遞減的同時,會展對旅游業的驅動作用變得更為顯著。受疫情影響,全球會展、旅游業備受唏噓,但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成功舉辦,體現了會展旅游不容質疑的社會發展價值,尤其是時代急需的經濟循環功能。辦展的決心不容改變,會展對城市的發展助推作用不可小覷。社會需要重新建立產業信心,讓會展與旅游業一同助力上海直面挑戰,繼續努力建設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一 會展與城市的關系:從城市到會展
(一)城市提供會展所需的社會條件
“聚落”是城市的雛形,隨著聚落的形成,社會出現了農業、手工業、制陶業、冶銅業等社會獨立生產部門與產品交換行為。而在固定時間地點發生多對多的產品交換行為就是會展的雛形[1]。在鄭州地區城市起源的研究中,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遺址內的大型排房建筑、城墻、廣場是承載聚落生活和祭祀的場所,證明了城市的經濟、文化交流功能,并創造了展會和祭祀等活動的社會條件[2]。
城市是發展會展的前提,但城市發展會展還需要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文化環境、便于展品運輸和客運的地理條件、完整可支撐展會活動的產業鏈的市場條件[3]。歐洲部分地區自然條件優渥、文化深厚、交通便捷、產業鏈完整、市場分工明確孕育出了一大批會展產業堅實的老牌會展城市,是中國發展值得參考的案例。
(二)城市發展造就會展業
城市在發展和壯大的探索過程中創造了會展。國共對峙時期,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目的是改善民生和戰時糧食供給、檢閱生產力、教育群眾發展產業同時擴大對邊區的影響力。這是為了社會進步和城市發展而組織策劃的大型活動,強化了民眾對延安的認同感、建立了積極的延安城市形象、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建設工作,并反映了地區政策變化與社會轉型[4]。
二 會展與城市的關系:從會展到城市
大型會展活動的營銷可增強城市對資本等發展要素粘性[5],使資本和產品從流動空間向場所空間進行轉變, 并對城市的物理空間、經濟、社會與政治等關系進行重塑,所以會展對城市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一)會展反映城市發展水平
在中國會展產業的發展史中,抗戰時期解放區展會的展品相對低端,以肥皂、牙刷、粉筆等為主;但新中國成立后,展品向中高端轉變,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升級。在展覽場所方面,建國前中國共產黨的展會僅使用簡陋的窯洞,而1954年為迎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的來華展示,國家先后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建造了四座展館,見證了中蘇友誼與國家經濟文化的成長,并肯定了四個城市的戰略地位。同時,展會的規模、受眾的范圍、資本的流動等方面都可展現城市發展水平。
(二)會展帶動城市經濟
在杭州的案例研究中,學者通過定量統計分析得出“會展對杭州的經濟發展有很強的促進作用[6]。”同樣,2010年世博會也為上海帶來了的巨大經濟效益,全市固定資產提升了10.68個百分點、勞動力投入年均增漲了5.14個百分點、產出指標年均增長3,68個百分點[7]。會展同樣有益于三線城市發展。研究發現,近年來鎮江積極舉辦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農產品博覽會、水產品博覽會等一系列展會,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投資合作,帶動了關聯產業,尤其對旅游業與房地產業作用明顯[8]。
(三)會展帶動城市建設
會展活動對場地的需求可直接優化城市硬件。1929年西班牙世博會并沒有幫助巴塞羅那和塞維利亞這兩個舉辦城市獲得直接的經濟盈利,但他們都在城市規劃與設施建設方面得到發展,并直接提高了國際知名度。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的承辦,幫助城市管理部門完成了計劃了數十年的基礎設施升級,加速了蒙特利爾新區的城市化,成為了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9]。
(四)會展塑造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城市給予人們的整體文化感受,包括歷史文化、現存物質與現代文明等,是文化資源或文化符號[10]。從傳播學認為“城市形象”可作為會展傳播的信息內容之一,在空間中發布和傳遞。會展是一個窗口,可面向世界展現國家或地區的科技水平、經濟實力和文化魅力[11],從而優化政府形象、激活產業活力、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城市服務能力、提升市民生活品味、增強城市凝聚力等[12]。通過以上幾個方面,最終強化城市的正面形象、淡化負面形象或塑造嶄新的城市形象。正如陳藝勻所說,“國際會展是最大、最有意義、最有特色的城市廣告”。
(五)會展提高城市競爭力
城市競爭力是城市的綜合指標,包含影響力、知名度、經濟實力、歷史文化、科技水平、設施建設等。會展產業是“火車頭型”服務業,具有高成長潛力、高附加值和高創新效益的特點,享有“城市面包”的美譽。會展還具有“文化熔爐”的作用,可傳播新技術、知識、觀念的傳播,可生產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效益[13]。研究發現,西安通過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展覽、體育賽事及文化活動”,帶動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優化。從而加速其與國際接軌,提高了城市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14]。
三 上海與會展產業的適配關系
城市會展業的生成、發展要與城市功能的“能性”“能級”“能位”相適配[15]。會展業的產生需要城市擁有一定素質的“三能”作為基礎,而城市的“三能”對城市會展的發展又具有約束作用,這將為上海適宜發展會展業提供依據。
(一)能性分析
“能性”包括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的總體功能,一般要求城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具有“工業生產中心、商品流通中心、交通運輸中心、金融中心、科學技術中心等。”而上海就具有十分堅實的“能性”基礎。工業方面,早在2010 年上海工業總產值超過3萬億元,2019年達35487.05億元[16]。交通運輸方面,統計結果顯示2019年上海穩居世界第三,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0年世界第一[17]。在金融方面,2019年上海市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1933萬億元[18]。在科技方面,至2018年有效期內的高企數量達到9250家,并且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微納電子、量子信息、腦科學與類腦、海洋、藥物等優勢領域開展布局”;同時擁有一大批高端創新人才和團隊,全年上海科學家在《科學》《自然》《細胞》期刊發表原創性文章共計85篇,全市有47項牽頭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獎[19]。上海的城市“能性”之強是國際化大都市的素質體現,具備發展會展業的堅實基礎。
(二)能級分析
“能級”表示城市的影響力,能級越大則城市影響力越大。依據能級我們可以將城市分為“國際性城市、全國性城市和地方區域性城市“三個種類。在科爾尼公司于發布的《2020年全球城市指數》中,上海綜合排名位居世界第12位,領先于舊金山、維也納、阿姆斯特丹等國際城市[20]。強大的國際影響力使上海備受全球最優秀企業和人才青睞,利于吸引投資,可為展會提供良好的市場基礎。
(三)能位分析
“能位”表示在地區中具有不同功能和規模的城市的地理位置關系。有利于研究會展業的形成與發展趨勢,同時合理化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分工合作。而目前,我們依據能為的概念發展形成了五大會展經濟帶,包括“長三角會展經濟帶,珠三角會展經濟帶,環渤海會展經濟帶,東部會展經濟帶,中西部會展經濟帶”。
上海是長三角經濟帶的龍頭,也是一帶一路的示范者。《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水平研究報告 (2017)》 構建了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并建議進一步明確長三角經濟帶的市場分工,以避免地區之間的產業趨同,從而更好地發揮經濟帶功能[21]。長三角一體化將有效地為上海提供全方位的優勢發展環境,有助于會展產業的更高更快發展。
四 結語
可見,會展對于城市發展至關重要,同時具有驅動旅游業的功能。而上海的優越條件是會展業的沃土,并將受益于“城市面包”的推動作用。堅持發展會展業是堅定疫后經濟信心,助力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性舉措。但健康是最根本的發展資料,法制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上海還要抓緊嚴防嚴控的治理措施并堅持完善會展法制,才能更為堅實的推進城市會展業工作,建設成為全球卓越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