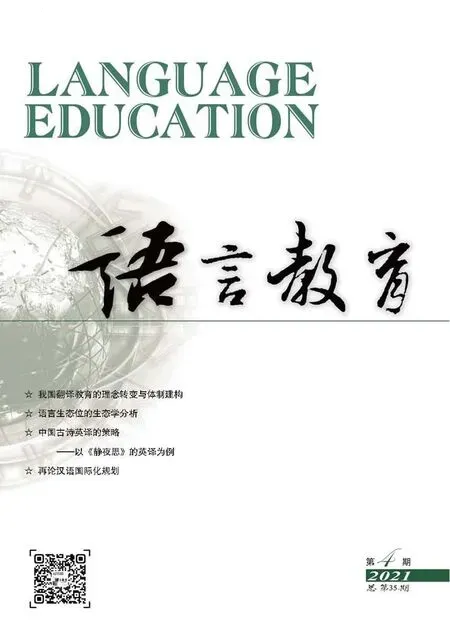語言生態位的生態學分析
李文蓓 黃國文
(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
1. 引言
自黨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總布局以來,國家把生態建設和發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生態移民”是實現脫貧和人民奔小康的重要政策之一。生態移民,是指為改善惡化生態環境而進行的人口遷移行為。它的最終目標是造福貧困地區人民,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同時對該地區進行生態改造,在修復環境的過程中實現國家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者王如松和歐陽志云(2007: 227)指出,生態退化地區都具有共同的特征:“環境污染與經濟貧困交織,資源枯竭與發展滯后共軛,生態脆弱與素質低下孿生”。由此可見,貧困與環境是相互影響的,生態環境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態移民是國家鄉村振興政策的關鍵。在實行生態移民的過程里,移民的身份重構是適應新社區環境的重點,也是構建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語言是人類獨有的技能,是重要的溝通工具,因此語言生態的和諧是構建社會至關重要的因素。生態語言學通過研究語言和生態的關系,以反映語言與自然的相互影響(黃國文,2016a)。生態語言學發展至今已涌現各類具有自身研究特色的研究模式,如豪根模式、韓禮德模式、生物語言模式、斯特芬森模式(周文娟,2018)等等,全球各地先后建立了多個與生態語言學相關的學會與網站,在全球化趨勢下繼續深入對語言與生態相互作用的研究并作出具有重要學科意義的貢獻。基于我國儒家與道家傳統,黃國文提出“一個假定(以人為本)和三條原則(良知原則、親近原則、制約原則)”作為在中國語境下和諧話語分析的核心要素(黃國文,2017)。在探索中國語言生態的研究道路上,中國生態語言學者都十分重視在中國語境下的和諧話語構建,強調對于任何語言的研究都必須立足于本土。中國本土研究應結合傳統儒學生態哲學觀,尋找符合中國語言生態國情的生態語言學發展道路。和諧話語是以中國國情為基礎,符合中國語言發展特色的話語。著名語言學家Halliday指出“語言主動構建現實”(Halliday,1990:11),這就是說,社會現實是語言構建出來的,人民要安居樂業,首先是語言生態要和諧,這樣才有營造和諧社會可言。生態語言學者Stibbe(2015)從生態語言學視角歸類了三種話語屬性,它們分別是破壞性話語(destructive discourse)、中性話語(ambivalent discourse)和有益性話語(beneficial discourse)。對于這三種話語的歸類,其主要衡量標準是判斷者的生態哲學觀(ecosophy)。本文從生態學的視角,在中國移民群體特有的語境下,分析構成中國生態移民和諧話語生態位的語言環境因子,從物種群落關系角度探討存在于移民群體中的破壞性話語、中性話語和有益性話語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發展路徑,并探討在和諧話語生態位中語言環境因子對和諧話語本體之間的雙向耦合作用。
2. 生態移民語言生態位
自人類社會進入后工業時期以來,為滿足快速增長的物質欲望與生產需求,人類無休止地向自然界索取資源并且投放過量廢物,對生物圈造成巨大的破壞,導致生態問題加劇。美國著名學者B·沃德和R·杜博斯指出:人類生活的兩個世界——他所繼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創造的技術圈已失去平衡,正處于潛在的深刻矛盾中(余謀昌,1982a)。在語言生態中同樣存在“語言廢物”,一旦廢物過量即會導致語言生態被破壞。在生態學中, 美國學者R. H. Johnson把生態位定義為環境對生物主體的支撐服務能力和生物主體對環境的影響和作用;用來表示生態系統中每種生物生存所必需的生存最小閾值,其內容包含區域范圍和生物本身在生態系統中的功能與作用 (趙豆,2018)。生態位具有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它是滿足生物生存所必需的環境因子的集合,即物理棲境(棲息地、水、環境、氣候)、代謝環境(食物和能量)和生物環境(物種與天敵和盟友的存在狀態);另外一方面是生物對周邊環境的潛藏影響和功能作用。生態位是動態的,因外部環境的改變和內部生長力的興衰而變動。生態位內部各種因子的變化,包括它們與生物之間雙向耦合產生的影響與作用時刻關聯著生態位的狀態;而在外部,生物之間在共存的情況下,因在相同環境中對食物或能量會產生競爭,強弱狀態的更替伴隨的是各自生態位的興衰變動,這就是生態位的動態性 (李文蓓,2018)。
在語言生態中,語言生態位的構成同樣需要滿足語言生態位的雙重性,即語言環境因子集合和語言本體。我們基于語言生態學對語言生態位做了傳統語言生態位和韓禮德模式(Halliday,1990)語言生態位的研究(李文蓓,2018)。兩種語言生態位在各自語言環境因子集合的成分上各有側重,本文將以韓禮德模式語言生態位對中國語境的語言環境因子展開探討。生態語言學的韓禮德模式是非隱喻的,它強調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突出語言為現實構建者(constructors)的角色。在韓禮德模式語言生態位中,語言環境因子包括自然環境和人群環境兩大因子,其中人群環境因子由社會環境因子和文化環境因子構成。
2.1 自然環境因子:自然環境的變遷
生態移民是環境移民概念之下的內涵之一。環境移民是指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和人居環境受到突發或漸進式的不利影響而產生的各種人口遷移行為(鄭艷,2013),它涵蓋了氣候移民和生態移民。生態移民則是以保護生態為首要,提高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價值為中心的人口遷移行為。中國實行生態移民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貧困地區的生態退化,貧瘠的自然資源未能支持地區的發展;貧困地區的生態退化并非短時間造成的,地區居民因缺乏環境再造的生態意識,在局部地區過度開采自然資源后,居民選擇另辟資源相對富裕的地區再進行生產活動,而對造成環境破壞的區域卻未能及時補救再造。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需要相應的足夠長的時間,而人類的生產活動對生態的影響卻遠超過其他的自然因子。因為人類的社會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如放火燒山、開墾耕地、砍伐樹木等,都會直接影響生物群落演替(succession)。因此,通過遷移貧困地區人民到新居住地這個重要方式,可以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質量,同時實現生態保護和環境修復。對語言發展而言,人群的遷徙意味著語言的遷移,實施生態移民改變的不只是移民居住的自然環境,還有語言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更是養育了一方講當地語言的人。生物文化倫理(biocultural ethics)學者Rozzi提到“生境與習性、生態系統與文化之間的整體性融合,包含了物理的、生物的、符號的實體”。①Ricardo, R. 2018. Biocultural ethics: Recovering the vital links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their habits, and habitats. 朱丹瓊譯.生物文化倫理:恢復由此可得,自然環境作為人群起居生活、生產作業的依靠,是語言詞匯、表達、語音形成和積累的基石。周國炎、朱德康(2016)在少數民族移民的語言調查中按移民不同的安置點歸納了三種類型,遷入地與原居地生態類同型、遷入地生態類城鎮化型和遷入地生態城鎮化型。其中,遷入地生態類城鎮化型是三種類型中最典型和最普遍的類型,即移民從山區遷移至以漢族為主并且靠近城鎮的安置點,移民的新家在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環境上都與原聚居地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而他們對新的自然環境的適應必然首先直接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生態移民下形成的自然環境變遷,必然改變了語言的原生自然環境,人群來到新的聚居地,語言同樣面對新生自然環境。因此,在語言生態位中,生態移民的語言自然環境因子因人群遷移而發生變化。
2.2 社會環境因子
移民在遷移到新聚居地的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是社會的適應性和社會的融合,而語言就是社會適應性和社會融合的一個關鍵。一個和諧社會的建立,依靠的是和諧語言所建構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語言和社會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語言和社會各自為變體,但二者通過接觸、影響和制約再共同產生變化,這種發展規律與生態學中的協同進化相符。新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環境的改變,必然首先反映在語言的使用上。移民來到新的環境,首要面對的是語言交際問題。因為語言的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移民之間因語言接觸造成的交際困難相應出現。新移民背井離鄉來到新家園,除了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居住環境和發展前景,更希望可以被新社群接納和融入新社群,因此語言認同感是拉近移民之間距離的重要社會因子。語言認同感可以加快移民之間、與當地居民之間社會生活上的精神融合,雖然各自的方言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別,但是語言認同感在某種意義上講便是一種身份認同感,方言之間的差別就可以在和諧融合的過程中被接受,隨著時間推移漸漸縮小最終消解。因此,語言認同感是和諧話語生態位發展的最關鍵社會環境因子之一。再者,在移民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教育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社會因子,它既積極解決移民之間的語言交際困難,加強溝通交流,但又同時影響移民的語言代際傳承。教育是影響語言和文化傳承的主要的卻又是間接的驅動因素,是生物文化均質化(bicultural homogenization)過程中語言均質化的影響因子。新移民來自不同的地區,為了交流,移民相互之間必然以普通話為日常交際語言,年輕移民走進學校基本以普通話為主,他們接觸最多的除了普通話就是當地方言。根據汪磊(2010)的調查研究,廣東省生態移民的語言使用情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以移民母語與新居住地方言差異小為背景,在這種情況下移民的母語方言被保持得很好,在新安置地生活六七年后,年輕移民依舊以母方言為主要日常交際語言。第二類以移民母語與新居住地方言差異大為背景,移民的母語方言出現了年齡分層和分化現象,7至20歲的年輕移民在求學過程中除了掌握普通話,基本都能聽懂新方言,超過半數能流利使用新方言。但是,在21至50歲中青年移民人群中,超過大半數不懂新方言。綜上所述,語言接觸、語言交際、語言認同感、教育與語言傳承都是移民適應社會和融入社會造就和諧話語生態位的關鍵社會環境因子。
2.3 文化環境因子
一種語言就是一種文化,是話語者對家鄉的情懷。土地在移民的心中就是文化的基石,移民對土地的情感是首要文化環境因子,這體現出居住者與他們所棲息環境的緊密關系。作為依靠家鄉土地生存、生活和發展的移民,土地對于他們的意義猶如生養他們的母親。土地給予了他們生活的資源,伴隨了他們幾代人的成長,孕育了屬于他們自己的人文素養。馬瑛等(2018)針對生態移民和生物多樣性的相互關系做了分析,指出移民的生活、生產方式與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風俗緊密相連,這種聯系是移民在棲居地千百年定居形成的傳統,移民的遷徙將面臨這些傳統的失傳甚至消失。以客家山歌為例,其隱藏的“山
居住者及生活習性與生境之間的關鍵聯系[J].國際社會學雜志(中文版),(4):7,11-12,42-61.性”便是在特有的地理環境下形成,客家村民隔山居住,村民以對山吆喝的方式來傳達情感,因此客家山歌的聲韻分外高昂嘹亮(汪國勝 徐采霞,2014)。離開家鄉遷移別處,對于移民來說就是切斷了他們與土地之間的根脈聯絡,改變他們長久的生活習慣與交際文化。移民對環境的歸屬感等同于他們對環境的安全感。只有當移民認為自己融入了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才能實現真正的“安居”,從而促進環境的和諧。第二,移民安置點的多元文化背景是他們適應環境的另一挑戰。多元文化背景意旨多種不同的文化共存,移民群體從原來單一文化的生活環境移居到多元文化的生活環境,多元文化和諧共存是移民群體融洽共生的重要積極影響因子。文化是一種群體性的思想、行為的共識與習慣。多元文化共存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接觸,在日常交際上是不同群體在生活習慣、風俗人情上的磨合,是不同群體價值觀和認識觀的碰撞。和諧話語生態位構成的重要環節之一就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下尋找語言認同感。語言認同感不只是語言的尊重,更是文化的尊重。任何的和諧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得到尊重是身份地位的認同,即存在的認同。
2.4 生態移民和諧話語的構成
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其整體性從空間結構角度來看是完整的系統,從時間發展角度來看是歷史發展的系統(余謀昌,1982b)。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呈現“線性動態”特征;東方傳統思想孕育下的中國生態價值觀視天人為一體,強調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的緊密聯系,追求天地人整體的和諧(余謀昌, 1994)。中國生態語言學儒家范式所闡述的儒學意義,包含了“線性動態”意義和“循環動態”意義。美國生態學家林德曼(R. L. Lindeman)在1942年發表關于食物鏈和金字塔營養基的研究報告,揭示了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物質運動規律(余謀昌,1982b)。余謀昌指出生態倫理學主張改變兩個決定性概念和規范: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的概念須擴大到對大自然的關心,對生命和自然的尊重;第二,道德權力概念應擴大到自然界的生命和生態系統。確認、確保它們在自然界中持續存在的權利(余謀昌,1994)。他提出了“仿圈學”概念,這個概念既順應了生態系統能量輸入與輸出運轉的循環規律,又折射出“生生之謂易”“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傳統易學和道家智慧——循環。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代表的科學、哲學忽略了人類以外事物的價值,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指導原則(余謀昌,1994)。西方經典生態語言學因受傳統牛頓—笛卡爾式二元論世界觀的影響,在概念、方法和哲學方面呈現價值中立、倫理弱化、道德弱化和缺乏美學等特征。中國語境下的語言生態研究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價值和生態倫理作為切入點,集“生態文明”“和諧社會”和“和諧話語”于一體(黃國文,2016b;周文娟,2017),結合傳統儒家智慧之“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陰陽和諧之美”,使中國語言生態研究具有了基礎理論意義、自然生態意義、社會形態意義、哲學意義和現實意義。中國生態語言學儒學范式的和諧包括四個方面的內涵: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心智和諧以及自我與他者和諧。每一方面和諧的具體內涵都有獨特的生態價值(周文娟,2018)。 儒學范式包括四大意義:“道法自然”“和而不同”“盡善盡美”和“知行合一”,即尊重與順應自然規律,以人為本構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結合音韻與心智之美學,樹“生態良知觀”立“生態人”。
黃國文和趙蕊華(2017)強調,語言的探索和研究需要回歸本土。在中國語境下,基于我國儒家與道家傳統,黃國文提出了判斷和諧話語的標準,“一個假定(以人為本)和三條原則(良知原則、親近原則、制約原則)”作為在中國語境下和諧話語分析的核心要素(黃國文,2017),并以此來指導和諧話語分析。話語的屬性,積極性(有益性)、消極性(破壞性)或中性的屬性是由分析者的生態觀,即生態哲學觀決定。生態哲學觀(ecosophy; ecological philosophy)是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不斷進化的意識形態。中國生態語言學以傳統思想智慧為生態哲學觀理論基礎,在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完成生態語言學的道德和倫理使命,摒棄西方二元論影響,樹立“知行效合一”的和諧發展觀。生態平衡的破壞、氣候變暖、環境污染等生態問題已成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一個語言環境整體里面,人群的生態觀不盡相同。生態觀的形成與文化、教育、經歷等因素息息相關,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成長經歷都會影響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是動態的,隨人的年齡增長、人生歷練而改變。因此,在語言環境整體中,必然存在持有不同生態觀的人群,在不同層次的生態觀指導下,不同的人群產生不同的話語或行為。積極向上的人群講述健康的、善良的、有益于關系發展的話語;消極抱怨的人群講述消極的、暴力的、不利于關系發展的話語;中性話語則是游離狀態的,其性質跟隨人群思維轉變而改變屬性的話語。因此,積極話語、消極話語和中性話語在一個語言環境整體中是共時存在的因子。中國當下所提倡的生態文明是尊崇儒家傳統之“以人為本”的理念,借鑒國外學者的成果和觀點,結合中國國情與本土文化,在面對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雙重挑戰中,構建“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知行效合一”的有中國特色的生態語言學范式。
3. 討論
3.1 物種群落關系角度下生態移民和諧話語因子相互作用路徑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對物質和精神的需求持續擴大,工業生產不斷創新高,但在其生產過程中,人類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廢棄物,給生物圈造成極大的壓力,生產過程所引起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已經形成全球化規模的地質營力,并且超過了自然界的某種地質營力。自然生態系統的特點是其功能和結構具有自動調節和自動控制的能力,使輸入輸出的能量保持動態平衡;自然生態系統在運轉中循環轉化輸入的物質,呈現逐等級轉變,生成可被下一等級利用的有機體,循環利用。對比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循環,人類的工業物質生產則是線性的非循環過程,其特征為大量排放無法被轉化為下一級利用的廢物(余謀昌 胡穎峰,2018)。
根據黃國文(2017)“一個假定、三個原則”之下的和諧話語的含義,從生態位的視角下,我們認為移民和諧話語是一個包含著積極話語、消極話語和中性話語因子的范疇,并且通過積極話語因子、消極話語因子和中性話語因子的相互較量,形成以積極話語因子為主、中性話語因子為輔、消極話語因子為少的本體。積極話語因子、消極話語因子和中性話語因子在和諧話語本體中的共存遵循群落物種關系(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的原則。
物種關系是指不同種群之間的相互作用,種群之間的關系可以是相互影響的,也可以是互不干擾的。如果彼此之間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種間關系類型一共有七種,它們分別是中性(neutralism)、競爭(competition)、偏害(amensalism)、捕食(predation)、寄生(parasitism)、偏利(commensalism)和互利(mutualism)(駱世明 ,2011)。在語言環境整體中,積極話語因子和消極話語因子兩者之間屬于競爭關系。積極話語與消極話語相互抑制,任何一方的存在都會給對方造成損害,削弱自身的發展。對于中性話語因子,它和積極話語因子或消極話語因子則屬于偏利關系,即中性話語的存在對于積極話語或消極話語而言都是有利的,因為中性話語是動態的、可改變性質的,因此它可發展成為積極話語或消極話語;在偏利關系中,中性話語在和積極話語或消極話語共存的情況下,自己本身的發展是不受影響的,即對中性話語本身既不有利也不有害。在和諧話語本體中,中性話語因子與積極話語因子、消極話語因子的偏利關系不發生變化,但是,積極話語因子和消極話語因子的關系則從競爭關系轉變為捕食關系。在生態學中,捕食關系是指某種生物消耗另一種其他生物活體的全部或部分身體,直接獲得營養(駱世明 ,2011:81)。捕食作用對調節種群數量有重要的生態意義,捕食者的數量直接影響獵物種群的數量,若缺乏捕食者,獵物數量可能猛增而導致環境資源的失衡。在一個穩定的生態系統中,捕食者擔負著調節各種群數量以保持環境相對穩定的動態平衡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和諧話語本體中,積極話語就是捕食者(predator),消極話語就是獵物(prey),積極話語的存在和發展是積極、有效地控制消極話語的發展,從而推動和諧話題本體的健康成長。
3.2 中國生態移民話語生態位發展的思考
中國生態移民政策的開展,一方面是通過移民的手段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使他們脫離貧困環境,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切實保護生態環境,做好生態修復,提高生態服務能力。中國生態移民語境下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發展對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和積極的作用。當一種語言能夠很好地反映社會變化,滿足社會發展需求,這種語言和社會的關系便是和諧健康的關系(張梅,2011)。在生態移民的語境下,和諧話語本體中的積極話語因子、中性話語因子和消極話語因子的各自發展和態勢的改變通過與語言環境因子中的自然環境因子、社會環境因子和文化環境因子的雙向耦合作用實現。如上文所述,在和諧話語本體中,積極話語因子和消極話語因子兩者之間是捕食關系,中性話語因子與積極話語因子或消極話語因子是偏利關系。因此,在捕食關系中,作為捕食者的積極話語保持良好健康的發展態勢是維持和諧話語本體發展的關鍵,只有和諧話語本體健康發展才可以保證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穩定。積極話語因子和消極話語因子的態勢變化與語言環境因子相互作用。生態移民語境下,自然環境的變遷、社會環境的更換、文化環境的改變對移民群體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作用于積極話語、消極話語和中性話語。自然環境的變遷是無法回避的,移民群體離開相守多年的土地,遷徙別處,這同時代表著他們的歸屬感和安全感的遷移;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他們需要面對新的交際場合、新的交際對象,在一個全新的社群平臺尋找身份的認同;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環境中,他們需要面對不同的習俗和民約,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適應多元文化接觸下的相互磨合。社會和諧是語言和諧的前提,沒有社會的和諧就不會有語言的和諧,社會和語言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為前提(張梅,2011)。若移民群體一直生活在貧困中,承受生存的壓力,或者在新遷移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中無法適應,困難重重,這種情況下的語言生態必然是消極的、抱怨的,對任何事物都是抵制的態度,此時社會矛盾必然會被激化,消極話語因此迅速強勢膨脹,與積極話語因子的關系為獵物與捕食者,吞噬積極話語因子,同時影響中性話語因子使其變為消極話語因子,在這種情況下,和諧話語本體將被消極話語因子占據而變為消極話語本體;消極話語本體反作用于自然、社會和文化環境,移民群體矛盾突出,形成消極話語生態位,消極話語生態位的出現無疑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反之,當移民群體可以適應自然、社會、文化環境,自然、社會和文化環境因子就能發揮積極作用,移民群體脫離原居住地貧困的狀態,居住環境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得到的提高,工作穩定,收入增加,子女教育有保障。在“安居樂業”的背景下,移民群體的語言生態必然是以積極的、向上的、健康的狀態為主,因此積極話語因子保持強勢,不斷吃掉消極話語,使消極話語因子呈弱勢,同時,積極話語因子會影響中性話語因子的態勢,使越來越多的中性話語變為積極話語,鞏固和諧話語本體。和諧話語本體的健康發展,又會造福移民群體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使移民熱愛自己的新家園,融入新社群,找到歸屬感和安全感,共同構建新的文化整體。
4. 結語
中國生態移民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是改善貧困民眾生活、幫助貧困民眾走出貧窮,實現保護環境、修復生態環境的有效手段。語言的和諧需要通過語言與自然、社會、文化和人群的積極相互作用和影響來實現。和諧話語生態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移民語境下,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發展影響著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度和社會融合度。本文從生態位的視角對生態移民語境下的和諧話語生態位做了解構分析,從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環境因子集合和和諧話語本體進行分析;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因子在生態移民背景下存在環境的變遷、語言接觸和文化碰撞等各種影響因子,和諧話語本體由積極話語因子為主、中性話語因子為輔、消極話語因子為少的態勢構成,在種群關系的基礎上探討積極話語、消極話語和中性話語之間的共存關系,以及環境因子和和諧話語因子的雙向耦合作用關系。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發展變化與移民群體的體量、位置、時間有關,具體的量化值還有待更多的實證研究探討。移民和諧話語生態位的穩定對語言和諧、社會和諧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