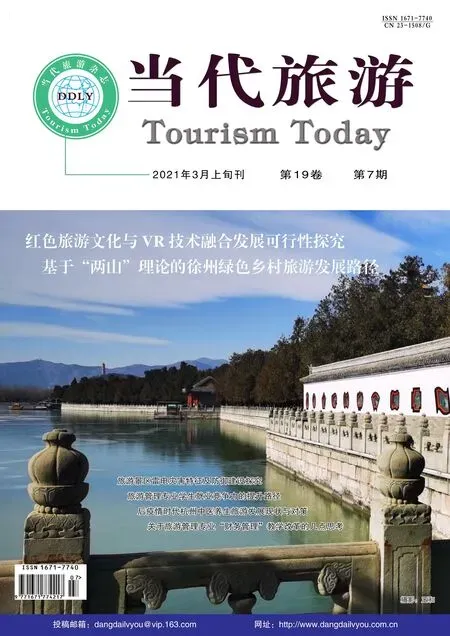揚州“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更名為“運河灣生態文化公園”的可行性探析
顧棟梁 徐曉梅
1.江蘇旅游職業學院國際商務學院,江蘇揚州 225000;2.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揚州 225000
引言
2020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考察揚州“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了解大運河沿線環境整治和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情況,與市民群眾“面對面”親切互動交流,盛贊“揚州是個好地方,特別是文明、文化、歷史古城,在全國都很有分量。”對此,我們跟著總書記的足跡領略古今交融的千年運河,堅持建設幸福河、致富河的美好愿景,千方百計地擦亮“中國運河第一城”這張國家名片,將“三灣公園”打造成“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核心展示園”乃至世界級著名景區。為了讓“好地方”有個“好名稱”,用“好地名”解讀“好地方”,必須進一步聚焦“三灣”,著力提振揚州文化自信,再塑高大上的旅游品牌,可將名稱頗有爭議的“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更名為“運河灣生態文化公園”。為此,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以期引起共鳴。
一 “三灣”更名“運河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運河與長江相匯而生揚州,歷史與文化相濟而衍古城”。揚州自古擁南北水路交通之要沖,號稱“水上都會”,千年大運河在這里向著浩渺的萬里長江奔騰而去,彎來折去,蔚為壯觀,形成了運河原點、運河與長江交匯點、運河與淮河連接點和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起點等沿運城市中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自然環境,這是古往今來揚州最大的“亮點”和最火的“賣點”。
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價值內涵是打造中華文化的顯著標志,成為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文旅體驗空間、凝聚中國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園、傳承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長廊。揚州要從“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戰略導向出發,以對歷史負責、對未來負責的科學態度,承載千年古河、歷史名城的復興希望,攜帶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做足“運河”這篇大文章,統籌整合優質資源,精心鍛造“國家標識”,努力建設歷史與現代、文化與生態、自然與景觀相得益彰的“好地方”,這是踐行“揚州作為”、推動大運河文化帶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展示“揚州實踐”、加快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創新發展的內在要求[1]。
知古方能見今,寬廣造就輝煌。鑒于2019年11月2日《江蘇省人民政府關于同意揚州瘦西湖旅游度假區改名為揚州大運河文化旅游度假區的批復》,同理,以“三灣”為中心進一步放大周邊地帶,延伸輻射古運河與揚子江交匯處以及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這方圓一大片區域,將“運河三灣”更名為“運河灣”,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既名正言順,又實至名歸;既有較強針對性,又有可操作性。其實,凝練提升只需刪繁就簡去除一個“三”字即可。雖一字之改,卻錦上添花,這樣內涵不同、外延不同、格局不同、品質不同,從而指向更明確、范圍更寬泛、底蘊更深厚、價值更非凡。
一是要以系統性思維面對百年之未有大變局,解放思想、開拓視野、破舊立新,展示時代站位,打造“揚州樣本”,將國家標識、地理特征、人文歷史等要素深度融合在一起,既留住“根”,又傳承“脈”,進一步認識“運河灣”視域下城市價值的回歸和提升。
二是要以運河為主基調、主色調、主標識,與時俱進、標新立異、挖掘內涵、畫龍點睛,著力提升揚州的“精氣神”,使物質文化得以保全,非物質文化得以活化,讓城市的門面和門戶更加耀眼,進一步體現社會心理、文化形態和地域認同的“運河性”。
三是要以“公園城市”建設為抓手,從“園林城市”邁向“公園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園,而是把城市建成大公園,彰顯“園在城中、城在園中、城園一體、水綠交融”的“新魚米之鄉”風貌,進一步渲染“最揚州”的新圖景。
四是要以文旅深度融合的“工筆畫”,續寫好“運河故事”,演繹新時代的傳奇,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格局,用”運河灣”新名稱來詮釋“揚州是個好地方”的深刻內涵,進一步打造具有中國特色、江蘇特質、揚州特點的“新地標”。
二 現名“三灣”的瑕疵
(一)俗稱與正名:“三灣”一說的不確定性
一部運河發展史,就是一部揚州發展史。全世界都知道揚州座這聞名遐邇的城市,那是從大運河開始的,而大運河又不能不提及最神奇的一段——“三灣”。千百年來這里是大運河揚州段的歷史斑斕處,蜿蜒回腸的河道猶如一條生態金項鏈鑲嵌在運河上,給人以忽遠忽近的視角空間和夾岸畫屏的美感享受,被譽為“千里運河最美的曲線”,成為閃爍在古城揚州的一顆璀璨明珠。自唐代后,鑒真大師東渡扶桑就是由此揚帆遠航的,大量的江南漕糧便在此集中運往北方。
然而,所謂揚州“三灣子”一說,僅是民間流行的約定俗成而已,史籍并未出現過“三灣子”之名,官方也未有此說法。查考明清等朝代歷史地圖,揚州古運河南端的三灣”,雖有其名,但無其實,沒有“三灣”,實有“兩灣”,即寶塔灣、新河灣。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98年《京杭運河志(蘇北段)》才明確記載:“文峰塔聳立于古運河南岸,揚州城西南角,俗稱僅僅20多年[2]。
穿越歷史。1582年(明萬歷十年)文峰塔建成后,“寶塔灣”之名約始于明末清初,俗稱就叫“三灣子”。由于揚州地勢北高南低,尤其城南古運河段地處下游,水勢變化莫測,迅疾洶涌直瀉長江,極易造成船只擱淺和傾覆。1597年(明萬歷二十五年)時任揚州知府郭光復,親率民工在城南因地制宜開挖一段“新河”,采用彎道技術,改直為曲、延長河道、降低坡度、滯緩流速、以利航行,左彎一下,右拐一下,使運河幾乎在這里劃了大半個圓弧,將100多米直道改為近1.8公里長彎道,解決了水運安全的一大難題,創造了中國水工史上的一個奇跡,流傳了“三灣抵一壩”的一段史話。“三灣”就像一把巨大滿弓將運河之水緊緊地收縛住,又如一個碩大問號留下了誰是主宰蒼茫大地“治水之神”的疑問[3]。
1928年 (民國十七年)《淮系年表·水道編》首次提及“三灣”:“運河南流,循城址,折而西,又折而南流,屈曲作三灣”。而以前多叫寶帶新河、寶塔灣、新河灣等,由此可見,“三灣”地名正式在官方書籍中出現尚不足百年時間。實際上,揚州市民口耳相傳的俗稱“三灣子”,就是指“寶塔灣”一帶的統稱。在空間形態上與今天“三灣公園”似乎南轅北撤,還相差近兩公里的一段距離,不完全是指同一個地點,“三灣子”與“三灣”也不完全是指同一個概念。此“三灣子”非彼“三灣”,不宜將似是而非的“俗稱”張冠李戴當成“正名”。在考證“三灣子”(“寶塔灣”)與“三灣”是否同一個地方時,不要忽略還有一個叫“新河灣”的地名。恰恰是始見于道光年間的“新河灣”,才是現在“三灣公園”所在地[4]。
(二)泛指與特指:“三灣”名稱的不嚴謹性
從空中俯瞰,揚州古運河南端水道形如“Ω”符號,并不像阿拉伯數字“3”,也不像英文字母“S”,卻狀似中國漢字“乙”字形,又猶如磅礴的大河奔流在黃河河套平原形成巨大的“幾”字灣,美輪美奐的運河流經這里并非嚴格意義上轉了“三道彎”,名曰“三灣”,名不符實,只有“寶塔灣”“新河灣”這“兩灣”。
“三”字在古代通常是個虛數或概數,泛指數量多。我國以數字排列稱謂地名者,確實不乏其例,但未必都科學。既然有“三灣”,那么就應該有“一灣”“二灣”或“四灣”“五灣”等類似排序的叫法。揚州歷史上一直有“古運河十三道灣”之說,“上揚州,攏灣頭”。“灣頭”古稱“揚子灣”,就是京杭大運河由北而南流經揚州古運河的第一道灣,遂有“頭灣”由來,日久以“灣頭”名稱。
古運河揚州老城區段從灣頭古鎮至瓜洲古鎮長達30多公里的運河河道,最為悠久、最具色彩、穿城而過、串珠成線、史跡密布、景觀眾多,曲折逶迤的彎道是歷代文人騷客、官人商賈進入繁華的揚州城主要水路。實際上這一段古運河可視作象征意義上的“揚州三灣”,即泛指古運河老城區段的“大三灣”(如灣頭茱萸灣、古邗溝遺址、康山大水灣、南門遺址碼頭等多個古運河著名彎道),并不僅限于特指古運河城南段的“小三灣”。
根據歷史場景轉換,有必要從內涵發掘和外延拓展上重新認識“三灣”、審視“三灣”、思考“三灣”和提升“三灣”。揚州“運河三灣”蘊含時空跨越、人文積淀、水工智慧和旅游價值,應該有狹義與廣義、歷史與現代之分,可以是一“點”一“段”,也可以是一“片”一“區”,甚至還可以是一“城”一“域”。可以這樣說,揚州老城區都環繞在兩岸翠柳的“運河灣”懷抱中,呈現出舟行碧波的綺麗畫卷,突顯出“綠楊城郭是揚州”的獨特魅力,直到如今整個揚州城還一直被千年運河之水源源不斷地滋養潤澤著,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運河城”[5]。
此外,從老祖宗是如何給經典景區“瘦西湖”取名的,可舉一反三,抑或大有裨益。1736年(乾隆元年)錢塘詩人汪沆慕名來到揚州飽覽美景后,揮毫留下“故應喚作瘦西湖”的千古名句。“揚州西湖”堪比漢朝美女趙飛燕,苗條婀娜、輕盈婉麗,而“杭州西湖”則可比唐代美女楊貴妃,豐腴嫵媚、華貴雍容。全國“西湖”大家庭成員有36個,唯有揚州為最“瘦”。一個“瘦”字十分確切、極富個性,活靈活現地勾勒出揚州清秀窈窕的畫風,既形象又生動。此后,“瘦西湖”便取代原名“保障湖”,成為揚州的“獨特印記”和“文化符號”。
(三)同名與歧義:“三灣”叫法的不規范性
熱搜“三灣”,首先躍入眼簾的便是“永新三灣”。江西省吉安市永新縣“三灣景區”是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家4A級旅游景區、國家森林公園。1927年9月28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永新三灣鄉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是“黨指揮槍”思想的發祥地,“支部建在連上”成為我軍政治工作的開端,在黨史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現存有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舊址、毛澤東舊居等紀念地并新建毛澤東銅像等。
由于“揚州三灣”是近幾年才建成開放的新景區,知名度還不高,成熟性也不夠,一時難以與著稱紅色經典的“永新三灣”相提并論。自從習近平總書記親臨“揚州三灣”視察后,“運河三灣”名聲鵲起、好評如潮,作為熱門主題和旅游目的地,爭相成為網紅打卡地。但在現實中,時遇困惑或尷尬,與國內不少同名“三灣”多歧義、易混淆。
例如:步入“不惑之年”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市,向海而興,青春大鵬,乘風破浪,加快建設“三灣”一區:深圳灣、大鵬灣、大亞灣;計劃單列市青島構筑海灣型城市新增長極,規劃擴容“三灣”三城:膠州灣、鰲山灣、靈山灣;江蘇省無錫市在新一輪城市發展戰略中整體構建“三灣”:運河灣、太湖灣、蠡湖灣;海南省三亞市建設一城“三灣”:大三亞灣、海棠灣、崖州灣,打造國際熱帶海濱風景旅游精品城市。此外,黃河“大河三灣”:一為乾坤灣,一為清水灣,此兩灣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乾坤灣鎮,另一灣老牛灣,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偏關縣;再有被“萬里黃河第一壩”三門峽水庫大壩攔腰阻截,在山西省運城市平陸縣黃河邊孕育出一片神秘水域——“三灣濕地”等。
時光流轉,物是人非。揚州“運河三灣”經歷了從“一汪死水”到“親水公園”的華麗轉身,歷史的“三灣”演化蛻變為現代的“運河灣”。解放后“三灣”片區地處城郊結合部和南部工業區,長期以來飽受詬病的是工廠多、煙塵大、污染重、環境差問題突出,散落著大量的工廠、倉庫、棚戶區及垃圾場、臭水塘、廢水溝等,成為典型的“城中村”和城市臟亂差的“洼地’。本世紀前10年,揚州拉開公園城市建設序幕。2014年啟動“三灣公園”建設,以迎接2018年9月在揚州舉辦的第十屆江蘇省園藝博覽會為目標,列入當年揚州30個重大城建項目之一,作為推進揚州公園體系“111”工程之一和揚州十大生態中心之一,征地拆遷、清理違建、搬移企業、疏浚水系、改造駁岸、修復濕地、開辟公園、綜合利用,持續推進生態環境整治,促進全面綠色發展轉型。
需要指出的是,“三灣公園”這樣一個重大文旅項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在名稱上似乎有“小家碧玉”的市井文化之感覺,缺少“大視野、大格局、大手筆”的氣勢。如果當初直接叫“新河灣公園”,一個“新”字直擊主題,頗具時代感,可能比現在牽強附會地叫“三灣公園”也許還要妥貼些。
再則,“運河三灣生態文化公園”不僅在“前綴”的“三灣”字號上存有疑義或異議,而且在“后綴”的功能定位上也較模糊或較游離,有多個版本、多個說法,如:“三灣公園”、“三灣濕地公園”、“三灣生態中心”、“三灣風景名勝區”、“三灣水利風景區”以及“三灣旅游度假區”和“三灣體育休閑區”等等,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群眾吐槽:“‘三灣公園’順勢出了名,儼然成了一個‘大雜燴’,什么‘牌子’都往那里掛,這對提升未來城市形象和品質并無益處”。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地名是社會變遷的“活化石”,而城市公園的命名,還涉及城市文旅品牌、城市生態環境、城市經濟發展、城市公共空間、城市社會安全、城市居民休閑等諸多問題。顯然,“運河灣”名稱比“三灣”名稱更加光艷奪目、驚駭世俗。千萬不要小看或輕看“運河灣”的作用和意義,關乎著擦亮“中國運河第一城”這張“國家名片”的大事。冠以“運河灣”這個金字招牌,既是新時代的命題,也是新格局的呼喚;既“叫好”,又“叫座”,讓名稱符合歷史、順應時代、昭示未來,有利于強化運河的高識別度和高認可度,有利于提升揚州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更好地突顯運河的文旅價值和揚州的歷史地位。
三 更名“運河灣”的好處
(一)稱謂“運河灣”更具霸氣
揚州因“州界多水,水揚波”而得名。在2500多年的興衰變遷中,與運河“同生共長、相依千年、感恩感念”。在新時代復興征程上再度“與運河同行、與運河共榮”。大運河是揚州的“根”,“運河灣”是古城的“魂”,無疑是一張最亮麗、最精彩、最形象的揚州名片。“水韻揚州”坐擁豐厚的歷史積淀和文旅資源,形成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和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無可撼動的。在城市定位和發展格局中,揚州是古運河原點城市,也是運河與長江交匯點城市,更是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融通點城市,還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點城市。“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公園”“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淮河生態經濟帶”“揚子江城市群”“南京都市圈”“寧鎮揚同城化”等眾多國家和省級重大戰略與重大工程在這里匯聚疊加,進一步成長為今天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關鍵節點城市。
(二)稱謂“運河灣”更是大氣
揚州是一座由歷史疊加起來的城市,歷史給予其豐厚的饋贈。生生不息的運河之水從古代流淌到現代,不僅沉淀了燦爛的文化遺產,也蘊藏了古城的未來密碼,更催生了人們的理念嬗變。登高望遠,源遠流長,把目光投向更長時間和更大空間,在揚州城市記憶里,時時處處都昭示著舒朗大氣、令人神往的“運河灣”主題:蜿蜒千里的水脈、綿延千秋的文脈、連亙千載的動脈、縱橫千年的人脈,具有博大精深的氣度和青春煥發的活力。可以說揚州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簡史,創造過興盛于西漢中葉、鼎盛于隋唐到趙宋、繁盛于明清至近代的三次輝煌時期,進一步見證了中華通史式的繁榮昌盛。
(三)稱謂“運河灣”更為神氣
揚州園林城市久負盛名,素有“園林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譽,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就是獨具一格的揚州古典園林風光。在老百姓中間流傳甚廣的一句話說得好:“沒逛過三灣公園,等于沒來過揚州。”如今古老厚重的“三灣”,脫胎換骨,生機勃勃,舊貌變新顏,高標準打造“新城市客廳”,活突突變成集中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個“窗口”。經國務院辦公廳批復定名的“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將于2021年7月1日在“三灣公園”開館。“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以及應“運”而生的“大運塔”平地拔起、雄姿巍然,將縱貫南北、穿越千年的歷史集于一體,進行全流域、全時段、全景觀、全方位的展示。作為時代經典杰作,具有標志性、辨識性、持續性,成為揚州文化底蘊、精神氣質和品格追求的一個縮影,推動大運河從“地理空間”轉向“旅游空間”,從“文化優勢”轉向“經濟優勢”,進一步以強烈時代感勾連歷史澤被當下啟迪未來。
(四)稱謂“運河灣”更接地氣
揚州在新時代面臨著嚴峻挑戰,沿運城市對于運河資源和品牌的爭奪日趨激烈。應該將運河作為揚州的“先手棋”,瞄準“運河灣”,主打“運河牌”,把風光無限的國家5A蜀岡——瘦西湖景區與風景誘人的國家4A“三灣”——寶塔灣、高旻寺景區,打造成為“雙子雙星”、南北呼應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經典景區,使瘦西湖水系與“三灣”水系無縫銜接。那句膾炙人口的揚州旅游形象廣告詞:“北有瘦西湖、南有古三灣”,也宜修改成為:北有“瘦西湖”、南有“運河灣”,這樣瑯瑯上口、更為貼切。2021年世界園藝博覽會(AIPH A2/B1認定)定于2021年4月8日至10月8日在中國揚州舉行,主題是“綠色城市、健康生活”,理念是“綠色引領城市、園藝升華生活”。揚州可借此造勢,創新文旅宣傳模式,向海內外廣為推介,進一步回答好“爭當表率、爭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時代答卷。
(五)稱謂“運河灣”更有底氣
揚州“運河灣”是“形象標識”,也是“文化瑰寶”。悠悠流淌的千年大運河成為一種生產方式,也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至今日,更成為一種“思維方式”。以“三灣”為代表的水工技藝是大運河的“活態遺產”,具有精湛的水工價值、豐厚的文化價值、重要的旅游價值和重大的民生價值,甚至可以與舉世聞名、無與爭鋒的四川都江堰相互媲美。因此,要跳出揚州來看揚州,放眼全國,面向世界,再創一句揚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全新旅游廣告詞:西有“都江堰”、東有“運河灣”。讓成就中國水工史上偉大創舉的“三灣”古今同輝、大有可為,使“運河灣”真正成為揚州的“代表符號”和“經典象征”。這樣名稱更正、名聲更好、名氣更大,叫得出、叫得順、叫得亮,唱響全國、走向世界,進一步高奏新時代“運河之歌”。
四 結語
綜上所述,在紀念中國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七周年的時候,新興的“三灣公園”進一步崛起成為古老運河的“活力核心”、江河交匯的“文旅中心”和現代揚州的“城市重心”[6]。勇于擔當、敢于亮劍,奮力扛起“讓古運河重生”的重大使命和特殊重任,將“運河三灣”更名為“運河灣”,揚州,你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