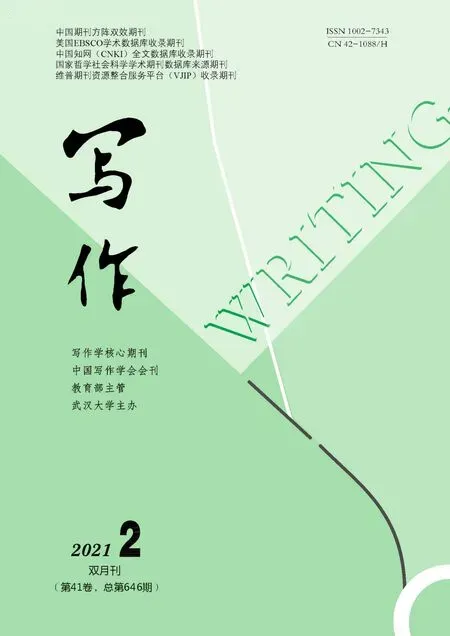作者是文學的故鄉:作者研究重構的問題與路徑
刁克利
一、問題的提出
每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都會給人帶來一陣熱議,但是有一個現象可能容易被忽略。諾貝爾和平獎也好,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也好,都是給某項具體的成就。也就是說,一位科學家可以因為他的發明創造,甚至可以獲得兩次諾貝爾獎。只有文學獎是獎給一位作家的,類似于終生成就獎,一生只能得一次。而這一次獲獎是以他的主要創作成就判定的,而不限于他的某一部具體作品。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獎給一個人和獎勵一部作品有什么不同?這其實是一個理論的問題。獎給一個人,肯定是考慮到作家整體的文學品質,整個的創作生涯,以及他對待文學的態度,他的作品質量。早些年也許是對某一部作品的肯定。而現在,由于作家寫作的便利,發表作品的數量的增多,就要考慮作家的整個創作生涯,創作的品質、內容、主題,以及他對藝術的貢獻等等。這是一個總體考量。
這個問題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我們的文學研究是對作者的研究,還是對作品的解讀。現在的文學研究大多是文本分析、作品解讀,缺乏作者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作者研究被淹沒在作品分析當中。那么,作者研究和作品研究等同嗎?作品分析和作者研究到底有沒有區別?是否應該有所區別?各自的任務是什么?
我們知道,文學課都是從作家講起的。那么作家的經歷是作為文學活動的開始,為了引起大家的興趣,還是希望從作家的興趣、經歷中找出作家創作的態度,他對文學的基本看法,他的思想和情感,找到了創作的底色和坐標呢?是為了講清這個作品的來源,而說明作者的角色和經歷呢?這顯然是對待作者研究的不同態度和評價。作者研究就是作家生平與經歷嗎?作者研究研究什么?作者研究如何展開?
無論在理論還是批評中,作者研究都處于困惑與困窘之境。離開了與作者的聯姻,文學研究與文學實踐漸行漸遠。文學研究既無力應對有關作者的理論挑戰,無法回答現實中的作者問題,也無助于文學創作的提升。有鑒于此,作者研究有待重構。重構之道在于:反思作者研究邊緣化的緣由,整理作者研究的理論資源,明確作者研究的問題與范疇,厘清作者研究的方向和原則。
二、作者之死與作者誤用
作者研究邊緣化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作者之死的影響。巴特以作者之死割斷作者與文本的聯系,提倡闡釋的自由與閱讀的開放,呼吁文本的多義性。對其提出的種種作者問題,一方面應該重新追溯作者的歷史,闡發作者的發生、發展和演變,重新建構作者與文本、與寫作、與讀者的新關系。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對作者與作品的關系理解并不只是作者之死與生,而在于人如何理解自己與自己所創造之物的關系。第二個原因是作者研究的誤用,混淆了作者和作品研究的界限。長期以來,把作者研究等同于作品研究,是普遍現象。作者研究和作品研究的區別是:作者研究是對人的研究,重點是對作者的研究。作品研究是對作品的研究,是文本分析。
作者研究是什么呢?作者研究是對為了寫作的、寫出了作品的、其作品產生了影響的作者的研究。它研究作者的生成、創作和影響。作者研究的對象是作為創作者與作為人的作者。作為現實中的作者,文本中的作者,作為文化符號的作者,作為歷史人物的作者,都屬于作者研究的范疇。我們要強調作者是創作的主體,強調他的獨立性,要研究的是創作過程當中的人,他如何創作出來作品。沒有作者的創作,作品無以產生。作者研究包括作品研究,其前提是這個作品能夠說明作者的生成、作者的形象確立和作者的影響。
作者研究的內容和資源有:文學理論中有關作者的論述,可以稱之為作者理論;作者傳記、作者訪談、作者文論中的文學思想;作者的創作、接受;現實中的作者問題。可以簡要的概括為三個方面:作者理論研究;作者專題研究;作者生態研究。作者理論研究是理論層面的作者研究;作者專題研究的范圍是作者創作與現實存在的實際問題;作者生態研究是一種理論建構與批評方法。
三、作者理論研究
作者理論研究是理論層面對作者的論述。作者理論研究的資源主要是文學理論中關于作者的論述。它可以是專門的論述,也可以是理論家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在20世紀之前,文學批評基本就是作者中心論,作者理論非常豐富。作者理論研究的資源首先是思想家的作者理論。這是經典的作者理論。經典理論家文獻中的詩人、藝術家、作家和本文的作者所指相同,意思一樣。統稱之為作者研究,只是為了使用術語的方便和統一。
比如柏拉圖在《伊安篇》中對詩人靈感的論述,對詩人是神的代言人的闡發,對詩人創作時迷狂狀態的解釋。再比如他在《理想國》中對詩人創作本質的論述,詩人是模仿者的斷言,以及詩人在理想國門外候審的位置界定。這些都是柏拉圖作者理論的重要內容。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也包含著豐富的作者理論,比如詩人是模仿者。賀拉斯在《詩藝》中專門論述詩人的修養,知識素材來源,與批評家的關系,詩人的作用,以及文學標準等,我們也可以從中總結提煉出他完整的作者理論。
這些理論家的著作中也都包含豐富的作者理論:錫德尼以及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叔本華、尼采、艾略特、弗洛伊德、榮格、薩特、波伏瓦等等。在他們的著作中,作者也被指稱為詩人、藝術家、作家,或者小說家、戲劇家等進行過專門論述。對其觀點的提煉、整理、論證和總結都是內容豐富的作者理論。這是理論家作者理論研究。實際上每一位理論家的作者理論都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話題,都值得單獨研究。
另一個思路是與作者相關的關鍵詞和術語的研究。比如靈感的來源、作用方式和演變過程。就像朗吉努斯寫作《論崇高》一樣,以“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偉大心靈的回聲”①[古希臘]朗吉努斯:《論崇高》,章安祺編:《謬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頁。立論,論述崇高與作者的品格、境界和追求的關系,論述作者崇高風格的概念、來源和習得要素,及其與時代的關系。還有與作者相關的天才說、神性說、游戲說等,每一種觀念都可以展開研究。還有通感、移情、白日夢、集體無意識、創傷等與文學創作有關的術語。每一個關鍵詞,每一種觀念都是一種研究思路。這些核心的術語和文學觀念都可以和作者研究結合起來。既可以作為作者理論研究,也可以結合具體作者研究,專門研究某一位作者某一部中的靈感、通感、崇高、移情、白日夢、創傷等的運用與體現。
第三種思路是文學理論流派中的作者研究。比如古典主義作者理論、浪漫主義作者理論、現實主義作者理論、象征主義作者理論、意識流作者理論、形式主義作者理論、女性作者理論、后現代作者理論、后殖民作者理論。研究其產生背景、總體特征、代表性觀點,也可以結合具體作者研究。不同的文學流派、創作群體,不同的文學理論作者都可以展開研究,都有其對作者的不同認識和理解,都有豐富的作者思想。
第四種思路是針對不同時間段的作者狀況進行研究。作者研究中,幾個重要時間段值得特別關注研究,比如上古時代的作者、古希臘時代的作者、中世紀的作者、文藝復興時期的作者、啟蒙時代的作者,工業革命時代的作者、讀圖時代的作者,電腦與網絡時代的作者,智能化時代的作者等。這幾個時段的作者各具鮮明的時代特征,對于考察作者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具有特殊意義。
還可以開展各種作者的形態研究。不同的寫作方式和作品發表方式會帶來不同的作者生態。在網絡時代、新媒體時代、短視頻時代、聽覺時代、智能語音錄入時代,書寫方式、發表方式、傳播方式、影響方式日新月異,作者出現了新的面貌。
專門研究作者的書寫方式與書寫工具的演變,也是一個重要話題。中國人過去用毛筆寫作。寫作前研磨鋪紙,甚至燃香。用鋼筆、圓珠筆寫作與毛筆寫作肯定不同。現在的電腦寫作,語言錄入,甚至視頻、音頻創作,都值得研究。刻印在甲骨、銅鼎和石碑上的寫作,與寫在宣紙、稿紙上,及錄入到可以無限存儲的數碼設備上,作者的感受不會一樣。寫作工具與作者的狀態、心境和寫作主題是否有關,大可以考證。這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現象研究,也都可以結合具體的作者進行個案分析。
以上種種,都是與作者相關的現象研究。還可以把作者研究和其他學科領域結合起來。借用各種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豐富作者研究的內容。比如作者與宗教、作者與倫理、作者與敘事、作者與地理、作者與生態等的關系。以作者與宗教的關系研究為例,可以進行有宗教情結的作者研究,作者的宗教思想的形成,宗教對作者的影響,作者的宗教思想在作品中的描寫和體現等。這些學科與作者的聯系都可以進行深入研究,進而構建作者倫理學、作者敘事學、作者生態學、作者地理學等。
作者理論的另一個別具特色的領域是作者文論。簡單地說,作者的文學理論稱之為作者文論。也可以說,作者文論即作者的文學思想的表達和闡發。很多著名的作者都有豐富的文學思想,有的獨立成篇,甚至有完整的著作,有的則散落在訪談、傳記,甚至隱藏在作品中,需要收集、挖掘、整理和闡發。一流的大作家、詩人,他都有自己對文學、對成為作者的看法和期待,知道自己做一個作者的使命,或者明確的作者角色,他通過寫作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他對寫作的認識等等。這是他寫作的基石。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和作者論代表了他的創作格調。所以,我們研究作者文論或者說作者的文學思想,應該和研究他的作品一樣。
作者文論是了解作者文學思想的第一手資料,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達。作者文論和作品可以結合起來研究,分析作者的寫作立場和角度、寫作的初衷和意義、敘述者與作者的關系等,進行作者文論與文學作品的互證研究及再評價。也可以重點研究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比如《荷馬史詩》中的游吟歌者,但丁《神曲》中的但丁,雪萊《西風頌》中的詩人,喬伊斯筆下的青年藝術家等。作者理論、作者文論、作品中的作者人物,和下面作者專題研究中的作者存在一道,構成完整的作者世界。
四、作者專題研究
作者專題研究針對具體作者現象及與作者息息相關的基本問題,與文學創作關系更密切,對推動文學創作與批評實踐有直接幫助,可以結合作者理論、具體作者研究與作品分析。
作者與語言的問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所以,語言是文學作者面對的首要問題。這里探討的作者與語言不是用語言學視角分析作品,而是作者對書寫語言的選擇,作者的語言水平和語言風格。在特定環境下,作者對語言的選擇就是一個大問題。比如但丁在拉丁語寫作時代選擇意大利語寫作《神曲》,喬叟選擇用倫敦方言創作詩歌,他們都做出了偉大的選擇。由于這種選擇,但丁為意大利語帶來了無上的榮光,喬叟則被稱為英國詩歌之父。民族作家選擇民族語言還是通用語言寫作,移民作家選擇母語寫作還是移居國官方語言寫作,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抉擇。作者與母語、作者與外來語,作者與第二語言寫作,當代中國作家受到的翻譯語言的影響,平時不用普通話的作家的漢語寫作,都值得結合具體作家進行專門研究。
作者與語言關系的第二個也是最普遍最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是作者的語言水準和風格形成。以莎士比亞為例,我們都知道他的語言別具魅力,他用過的詞匯有3萬4千多,新詞20,138個①張勇先:《英語發展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頁。。他賦予英語新的活力。他的語言深入到英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語言為什么獨具魅力呢?莎士比亞是個善于學習的人,他吸收了那個時代的語言精華。他是英語學得最好,用得最好的人。當時,英語的地位并不高。學術語言是拉丁語,宮廷用法語。英語更多是口語,作為書面語還不像現在這么成熟。但是,中世紀神學文本的莊重典雅,作為學術語言的拉丁語的嚴謹縝密,宮廷提倡的法語的優雅,市民階層的活潑的口語,中古英語的影響,倫敦方言的親近活潑,還有各種外來語的影響,都反映在他的戲劇中。
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家的語言環境同樣得天獨厚,他們的文言文根基扎實。文言文是書面語,特點是言簡意厚。他們還是大范圍使用白話文的第一代,推崇生動自然。有些作家留學海外,在西方的語言環境中受到熏染影響。正是對古今中外的語言有效地吸取,才會出現那個時代作家的語言特色。每位作家受到影響的國別、語言、文化背景有別,也是他們語言風格各有特色的原因之一。當代作家接受不同國家不同語種的水平不一、背景各異的翻譯語言的影響,這不能不影響他們的語言表達。從語言影響的角度考察當代作家與翻譯文學的關系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作者與傳統的問題。這就是作者與前輩、文學的傳承與作者的相互影響研究,寫作者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文學經典有長久的傳統。每一位后來的寫作者都要想如何面對已有的文學遺產,如何突破以往的寫作,如何在題材主題或寫作藝術上創新。T.S.艾略特的《個人才能與傳統》就是對作者與傳統關系的研究,是對作者個性如何融入文學傳統的闡發。“詩人必須獲得或者發展對于過去的意識,也必須在他的畢生的事業中繼續發展這個意識。”①[美]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卞之琳譯,朱立元、李鈞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頁。布魯姆把這個問題表述為“影響的焦慮”。這是作者與傳統關系研究的一個觀點。
作者與傳統的問題反映在同時代作者之間的關系中,就是作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研究,除了理論層面,也可以進行具體作者關系研究。一個作者從另一個作者的作品中在題材、細節上的借鑒和參照等等,就是兩個作者之間的研究,或者也可以是不同時代作者之間的影響和傳承。比如莎士比亞對馬洛題材的借鑒、創新與超越。比如馬洛的《帖木兒大帝》影響了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創作,而這些歷史劇似乎有反過來影響了馬洛《愛德華二世》的創作②[英]彼得·阿克洛伊德:《莎士比亞傳》,譚學嵐主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頁。。再比如莫泊桑與福樓拜的關系研究。還可以從作品的互文性入手研究作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現在的文學研究中對互文性的研究,都是研究作品的互文性。其實可以倒過來研究,從作者相互影響的角度,研究作品的互文性為什么發生,如何發生。這個角度才能真正對文學創作有幫助。作者的互文性也是作者與傳統的相互關聯。
作者與時代。作者的寫作必然反映時代特點,時代也影響作者寫作。作者的生成與寫作都離不開時代的環境。還是以莎士比亞為例。首先,莎士比亞的寫作成就是他個人才華的體現,也和那個時代有關。莎士比亞創作前期英國處于伊麗莎白一世當政時期,國家政局相對安定。英國對外殖民擴展效果初顯。中世紀神學的影響很深,封建秩序穩固,新興資產階級勢力上升,市民階層受到重視。所以,王權、神權、貴族勢力、世俗生活、殖民擴展等的影響都反映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各方面充滿了矛盾,又充滿了張力。這是一個人性張揚、提倡冒險、大膽探索的時代。所以,莎士比亞戲劇主題多樣,包容性強。女王對各種勢力和影響采取包容平衡的政策。這又是相對寬容、自由的時代。劇院普及,戲劇是主要娛樂形式。各階層能夠聚在一個劇場里,共同開懷大笑,或同情感懷,欣賞或戲謔。莎士比亞創作后期的詹姆斯一世時代也推崇戲劇。所以,莎士比亞的各種人物都個性張揚,充滿生命的意志力。
作者與市場。或稱之為市場中的作者現象研究,可以研究具體作者的市場行為,可以研究市場狀況對作者的普遍影響,可以專門研究作者的稿酬制度、作者版稅制度的演變也可以研究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作者版稅變化與其生存狀況與創作狀態如何等。
比如狄更斯與其所處的文學市場的關系很值得探討。當時,印刷術的改進,期刊報紙對小說的連載方式,書籍的普及易得,整個社會教育水平的提高,閱讀人群擴大,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學市場,影響了作家的創作方式和發表方式,還影響到作者的經濟收入和他與讀者的關系。可以說,文學市場的繁榮促成了狄更斯成為真正的職業作家。他成名之后的創作都是先預付稿費,這讓他既有條件進行創作,也限定了交稿日期,提高了他的寫作效率。發表后還有收益分成。發表方式則是先在期刊連載,再成書售賣,連載的過程也是觀察讀者反應的過程。狄更斯的創作是邊寫邊連載,有了構思和題目就在期刊上發表作品預告,寫出一兩章就開始連載,后面則是快到連載日期他才寫出來一章。很少整本寫完才連載,有時候是兩三本書同時開寫。這就是一個職業作家的寫作節奏和方式,這也影響他的生活狀態。狄更斯在創作生涯后期,發現了演講和朗讀作品的好處。他聲情并茂地朗讀作品給他帶來可觀的收益,激發了他的熱情。“公共朗誦會再次成了他生活中的重頭戲。”①[英]彼得·阿克洛伊德:《狄更斯傳》,包雨苗譯、譚學嵐校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46頁。他專門找人負責給他安排作品朗誦會,甚至到美國舉辦朗誦會。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和他的熱愛朗誦,或者能夠體會作品朗誦效果不無關系。文學市場和作為職業作家的狄更斯是相互成就的。
文學作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作者的寫作按照市場衡量具有特殊性。如何維持市場驅動與寫作的內在平衡,這是每一個作者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應該是作者研究不能回避的課題。有的作家靠寫作就能夠生活得非常好,這對他的寫作狀態和成就有何影響,這類案例值得研究。考察作者與市場關系的另一個例子是巴爾扎克。他的創作力驚人,主要的動力或者壓力是要償還債務。他要還投資失敗欠下的那么多的錢。這驅使他高強度地寫作。巴爾扎克的寫作一方面是他的天才和旺盛的創造力,另一個方面也是一種市場行為。馬克·吐溫晚年舉辦全球演講也和他的投資失敗,急于找出辦法還債有密切關系。狄更斯的朗誦,馬克·吐溫的演講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市場行為。這種行為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也影響他們的寫作,損害了他們的健康。
作者與地域。作者與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的關系,某一地理環境下的作者群,比如美國南方作者研究,比如河南作家群、湖北作家群、陜西作家群等,都有獨特的地域特色。
作者與故鄉的關系。很多作者都從他的故鄉寫起。有些作者一輩子的寫作擺不脫故鄉的影響。遠離故鄉的作者終歸會正視他的故鄉,不管他離開故鄉有多遠。移民作家終歸會撿拾故國給他的影響,不管他用何種語言寫作。很多作者的經驗說明,寫作最好的起步在故鄉,這里有心路歷程的起點,有最深厚的體驗,最可靠的素材。對故鄉的寫作造就最獨一無二的作者,比如福克納與約克納塔法縣,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山東高密。由于馬克·吐溫對于美國現代文學的貢獻,人們把馬克·吐溫度過少年時代的漢尼拔鎮稱為“美國文學的故鄉”。他的《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克貝里·芬歷險記》都寫了作者在這里的童年。
故鄉是作者的精神臍帶。故鄉是作者文學的發源地,造就作者特質的根基。文學研究也應該這樣,從作者的建構開始。因為作者是作品的書寫者,是文學活動的初始環節,所以,我說作者是文學的故鄉。
作者的人生與寫作的關系。這個專題主要關注作者與現實生活的距離,有些作家有意選擇一種不一樣的生活,甚至不大眾化的生活。亨利·詹姆斯選擇旁觀者的角度看世界。安徒生執意要過一種孤獨的生活。羅伯特·弗羅斯特一心從大都市倫敦回到美國鄉下的新英格蘭農場。有些作家的生活方式,他觀察生活的角度成就了他的創作。有些作家很自律,歌德嚴格地分隔自己的日常事務與寫作,《浮士德》雕琢了六十年。威廉·薩默塞特·毛姆每天寫作五千字,五十多年始終如一,他的文筆才那么流暢自然。
作者的寫作立場和角色。這主要是看作者從什么角度寫作。莎士比亞寫得好,還在于他得天獨厚的作者角色。他是一名演員、編劇和股東。他從演員的角度寫臺詞,容易記誦,適合在舞臺上表演,演出效果好。作為股東,他總能夠捕捉到時代的熱點,和觀眾關注的話題,盡量娛樂所有的觀眾。所以,他的劇本演員愛演,觀眾愛看。
作者的氣質和狀態研究。比如孤獨或憂郁,像波德萊爾的憂郁。作者是孤獨的職業,寫作是一個人的事業,孤獨是免不了的,甚至是作者的常見狀態和命運。屈原的“舉世濁濁而我獨醒”,陳子昂的“獨愴然而涕下”,李白的“自古圣賢皆寂寞”的感慨,表達的都是那種遺世獨立的姿態。荷馬的漂泊,但丁的“一個人的黨派”等等,是一種清醒的孤獨。所以,孤獨是作者的常態或曰天命。當然,每個作者各有孤獨的原因。這種普遍的宿命和特殊際遇造成的孤獨狀態,結合到具體作者研究,才能理解作者寫作的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這是理解作者的共性與個性的一把鑰匙。
成為流行作者還是經典作者?寫作是為了長久還是當下?每個作家都有此一問。作者的寫作追求和社會評價的關系是很現實的話題。評價好卻賣得不好的作品多的是,作品銷量好但得不到好評的作者也有的是。作者名聲是評委獎項、營銷機制、文學風尚、國家意志、批評傳統、讀者心理等多方面綜合的結果。還是應該相信古羅馬朗吉努斯的箴言:好作品能夠贏得所有時代所有人的好評。美國小說家麥爾維爾和詩人狄金森都是生前默默,死后寂寥,現在卻被公認為美國的經典作者。
以上種種,是作者研究的基本問題,可以不斷羅列下去,納入作者專題研究。
五、作者生態研究
作者研究既需要理論建構,也應該能夠應對現實問題,還可以明確建構文學批評的方法論。作者生態研究就是這樣一種解決方案。其核心觀點是,作者是一個處于動態生成系統中、不斷建構中的角色。這個系統包括作者成長、作者角色、作者創作和作者接受等四個方面。“四個方面的相互作用構成完整的作者生態系統。”①刁克利:《作者》,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頁。具體說來,作者生成論指的是作者的成長研究,即一個人如何成為作者。作者角色論指的是作者的自我認知和作者角色的確立。作者創作論是對作者的創作研究。作者影響論指的是作者作品的傳播、接受和影響。下面從這四個方面分別舉例,說明什么是作者生態研究。
從作者角色論看荷馬,不是為了論證“誰是荷馬”,而是要回答“荷馬是什么”,要說明荷馬的作者角色,及其啟發和意義。荷馬奠定了神啟者、漂泊者和辯護者的作者角色。他為文學如何應對時間樹立了典范,也成就了作者的不朽。文學作者能夠享受到的榮耀和可能的遭遇,在荷馬身上,都能看到預兆。荷馬的作者角色具有多重意義。
從作者生成論看但丁就會發現,《新生》的寫作,從素材提煉,情感表達的形式與內容,到詩人的自我剖析等,就是但丁作為一個詩人的生成過程。《論俗語》和《饗宴》是但丁的文學思想的沉淀。《神曲》作為其代表作,雖然寫的是地獄、煉獄和天堂,道的卻是人間事。但丁是作為詩人自我生成和自我經典化的典范。
從作者創作論的視角理解華茲華斯,得到的啟發則是,自然與詩人的相互成就。華茲華斯的自然是良師、益友、佳伴。自然作用于詩人的心靈,詩人傳達自然的啟迪給讀者,使讀者受益華茲華斯啟迪了對自然的認識,強調自然人格化。自然作用于詩人的內心,促進詩人的自省與成長,這是華茲華斯詩歌的現代意義。華茲華斯在英雄的經典傳統的情結的影響下,寫出了詩人心靈成長的史詩。
從作者影響論的視角研究彌爾頓及其《失樂園》可以知道,早期批評家的最大挑戰是分離彌爾頓的詩歌和他的政論文章,把《失樂園》從誹謗中傷中拯救出來,以建立他的詩名。現代學者的最大努力是重新將二者聯系起來,從彌爾頓的政治信仰方面理解這部杰出的史詩。彌爾頓的接受軌跡是一個先從對詩人政治身份的關注到詩人身份的轉化,又由詩人身份轉而關注其作為人的多方面存在的過程。
作者生態研究既是一種理論建構,也是一種批評方法。作者生態研究可以按照作者的角色、生成、創作與影響等分門別類,進行專題研究,也可以用來分析一個作者形態,還可以用來進行兩個作者的比較研究,又可以用來描述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作者特征。
華茲華斯和白居易各寫過一首關于刈麥的詩歌,可以作為作者生態研究視域下比較研究的例證。前者的詩名為《孤獨的刈麥女》,后者的詩名為《觀刈麥》,都是兩人代表性詩篇。兩位詩人都善于以詩寫畫。兩首詩相似處甚多,比如語言直白,題材日常化。讀之歷歷在目,又意蘊悠長。但是兩首詩旨趣各異,效果有別。
《孤獨的刈麥女》中,華茲華斯在刈賣女的歌聲中,發現了一種巨大的魅力。他將這歌聲深埋心中,久久難以忘懷。詩人傳達了三重喜悅:少女勞作之景象,少女一人在田間勞作畫面之美,靜觀足以娛目;歌聲之悠揚動聽,聞之足以悅耳;歌聲充盈山谷,充盈詩人的心靈,響徹遼遠的沙漠,思之足以心馳神往。詩人欣賞這歌聲,贊美這少女。詩人寫歌聲之美,聆聽之喜,也寫出了孤獨中的歡暢,心靈洗滌蕩氣回腸之愉悅。所以,這是一首歌詠刈賣女歌聲之美的詩篇,是一首審美的詩。其意不在刈賣女,也不在歌聲的內容,而在于歌聲之悠長和難忘。歌聲讓人忘情、忘憂,歌聲中有撫慰人的美感與力量。
白居易在《觀刈麥》中,描寫了刈麥者的艱辛勞作,將自己作為官員的優裕生活和刈麥者的悲慘處境進行了對比,表達了對刈麥者的巨大同情。引發詩人感慨的是情感思緒,而不是審美。提醒詩人作為對比面的存在,而不是忘掉自己。他以寫實的筆法帶動感情升華和凈化,他的體驗沉重而厚實。如果說華茲華斯的詩歌重在聆聽、聽得忘記自己,白居易的詩歌則重在觀,觀農人,亦觀自身。他寫出了三重苦:農人勞作之苦,婦人生活之苦,民賦稅沉重之苦。同時,也寫出了身為官員的自省:對比農人之苦,官員卻免除賦稅且有俸祿,心生愧疚。
雖然寫作的題材相似,詩歌效果和感染力的方向卻不同。一欣然一苦楚,一飛揚一沉重;一審美神思,一躬身自問。究其原因,宜從作者角色論加以說明。也就是說,兩首詩之不同在于詩人的現實身份和角色的差異。華茲華斯身份是漫游者。詩人雖然知道刈賣女孤獨,雖然對于刈賣女的憂傷感到些許不幸(如果那歌聲中有這些內容),但他無意訴諸自己的同情。他在意歌聲本身的效果,旨在通過想象激發美感,陶冶情操,無知覺中得到撫慰和超拔,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華茲華斯是受到美的感召的詩人。白居易的現實角色是當地官員。他的詩歌旨在告白與體察時事,亦反省自身。在對刈麥者的審度中,他體恤民情民病,感同身受,化勞動者的身苦為詩人的心愧,寫出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形象。簡言之,兩首詩之不同,在于兩位詩人的角色不同。
從以上關于作者理論研究、作者專題研究、作者生態研究的論述和例示中,可以得出:但凡作者遇到的現實問題,但凡關于作者的理論問題,都是作者研究的應有之義,都應該歸于作者研究的范疇和領域。將作者研究的基本問題結合不同時期的作者狀況,借助于作者理論的研究資源,能夠給作者帶來切實的幫助,拓展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的視野,為文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在作者研究中,需要明確幾個基本觀點。第一,作者研究可以是一種自成體系的獨立存在。作者理論和讀者理論、文本理論一樣,構成最基本的文學理論。第二,作者重構必須擺脫將作者與文本隔裂的思路,加強作者與作品的密切聯系,關注作者的生成與角色、作者的創作與傳播,關注文學的動力源泉以及文學對于人類精神生活的貢獻。第三,作者是文學的基本動力,重視作者問題,是回到文學的源頭和發生的根本,重視文學研究中的人的因素,重視文學的詩性特征。第四,作者研究要置于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亦如要重新定位作者在文學中的地位一樣,作者研究啟發我們重新理解人與世界的聯系。
人文學科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守護和傳承經典。作者是經典的書寫者,作者是文學的故鄉。作者研究注重回溯作品的來處,關注經典產生的緣由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