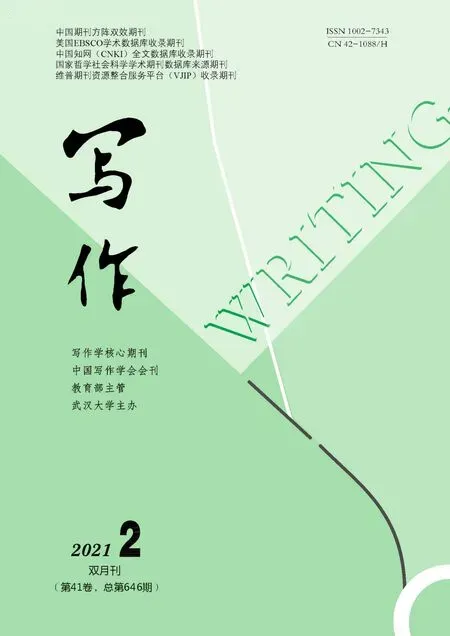從《再擊壤歌》看寫作中的二律背反問題
胡 亮
一
要談詩人陳先發的匠心之作《再擊壤歌》,當然,就要先談某個上古初民的即興之作《擊壤歌》。《擊壤歌》的作者以及時代,都已經渺不可考。“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詩心橫跨的斜拉橋,永遠看不到橋頭堡。同樣的道理,還當有更加晚來的“陳先發”。想想,就覺得很有意思。就覺得,好多東西都新得可疑。卻說《擊壤歌》,首見于《論衡》。鑒于此處及下文多處需要,必須引來這段古老的文字:“堯時,五十之民擊壤于涂。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①王充:《論衡·感虛第十九》,袁華忠、方家常:《論衡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論衡》作者王充,出身于“細族孤門”,生活于公元1世紀。到了公元5世紀,范曄著《后漢書》,對王充下了一個評語:“好博覽而不守章句。”②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299頁。這個評語很奇怪,似乎在說,王充既是學問家,又是自以為是派。堯之于王充,恰如王充之于我。我今目擊王充之舊籍,恰如王充當年耳聞堯之逸史。可信度,也許會兩次打折。如果王充的記載屬實,那么《擊壤歌》就應該是漢詩的“元典”。“元”者,“始”也。“原始”,如今已是一個雙音節詞。杰出的古典詩學者朱自清先生,似乎就采信了王充。他當年編纂《古逸歌謠集說》,置于卷首的一篇作品正是《擊壤歌》。
《論衡》算得上是一部哲學散文,與詩無涉,后來才有人從中摘引出并修訂為傳世單行本《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從哲學散文,到詩,變化并不大。然而,卻是高手所為。為何這么講?哲學散文在“吾”后連用五個四字句,已然板滯,幾乎讓人難以忍受。詩將“堯何等力”,改為“帝力于我何有哉”,一則語氣更加有力,再則句式更加多姿。這個細小而微的文字調整,甚至預言了漢詩的大趨勢:從四言,到七言。你說奇妙不奇妙,重要不重要?這是閑話休提。
對于陳先發來說,《擊壤歌》既是漢詩的“元典”,也是《再擊壤歌》的“原典”。“原”者,“本”也。“原本”,如今亦是一個雙音節詞。那么可否這樣講,《再擊壤歌》,本于《擊壤歌》?這個問題卻不能輕率作答。即便《擊壤歌》關乎勞動(稼穡之勞動),《再擊壤歌》亦關乎勞動(詩之勞動),也不能強行將前者看作是后者的絕對上游。況且,著眼點如果只是勞動,是不是太皮表了呢?至于王充,在這個問題上,那就顯得更加皮表——他在《論衡》里引來《擊壤歌》,不過是為了證明“堯時已有井矣”①王充:《論衡·感虛第十九》,袁華忠、方家常:《論衡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二
《擊壤歌》被視為勞動之歌,或田野之歌,其實卻是游戲之歌。“壤”,并非土泥,而是一種古代玩具;“擊壤”,并非勞動于田野,而是一種古代游戲。卻說有個浪子回頭的周處,生活于公元3世紀,著有《吳書》,又著有《風土記》。這部《風土記》,已佚,幸而被其他古籍征引而保留下這樣一個片段:“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后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②轉引自王應麟:《困學紀聞》卷20,轉引自朱自清:《古詩歌箋釋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頁。可見擊壤游戲共有兩個壤,手中壤,地上壤,前壤擊中后壤,就算是取得了勝利。手中壤與地上壤,既有排斥力,又有吸引力,既是一對充滿敵意的矛盾,又是一對充滿愛意的雌雄。
而陳先發的《再擊壤歌》,已將這個擊壤游戲,看似巧合般地落實為詩學隱喻。這首新詩當然是一首“元詩”(Metapoem或Metapoetry),更狹義地說,是一首“論詩詩”(The Poem on Poetry)。詩人拋出了寫作的二元論,卻又企圖皈依于更加高妙的一元論。何謂寫作的二元論?一元是“我渴望在嚴酷紀律的籠罩下寫作”(全詩第一行),一元是“也可能恰恰相反,一切走向散漫”(全詩第二行)。對于任何詩人的青年時代來說,對于多數詩人的一生來說,這都是一對矛盾;而對于杰出詩人的中晚年來說,反而是一對雌雄。何謂寫作的一元論?“在嚴酷紀律和隨心所欲之間又何嘗/存在一片我足以寄身的緩沖地帶”(全詩最后兩行)。“嚴酷紀律”,進階也;“散漫”,化境也。兩者有可能反復交手,反復擦肩,反復紅臉,此消而彼長,也有可能前者最終重疊于而不是繞開了后者。矛盾冰釋,雌雄齒合。“月亮,請映照我垂注在空中的身子/如同映照那個從零飛向一的鳥兒”——這首詩只有此處所引之兩行,好比半首絕句,卻偏要無愧地叫做《絕句》。這是閑話休提。
筆者早就注意到,前述想法,于陳先發可謂由來已久。詩人講過一個數學壞故事,或者說,一個詩學好故事:他誘導五歲的兒子,做算術題,得出了豐富的錯誤答案,故意違悖了老師的努力和教育的要義。為何這么做?在孤獨的黑池壩,詩人如是說:“但我要令他明白,規則緣于假設,你要充分享受不規則的可能性,要充分享受不規則的眩暈與昏暗,要充分享受不規則的鋸齒狀幸福感,才不致辜負大自然在一具肉體成長時所贈予的深深美意。”③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61頁。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許稍異于詩人——對于算術題而言,答案越多,機會和幸福感越少;對于詩學而言,答案越多,機會和幸福感越多。詩人故意混淆兩者之差異,不過是明里犧牲數學而暗里成全詩學。“規則”,“嚴酷紀律”也;“不規則”,“散漫”也。這是兩座看似對峙的昆侖,而詩人并非如他恰才所說,總是罔顧“規則昆侖”(亦即“嚴酷紀律昆侖”),而只想登上“不規則昆侖”(亦即“散漫昆侖”)。讓我們來看看,他是多么地矛盾重重——有時候,他會鐘情于“兩岸的嚴厲限制”,以其“能賦河水以自由之美與哺育之德”④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61頁。;有時候,他會遷怒于“邏輯所要求的某種嚴謹”,以其“毀掉了我們最美的旋律、囈語和棺槨”①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7、165頁。;有時候,他欲罷不能地想要化身為一條魚,這條魚乃是擊壤游戲的高手,以其深知“二分法之謬”,故而能夠“同時寄身于鋼鐵之疲勞與河水之清冽”②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7、165頁。。有正,有反,有合,詩人恰在捶打詩學的繞指柔。這且不提;卻說這條魚如果洄游,不出意料,最終將會重返巨河之源(亦即人類文明之源)——佛家所謂“不二法門”③賴永海、高永旺譯注:《維摩詰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0、152頁。,道家所謂“抱一為天下式”④朱謙之:《老子校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2頁。,抑或儒家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⑤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6頁。。
三
從數學到詩學的跨欄,其“風險”,可能遠遜于從詩學到佛學的通犀。《維摩詰所說經》怎么講?“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⑥賴永海、高永旺譯注:《維摩詰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0、152頁。那么,佛學如何引導心猿?——其下境為“有縛”,其中境為“有解”,其上境為“無縛無解”。舉一反三,以此類推,不二法門還意味著無受無不受,無垢無凈,無相無無相,無善無不善,無罪無福,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無死,無盡無不盡,無我無無我,無色無空,無身無身滅,無取無舍,無暗無明,無實無不實,最終歸于無言無說。那么,詩學如何引導心猿?——其下境為“詩”,其中境為“非詩”,其上境為“無詩無非詩”。如汝所見——“風險”逐步升級,佛學最終孵化出一種遠在天外的烏托邦詩學,或一種近在眼前的虛無主義詩學。如果詩學盲從了佛學,詩與詩人,最終難免自割頭顱。
筆者很早就意識到,學佛不可學詩。但是呢,學詩不妨學佛。怎么學佛?只到中境,勿入上境。詩人的特種行囊過于沉重,裝滿了詞和妄念,那就正好在中境送別燕子般的和尚。且容詩人漫步于“有縛”與“有解”,而讓和尚縱身于“無縛無解”(盡管這于他們也甚是艱難)。“有縛”,“規則”與“嚴酷紀律”也;“有解”,“不規則”與“散漫”也。詩人與詩不必——不可——也不能臻于“無縛無解”的佳境,究其實,正是為了小心翼翼地避開“無詩無非詩”的困境。
這里,且以民國的一次著名唱和為例——周作人《所謂五十自壽打油詩》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以其“有分別心”,故而“有縛”;蔡元培《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壽》,“何分袍子與袈裟,天下原來是一家”,以其“無分別心”,故而“有解”;然則兩者都是詩人說話,而非和尚說話;臨到和尚說話,既無“袍子”,亦無“袈裟”,甚或也就“無言無說”。“有分別心”,“無分別心”,或許對應了陳先發所謂“從一到二的寫作”與“從零到一的寫作”——這對有趣的寫作學術語,出自組詩《居巢九章》中的《零》。《再擊壤歌》當是兩種寫作的一個結晶,既是“周作人”說話,又是“蔡元培”說話,既是“有縛之詩”,又是“有解之詩”,卻絕非“無縛無解之詩”。此乃和尚之殘局,卻是詩人之勝局,且容筆者后文從容講來。
四
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一個罕遘之機遇,來鑒賞這樣一種詩之狀態(或思之狀態)——“有縛”是個車站,“有解”也是個車站,“袍子”與“袈裟”亦當如是觀,“有分別心”與“無分別心”亦當如是觀,乃至“精確度”與“即興性”亦當如是觀。詩人在前者與后者之間反復往返,從而源源不斷地為詩提供了發生學意義上的“核動力”。此乃詩人之使命,亦是詩人之宿命。倘若往而不返,詩人或將真個做了和尚。陳先發搶購了一大把“往返票”,因而這首《再擊壤歌》,無論是從“語義”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詩形”的角度來看,都呈現為剪刀般的兩刃相割式結構,或麻花辮般的纏繞狀結構。
首先,從“語義”的角度來看——第一行,“我渴望在嚴酷紀律的籠罩下寫作”,初說“有縛”;第二行,“也可能恰恰相反,一切走向散漫”,初說“有解”;第三至第六行,“鳥兒從不知道自己幾歲了/在枯草叢中散步啊散步/掉下羽毛,又/找尋著羽毛”,隨手取譬,細說“有解”;第七行,“‘活在這腳印之中,不在腳印之外’”,以畫外音方式,再說“有縛”;第八至第九行,“中秋光線的旋律彌開/它可以一直是空心的”,隨手取譬,巧用通感,細說“有解”;第十行,“‘活在這緘默之中,不在緘默之上’”,以畫外音方式,再說“有解”;第十一至第十二行,“朝霞晚霞,一字之別/虛空碧空,祼眼可見”,隨手取譬,借“朝霞”異于“晚霞”,“虛空”異于“碧空”,初說“有分別心”;第十三至第十四行,“隨之起舞吧,哪里有什么頓悟漸悟/沒有一件東西能將自己真正藏起來”,忽視兩種方法論——“頓悟”與“漸悟”的不同,突然將“有分別心”變頻為“無分別心”;第十五至第十六行,“赤膊赤腳,水闊風涼/楓葉蕉葉,觸目即逝”,隨手取譬,借“赤膊”無異于“赤腳”,“楓葉”無異于“蕉葉”,再說“無分別心”,“觸目即逝”亦即詩人所謂“完整地消失是我們在現象上最終的勝利”;第十七至第十八行,“在嚴酷紀律和隨心所欲之間又何嘗/存在一片我足以寄身的緩沖地帶?”,最終歸結于“有縛有解”。全詩起句(前兩行)的“嚴酷紀律”復見于結句(末二行),這是長蛇銜尾的一般句法;起句的“散漫”在結句中換成“隨心所欲”,則是長蛇銜尾的花式句法。花式,“花”得特別好,否則就會平添至少兩噸重的板滯。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全詩總十八行,由肯定而否定,由否定而否定之否定,構建了令人目眩而又如此理所當然的“自反”(self-negative)風景。詩人獨以個我之生命,接通世界之生命,就漸次進入了大自如的境界。這個風景,堪稱絕景。
上述觀點還將易如反掌地引出另外的觀點,比如,這首詩交替展開了兩套同義詞系統。而這兩套同義詞系統,合成了一套反義詞系統。先來看第一套同義詞系統——從“嚴酷紀律”,到“腳印”,到“中秋光線的旋律”,到“一字之別”,到“祼眼可見”,到“漸悟”;再來看第二套同義詞系統——從“散漫”,到“散步啊散步”,到“空心”,到“緘默”,到“隨之起舞”,到“頓悟”,到“水闊風涼”,到“觸目即逝”,到“隨心所欲”。顯而易見,第一套同義詞系統的規模,遠遜于第二套同義詞系統。這說明,就總體向度而言,這首詩由“有縛”奔向了“有解”。而在所有這些詞與詞組里面,最為突兀的,不是“中秋”,而是“緘默”。“中秋”,經筆者采訪詩人證實,或為必然,或為偶然,乃是此詩的成稿時間。而“緘默”,似乎更像是一個中性詞,隨時都有可能出離第二套同義詞系統,甚至可以加入第一套同義詞系統。這個發現,甚是奇妙,可以說令筆者大為驚訝。在孤獨的黑池壩,詩人曾多次自釋“緘默”。一次,他如是說:“感官雷動,有默為基。默中之默,猶巨枝生于微風之中,不解己之為枝,不知風之為動。相互咬合,無技可分。”①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8頁。一次,他如是說:“假設某種‘永恒沉默的部分’可以成為我們的目的——我們創立語言并不斷地寫作,是為了加速讓它顯現——而我們所做的一切事實上又在否定著它。像卑微的鳥鳴與附于其上的深不可測的寧靜,執著于鳴之清越、鳥之短暫,忘乎所以,又不知其忘;處其短而不以形役,聞其聲而不計其鳴。”②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8頁。可見“緘默”也者,乃是《維摩詰所說經》所云“無言無說”——這樣一座文字的斷頭臺,超越了理性邊界,既絞殺了“嚴酷紀律”,又絞殺了“散漫”。這說明,就某個瞬間而言,這首詩由“有解”奔向了“無縛無解”(這是這首詩的一個虛無主義邊陲)。可見佛經也罷,新詩也罷,誰又沒有陷入過爛泥般的“文字障”?
現在,從“詩形”的角度來看——第一至第六行,第八至第九行,第十三至第十四行,第十七至第十八行,都用散句;第七行和第十行,中間隔著兩行,組成了一對駢句;第十一至第十二行,組成了一對小駢句,第十五至第十六行,組成了一對小駢句,兩對小駢句中間隔著兩行,組成了一對更大的駢句。當然,駢句不一定服務于“有縛”,散句不一定服務于“有解”——可見“詩形”與“語義”,有時候心心相印,有時候則同床異夢或背道而馳。散句與駢句的反復往返,不太顧及“所指”(Signifié),而頗為任性地打造了能指(Signifiant)層面上的視覺節奏和聽覺節奏。這首詩的形式感或儀式感,可謂用心良苦,綽乎有余地響應了艾略特的反面立論——“自由詩并不存在”①轉引自[美]斯蒂芬妮·伯特:《別去讀詩》,袁永蘋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97頁。,也響應了桑塔格的正面立論——“一切藝術皆趨向于形式”②[美]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頁。。
五
前文一再談到的“往返”,也可以譯為“爭論”。那就讓我們從耽溺太深的《再擊壤歌》,回到冷落有時的《擊壤歌》。準確地說,是回到由后者引發的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一方是籍籍無名的鮑敬言,一方是鼎鼎大名的葛洪(也就是抱樸子)。葛洪與鮑敬言,生活于公元3世紀到4世紀。到了4世紀,葛洪著《抱樸子外篇》,曾如是介紹鮑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③葛洪:《抱樸子外篇》,張松輝、張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頁。又曾如是介紹自己——“期于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④葛洪:《抱樸子外篇》,張松輝、張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頁。歸納一下兩段文字的意思:鮑敬言喜歡爭論,葛洪不喜歡爭論(除非棋逢對手)。然則,兩者終于發生了一場爭論:針鋒相對,而又幾乎不為人知。
鮑敬言與葛洪都是道家人物,這場爭論,卻幾乎把葛洪逼成了儒家人物。《抱樸子外篇》的相關記載,甚為翔實,此處且引來雙方主要論點。鮑敬言說:“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⑤葛洪:《抱樸子外篇》,張松輝、張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頁。鮑敬言暗引《擊壤歌》,將“鑿井而飲”,改成“穿井而飲”,又將一二行與三四行對換,由此遞進而立論,頗近于今人所謂“無政府主義”。葛洪則說,“明辟蒞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⑥葛洪:《抱樸子外篇》,張松輝、張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頁。,“是以禮制則君樂,樂作而刑厝也。若乎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⑦葛洪:《抱樸子外篇》,張松輝、張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93、1112、996、1003、1006頁。葛洪所謂“明辟”“良宰”,還曾表述為“明王”“圣人”或“皇風”。鮑敬言提出了一種“無君論”,緣于“無為論”,乃是道家思想之正脈;葛洪則提出了一種“有君論”,緣于“有為論”,乃是儒家思想之正脈。除了《抱樸子外篇》,鮑敬言不見于任何古籍。他會不會是葛洪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呢?這個假設過于大膽,那就不妨更加大膽:這場爭論會不會是葛洪的此我與彼我的一次或若干次爭論呢?
《抱樸子外篇》的政治學命題,或思想史命題,預演了《再擊壤歌》的詩學命題。“無君論”之“君”,暴君也;“有君論”之“君”,明君也。道家儒家,相反相成。“有君論”與“無君論”的雙向修補,“有為論”與“無為論”的相互修補,就像“嚴酷紀律”和“散漫”的雙向修補。葛洪本是道家人物,卻轉而提倡禮樂,亦堪稱道家修正派。而陳先發,則堪稱儒家修正派。詩人之急需不是道家修正派,而是絕對道家,只有后者才有可能封堵他的儒家思想的蟻穴。詩人賦有一首《深嗅》,結尾時,曾發出過極為虔敬的詩學吁請,“等這場小雨結束/‘無為’二字將在積水中閃光/葛洪醫生/請修補我。”這位葛洪醫生,反而等于鮑敬言,正是所謂絕對道家。
六
筆者已經反復談到《再擊壤歌》,反復談到《擊壤歌》,現在正好由兩者之關系,談到“傳統與個人才能”之關系。前文曾有提及的艾略特,曾從兩個維度闡述過這個問題:其一,“理解過去的過去性”;其二,“理解過去的現存性”①《傳統與個人才能》,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楊煉所謂“同心圓”②參見《同心圓》,楊煉:《鬼話·智力的空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20頁。,有證據表明,也是對這種觀點的重釋。而陳先發,似乎另有一番見解。在孤獨的黑池壩,詩人曾多次自釋“傳統觀”。他用得最多的詞組,就是“共時性”——“我確知自己能找到‘某個時刻’——在它之內,不管有著往日的隱士,還是明日的變形戰士;不管是莊周在喂養母龍還是希梅內斯在種植石榴樹。”③陳先發:《黑池壩筆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頁。《再擊壤歌》與《擊壤歌》,既平行,又交叉,故而不免參差。借用艾略特的觀點,或許可以說,《擊壤歌》催眠了《再擊壤歌》,前者呈現出一種倔強的“現存性”;按照陳先發的觀點,或許可以說,《再擊壤歌》喚醒了《擊壤歌》,后者提供了一種令人喜出望外的“共時性”。“現存性”與“共時性”有同有異,其異,導致了大相徑庭的結果:艾略特的詩學旅行,投宿于一種安全的“非個人性”;而陳先發的詩學冒險,立錐于搖搖欲墜的“個人性”。已知與未知,名勝與秘境,端看詩人如何取舍或搭配。
艾略特與陳先發似乎都沒有致力于某種條分縷析,在這里,筆者樂于稍作嘗試。如果將中國古典詩——當然包括《擊壤歌》——視為“賦能者”,從而察看新詩之反應,就會厘出好幾種大異其趣的“接受模式”。第一種,“貌合神離”,可以魯迅先生為例。比如《故事新編》各篇,亦即《補天》《奔月》《理水》《采薇》《鑄劍》《出關》《非攻》和《起死》,其“原典”,包括《尚書》《左傳》《莊子》《墨子》《山海經》《淮南子》《史記》《列異傳》和《搜神記》。“今典”之于“原典”,全是后現代主義式的“滑稽模仿”(parody)。除了短篇小說,還可以舉出魯迅的新詩。比如《我的失戀》,其“原典”,乃是張衡的《四愁詩》。來讀《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再來讀《我的失戀》:“愛人贈我金表索;回她什么:發汗藥。”后者,居然步前者之原韻。這樣的“滑稽模仿”,正是所謂“貌合神離”。第二種,“貌神俱離”,可以穆旦為例。比如《饑餓的中國》(其三),其“原典”全是“西典”,既包括葉芝的《再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又包括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還包括奧登的《西班牙》(Spain)④參見《偽奧登風與非中國性:重估穆旦》,江弱水:《中西同步與位移——現代詩人叢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4頁。。既然無涉中國古典詩,那就毋須引來原文。這樣的“非中國”⑤王佐良:《一個中國新詩人》,王圣思選編:《“九葉詩人”評論資料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頁。,正是所謂“貌神俱離”。第三種,“貌神俱合”,可以張棗為例。比如《何人斯》,其“原典”,乃是《詩經·節南山之什·何人斯》。來讀《詩經·節南山之什·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再來讀《何人斯》:“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聲音/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測。”這兩件作品,正是所謂“貌神俱合”。第四種,“貌離神合”或“遺貌取神”,可以陳先發為例。比如《再擊壤歌》,其“原典”,乃是《擊壤歌》。單就標題而言,兩者確已建立顯而易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而就正文而言,兩者既可以說是毫不相關,也可以說是心心相印于某個肉眼看不到的隱形峰頂。這兩件作品,正是所謂“貌離神合”或“遺貌取神”。陳先發與張棗另有一個不同:后者的《何人斯》,標題沿襲自“原典”;前者的《再擊壤歌》,標題改竄自“原典”。陳先發有意添上去的這個字——“再”,似乎預示著這兩位詩人,或這兩首新詩,將在不同的半徑內分頭完成各自的蹀躞。
魯迅和穆旦正當一個弒父時代(亦即破壞時代),前者正當弒父時代的初期,后者正當弒父時代的后期。張棗和陳先發或值一個拯父時代(此乃筆者杜撰,亦即建設時代),前者正當拯父時代的初期,后者正當拯父時代的中期(誰知道呢,也許仍屬初期)。魯迅的“故事新編”,穆旦的“西詩東漸”,張棗的“古典今譯”,乃至陳先發的“舊題重寫”,可謂各自奪取各自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時代的自覺與個人的自覺,兩者,有時候是水推沙,有時候是金鑲玉。從當年的“大破”到如今的“小立”(尚不是“大立”),詩人或已迎來轉機,可望攀上那如此崔嵬的“共時性”。陳先發已經用個人的自覺,響應或強化了時代的自覺。所謂傳統不再是外在的甲胄,而是內在的氣息。如鹽入水,半穿袈裟。這個意義,應該放到新詩史上去總結。閃轉騰挪,莫非偶然。偶然也者,莫非必然。所以說,從新詩的苗頭,也就可以見出百年中國文化的趨勢。
七
筆者已經借道于或者說受教于《擊壤歌》和《再擊壤歌》,論及至少兩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從時間的角度來看,乃是“離”與“合”的二律背反;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乃是“嚴酷紀律”與“散漫”的二律背反。哲學家康德所謂“二律背反”,已被如此篤定的陳先發而非氣喘吁吁跟上來的筆者,三申為以不變應萬變的詩學之鎖與詩學之鑰。
因而,謝天謝地,本文的起步點以及落腳點都是“詩”,都是“詩學”,而非廣義上所謂“文化”。筆者無意于展開過于洋溢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然則看起來有點兒繚亂的東挦西扯,或許也曾誤入過艾柯所謂“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那就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好在,詩人陳先發從來就不反感“過度詮釋”。在孤獨的黑池壩,詩人早已預支給筆者一根如此如意的定海神針——“小說家自身容量大于他的小說之和,而詩人小于他的任何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