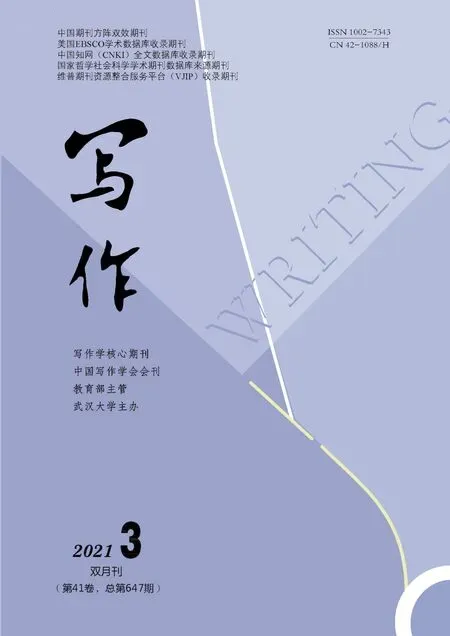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敘事倫理
田 豐
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敘事絕非僅僅是講故事,而是自誕生之日起便與人的倫理觀念緊密相關。正如同布斯所言,敘事作品都是關乎道德教誨的,因而在人類倫理道德傳承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有著宗教觀念傳統的西方古典文學相比,中國傳統文學匱乏懺悔意識和超越精神,但在濃郁的現實關懷意識指引下,也有著注重倫理教化的優良傳統。中國自古以來便極其重視倫理道德,由此使得文學作品也浸染著濃得化不開的倫理色彩,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有著“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①《毛詩序》,孫秋克主編:《中國古代文論新體系教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頁。的倫理道德功效。現代小說“敘事”極其注重個性化和客觀性,與傳統小說相比敘事主體的介入程度有了很大差異,但想要保持絕對中立、客觀的態度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無限接近,但始終無法抵達真正的“零度寫作”。原因有三,其一在于小說創作本身是作家主體心靈對于外界事物的感知體驗,難免會在觀察和講述的過程中融入自身所秉持的倫理觀念,實際上也正是“故事使與其他人在倫理上分享一個共同的世界成為可能”②[愛爾蘭]理查德·卡尼:《故事離真實有多遠》,王廣州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頁。;其二文學是人學,而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倫理化的,這就使得關乎人的敘事自然無法脫離倫理觀念的拘囿,就像尼采所說的“‘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能夠‘生成’”①[德]尼采:《權力意志》,張念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86頁。;其三文學創作的媒介語言本身就“并非道德中立,因為人腦的欲望并非中立”②[加]瑪格麗特·艾特伍德:《與死者協商》,嚴韻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79頁。,比如“雜草”一詞就包含著人為的對于某些植物的負面評判。
總體而言,作家在從事文學敘事時無論思想意蘊的傳達,還是語言風格的擇取,都會受到倫理道德的規約。敘事倫理不僅會直接影響作品的精神價值取向,而且也關涉著小說文本終極價值的實現。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中本著對鄉土生活的熟悉,以及對農民個性氣質的了解,將敘事倫理指向人性和心理復雜性的呈現,有助于人們深入體會農民在劇烈社會變革下真實的倫理道德狀況。
一、關注個體生命感覺的倫理姿態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敘事倫理并非像十七年時期政治化小說那樣,將不容置疑的倫理道德觀念傳達給讀者,以此進行倫理教化和道德規訓,而是從集體觀念中解放出來,致力于個體生命感覺的呈現,也即從“大我”轉向“小我”,由人民倫理轉向個體倫理。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敘事倫理關乎但并不完全屬意于是非曲直的價值判斷,而是在其中滲透著作家個體的生命感受。其著眼點并非要通過哲學思辨或者理性審視,來教導人們應該怎樣生活以及生命應該怎樣,而是告訴人們個體生命曾經怎樣或者可能怎樣,啟發讀者進行思索和評判,有助于久在藩籬中的人們擺脫現實生活視野的局限,從而喚醒真切的生命感觸,啟示人們反思自身的倫理處境和生存狀態,進而明確生活的意義或者怎樣的生活才是值得的。雖然文學敘事離不開虛構,但在此過程中也勢必融入作家的個體感受和個人經驗,從而在不斷喚醒往事記憶的同時,也自然地摻雜進作家個人的倫理觀念和精神信仰。文學敘事不僅關乎著氛圍的營造、結構的安排和視角的選取,同時也關乎著作家內心的道德倫理感受,以及對于世界與人生的基本認識。由于作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不同,也賦予作品鮮明而獨特的敘事倫理。
詹姆斯·費倫認為敘事是作家帶有特定目的的修辭行為,“在虛構性敘事中,修辭行為在兩個層面上存在:敘述者為了某個目的向接受者講述他的故事,而作者則通過向讀者傳達故事內容以及表現故事的講述行為來實現某個目的”③James Phelan,Experiencing Fiction-Judgment,Progressions,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4.,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作為虛構的故事系列,也與倫理規范有著內在聯系,透過敘事修辭向讀者傳達不同時代個體所做出的倫理抉擇對其人生命運走向所產生的影響。在具體敘事方式的安排上,李佩甫也時常從傳統小說中汲取營養,比如《生命冊》中人物的出場方式就與《水滸傳》頗為相似,人物的命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如同一棵大樹那樣不斷分叉,卻又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形成縱橫交錯但并不顯雜亂的樹狀結構,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的生活事件,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生命景觀,從而激起人們對于個體命運的關注和思索。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生活道路的選擇必然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政治語境的深巨變動,農民對于土地的情感以及個體發展道路的選擇,都發生了重大調整。李佩甫《羊的門》中呼天成對于自我有著深刻的認識,早年間他原本有機會進入仕途,但他不愿撇棄自己熟悉的呼家堡,而舍棄了奔向城市大展宏圖的機會;《城的燈》中的連長蔡國寅因戰功卓著有著可以預見的光明前途,但他為了愛情毅然決然地從軍隊離職入贅無梁村。然而隨著時過境遷,《羊的門》中的呼國慶、《城的燈》中的馮家昌兄弟和《生命冊》中的吳志鵬等人卻并不作如是觀,他們身在鄉村卻熱切地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徹底告別土地,為此甚至不惜出賣人格尊嚴。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人們的經濟意識不斷覺醒,這對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但由此也導致金錢至上觀念盛行,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不斷被侵蝕。鄉土社會在現代文明的不斷沖擊下,逐漸脫去了自然樸實、古老祥和、溫暖可親、平靜明凈的舊貌,而展露出急功近利、精明算計、鉤心斗角、弱肉強食的容顏,使得原本純凈美好的人性蒙上了陰影。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對此進行了深刻揭示,但他并非要充當道德法則的制定者,而是致力于指示出精神信仰亟待重建這一迫切問題,以期引起人們的關切和注意。
進入新時期后,人們的人生道路選擇開始趨向多元化和自主化,無數由鄉入城的鄉村人得以擺脫群體觀念束縛成為原子式的個體。在適應城市運行法則的過程中,他們逐漸剝離掉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但也因脫離了熟人社會難免會產生強烈的孤獨感。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本著人文關懷意識來解析生命和撫慰生存,透過對呼國慶(《羊的門》)、馮家昌(《城的燈》)、吳志鵬(《生命冊》)等為代表的縱橫城鄉兩界的所謂成功者共有的孤獨感的揭示,不僅展現出鄉村出身者左右為難的倫理處境,而且超越了特定的時代局限,指向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會面臨的孤獨和死亡、希望和絕望等所引發的精神問題。呼國慶、馮家昌和吳志鵬等人都有著備受磨難的苦難經歷,也都親身感受過來自故鄉親人的悉心關愛,以及鄉村戀人的美好情愫,然而他們在城市異質道德觀念的不斷熏染下,使得曾經親炙的鄉村自然、健康、純樸、優美的人性人情,最終未能經受得住城市現代文明的反復清洗而逐漸褪色。對于那些根在鄉村而身處城市的人而言,在擺脫了身體苦難甚至獲得物質方面的徹底解放之后,卻又面臨著靈魂無處寄放的尷尬處境。他們對于寄身的城市極度缺乏歸屬感,對于曾經主動拋棄的故鄉而言,他們又被作為鄉村社會的背叛者遭受著道義譴責。呼國慶、馮家昌和吳志鵬等人當年無論通過何種方式進城,也無論其態度如何決絕,都無法全然隔斷與鄉村的血脈聯系,然而讓他們回歸鄉村卻又情非所愿,從而深切地感受到游離于城鄉之間的漂泊無依感。他們都有著堪稱凄苦的身世和備受煎熬的苦難經歷,進入城市后又因著對于名利地位的過度沉迷而導致人性變異,成為游弋在城與鄉之間的孤魂野鬼。尤為可悲的是,雖然呼國慶當上了縣委書記,馮家昌更是一路攀爬成為廳級干部,但他們始終無法擺脫對于專制權力的人身依附。
《羊的門》中的縣委書記呼國慶,曾經因關心民瘼疾苦而被贊譽為“呼青天”,但他的仕途之路并不順遂,每當遭遇困境時不得不乞求呼天成出手相救,他也曾想過脫離呼天成,但自始至終都像無骨的平原植物那樣無法真正自強自立。《城的燈》里的馮家昌一心想在城市立足,以徹底改變馮氏家族在村子里備受欺凌的地位,為此他甘愿背棄道德良知臣服于權力掌控之下,經不起一張提干表的誘惑,迅即拋棄了為他和馮家付出巨大犧牲的鄉下戀人劉漢香,轉而追求市長女兒李冬冬。《生命冊》中的孤兒吳志鵬是由家鄉人共同撫養和教育成人的,他之所以能夠進入大學,也是村集體花錢送禮跑來的指標,在他碩士畢業到省城一所高校任教之后,由于不堪忍受家鄉人無休止的電話求助而選擇辭職下海,此時的他因為能力有限也確屬無奈。待他在商海浮沉中終于成為巨富之后,原本有能力回饋家鄉父老,但依舊不愿意回去施以援手。雖然他擁有的物質財富在不斷增長,卻逐漸淪為金錢的附庸而罔顧親情,當他意識到這一切時為時已晚,對他有著養育之恩的老姑夫早已魂歸黃泉,而當年熱戀過的梅村也已形同陌路,曾經有恩于他的鄉親們因得不到回饋而對他心生怨懟。直到發生車禍后,他仿佛聽到了故鄉“孩兒,回來吧。孩兒,回來吧”①李佩甫:《生命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頁。的熱切呼喚,這才借著給老姑夫遷墳之機回到家鄉。表面上他有心要給故鄉找到“讓筷子豎起來”的方法,但實際上卻不過是以此來尋求自我安慰,以填補靈魂無依的恐慌感和失去人生追求目標的失落感。也正因此他才會猶疑自己像“一片干了的、四處漂泊的樹葉,還能不能再回到樹上”①李佩甫:《生命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33頁。。
二、倫理價值判斷的相對模糊性
十七年小說敘事背后因為有著先驗的政治價值觀作為指導,會提供毋庸置疑的政治倫理價值標準,人物故事的講述不過是用來強化此種倫理意圖。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卻并非如此,他并未直接給出簡單明了的答案,而在是非善惡的倫理價值判斷上呈現出相對模糊性。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村里人之間不僅相互熟悉,而且追本溯源大都有著血緣關系,由此形成基于血緣親情的倫理共同體,行為處事往往難以擺脫無所不在的倫理觀念束縛。李佩甫雖然生在城市,但他年少時為了吃頓飽飯,經常趁著周末到鄉下姥姥家去,自幼便真切地感受到傳統倫理道德的脈脈溫情。由此促使他摒棄了善惡截然對立的二元劃分模式,避免對人性進行簡單的道德判斷,既在現代啟蒙思想影響下揭示和批判那些窒息人性、阻礙個體自由和違背時代發展趨向的傳統倫理道德規范,同時又基于現實感悟對傳統倫理道德中所包蘊的優良質素給予熱情禮贊。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快速推進和經濟的持續繁榮,中國社會開始從政治化的時代轉向世俗化時代,這給長期處于社會體制和傳統家庭雙重束縛中的農民提供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機遇,然而人們的精神信仰也在金錢觀念和個人私欲的不斷侵蝕下發生變異,呈現出倫理秩序紊亂的現實道德問題,“善惡分明的道德原則不存在了,這些原則的制定者走了”②劉小楓:《永不消散的生存霧靄中的小路》,《守望靈魂:〈上海文學〉隨筆精品》,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頁。。
具體而言,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舍棄了五四鄉土小說將鄉土世界描繪成愚昧麻木、蠢笨無知、腐朽墮落的罪惡淵藪的敘事模式,而是基于生活真實將正邪交融、優劣共生的本真鄉土世界呈現給讀者。李佩甫在對鄉土出身的人物進行價值評判時,不像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鄉土小說家那樣,以俯視的姿態基于現代文明觀念對傳統鄉土世界進行倫理道德批判;也不像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鄉土小說家那樣,以近乎仰視的姿態著力展現鄉土世界的人性人情美,而是致力于以平實的眼光和平等的姿態,來展現鄉土社會善惡交織、正邪并立的倫理道德圖景。在“平原三部曲”中既沒有絕對的壞人,也沒有純然的好人,每個個體都是復雜的生命存在。綜而觀之,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的敘事倫理,摒棄了傳統小說敘事常常對無限豐富的現實生活進行簡化和提純的敘事套路,對于善惡美丑能夠一視同仁。在其小說文本中,即便是有著諸多污點的卑劣人物身上也往往有著閃光的一面,由此使得其價值取向呈現出相對模糊性。李佩甫筆下所描摹的人物形象已經很難再進行正面/反面、進步/反動、先進/落后的二元劃分,這恰恰是對于真實生活進行深刻把握方才促成的結果。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的世道人心,原本就是異常駁雜而有著無限可能性的,絕非像十七年小說流行的那樣,可以進行簡單徹底的二元對立式的道德劃分。這倒并不是因為李佩甫缺乏道德評判的決斷能力,而是以此來展現人性和心理的復雜性。
《羊的門》中的呼家堡村民之所以甘愿屈膝在呼天成的統治之下,不僅緣于呼天成通過經營“人場”讓他們得以擺脫窮困,獲得了經濟上的徹底翻身解放,而且也在于呼天成為了樹立和維護自身在村民們心目中的形象,始終嚴格恪守傳統道德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為此甘愿舍棄個人情欲和物欲的滿足。表面上,《城的燈》中對劉漢香和馮家昌婚戀變故的描寫,沿用的是“負心女子癡心漢”的傳統敘事模式,但在對人物的倫理道德觀念評判上卻呈現出復雜面相。從社會角度而言,馮家昌無疑是個成功者,他不僅自己在城市立穩腳跟,而且還將三個兄弟弄進城市,在政界、商界、軍界都有了自家人,然而這一切卻是以拋棄道德良知和人格尊嚴換取的;從個體角度而言,馮家昌固然有著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等違背道德規范的不齒之舉,但他又是一個為了弟弟們的成長甘愿犧牲個人尊嚴的好兄長。劉漢香身上無疑有著諸多值得贊揚的優良傳統道德,她在中學時對赤腳上學的馮家昌不僅沒有絲毫歧視,還本著仁愛之心將哥哥從部隊帶回的軍鞋捎給他穿。后來兩人在幽會時被人發現,她不僅極力阻止父親打斷馮家昌一條腿的念頭,而且還為馮家昌爭取了參軍入伍的機會。在馮家昌服役期間,她頂住壓力只身來到馮家辛苦操持了八年之久,但等來的卻是馮家昌已與城市姑娘結婚的噩耗。氣憤不過的劉國豆為了逼迫馮家昌就范想出種種招數,完全可以將馮家昌置于死地,劉漢香卻再次極力阻攔父親復仇。當她從城市學得園藝技術后,原本可以留在城市生活,但為了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毅然決然地回到村里。然而,劉漢香終其一生也未能擺脫從一而終的傳統貞潔觀念的束縛,由此導致個人愛情的失落和生活的不幸。《生命冊》中矮小瘦弱的蟲嫂因丈夫殘疾只能獨自支撐家庭生活重擔,為了養活家人她不得不偷盜,為此飽受村人的責罵和侮辱。然而她含辛茹苦養大成人的兒女們尤其是大國卻對她百般嫌棄,以至于最后孤身一人無奈地拖著病體返回村里等死。村人們在老姑夫主持下,用蟲嫂收破爛攢下的一筆錢為她辦了一場風風光光的葬禮,而將事母不孝的大國三兄妹拒之村外。在大國當上教育局副局長后,村里人卻又轉而對其巴結奉承。城里教師老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生活作風問題被下放村里接受勞動改造,干的是最骯臟的挑大糞活計,在他最為艱難之時劉玉翠毫不嫌棄地與他結為夫妻,讓身陷逆境中的他感受到家的溫暖。“文化大革命”結束落實政策后,老杜得以返城,在離開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接劉玉翠到城里一起生活,但之后卻編造謊言哄騙劉玉翠辦理了離婚手續。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之所以呈現出倫理價值判斷的相對模糊性,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李佩甫本著生活真實舍棄了十七年小說常見的將英雄人物神化的敘事模式,而有意將人物的“人性”置于“神性”之上,將人性、人情作為重點關照對象。《羊的門》中的呼天成、《城的燈》中的劉漢香以及《生命冊》中的駱駝等人身上,都有著超類拔萃的卓越能力和氣質稟賦,在以往寫英雄、贊英雄、頌英雄的創作原則指引下,往往會著力彰顯這些人物的神性色彩。但李佩甫卻是本著生活真實將這些人物還原為食人間煙火的凡俗人物,在他們身上同樣有著肉體凡胎的七情六欲和種種的人生缺憾。其次,李佩甫還在“平原三部曲”中獨辟蹊徑地揭示出貧窮所造成的人性壓抑和精神創痛,打破了往常小說中所習見的將人性變異歸結于金錢萬惡的敘事套路,從而揭示出“‘貧窮’才是萬惡之源(尤其是精神意義上的‘貧窮’)”①舒晉瑜、李佩甫:《看清楚腳下的土地》,《李佩甫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頁。,從而見人之所未見。比如《城的燈》中的馮家昌之所以一心渴盼擺脫農民身份而在城市落戶,主要是因為小門小戶的馮家備受村人們欺凌而無出頭之日,由此導致逼仄的生存空間以及嚴重的精神創傷,從而讓讀者指斥馮家昌忘恩負義拋棄劉漢香的同時,也能夠觸發同情之理解,不至于陷入一邊倒的道德指控。再次,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是以對生命靈魂的深入體察和細微呈示為聚焦點的,關注的重心在于作為精神主體的人的靈魂體驗和精神感受,而并非著力于對人物進行簡單的是非善惡的二元化道德評判。譬如《生命冊》中的吳志鵬當初為了躲避家鄉人無休止的煩擾,無奈選擇辭職下海,準備等發財致富后再來償還鄉親們的人情債。然而等他有能力回報家鄉時,卻發現早已物去人非,面對滿目瘡痍的故鄉失卻了歸屬感,與此同時對于城市生活也心生厭倦。梁五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性格“傲造”而遭到不公平對待,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譽和被沒收的房屋,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上訪,但在年老之時無力掌控自身命運的他卻成為遠近聞名的“陰陽先生”,前來找他算卦的農民絡繹不絕,由此昭示出為數眾多的農民靈魂無依的精神病態。
三、對于城與鄉的雙重反思
敘事技巧往往服務于特定的倫理意圖,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運用的是城鄉相互交織映襯的敘事方法,但他無意于做教條式的是非善惡的二元價值評判,而是呈現出“田園”與“反田園”、“城市”與“反城市”的雙重肯定與否定的敘事倫理,從而對鄉村傳統倫理道德和城市現代文明觀念進行雙重反思。
具體而言,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的城鄉對比和互補敘事超越了善/惡、文明/愚昧、現代/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而是以復雜的眼光來重新打量現代文明沖擊下的城鄉關系。既以現代文明世界來映襯傳統鄉土世界倫理道德觀念的保守落后和愚昧殘酷,同時也以傳統鄉土世界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脈脈來反襯現代城市世界的冷漠無情,從而呈現出中國社會在由傳統向現代急速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城市文明之間的激烈沖突,以及由此導致的人的精神困惑、身份焦慮和倫理道德觀念變異。為了形成對比映襯,也為了更加客觀地表現小說主題,李佩甫在《生命冊》中采用了城、鄉逐次交錯描繪的敘事方式,形成復調敘事結構,奇數章節寫城市,偶數章節寫鄉村,直到最后一章才合在一起,由此構成城、鄉之間的相互對話關系,城市與鄉村、歷史與現實等多重話語之間交相輝映和彼此碰撞,有利于擴展生活的表現面,并激起讀者的深入反思。復調敘事的重要特質在于,作者的主體意識在小說中失卻了傳統全知敘事那樣居高臨下的優越性,作者的聲音與小說中人物的聲音處于平等地位,形成相互對話而非統攝關系,以此來展現劇烈的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革進程中鄉土百姓所面臨的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當然,這也并非意味著作者的主觀態度絲毫也不顯現,只不過更為隱蔽罷了,正如同布斯所言“我們決不要忘記,縱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選擇他的偽裝,他決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①[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付禮軍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通過在小說文本中不時穿插的作者聲音以及小說敘述者的話語,能夠讓讀者感知到作家的敘事倫理姿態。《城的燈》中在描繪劉漢香為了帶領村民致富而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以及想方設法教育引導農民改變落后的生活習慣時這樣直白地評論道:“對香姑,人們是越來越尊重了,那是對善良、對公平的一種尊重”②李佩甫:《城的燈》,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頁。,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對于舍己為人和一心為公的倫理道德的贊許和欽敬。
李佩甫在《生命冊》里通過城鄉相互交錯映襯的敘事修辭,生動地揭示出鄉下人既對城市充滿怨懟和仇恨,同時又心生艷羨和敬畏的心理。長期實行城鄉二元化的管理體制,加之城鄉戶籍制度的建立和集體經濟所形成的身體依附性,使得中國城市和鄉村處于相對隔離狀態。農民對于城市的日常生活運行法知之甚少,他們在官本位意識驅動下想當然地認為城市人因為離“官”近而有著呼風喚雨的能力,能夠游刃有余地化解他們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難題。李佩甫在作品中還經常借著對比手法,來強化城市文明所引發的欲望泛濫與注重欲望節制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間的強烈反差,比如《羊的門》中呼天成的節欲和呼國慶的縱欲。《城的燈》中采取雙線交錯的敘事方式,分別講述尚未正式婚配的劉漢香以“兒媳”和“長嫂”的身份自行來到馮家的感人之舉,與馮家昌為了個人前途不惜出賣道德良知的自私自利行為形成鮮明對照,較之單向度的倫理道德批判更容易收到震撼人心的功效。《生命冊》中吳志鵬的適可而止和駱駝的貪得無厭形成鮮明對比,由此也造成兩人個體命運的差異。隨著商品經濟時代的到來,金錢觀念盛行所帶來的鄉土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變化是異常強烈的,《生命冊》中當年村人們對于蟲嫂為了養家糊口而與男人們發生媾和關系深惡痛絕,對其進行了“篩羅”懲戒。但對于后來在城市里靠出賣身體為生的蔡葦香卻又另眼相看,艷羨她所蓋起的全村第一座小白樓,引發全村人對于金錢的膜拜,而對于金錢的來歷卻不予深究。以致于在蔡葦香返回城市時,竟然一下子從村里帶走了六個姑娘,昔日村民們世代傳承和秉持的倫理道德觀念在金錢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采用城鄉對照和今昔對比的方式,目的是為了彰顯城鄉倫理觀念的差異,以及隨著時代轉換所發生的演變狀況,現在的故事和過去的故事交錯,描繪出人們倫理道德觀念的演變軌跡。他筆下鄉村人物之間的倫理糾葛,雖然也夾雜著悲歡離合和辛酸苦樂,但由于可供人們爭奪的利益空間有限,較之城市而言要簡單得多。城市由于集中了主要的社會資源,充斥著揚名立萬和發財致富的機會,這對于長期在落后鄉村掙扎的窮困農民而言,自然有著超乎尋常的誘惑力,促使他們抓住一切機會奔向城市來改變自身命運。《生命冊》中吃著百家奶和百家飯長大成人的吳志鵬來到城市后,首先感到這是一個喜新厭舊的地方,被欺生又怕生不要回頭客的商業氛圍所籠罩,但待久了又覺得它是寬容的、保守的和有情有義的。反觀農村則是另一番景象,鄉土熟人社會重視親戚故交,顯得有情有義,然而卻也使得人們被一張看似無形,卻又實實在在發揮著作用的人情網所覆蓋,人情往來如同長線投資那樣也是要求得到回報的。老姑夫“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①李佩甫:《生命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當年老姑夫動用村支書的權力強迫全村人承擔起共同養育的責任,才使得吳志鵬存活下來,并且還托關系找門路為他爭取到上大學的名額;然而當吳志鵬碩士畢業到高校任教后,正準備雄心勃勃地大展宏圖,老姑夫親筆寫的“見字如面”“給口奶吃”的條子卻成為他無法躲避又不堪忍受的人情重負,最終不得不辭職下海。
城市在提供眾多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在不斷刷新著人們的倫理道德觀念,稍有不慎便會卷入欲望旋渦之中被吞噬掉。無論《羊的門》中的呼國慶、《城的燈》中的馮家昌,還是《生命冊》中的駱駝、范家福等人,都面臨著精神信仰失落的嚴峻問題,不同程度地發生了人性變異。《生命冊》中的范家富雖然為官清廉,但是因著對于“名”的過于執迷失卻了自我,已經是副省長的他終究由于經受不住“名”的誘惑和“色”的侵襲而身敗名裂;駱駝則由于沉浸在無止境的“利”的追求中而變得欲壑難填,最終走向絕境、跳樓自殺。無數從鄉村來到城市的謀生者,起初都滿懷著對于鄉村苦難生活的厭倦,往往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期冀自此可以完全擺脫陳腐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而脫胎換骨,然而實際上他們始終無法真正地徹底擺脫鄉村的烙印。《城的燈》中的馮家昌兄弟四個可謂官運亨通、志得意滿,但在進行45歲生日慶祝聚會時,酒至半酣的馮家昌突然憶起昔日與戀人劉漢香約會那夜草垛上的月亮,三個弟弟也懷念起當年“嫂子”對于他們的撫育之恩,然而當四兄弟連夜驅車趕回家鄉時,卻再也無法找到回家的路,直到天大亮時找到老四,才在他的指引下來到劉漢香的墳前。從道德層面而言,李佩甫在《城的燈》中著意展現的是城市對于鄉村的虧欠,《城的燈》中的馮家四兄弟不僅在城市中早已站穩腳跟,而且還手握重權或者掌管著巨額財富,能夠呼風喚雨,但他們的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當年劉漢香無私奉獻和犧牲自我的基礎之上的。劉漢香從城市學得園藝技術后,原本可以留在城市謀生,她之所以要回到家鄉正是像《生命冊》中吳志鵬所言的那樣要尋求“讓筷子豎起來”的方法。劉漢香在被馮家昌無情拋棄后,并未怨天尤人、伺機報復,痛定思痛后她認識到正是貧窮落后方才致使馮家昌拋棄道德良知而對城市頂禮膜拜。為了從根本上尋求改變,她想以從城市習得的先進技術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以便徹底消除家鄉人的物質貧窮和精神貧困,讓自己所遭遇過的愛情悲劇不再重演。
大地無言卻能承載萬物,許多鄉村出身的青年不顧一切地想要擺脫土里刨食的貧苦生活向城而生,但在經歷一番拼搏終于在城市獲得一席之地的他們卻發現,自己永無可能徹底割斷與故鄉的血肉聯系,原本視作沉重負擔的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一切實際上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生命冊》中身為孤兒的吳志鵬正是從老蔡、梁五方、杜秋月等人身上汲取的生活經驗,方才鑄就了他持之有度的生命底色,從而在商海博弈中能夠始終堅守一定的道德底線,因而與駱駝有著近乎相同人生軌跡的他,并沒有像駱駝那樣走上不歸路。這從吳志鵬和駱駝在收購小藥廠時的意見分歧便初見端倪,作為談判代表的吳志鵬同情工人的處境,盡量地要為工人爭取更高的利益保障,希望適當抬高收購價格,但駱駝卻本著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要將價格壓至最低。在駱駝看來,藥廠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在偷偷考察工廠時發現他們偷吃廠里生產的產品山楂丸,但有過長期農村生活經歷的吳志鵬對此卻抱著同情心,認為那些工人本質上還是善良的,有是非觀的。尚且保持著道德良知的吳志鵬,雖然與駱駝一道長期在商海中浮沉,但并未沉浸在金錢的泥淖中不可自拔,當他明了駱駝已經陷入金錢欲望的旋渦中難以自拔時,果斷地與之分道揚鑣。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并不能據此認為李佩甫守望鄉土傳統道德,而有意排斥現代倫理道德觀念。實際上《羊的門》中呼國慶之所以會聽從內心的真實情感召喚和謝麗娟走到一起,而未重復呼天成和秀丫所經歷的愛情悲劇,正是緣于他接受了現代文明觀念熏染的結果。
有意味的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結尾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蘊,《羊的門》中那聲伴隨呼天成離世所發出的超乎尋常的“炸雷”,預示著他一輩子傾盡心力經營和維系的集體經濟必將走向崩塌的結局,隨著他的離世將會有更多像“狗兒”那樣的反叛者離開這塊“腌人”的土地,重拾做人的骨氣和尊嚴。《城的燈》中集合了諸多傳統優秀道德品質的劉漢香儼然如同圣母般的存在,她傾其全力想要讓農村子弟不用逃離土地也能過上夢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但可悲的是最終卻死于來自鄉村的六個“小獸”一樣的孩子之手,由此也暗示了單憑劉漢香一己之力是不足以徹底戰勝鄉村中邪惡、愚昧和狂躁的精神負面的,她的死也宣示著建構鄉村道德烏托邦努力的失敗。《生命冊》中的大姑父的離世,也宣告著傳統鄉土倫理道德的坍塌和崩潰,喻示著鄉村傳統文化在現代商業文明沖擊下必然走向沒落的趨勢,為鄉村傳統文化譜寫了一曲凄婉的挽歌。